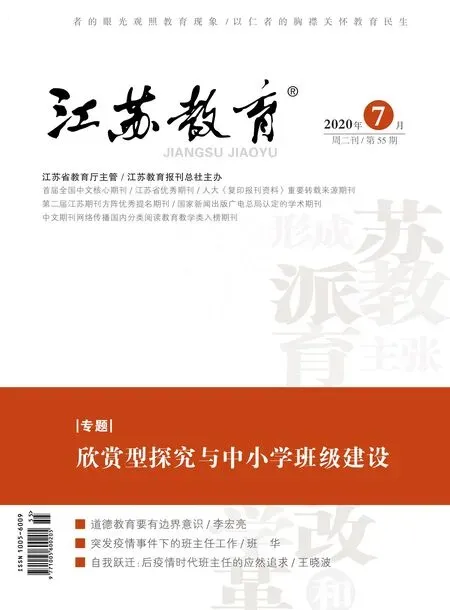自我躍遷:后疫情時代班主任的應然追求
王曉波
2020 年初,一場蔓延全球的疫情,讓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教育方式、教育地點、教育內容都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這一系列變化讓教育者不得不直面現實:我們還能以傳統的方式進行教育嗎?我們還能以原本的方式存在嗎?杜威的話其實已經給了我們答案,那就是“用昨天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就等于抹殺孩子的未來”。整個世界都在發生變化,教育需要堅守一些東西,但不能無視這些變化而獨立于世界之外。此次疫情既是危機也是契機,班主任如何化“危”為“機”,趁“機”而為?我以為,班主任應該通過認知迭代、角色轉變、行動升級,實現自我躍遷。
一、認知迭代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到:重大的商業和技術突破,往往不是技術突破,而是對于技術的應用和認知方式帶來的范式的突破。同樣,后信息時代的教育,班主任如果想實現突破,也必然要從改變自身的認知方式開始。而2020 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無疑加快了這種改變。我以為,透過疫情,班主任至少需要實現三種認知迭代。
1.重新定位角色:從“教學科的教師”走向“教學生的教師”。
自加長版寒假的居家學習進行以來,我曾就“在學生居家學習期間,您作為班主任有何困惑或困難?”這一問題對相關班主任展開調查。從反饋的結果看,大多數班主任的困惑主要集中在學科學習上,比如“如何促進后進生的自主學習”“如何引導學生端正學習態度”“如何讓學生在線上學習時保持注意力”。班主任一方面承擔著“教書”的責任,另一方面更肩負著“育人”的使命,但從上面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在多數班主任的眼中,“教書”或者說“教學科”依然是放在教育的首位的。
《中小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中對班主任的任務做了明確規定:按照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要求,開展班級工作,全面教育、管理、指導學生,使他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身心健康的公民。肩負著學生全面發展重任的班主任,需要有超越學科的認知,將學生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將自己定義為一名“教學生的教師”,而非僅僅是“教學科的教師”。教學生的教師,思考的就不僅僅是本學科的教學,更多的是學生的成長。以本次疫情為例,班主任可以進行如下思考:疫情能給學生成長帶來些什么?如何抓住全民抗“疫”這個事件給學生上一堂人生大課?怎樣讓學生從鐘南山、李蘭娟、張定宇、汪勇等人物身上汲取力量?如何看待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怎樣利用居家學習契機為學生補上一堂生活常識課?等等。認知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當認知轉變,思路便開闊了。
美國教育思想家內爾·諾丁斯認為,教師也許是當前唯一需要文藝復興特質的職業,即對于許多學科和永恒問題應有著廣博的知識。教師的學習應該強調聯系——“與其他學科相聯系、與人類普遍問題相聯系、與個人對具有普適意義之問題的探索相聯系”。學術課程、職業課程或通識課程的課程設計,都應該考慮“把要教授的主題(技能)與日常生活、個人成長、其他學校課程、精神問題等聯系起來”。如此一來,每位教師所教授的學科都能夠從內部得到拓展,因而也能夠為學生提供更豐富更有意義的學習。我以為,這種能力的發展需要建立在班主任認知轉變的基礎上。同時,這種超越學科的教師專業成長取向應該成為班主任專業成長的方向。
2.重新定義學習:從“知識為中心”走向“學生為中心”。
2020 年1 月29 日,教育部就疫情防控之下的加長版寒假做出了“停課不停學”的指示。一時間,各方解讀四起,但各所學校所采取的行動卻出奇的一致——各地紛紛開啟云端教學模式。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全國性線上教學活動拉開序幕。由于這樣的教育教學方式于大多數師生而言都是首次嘗試,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問題,而教育部也通過下發一系列文件通知,不斷規范和完善“停課不停學”的內涵。
那么,作為離教育、離學生最近的班主任,透過這樣一場教育風暴,看到什么?又想到些什么呢?我們不妨從風暴眼中跳出來,去重新審視“停課不停學”中“學”的意義。究竟要學生“學”什么?是教材中的知識嗎?如果是,疫情防控期間,這些知識的價值何在?如果不是,什么才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在一連串的追問之下,我的眼前出現了兩條路,一條通往“知識”,一條通往“學生”,它們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通往“知識”的路催促著我加快教學,趕上進度,把書上的知識點盡快教給學生;而通往“學生”的路則提醒我,慢一點,再慢一點,好好想想什么才是學生真正需要的。
學習,不是被動、機械地習得現成的知識與技能,也不是孤立地訓練各種認知能力,而是在情境中獲得生長性經驗,再實現遷移、創造性運用的過程。泰德·賽澤在《霍勒斯的妥協》一書中寫道:“教育的使命不能以傳達信息為重,而是要幫助人們學會如何利用這些信息,換句話說,就是要教會人們如何主動運用他們的思想。”芬蘭在2014 年《基礎教育國家核心課程大綱》中提出了類似的學習觀:學生是積極的學習者,唯有幫助他們成為自我學習者(自己設定目標、掌握學習策略、反思學習)并讓他們體會到學習的樂趣,才能讓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這次疫情的爆發,讓我們更加堅信了一點——學習,是時候從“知識為中心”走向“學生為中心”了,是時候從以教師的“教”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的“學”為中心了。
3.重新厘定教材:從“教材是世界”到“世界是教材”。
由疫情引發的“停課不停學”倡議,讓教育者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的問題,即對學生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的學習內容?什么才是真正的教材?傳統意義上的學習內容,是狹義的教材,是人類過去經驗的結晶。這些內容歷經歲月打磨,依然熠熠生輝。然而,真正的學習是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而且每一次新的學習產生的長期影響,都取決于這次學習與我們周圍世界的關系。
伴隨著疫情的全球蔓延,確診數據的不斷攀升,每天都有大量故事發生,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家,家與國,國與國……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甚至每一種關系都值得我們去反思。災難讓我們警醒,“教材是世界”的時代即將過去,對于未來而言,世界(生活、自然、社會)才是更為生動鮮活的教材。當學習內容被看作一種有生命的、持續變化的存在,而不是一成不變、必須死記硬背的事實,學習過程才會變得生機勃勃。
二、角色轉型
疫情,讓未來教育模式提前到來,也讓我們提前窺探到未來教師的模樣。未來,還會有班主任嗎?我想,到那時,“班主任”或許不再是某一類教師的特定稱謂,而是特指所有教師必須要擔起的使命職責。也就是說,未來的每位教師都要扮演班主任的角色,同時還要不斷提升自身的課程設計力、學習協助力、情緒調動力,以便順利轉型并從事機器所替代不了的工作。未來教師,他們不再是一個知識的傳授者,而更可能是課程的設計師、學習的協助者、情緒的調動者。
作為課程設計師,未來教師要能從學生成長的角度出發,在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中選取合適內容,為學生定制課程。比如,在延期開學的背景下,如何將疫情中的世界萬象整合為課程資源,讓學生在家也能成為一個學習者、探索者?擁有課程思維的教師設計了針對小學低年級學生的課程——“今年過年,為什么不能出門玩”,并通過每天一個子問題“這個寒假與往年有什么不一樣”“為什么不能出門玩”“在家我能干什么”“我心中最可愛的人”等,引導學生關心生活,關注社會,關愛他人,涵養社會責任。如果設計的課程足夠開放,能不斷自我更新優化調整,并且讓學生盡可能地擁有選擇權——選擇自己需要的、自己喜歡的學習內容,可以在學習過程中組成自己的學習團體,依照自己的狀況安排學習進度和學習時間……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學校,讓教育變得更加個性化,讓學生參與度更高,更有成就感,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
作為學習的協助者,未來教師會給予學生幫助和支持,及時發現并協助學生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就像這次延期開學后的線上學習,從國家到地方都提供了大量優質的在線學習資源,并不需要每位教師都來做直播。學生可以學習老師推薦的課程,還可以自我拓展課程;如果一遍沒看懂,還可以多次回看;如果覺得教師授課速度慢,可以自動調至1.25或1.5倍速……總之,線上學習的方式更加靈活,更加個性化。教師能做什么?答疑解惑,協助學生學習,甚至指導學生更好地生活。比如,我女兒的學校就有不少提供個性化指導的群,旨在為學生解決各科學習、心理輔導等問題。這個假期,我女兒把每個老師的微信都加了一遍,她甚至主動聯系心理老師,把困擾自己多年的問題告知老師并尋求幫助,老師不僅幫她剖析了心理問題的形成原因,更教給她一些專業的調整方式,她采用后覺得很有效。她對我坦言:“雖然你也和我說過一些道理,這些道理我自己也明白,但我就是走不出這個困境。心理老師的指導就不一樣,她講的道理和你說的差不多,但她更專業,她的方法更有指導性,我覺得自己好多了。”時代在飛速發展,很多課程已經可以外包給專業機構,不少資源也可以直接購買,教師的角色是時候升級迭代了。
2019年10月,馬云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的第14 屆國際校長聯盟大會上說:“未來的教育需要培養智商、情商,更要培養愛商……機器只有芯片,只有人類才有偉大的心、有愛。機器有精度,而人有溫度。只有這樣,人類才不會被機器所取代,才不會在變革中被淘汰。”也就是說,與人工智能相比,我們的優勢恰恰就在于擁有情感交流和人文關懷的能力。因此,作為情緒的調動者,未來教師會更加注重與學生的情感溝通,注重學生成長的內在需求,經常給予學生鼓勵,讓學生有更多獲得感。《全新思維》的作者、美國未來學家丹尼爾·平克認為,世界已經從過去的高理性時代,進入一個高感性和高概念的時代,當AI 能處理大部分左腦工作時,唯有感性和創新能讓你獲得“人”的優勢。有六種能力極其重要:設計感,故事感,交響能力,共情能力,娛樂感,探尋意義。我以為,就教師而言,未來教師會更具有情感性和互動性,未來教師也應該增強自己的親和力,比如多關心學生的內心世界,關注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努力成為學生的知心朋友,成為學生的成長伙伴,走進學生的心靈世界。
教育會永續存在,教師也無可替代,但未來的教師一定是一群“人機合一”的新教師——擁有全新思維力,善于系統思考,能有一技之長,長于情感交流,他們是掌握了最新呈現方式的各領域專家。
三、技能升級
危機催生變革。當教師將傳授知識的任務轉交給人工智能或者外包給專業機構時,其傳統的專業技能必須轉型升級,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對應著角色的轉變,我認為未來教師至少需要升級三種能力,即甄別選擇的能力、設計創新的能力、協同共生的能力。
這是一個紛繁復雜、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撥開重重云霧,識別有利于學生成長的高價值信息,是教師必須要習得的重要能力之一。以本次疫情為例,疫情初起,大量真真假假的信息紛至沓來,讓人陷入焦慮。對此,教師首先要學會甄別真偽,其次要想辦法為己所用。比如,如果教師希望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可以選擇“民眾瘋狂搶購雙黃連”事件;如果教師希望學生理解“沒有一個人是孤島”“世界是一個整體”這些道理,可以選擇舉國抗“疫”的事例,從專業人士、一線醫護人員、快遞員、清潔工、社區工作人員等不同職業不同角度展開設計;如果教師希望學生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可以聯系2020 年初發生的自然災害開展討論,可以一起共讀《寂靜的春天》《林間最后的小孩》等書籍,甚至可以看一些相關的電影……除了為全體學生選擇適合的學習內容外,教師還可以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特點進行個性化推薦,在內容之外,還要兼顧學習平臺的選擇。當然,最終還是要教會學生自己選擇內容、選擇平臺。所以,甄別與選擇信息的過程其實也是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過程。
在確定教學內容之后,需要教師進行創造性的設計。帕克·帕爾默在《認知與自我認知:教育的精神旅程》一書中寫道:“一名優秀的教師會讓自己要教授的學科內容與學生形成一種息息相通的狀態,他們把學生帶入了由自己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組成的社區。”以“民眾瘋狂搶購雙黃連”事件為例,教師可以把它設計成一次項目化學習,也可以設計成一次辯論賽,學習方式的選擇取決于教師希望學生從事件中能夠學到些什么。一個好的設計,會同時達成好幾個目的;一個好的設計,會有很多人參與,包括學生家長、各科教師、同伴,甚至社會其他人員。
協同共生是一個奇跡,它是整個自然界運作的基本法則。綠藻和真菌共生而成地衣,附著在光禿禿的巖石上;雁陣排成“V”字形,利用拍動翅膀造成的上升氣流持續飛行,距離幾乎達到單只雁飛行的兩倍;兩塊木頭疊放在一起,能夠承擔比單塊木頭更多的重量……從以上可以得知,整體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就教育而言,家庭、學校、社會三者之間,應該從分工走向協同,盡快實現“1+1+1>3”。人們常說,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座村莊。未來教師需要擁有開放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能夠協同更多的人參與教育,比如家庭、社區,以及其他很多人和組織,甚至是人工智能,這些都是教育生態的一部分,他們對教育的發展也負有責任。未來的教師不會一直待在學校里,一定會走出校園,去鏈接各種資源,一起為學生的成長服務。
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在小說《在輪下》里寫道:“面對呼嘯而至的時代車輪,我們必須加速奔跑。有時會力不從心,有時會浮躁焦慮,但必須適應。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將每一個落伍的個體遠遠拋下,碾作塵土,且不償命。”整個教育系統迭代的時刻已經到來,作為教師,唯有理解時代的趨勢,主動擁抱變革,提前思考行動,不斷升級躍遷,才能在疫情中化“危”為“機”,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