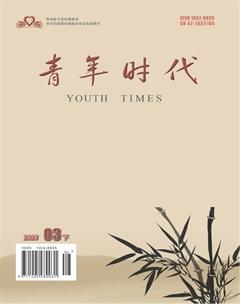微博語境下的公共空間實踐探究
徐英波
摘 要:社交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公共事件發酵在微博語境中,媒體為應對新媒體環境變化,進行了新報道形式的實驗;個體也在經受外界和自身心理機制的不同影響。本文嘗試通過“江歌案”的分析,探求如今環境下在微博構建新“公共空間”的過程中是否符合傳統公共空間的條件,又產生了怎樣的嬗變。
關鍵詞:公共空間;微博;嬗變
一、概念闡述
公共空間這一概念最早由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之后哈貝馬斯重點厘清和闡釋了這一概念,他把公共空間看作政治權力之外、介于國家和社會之間、普通市民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認為公共空間包含三要素。一是參與成員的平等性。交往關系中每個人都是主體,通過理性溝通、批判、交流、協商而達成共識,形成公共輿論。二是討論議題的公共性和開放性。公民聚在一起討論所關注的公共事務。三是參與成員的廣泛性。他們具有一定規模,人格獨立且自愿性強。
但是,公共空間隨著媒介的發展也經歷了3次轉型,第三次轉型是隨著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的發展,網絡公共空間以其為主要平臺的深化。而本文要討論的是第三次轉型后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在新媒介環境下構建的新的公共空間的雛型,而這其中,多方因素的參與使得微博在其構建“新公共空間”的過程中極具復雜性,既與哈貝馬斯所言的“公共空間”有相似之處,也發生了新的嬗變。
二、案例分析——以“江歌案”在微博的發酵為例
2016年11月3日,女留學生江歌在日本公寓門前被室友劉鑫前男友殺害,案件引起廣泛關注。此次事件在微博上發酵,從一個私人議題演變為公共事件,專業媒體、自媒體、公眾以及微博本身作為一個空間性的存在,都在本次事件的發展中產生了不同的作用。微博這一目前較理想或較接近公共空間的載體在向新“公共空間”發展的過程中,各方力量的表現對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還是讓其距離真正的公共空間越來越遠?帶著這一問題,下文將從專業媒體、自媒體、個體以及微博本身的特性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專業媒體
1.專業媒體仍是微博議程設置的主角,其是否會出現公共空間的“再封建化”
“江歌案”的實際發生時間是2016年11月3日,而當時事后基本上只有《新京報》、央視新聞以及《北京青年報》的官方微博發布了相關消息,其內容也基本上停留在背景的描述,偶爾穿插尚未被完全確認的事實,并沒有引起較大的關注。而在時隔一年之后,《新京報》旗下的《局面》欄目在微博上連續播出了25段關于江歌母親與江歌室友劉鑫的視頻,重新把這個議題以另外一個選題角度呈現在了公眾面前,由此在微博上掀起了輿論狂潮。由此觀之,理想公共空間中所言的“大家都關注的公共議題”在網絡時代依舊是由媒體來選擇,并提供給公眾來討論的,專業媒體依舊是議程設置的主角,甚至決定了對議題的解讀角度,那些堅守嚴肅類新聞報道的媒體能夠肩負打造公共空間的職責,但他們也在尋求變化,試圖在市場化的環境里生存,而由此改變的議題選擇標準,如果更偏向帶刺激性字眼的話題,便可能造成“公共空間的再封建化”。
2.專業媒體進入微博語境后,是否還在堅守“新聞專業主義”
《局面》在選取報道角度時,沒有將重點放在“兇手”本身,而是將事件中的另外一個人物劉鑫以及江歌媽媽之間的矛盾作為主線,從而引發了大家對劉鑫的道德批判。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選題角度是不是在一開始就注定“促進溝通,彰顯理性”的愿望無法實現?在核心事實不足的情況下,只采用人物雙方自我闡述的單薄信源、碎片化的多段視頻,選擇性事實的呈現,后期的剪輯節奏,都帶有一種隱含的“同情弱者”的情緒。媒體情緒的呈現以及由此產生的深度報道,很容易造成“議程失焦”的現象,由此使得公眾不能理性地參與公共討論,引起輿論的偏向。
如果專業媒體不能以一個中立的、專業的事實記錄者的形象介入到構建公共空間的過程中,我們如何期望公眾能基于客觀的事實作出正確的判斷,發表理性的意見,最終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統一意見?
(二)自媒體
網絡話語權存在階層性,公共事件中左右輿論導向的仍然是少數的意見領袖。
在“江歌案”中,事實上,真正掀起輿論狂潮、煽動網民激烈情緒的是一些自媒體意見領袖,例如:2017年11月11日,微博大v“東七門”發布文章《劉鑫,江歌帶血的餛飩,好不好吃?》,其中選取《局面》中的部分視頻,將矛頭指向劉鑫;11月13日,熱門博主咪蒙發表文章《劉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文中大量歪曲事實,用激烈的話語煽動網民的情緒,引起了網友的瘋狂轉發和評論,評論語言多為情緒化表達。
哈貝馬斯所言的理想的公共空間,其中的參與成員是平等的,其話語的影響力也應該平等,但在微博空間中,話語影響力更強的是輿論領袖,他們的觀點和情緒往往能左右整個輿論的導向。雖然在自媒體時代,技術賦予了每個人發表意見的權利,但網絡話語權依舊存在階層性。這也是未來微博公共空間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阻礙。
(三)網民
1.基于有限的事實判斷,受群體情緒影響,網民的言論呈現非理性傾向
哈貝馬斯所言的公共空間,還有一個前提條件是人格獨立,能通過理性溝通、批判、交流、協商而達成共識。但在本次“江歌案”中,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網友的評論都帶有很偏激的感情色彩,同時也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對劉鑫進行了非理性的謾罵、騷擾等,由此而產生了網絡暴力。受群體心理、群體意見和信念的影響,網民容易在微博中被激化情緒,從而產生非理性的言論,形成偏激的網絡輿論,對當事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和影響。由于群體機制的作用,微博成為了網民情緒的發酵池。
2.網絡輿論不等于輿論,但“公眾同情”有益于微博公共空間的建構
如今,情感與理性不再是絕對二元對立的概念。公共空間的建立需要理性,但不意味著絕對的無情,一個真正理想的公共空間,也需要充滿人情味。在“江歌案”的討論中,雖然充斥了大量非理性的言論,但我們也應看到大量關懷、支持江歌媽媽的言論。公共空間內的交鋒,絕不是誰勝過誰的辯論比賽,而應是努力去彌合裂痕,尋求不同群體的共識。這與哈貝馬斯所言的構建公共空間最終的目標是一致的。
此外,我們也應看到,網絡輿論并不等于輿論,網民也不能代表全體公民,所以這也與理想公共空間中的“參與成員的廣泛性”產生了矛盾。
(四)微博空間
1.微博空間作為當下互動性最強的廣場型社交媒體,形成了新的“議事廳”模式,為公共空間的建構奠定了基礎
微博用戶不僅可以在每條微博下留言,還可以通過私信、話題討論等方式形成充分的、即時的、點對點的互動,這無疑“復活”了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傳統社會“講故事”的群體氛圍,也“復活”了哈貝馬斯口中公共空間建構過程中的咖啡吧的角色。
2.微博作為開放式、廣場型的言論空間,熱點更迭快,有出現爛尾新聞的可能
理想的公共空間使得每個公共議題得以被充分討論,最后達成統一共識,促成公共事件的解決。而在微博空間中,焦點更迭迅速,網民的注意力會迅速被下一個焦點占據,這使得人們對某一公共事件的討論不充分,事件得不到妥善解決,不能有益于整個社會發展進程。“江歌案”在被持續討論了一周左右就迅速被后來發生的“大興大火”“紅黃藍虐童事件”等新聞掩蓋,在2017年12月11日該案件宣判后,對其結果繼續關注的網友可能會大大減少,其本身也就失去了公共討論、構建公共空間的根本意義。
三、結語
微博作為一個低門檻、開放性強、互動性強的廣場式的媒介平臺,與哈貝馬斯所言的公共空間的基本條件有相符之處,也有發展成為真正公共空間的雛形。但隨著時代變遷、技術發展、人類進化、民眾心理變化等,微博在構建公共空間的過程中參與因素不斷增多,“公共空間”嬗變成了新的含義。這其中有關于專業媒體的角色、“新聞專業主義”的問題,也有民眾媒介素養、公共事務參與度、心理機制等問題,以及網絡話語權的階層性、資本力量入侵帶偏輿論等問題,使得微博在公共空間構建的過程中阻礙重重。對當前的微博來說,其還不能算作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未來隨著各方面問題的不斷解決,微博會朝著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不斷接近。
參考文獻:
[1]吳旭.“公眾空間”的特征及其在三種媒介形態上的比較[J].國際新聞界,2008(9):25-30.
[2]盧鋒.論網絡空間的“類公共”特性[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7):132-135.
[3]蔡斯敏.微博語境下的中國網絡公共領域探析[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4(6):92-97.
[4]張軼楠.論大眾媒介對公共空間的建構[J].現代傳播,2010(12):141-142.
[5]羅以澄,姚勁松.中國傳媒在公共空間建構中的角色考察[J].新聞大學,201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