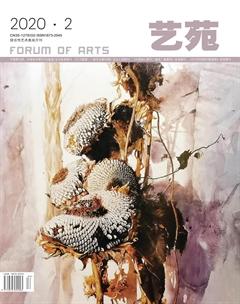類型的初探
尹相潔
【摘要】 馬徐維邦在中國早期電影類型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其代表作《夜半歌聲》更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恐怖片。《夜半歌聲》是馬徐維邦根據好萊塢電影《歌場魅影》改編而來,本文將以《夜半歌聲》的本土化改編為例,通過對影片的敘事結構、導演對于主要角色的改造以及影片本身呈現出的西方審美形態進行分析,指出《夜半歌聲》在表現恐怖的同時,或可作為受早期美國電影影響與本土化語境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特殊類型。
【關鍵詞】 《夜半歌聲》;馬徐維邦;敘事;類型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自1935年爆發“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后,“新興電影運動”進入新階段。1936年,電影界成立上海電影救國會,展開了“國防電影”的討論。影片《夜半歌聲》的上映正值全面抗戰前夕的1937年初,此時國內救亡運動興起,本土電影市場被各種好萊塢大片傾軋。但《夜半歌聲》一經上映便引起轟動,不但票房大賣,編導馬徐維邦更因此片被譽為“恐怖大師”。拋去新華公司當時成功的商業化宣傳不談,單就影片本身而言,《夜半歌聲》在當時的本土電影環境中也是較為獨特的一部。從電影情節不難看出其脫胎于1926年初來華的好萊塢巨片《歌場魅影》,甚至可以說,《夜半歌聲》是導演馬徐維邦對好萊塢電影《歌場魅影》的本土化改編。從影片本身來看,這種改編是結合了本土語境與導演個人經歷的結果,不僅雜糅好萊塢電影元素與德國表現主義風格,也呈現出隱晦的意識形態立場。在《夜半歌聲》后,本土電影市場興起“恐怖片”的拍攝,“1938年至1942年初,在上海‘孤島,被冠以‘恐怖的國產影片應該接近30部,超出全部出品的十分之一”[1]28-35。這些國產恐怖片質量并不可與《夜半歌聲》相比,但受《夜半歌聲》的影響,國產恐怖片在當時都或多或少的呈現出一種“馬徐風格”。本文將以《夜半歌聲》為例,從影片的敘事結構、導演對于主要角色的改造,以及影片本身呈現出的西方審美形態展開討論,指出《夜半歌聲》所引領的“類型電影”的特殊性。
一、敘事的本土化:回憶、鏡像、音樂
在中國電影工作者們積極探索的30年代,電影批評者們對好萊塢傾軋本土市場的大片常持不屑一顧的態度,在左翼領導下的諸如《申報》《時報》《大公報》等上海各大報刊紛紛開設專欄,“以有理論有組織的方式,發起對美國電影的批評”[2],不僅如此,“對美國電影的左翼觀照主導了中國的美國電影批評”,這些批評常常是“泛政治化”的,然而在電影創作中,正如夏衍所言:“……那時候中國電影,簡單的講,理論上學習蘇聯,技術上學習美國。”[3]他認為,中國電影“首先是受美國電影的影響”“在電影藝術——特別是敘事法、結構、電影語言等方面受西方電影的影響是很深的”[4]177,反映在當時大部分中國影片中呈現出西方電影技巧和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并存的現象。但與之略存差異的是,馬徐維邦對本片的改編是基于《歌場魅影》的基本劇情,因此,他獨特的影像風格對于影片敘事的影響更加不可忽略。在《夜半歌聲》中,導演通過回憶、鏡像、音樂這三個要素對好萊塢式的敘事進行了改編。
對于主人公宋丹萍人格的展現和身世的剖白是通過三段倒敘進行的回憶。影片沒有按照《歌場魅影》原來的線性敘事,而是通過“倒敘”進行插入式回憶,向觀眾展現宋丹萍的過去、宋悲劇的開端,以及宋對孫曉鷗的期待。在宋丹萍與孫曉鷗第一次會面場景中,宋回憶起自己曾做過革命軍和演員的輝煌過去、與小霞的戀愛等等,然而命運不公,封建勢力迫害、毀容使他再也不能和小霞在一起。倒敘弱化了原劇情的感情線,導演的處理將觀眾的注意力短暫吸引至“宋丹萍為何變成如今的樣貌”,這一問題在原作劇情中并不重要,而在《夜半歌聲》中,借此對封建軍閥勢力的批判、對新一代自由精神的展現都得以發揮。除此之外,在馬徐維邦的大部分影片中,“毀容”是一個出現率很高的情節,如《麻風女》《秋海棠》等,主人公都經歷過“毀容”,可以說,導演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展現被毀壞的面容來達到恐怖的目的,而在“展現”的過程中,對鏡像的使用就不可避免。在《夜半歌聲》中,通過鏡像展現并使主人公意識到自己已經“毀容”的片段可以說是后續此類影片的開端。在回憶片段,也是宋丹萍得知自己毀容的一場中,宋丹萍坐于鏡前,導演從其背部給出中景,將眾人反應展現出來,鏡頭推進,雷聲轟鳴,隨著繃帶一層層打開,宋丹萍催促“快些,我要去見她”,觀眾的心懸了起來,雷聲大至頂點,畫面中眾人驚恐散開,鏡頭跟隨宋丹萍來到鏡前,我們終于在鏡中看到他的恐怖、扭曲的臉。下一刻,鏡子被打碎,仿佛打碎了他自己的靈魂,伴隨著凄涼的背景音樂,宋丹萍痛苦地咆哮:“我不能去見她,告訴她我死了。”導演以令人無法忽視的場面調度和鏡頭運用營造了這個“怪人”痛苦命運的開端——毀容,這使其再也不能接受丑陋的自己與相愛的人相見。宋打碎了鏡子,正是無法接受自己的表現。鏡像的使用使人物展現更加立體,也制造了矛盾——我們透過鏡像,從主人公的眼中看到他自己,再結合悲劇性的音效,進一步加深觀眾對于人物本身矛盾與傷痕的理解,從而達到推進敘事的目的。
另一個對好萊塢敘事的本土化改編不可忽視的元素則是影片中的音樂。反觀導演自己對于拍攝恐怖場面的經驗:“譬如拍一個地窖里突然出現怪人的場面,在攝影和燈光上,先便是一條黑影映在墻壁上,然后用推鏡頭使黑影漸近漸大,而在配音上,用先緩后急的音響,雜以急促的鼓聲,使觀眾的心情為之緊張起來,再加上屋外的雷聲和閃電之光,使空氣格外恐怖。而在置景上,例如墻角滿布著蜘蛛網,破壞的桌椅傾斜地放在一角……同時配上演員恐怖的化裝或是驚駭的動作……”[5]可見,繪畫出身的馬徐維邦對德國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的電影語言的運用是一以貫之的,無論是攝影、燈光還是音效和置景,不難看出導演對于許多技巧的使用是延續自西方的恐怖片傳統,然而在《夜半歌聲》中,話劇舞臺上幾次演唱的音樂卻是飽含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為了增強劇本的時代氣息,新華公司委托馬徐維邦從著名劇作家田漢那里尋求幫助。馬徐維邦帶著劇本,數次往返滬寧線,請求田漢先生潤飾加工。田漢不僅修改了劇本,而且與作曲家冼星海攜手譜寫了三支插曲。”[1]28-35三支傳奇般的插曲穿插在電影的回憶與現實之中,有時呈現于舞臺之上,呼喊自由與光明,有時伴隨著主人公的掙扎與反抗,祈求希望降臨。音樂的本土化使得整部影片在敘事的改編上更加流暢,也更具“時代氣息”。
二、主人公的分化與移除
古往今來的改編作品都會面臨對原有故事主人公的處理,主人公的變動關乎故事情節的變化和結局的走向。例如改編自《綠衣人傳》的傳奇作品《紅梅記》,作家在改編過程中將“一人一鬼”的前世今生轉化為“一生雙旦”[6]64-66,把原作中女主人公的一人經歷分化為性格具有鮮明差異的“雙旦”使得情節更加曲折離奇,也將故事最終結局的“凄慘伶仃”推向“大團圓”。甚至在傳奇作品逐漸演變為折子戲這一形式的過程中,《紅梅記》因“雙旦”的故事線各成“一折”[7]49-52,“雙旦”幾乎不分千秋了。誠然,傳統的戲文改編傳奇作品是作家在潛移默化中受腳色制的“大團圓”傾向影響的結果,而在電影《夜半歌聲》中,馬徐維邦導演的改編行為雖與之相似,但也略有不同之處。
在《歌場魅影》中,男主角只有一個,就是“魅影”,而女主人公也只有克里斯汀,但在《夜半歌聲》中,導演將劇情中的男主人公分化為兩位男性,一人陰暗恐怖,承擔悲劇命運,另一人明朗俊俏,象征新的希望;女主人公也分化為兩位,一人瘋癲迷糊,柔弱哀婉,一人嫉惡如仇,現代且摩登。可以看到,導演對原作故事主人公的改編具有我國傳統戲文改編的影子——如人物性格的差異、人物關系走向團圓的結局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迎合觀眾的表現,但影視改編中編導者的意圖顯然比戲文作家更加復雜和多樣,其在人物形象和人物關系的設定上更進一步,也更具有個人特點。“在他的影像圖譜中,總會出現兩個有著對應的人物,后一個人物總是前一個人物命運的再版,當然影片中真正的悲劇人物是前者。”[8]85-88正如孫曉鷗是宋丹萍命運的再版,在影片末尾,曉鷗和綠蝶遭受了與他們所對應的“前一人物”相同的命運——來自同一個反派軍閥的迫害。在這一場景中,綠蝶被迫害,宋丹萍現身斗反派,被眾人發現遭到圍攻投海自盡,觀眾迎來戲劇性的高潮。導演在此處沿用“最后一分鐘營救”的剪輯模式,對于影片節奏的熟練把控令人驚嘆。追逐圍攻的戲碼和鏡頭話語又帶有原作的影子。在這里,導演通過對主人公的分化對比展現了兩代人面對迫害的不同反應,而作為“真正悲劇人物”的宋丹萍最終投身入海,被移除于主人公之外,同樣遭遇的還有綠蝶,這位曉鷗曾經的戀人(大團圓的絆腳石)被移除之后,作品不可避免地回歸觀眾喜聞樂見的大團圓結局——“新一代的希望”拯救了迷霧中的“公主”,被毀容的“怪人”和曾經的“愛人”都因保護他們而死,那么“團圓”就順理成章了。
根據當時的電影語境和觀眾群體中占較大比例的市民階層的取向,導演將主人公一分為二后又分別移除,為觀眾畫下一個完美的結局:既展現了大團圓的和諧,又表達了新生階級的自由反抗精神對愚昧人民的拯救,這是與《歌場魅影》的結局大不相同的。在《歌場魅影》中,女主人公克里斯汀接受了魅影的指導從而獲得成功,但最終沒有選擇魅影,原作更突出了主人公個人的“悲劇性”,《夜半歌聲》則更多呈現出隱晦的“意識形態”立場,這也是與當時大的社會背景所相關之處。而這具有明顯本土色彩和馬徐風格的影像圖譜,在馬徐維邦之后的作品中也隨之可見,不論是《夜半歌聲續集》還是《鴛鴦淚》《寒山夜雨》,即便沒有改編這一過程,其人物關系的分配卻也似曾相識。通過這命運的重疊,導演往往展現出新生者的“勝利”和真正悲劇人物的“無奈”,這正如當時的電影批評者們對馬徐維邦導演作品的評價:“用恐怖的形式來表現我們所需要表現的。”[9]
三、夾帶國防精神的西方審美
自1936年起,國內外形勢逐漸緊張,各大報刊紛紛發表社論探討出路,在電影界則成立上海電影救國會,電影工作者們逐漸由左翼轉向國防電影的討論,國產片創作也紛紛向“國防”靠攏。在此時期,電影演員在演出風格上仍未做到完全脫離戲劇舞臺,而由于時局的影響,電影臺詞的設計也更加直白地呈現出階級對立的意識形態立場,說教性質更強。如與《夜半歌聲》同時期的影片《馬路天使》以及吳永剛導演的《浪淘沙》等,其臺詞和表演都具有戲劇舞臺的特點,這可以說是當時影壇的普遍現象。但在《夜半歌聲》中,這一現象被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即影片中一直存在的話劇舞臺和“戲中戲”的設計,話劇舞臺需要戲劇式的表演,“戲”中的“戲”又隱晦地表明了電影人物反封建的意識形態立場,這是導演對《歌場魅影》進行本土化改編的結果。由此,所謂的“馬徐風格”則在與原作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故事情節的融合中體現出來。除去對“怪人”面具西方化的美工設計,馬徐維邦導演對于電影藝術的西方審美傾向在影片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比例。影片中直白的對“自由”的向往和“不做奴隸”的呼喊中夾雜著西語翻譯式的腔調,結合女演員小霞的裝扮以及夢幻的場景布置,足以體現出導演的改編結果是夾帶隱晦國防精神的西方審美形態。
由于好萊塢電影對國產電影市場的傾軋,此時期的國產電影不可避免地會雜糅進好萊塢元素,《夜半歌聲》也是如此。在一些場景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好萊塢電影的影子,如綠蝶被害一場,綠蝶在化妝室內換衣服,燈光在圍住她的屏風上透出她曼妙的身影,而此時,已是軍閥的反派人物湯俊闖入化妝室,對這曼妙的身影玩味般觀賞著。投影這一巧合設定令人不由想到好萊塢20年代的大片《一夜風流》,女主人公也是如此接受來自男性和廣大觀眾的“圍觀”的。但不同之處在于,綠蝶并非如經典好萊塢的摩登女郎一般嬌弱似花朵,恰恰相反,她向往自由,明確且肯定自己的價值觀,勇于反抗且富有犧牲精神。面對強權的誘惑與壓迫,她的態度是正面拒絕,且回答:“我有靠了!我靠我那辛勤、鮮血建筑成功的藝術!”這也是導演對本土摩登女性的想象與刻畫。除此之外,在小霞尋覓歌聲與孫曉鷗相見一場,小霞的裝扮是現代且西化的,她身著白紗,在詭異唯美的夜色中尋找愛人。在場景的布置上,霧氣、昏暗的光線、凌亂交錯的樹枝,處處體現出德國表現主義風格,此處的配樂更是使用了德彪西的名曲《亞麻色頭發的少女》,置景與音樂的相融使整體氛圍清新而又富有詩意。其后,孫曉鷗假扮宋丹萍來見小霞,規勸她“我們怎么樣的遭人迫害,就當怎么樣的去斗爭”,由此,小霞發出“光明!光明,光明”的感嘆。天亮了,她恢復了正常。在這一場中,明顯可以看出導演雜糅了好萊塢元素的西方審美,臺詞的隱晦說教在詩意的音樂陪襯下削弱了意識形態立場的展現,但天亮后小霞的恢復又表明了所謂“光明”的指引作用。導演在視覺表現上的西方審美形態與當時國防電影宣傳的集體政治主義和現實主義風格完全相反,也因此曾被排除在左翼電影之外,如程季華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中的觀點,電影贊美的是“宋丹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我奮斗、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以及他與李小霞纏綿悱惻的愛情,卻是和國防電影的主流思想相背離的”[10]。但在今天,拋去階級立場來看,我們也能夠發現,所謂的“背離”只是由于導演對原作在劇情上的保留和在技巧上對好萊塢元素以及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雜糅,影片中隱晦的國防精神已經縫合到主人公的一舉一動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