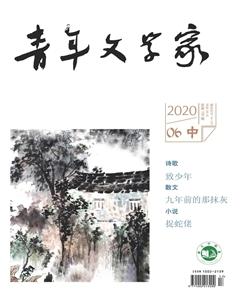選擇與責任:《北遷季節》①中的存在主義
楊旭云
摘? 要:蘇丹小說家塔依卜·薩利赫的作品《北遷季節》流露出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因此用該思想的自由選擇與承擔責任觀點對小說中的兩位主人公進行分析,可以解讀二者在面臨選擇時的內心矛盾和沖突,揭示出作者對蘇丹本土人才為國家和民族帶來新面貌的希望。
關鍵詞:《北遷季節》;薩特;存在主義;自由選擇;承擔責任
引言:
《北遷季節》是“阿拉伯小說天才”塔依卜·薩利赫的代表作品,阿拉伯文學協會稱其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說之一”。在小說中,薩利赫從無名敘述者的視角講述了有著相似教育背景的兩代人在北遷倫敦又回歸蘇丹后,在故土上是否克服內心焦慮、找到生存意義,以及承擔起個人與國家責任的故事。國外學者對該作品的解讀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義[1],也有從心理學[2]、互文性[3]等角度的分析。國內學者主要從后殖民角度對小說進行了解讀,關注小說中的流浪主題[4],以及身份[5]、文化[6]等問題。在國內外的研究中,穆斯塔法(以下簡稱穆)以及無名敘述者的身份問題一直都是關注重點,因為它對二者的人生態度和選擇有重要影響。穆說自己“不過是一個幻象,一個謊言”[7]27,過著虛偽的一生。敘述者雖沒有經歷過他的荒謬生活,但卻被其深刻影響著,正如他所說,“他就像一個幽靈”[7]44。用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提出的自由選擇與承擔責任或許能夠更好地理解二者的經歷和結局。
薩特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能自由選擇,那他的個性和自我就已失去,更不要談真正存在過”[8]21。然而,人一旦做出選擇,就意味著對他人也進行了選擇。因此自由選擇就意味著承擔責任。責任的逃避或缺失,自己都將成為他人和自我的“地獄”[9]8,導致與他人關系的異化以及使自己陷入精神困境。用薩特的存在主義對小說可以解讀出小說的兩名主人公在自由選擇與承擔責任中分別陷入的內心掙扎與道德沖突如何導致穆的悲劇和喚醒敘述者的責任意識。
一、“他只是一個幻象,一個謊話”:責任的缺失
薩特認為“存在先于本質”[10]8,世界是一個自在的整體,不受外力干擾地存在著,但人是被偶然地拋在“自在”的世界上,直到生命結束都在自由選擇中用行動塑造自己。因為自由,人才能存在。但是“人是處在一個有組織的環境中,他是擺脫不掉的:他的選擇牽涉到整個人類,而且他沒法避免選擇”[8]24。《北遷季節》中,穆的一生極盡荒唐,他的人生軌跡無處不體現著逃避責任。一個來自殖民地的黑人能夠在英國留學,說著和老師一樣流利的英語,甚至成為倫敦社會的“寵兒”,這讓他的行為更加肆無忌憚。憑借“好使的腦袋”和“冷若冰霜的心靈”[7]23,以及外在的東方形象,他利用歐洲女性的獵奇心理,將自己偽裝成一個富有東方魅力的“黑皮膚英國人”[7]24,讓她們沉淪在神秘的東方氛圍中無法自拔,最終都以悲劇收場。他自己也承認“我的臥室是座墳墓”[7]48。
世界荒謬,人生痛苦。但如薩特所說“在這個虛無的世界中,人依然是自由的,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8]47。穆從蘇丹北遷到歐洲,有意無意地塑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腦袋裝滿了西方文明,但卻無法擺脫外在的東方形象。里外不一的碰撞使他的身份選擇和認同陷入了混亂。薩特認為,“荒謬的人滿懷激情地注視著死亡,死亡的眩暈感使他得到解脫,他體驗到奇妙的不負責任感”[9]13。穆的責任是作為丈夫和父親對妻兒的責任,作為知識分子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來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負擔起來。對自己負責,不僅是對自己的個性負責,而是對所有人負責”[8]12。但他卻選擇了逃避,完全變成了自己口中的“幻想、虛妄、謊言”。或許如他所說,“要是每個人都知道何時拒絕走上這一步的話,那么許多事情都會全然不同”[7]36。
二、“我就像那棵植根于地的棗椰樹”:道德與選擇的沖突
“一個存在主義者永遠不會把人當作目的,因為人仍然在形成中”[8]30。敘述者希望能從“一根隨風飄零的羽毛”回歸到“植根于地的棗椰樹”[7]4。
敘述者也和穆一樣,到過倫敦上學,但他之后回蘇丹為新政府工作。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充實完備的人,像一顆投入田地的麥種,正準備發芽。原來滿懷希望地回到家鄉,但在與故人的相處,以及從身邊發生的事中逐漸發現他已經無法再真正回歸故土了,甚至變成了穆口中的“外鄉人”。他發現充滿溫暖和人情味的家鄉,其實每個人都麻木不仁,對任何事情無動于衷,固守著那一套舊思想。敘述者在倫敦學到的東西沒能在家鄉派上用場,因此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的內心雖然清楚家鄉信奉的道德價值和政府采取的政策自己已經不能接受,但卻沒有任何表態,只是選擇逃避,留下村民繼續在“舊”環境中掙扎。
按照薩特的觀點,人和自在的世界相遇會產生一種對外部世界感到荒謬、不可理解的無奈,這種感受就是“惡心”[9]31。但他卻未看到自己的責任,因為他所做的選擇都以自我為核心,時刻準備逃避。從個人層面上來看,敘述者有自由做任何選擇,但是他作為蘇丹新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選擇不僅是個人行為,更代表了蘇丹的未來。他要成為“植根于地的棗椰樹”,唯有用行動改變這種想逃避的狀態,擔起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
三、“他就像一個幽靈”:責任的繼承
穆溺亡后,敘述者總能感覺到其存在的氣息。“一個白癡,一個孩子,或者一個外國人,只要有足夠資料,總是有法子了解的”[8]23,敘述者總感覺到被他的靈魂縈繞著。正如薩特所說,“在模鑄自己時,我模鑄了人”[8]9。只不過這里的“我”是穆,“人”是敘述者。“我在創造一種希望人人都如此的形象”,穆的荒謬生活和希望顯然與存在主義的這個觀點不合。但是,如果反過來看,穆創造的是一種希望人人都不要如此的反面形象。與穆初見面時,其身世就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特別是知道他在倫敦的糜爛生活后,對他產生了奇怪的感覺,認為他是“永動世界里一個一動不動的物體”[7]59。
鏡子被認為是人審視內在自我的意象,敘述者正是在穆的“英式房間”中的鏡子里看清了本來的自己。他將鏡子中的自己誤認為穆,他對鏡子中出現的影像如此敏感,暗示了他從進入穆的生活以來內心的恐懼和焦慮。薩特提出,“恐懼是對世界上的存在的恐懼,而焦慮是在‘我面前的焦慮。之所以焦慮,不是因為‘我畏懼落入懸崖,而是因為‘我畏懼‘我自投懸崖”[9]117。敘述者自認為對穆充滿鄙視與“惡心”,但其內心深深恐懼著將會重蹈悲劇。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他感覺到被穆的幽靈包圍著。
敘述者認為自己一生都沒有做選擇,但是用存在主義的觀點來看,不做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審視完穆的“英式風情”房間后,敘述者又一次選擇了逃避,帶著絕望走進尼羅河。在“非生即死”的狀況下,他終于在河中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那些穆傳遞給他的責任。小說結尾并未交代敘述者獲救與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經做出了選擇,“我要活下去”[7]133。這一選擇也暗含了作者對蘇丹知識分子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全新面貌的希望。
結語:
《北遷季節》中穆和無名敘述者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是人與自我的斗爭,也是人自由選擇的一生。他們充分證明了薩特所闡述的“選擇的自由”。“存在主義是一種是使人生成為可能的學說,因為它把人類的命運交在他自己手里”[8]37。因此,無論對于穆或是敘述者,他們都能在任何時刻做出選擇,并承擔起對自己和所有人的責任,為國家和民族帶來希望。
注釋:
①小說原文內容引用自2017年的譯本《移居北方的時節》,但本文標題和內容均用另一譯名《北遷季節》。
參考文獻:
[1]Jabbar, W. K. "The mimetic discourse in Tayeb Salih's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J]. Rocky Mountain Review 66.2 (2012): 130+. Rpt.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15 Oct. 2019.
[2]Zeidanin, Hussein Hasan.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Borderlands in Tayeb Salihs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Advances in Language & Literary Studies, 2016.
[3]Huebener, P. "Metaphor and madness as postcolonial sites in novels by Jean Rhys and Tayeb Salih." Mosaic [Winnipeg] 43.4 (2010): 19+.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15 Oct. 2019.
[4]吳曉麗.《北遷季節》:兩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危機及艱難探索[J].雞西大學學報,2013,13(09):103-105.
[5]夏藝. 原型視角探尋《北遷季節》的身份追尋主題[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8,31(04):184-187.
[6]許佳媛,原一川,李昌銀. 文化雜糅者的悲劇——《北遷季節》的后殖民解[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2(02):11+137.
[7]塔依卜·薩利赫.移居北方的時節[M]. 張甲民,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17.
[8]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M]. 周熙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9]薩特.薩特自由選擇論集[M]. 周熙良,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0]薩特.存在與虛無[M]. 陳宣良,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