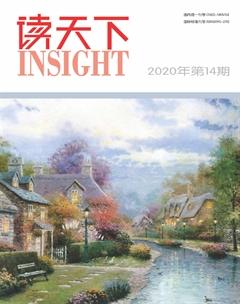走向學生生命的師愛藝術
摘 要:愛作為教育的原動力,但在當今師生關系里,卻把愛之外其他的一切事情看得更為重要,師生之間渴望親近卻又略顯疏遠,這二者之間的矛盾使得師愛藝術這一古老話題重新活躍起來。本人通讀弗洛姆的《愛的藝術》,全方位解讀書中愛的理論、對象、瓦解、實踐,從而展開對師愛的沉思,找尋在師生關系里教師走向學生生命的藝術精華。
關鍵詞:師愛;學生生命;實踐
因為社會要求和急躁風氣使大多數一線教育者沉浸在實際的感受中而不再去深入思考教育中最重要的問題。失去原初的動力導致教育的力量感不會持久或根本不具備向學生傳遞知識的能力。弗洛姆這本《愛的藝術》讓教育者開始可以試著去除浮躁和功利心,仔細聆聽舒服而懇切的文字,在世俗迷霧中找回在師生關系中應然存在的自我。
一、 以愛走向學生是教師個體生命的切實需要
個體生命發展的原初性動力來自身體的愛欲,愛的發生意味著個人身體對愛所指涉的事物的傾入,即調動個體生命的內在力量于愛所指涉的事物,愛的上升意味著個體生命自我向上的活力與力量的充分激活指向更高的事物,由此擴展個體生命發展的視域與境界。以愛走向他人正是一種愛的上升過程,是個體生命的切實需要,不僅是個體生存的現實性需求,還是個體存在的精神性超脫。
首先,愛是作為教師個體生存的現實性需求。愛于人而言不是錦上添花的東西,而是積極生存的基礎性建設之一。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里面就提到人是有性本能、親子本能和社會本能的生物中就有所體會,性本能讓生物走出自我產生幫助和關心他人的需要;親子本能促使人類愿意主動照顧后代;社會本能引導我們克服利己主義從而走向群體責任意識。每個人都不能與以否認這一點事實,愛具有強大的效能,當個體生存的這個必需品滿足后,繼而個體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
其次,愛是作為教師個體存在的精神性超脫。師生乃至人與人之間為什么需要“談愛”?人首先意識到自己生命的存在,緊接著便會發現那種生而自得的強烈孤獨感,這促使我們每個人都產生了克服分離的深切需要,弗洛姆提出雖有迷狂狀態、民眾一致、創造性活動這三種方式幫助人暫時從孤獨的包圍中解脫,但通過這些途徑達到的一致結合僅僅只是生存的部分答案,對于生存最圓滿的回答則在于愛。愛其實是人性精神品質中一種潛在的能力,當它理所當然成為個體求知真理與智慧的基礎時,個體的理智活動才稱得上是站在完整生命的角度上出發。愛作為個體存在的精神需要也是人的一種扎根方式,這種方式首先要走出自我、走向他人,像樹根將根須伸向大地那樣把自己的情誼朝向他人。盡管人和人之間是會有一種天生的距離感,但我們卻有用愛克服這種距離的欲望,并期待著從克服與他人距離中得到幸福。因此“以師愛走向學生”并不是說教,它是教師個體存在最終極、最實際的精神性需要。
二、 走向學生生命之“愛的踐行”
愛作為一種每個人只能通過自身并為自身獲得的個人體驗,它的技巧雖然無法從別人那里得到具體的教授,但在師生關系中,愛也是能夠通過自身花費心思去獲取的奢侈品,教師若想擁有愛的能力和愛的體驗,走向學生生命,就必須要具備愛的藝術知識和愛的踐行努力。
(一)愛的給予使雙方共享復活的精神樂趣
弗洛姆明確提出愛是保持自己尊嚴和個性條件下的結合,它是一種主動的能力,通俗表達為一種“給予”。“一個人奉獻給另一個人最寶貴的東西并不意味著為他人犧牲生命,而且意味著他把自身有活力的東西給予他人,他給他人以快樂、興趣、理解、知識、幽默、傷感,把他自身的一切充滿活力的東西表現出來并具體化。”教育愛超越了普遍之愛和特殊之愛的界線,具有類母愛的性質,實質在于教育者付出自身的生命活力,以期喚醒受教育者的生命活力。不由得我想到古往今來歌頌教師無私奉獻的“蠟燭論”,這種言論的道德枷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當今新時代下教師職業幸福感的日益低迷和教師自身生命的徒勞消耗,通過弗洛姆的給予一說,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這種贊美,劃分清楚“蠟燭”和“教師”二者本質上的區別。教育中理想的情境是在老師愛的“給予”下,師生共享這種由愛而復活的勃勃生命氣象,不只是單向的“生命服務于生命”,更應該是雙向的“生命成全生命”,真正達到教學相長。
究竟對所愛之人要給予什么呢?弗洛姆在愛的所有形式中歸納出共同的基本要素:關心、責任、尊重和了解。“愛是對所愛對象的生命和成長的積極關心”;至于愛的責任則是完全自愿地對另一個人表達或沒有表達的需要的反應,“成年人的愛中,責任主要是指對精神需求的關懷”,那么教師對學生愛的責任就表現在滿足對學生的知識和心靈需求;尊重便用來保證責任扭曲為支配和占有的蛻變了,“尊重不是害怕和恐懼,它表明按本來面目發現一個人,認識其獨特個性”,這與我們教學中要提倡順應學生自身規律和意愿,引導他去充分的認識自我而非服務于他人的管制不謀而合;最后是通過愛達到了解,在對他人的洞察之中了解別人也了解自己,它啟示我們不要帶著愛的名義理直氣壯去破壞對方自身生長狀態,如教師要盡量在減少威脅的情境下去了解學生的真實自我,建立在親密關系上的教育才能被真正接納。
(二)自愛是走向他人的重要階梯
在愛的給予中,我們很容易過度關注對方而迷失自我,自愛則是協調各種愛的關系的平衡點,決定了我們對待他愛和博愛等關系時的內心態度和行為選擇。任何形式的愛都是需要與自愛獲得統一的,弗洛姆是通過論述自愛與自私、無私的區別來展開分析的。自私者與自愛者不僅遠非一回事,自私不是過于自愛而是缺少自愛的表現,他缺乏對自己的自愛和關心,必然只是焦慮關注著從生活中攝取某種滿足,這種滿足限制了他自身的獲取。此外,弗洛姆還提出“無私”本質是“自私”的理論,如“無私”的教師在“一切為了孩子好”的美德掩護下讓孩子更有壓力卻又無法批評她們,它始終束縛著孩子也禁錮了自己。
(三)在追問中踐行走向他者之愛
在快節奏的當今社會背景下對知識教育要求加劇,師生之間的距離感更加顯而易見,生命的意義儼然也越來越變形為一種競爭,這種精神鴉片造成師愛的瓦解。弗洛姆提出“理解人類的途徑不是軀體而是人類生活的實踐”,愛的實踐是不斷完善人際關系,提高能力的關鍵所在,在追問中不斷踐行走向他者之愛是個體獲得生命藝術的制勝法寶。教師把握師愛的實踐需要四個因素:規范、專心、耐心和最大關注。弗洛姆也講述到關于愛的能力所需的重要品質,一則克服自戀,二則是信仰的實現。克服自戀要求我們盡量客觀,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存在被自戀傾向歪曲了的非客觀態度,而做到客觀則需要我們理智的思考和謙卑的態度;這種信仰來自對自己能力的信任,不因人際關系中的各種聲音給自我堅持帶來破壞性,當然理性信仰的基礎是個人的創造性、勇氣和自信。
三、 師愛在走向學生生命中返還自身
認識自我是每個個體生命縈繞一生的難題,我們始終活在謎里也始終活在答案本身。而走向他人的可貴之處在于人由于有自知之明而能夠鑒定別人,又通過和別人交往獲得他者映照出的自我鏡像,不斷在愛他者中完滿自身,這樣形成一個閉合循環的回路。
人性中的感性使自己是無法從客觀的角度看到和自身的,要想認識自我就必須尋找一種客觀的參照物作為手段,學生就作為教師號自我鏡像的映照,只有開始接近學生、走向學生、在與其交往中認清你以外的他者和世界時,加深對外在物的敏感性,加深對自我的認識。用愛的實踐去不斷圓滿愛的體驗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就會拉近,我們便能無限接近真實的他者,接近一個于自己而言珍貴的鏡像,享受認識自我的愉悅體驗。
“相信一種作為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個別現象的愛的可能性,這正是基于對人的本性的洞察之上的理性的信仰”,一個未經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過的生活,人之本性有一種不斷實現自我的欲求,這種強烈愿望也包括在愛他者中獲得自身的不斷完滿,在這個愛他者的過程中讓對方認可你回愛你,愛給雙方帶來意義也是個人價值的彰顯和提升。《愛的藝術》意圖切實影響到教師真實的生活,成為教師看待教育、看待學生的復眼。啟示教師怎么去發現愛,怎么在愛學生的關系里反思,在師愛中遇到問題如何修正,從而在過程中更加接近美善事物,遇見更好的自己。
參考文獻:
[1]劉鐵芳.智慧之愛何以可能:蘇格拉底愛的教育哲學一解[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36(4):88-94.
[2]高德勝.論愛與教育愛[J].中國教育期刊,2018(12).
[3]弗洛姆.愛的藝術[M].劉福堂,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作者簡介:
王星杰,湖南省長沙市,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