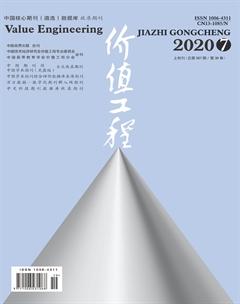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社會信任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綜述
江蕊
摘要:家族企業公司治理問題在我國廣泛存在,在外部發展環境尚不完善的轉型經濟體中,社會信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成為影響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的一個因素,進而影響企業績效。本文在比較國內外學者對社會信任、家族企業的度量與界定的基礎上,從正反兩方面系統地梳理社會信任對家族企業治理方式與形成企業績效的激勵要素,傳導路徑,作用機制等,期望引起國內學者對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社會信任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amily companies is widespread in China.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where the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s not yet perfect, social trust as an informal system has become a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family companies, which in turn affects corporate performance.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the measurement and definition of social trust and family busines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social trust on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and the incentive elements, transmission paths and mechanism for forming business performance, to arouse domestic scholar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 company corporate governance, social trust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關鍵詞: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社會信任
Key words: family business;corporate governance;social trust
中圖分類號:F276.5;F272;F279.1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6-4311(2020)19-0048-03
0 ?引言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1]。肯定了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坦言在新的發展環境下,民營經濟在發展進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在我國95%的民營企業都是家族企業,所以對家族企業的研究是解決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突破口。此外,信任是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無形之手”。信任是經濟運行中的潤滑劑,直接影響一個社會經濟實體的規模、組織方式、交易范圍和交易形式,以及社會中非直接生產性尋利活動的規模和強度[2]。社會信任與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本文通過研究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社會信任與企業績效關系,說明社會信任與微觀主體間的作用機理,積極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1 ?家族企業的內含界定與度量方法
1.1 關于家族企業內涵界定的國內外觀點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家族企業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但是由于各個研究學者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的差異,對家族企業的界定與衡量方式也存在差異,目前針對家族企業的內涵,學術界尚無嚴格統一的界定。
國內外多數學者從兩權歸屬及家族成員職責的視角來定義家族企業。蓋爾西克等認為,劃分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的標志是所有權是否在創辦者家族成員中;此外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非正式制度因素來定義家族企業,如恩納斯托·J·珀扎認為家族企業是一個創業者或后代CEO以及更多家族成員在其中發揮影響作用的這類企業。他們通過參與、對所有權的控制,其戰略傾向及其賦予企業的文化和價值來發揮影響作用;葛永盛(2018)的觀點是家族企業是利益相關者間的多變契約,它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契約關系,也是一種經濟、權力等的配置與激勵機制;家族內部成員掌握企業控制權、所有權且家族成員擁有家族傳承、家族控制的愿景;家族企業是企業與家族的統一體,既是經濟組織又是文化倫理組織[3]。由此可見,國內外學者關于家族企業的定義大同小異,隨著時代的變遷、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問題的深入,學者對家族企業的界定不斷完善。
1.2 關于信任的界定與度量方法
信任是無形的,卻又是存在的,存在于人們的理念中,展現在行為習慣中。祖克爾對信任做了系統的概括,她認為信任產生于過程、特征以及制度三種模式。儲小平(2003)在借鑒祖克爾對信任界定的基礎上總結出信任產生于三種機制:家庭;綱常倫理、法治制度;習俗、道德規范等。薛晉潔,史本山(2016)認為信任為對對方無機會主義的一種期望[4]。社會學家普遍認為人們之間普遍的信任來自志愿性社團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在重復博弈中,經濟學家得出人們追求長期利益會導致信任的結論。
信任作為一種社會學、心理學、人文學等概念,對其度量多采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薛晉潔通過問題測量機會主義行為,關系治理,合約治理等來度量信任。張維迎與柯容柱通過“中國企業家調査系統”對31個省份中近15000名企業經理人進行問卷調查,統計得出各地區信任水平。
2 ?社會信任對家族企業公司治理、企業績效的作用機制
文化決定一個社會信任的特征、半徑和深度。潘越等(2019)從文化的角度研究信任對公司治理模式的影響。宗教文化下形成的天然信任是契約交易所不可比擬的,親屬處于實際控制人的核心信任圈[5]。社會信任是家族信任的拓展,由此社會信任會通過企業間、企業與顧客間、企業與員工間、企業與政府間的活動來影響家族企業的發展,并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家族企業的治理與企業績效。
2.1 社會信任對家族企業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的貢獻機制
2.1.1 提高運營效率
家族成員間往往有著較為相似的價值觀念與更為一致的利益訴求[6],擁有共享的隱性知識、同甘共苦、互利共贏的理念,有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另一方面,家族成員將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統一,治理上具有雙重權威,進而能夠提高公司運營效率。陳然方(2006)通過研究2001-2003年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家族控股的360個上市公司發現:在中國當時階段,家族經理人治理下的業績要比職業經理人治理更具優勢[7],進而證明了上述觀點。
2.1.2 降低成本
信任有助于穩定心理預期,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較小,溝通及時準確有效,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具體來說,面對不確定事件,雙方存在良好的信任基礎,更傾向于致力于共同解決問題并達成共識,進而促進合作;合作達成后,信任的存還可以削減執行交易中那些不必要的監督與執行成本。信任水平會影響企業融資,信任度較低的家族企業對當地政府的依賴性較高,向政府的投入相對較高。而交易對方愿意為高信任度的企業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因此,被信任的企業有機會得到一些隱性優惠[8]。
2.1.3 避免“短視”
由于商業信用可作為企業的一種籌資手段,家族企業被賦予不同的信任水平,就會形成不同的商業信用,進而影響家族企業的籌資決策及資本結構。此外,由于家族企業所有權比較集中,家族企業控股股東投資決策更注重公司的長期發展,做出“短視”決策的可能性較小,過度投資傾向也較小。
2.1.4 刺激企業創新
部分學者研究信任影響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李丹和楊建君(2018)研究結果顯示關系持久性和公平性傾向于通過經濟型信任促進合作創新績效,而關系強度傾向于通過情感型信任促進合作創新績效[9]。楊建君等(2017)以實證方法研究了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信任度、經理人風險承擔、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及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表明,股東與經理人的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企業創新績績效的提高,股東與經理人的信任度對企業創新績效有直接影響[10]。
由此可見,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社會背景下,社會信任通過作用于家族企業的代理機制、投資融資結構、創新活動等,完善家族企業治理,提高家族企業績效。
2.2 社會信任對家族企業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的負面機制
2.2.1 家族成員過度參與公司治理
家族企業內部基于血緣關系、創業關系、宗族文化等積累的高信任性,家族成員有條件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從事利己行為。例如,家族成員過度參與公司治理,不僅會擠出有才智的職業經理人,引發代理問題;還會助長企業內部任人唯親的不良風氣,使得公司的競爭機制有失公平。非家族成員的工作會受到家族成員的干預與威脅,很難真正融進家族圈,員工的發展空間受限,會產生不被重視的無歸屬感、壓抑感等負面情緒,工作上缺乏利他行為,組織凝聚力不足,從而抑制家族企業的內部創造性。此外,由于成長環境、價值理念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家族成員擔任高管不利于家族企業獲取多樣化信息與建議,進而降低家族企業決策質量與水平[11],不利于企業長遠發展。
2.2.2 投資融資問題
家族企業具有多元化的目標導向,追求社會責任、家族聲譽、家族基業長青等。不僅傾向于任命家族成員擔任高管。此外,為秉承代際傳承目標,追求企業長遠發展,家族企業厭惡短期風險而偏好長期風險的特征。以家族為中心的經營方式時的企業融資結構受限,不利于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
2.2.3 代際傳承問題
家族企業注重代際傳承,但傳承失敗的案例仍不勝枚舉,這成為家族企業長久保持家族本色的“攔路虎”。究其原因,很多在于,中國富二代接班人不如父輩。郎咸平(2014)認為中國很多富一代將子女送至國外讀書,接受的管理理念與中國國情并不吻合[12],不能很好的在國內的游戲規則中管理企業,但又無力改變游戲規則。焦康樂(2019)認為家族企業內部權力分配不當會導致家族感情破裂,影響代際傳承[13]。
2.2.4 履行社會責任問題
社會信任被家族企業濫用時,就成為企業牟利手段。張茵等(2017)研究社會信任與公司避稅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地區社會信任水平會激勵公司的避稅行為。家族企業所在地區社會信任水平低、公司治理不佳以及信息透明度低的情形下,家族企業避稅傾向就較大[14]。從長遠角度看,避稅行為會影響公司形象,不利于家族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良好的社會信任環境有利于家族企業獲取資源,但我們也不可忽視資源易取的同時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問題。高度的社會信任會誘使家族企業控股人的投機行為,影響家族企業的經營效率和激勵機制導致低效率的資源配置。
3 ?結論與啟示
3.1 結論
社會信任在無形中會對家族企業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會隨著社會信任度的變化而變化。當今國內社會信用體系尚在建設完善階段,社會信任的改善在多個方面對家族企業公司治理、企業績效帶來正面效應。但當社會信任過度時,或被濫用時,會對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3.2 啟示
根據信息傳遞理論,要形成長期而又穩定的社會信任環境,需要有信息交流,重復博弈的機會。為形成良好的社會信任環境,促進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提高企業績效,企業、政府、社會公眾應采取多種措施。
3.2.1 “泛家族化”治理
家族企業的局部信任性會阻礙企業發展,因此,家族企業需要進行“泛家族化”管理,避免固步自封,以防家族企業的發展受到限制。“泛家族化”是創始家族把家文化規則泛化到家族外部。“泛家族化”治理要求轉變對員工的態度,將員工與家族成員一視同仁,注重以人為本,多給予員工家人式關懷;家族成員充分尊重并信任員工,資源適當的下放給德才兼備的家族外員工,并給予鼓勵支持;家族企業要“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營造公平競爭的晉升環境;多開展團建活動,團隊比賽項目等,給員工提供交流合作機會,形成統一的利益目標,在輕松的活動氛圍中增強員工團隊意識,建立團隊內部信任。此外,“泛家族化”治理可以促使企業突破家族企業的狹隘性,突破血緣、親緣與地緣關系,形成企業聯盟[15],強化家族企業發展勢力,推動家族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3.2.2 正式制度作保障
信任會促進家族企業有效運轉,但長期無正式制度約束下的信任,會滋生偷奸耍滑的不良風氣,信任到達一定界限后會滋生弊端,就需要規范的正式制度作為保障。信任與正式制度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正式制度的有效發揮離不開信任在其中的輔助作用,信任作用的長期有效發揮也離不開正式制度的支撐。為此,家族企業內部應建立合理的監督約束機制,用科學合理的正式制度規范家族成員與員工的行為,家族成員與員工觸犯企業章程應一視同仁,確保企業內部約束機制無“漏網之魚”,不會成為一紙空文。家族企業作為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一份子,其經濟活動離不開社會環境,離不開政府的經濟政策規范。為此,政府積極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的落實,堅定落實信念,逐步開展,積極推進,努力構建良好的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的社會環境;要明確法律規范,加強信息數據管理,嚴懲失信行為;積極完善基礎設施,促進交通條件的改善,社會群眾文化素養的提高,進而為有質量的信息交流提供更多的契機;同時,加快公共數據整合,實現公共數據資源共享,形成家族企業的信用記錄,促進家族企業信用增值。
通過信任與社會,企業正式制度的結合,剛柔兼俱,實現對企業的全方面約束治理,將不誠信、不道德、不合理的的行為泯滅在萌芽中,也可以將其終止于實施過程中,從而有效促進家族企業的健康有序運營,實現企業經營目標。
3.2.3 做好代際傳承準備
家族追求基業長青的發展目標,應做好代際傳承的準備。在送子女接受國外管理教育的同時,注重對子女的本土化教育,進行實戰磨練并給予指點,讓子女了解中國社會特征,講正氣,走正道,誠信經營,依法經營,致力于將家族企業發揚光大,并且要處理好子女間的利益分配問題,避免因利益分配問題產生二代間的感情裂痕,引發家族企業分崩瓦解。
3.2.4 發揮企業家精神
家族企業的傳承不僅僅是權力與財富的傳承,更重要的是企業家精神的傳承。企業家們在探索中所具備的感悟力、判斷力,是常人所不具備的。當地政府應加快形成企業家顧問機制,吸收優秀企業家參與政府規劃,塑造和諧的政商關系[16],營造社會“尊商”文化;企業家精神需要激活創新環境,為此金融機構需要完善創業基金、創業保險,為企業家提供資金支持,政府要制定營造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的規章制度,為企業家發揮自身精神氣提供良好的空間。
3.2.5 家族企業文化自信
家族企業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而來的,創造了“本土化”的管理經驗。誠然,家族企業治理中存在些許不足,需要走出家治化的局限,但我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的治理方式,忽視其長期發展中的合理性,應在順應時代潮流的同時也不忘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優秀的家族企業文化不僅可以樹立企業的權威與信任,同時可以提高員工的凝聚力,讓員工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調動員工工作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本報評論員.新一代民營企業家要更加奮發有為[N].人民日報,2018-11-07(002).
[2]張維迎,柯榮住.信任及其解釋:來自中國的跨省調查分析[J].經濟研究,2002(10).
[3]葛永盛.家族企業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8.
[4]薛晉潔,史本山.信任、治理策略與合資企業社會困境[J].管理科學,2016,29(05).
[5]潘越,翁若宇,紀翔閣,戴亦一.宗族文化與家族企業治理的血緣情結[J].管理世界,2019,35(07).
[6]翁若宇,陳秋平,陳愛華.“手足親情”能否提升企業經營效率?——來自A股上市手足型家族企業的證據[J].經濟管理,2019,41(07).
[7]陳然方.親族信任、治理結構與公司績效:以中國家族上市公司為例[J].世界經濟,2006(04).
[8]劉鳳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與商業信用模式[J].經濟研究,2009,44(08).
[9]李丹,楊建君.關系狀態、信任、創新模式與合作創新績效[J].科研管理,2018,39(06).
[10]張峰,楊建君.企業內部信任、經理人創新動力與能力關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7,38(08).
[11]于曉東,劉小元.不同類型親屬關系如何影響家族企業治理——基于中外研究的文獻回顧與理論歸納[J].經濟管理,2017,39(04).
[12]郎咸平.中國富二代接班人為什么不如父輩[J].IT時代周刊,2014(22).
[13]焦康樂,李艷雙,胡望斌.家族企業傳承模式選擇動因研究——基于社會情感財富視角[J].經濟管理,2019,41(01).
[14]張茵,劉明輝,彭紅星.社會信任與公司避稅[J].會計研究,2017(09).
[15]程霖,周艷.近代中國家族企業代際傳承與“泛家族化”股權融資思想[J].財經研究,2018,44(11).
[16]馬忠新,陶一桃.企業家精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學動態,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