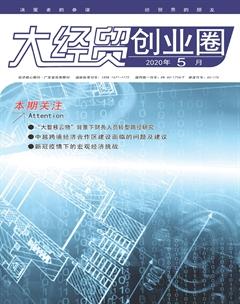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思考與探索
【摘 要】 2019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孫小果案依法再審開庭。與此同時,有19名涉案公職人員被移送審查起訴,其中,云南省檢察機關對6名司法工作人員立案偵查并移送審查起訴,體現(xiàn)了檢察院依法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的效能[1]。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和國家監(jiān)督體系,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自然承擔著對公安、法院等司法單位的監(jiān)督。在國家監(jiān)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檢察院積極承擔起對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偵查權,積極行使法律監(jiān)督職能,積極履行新《刑事訴訟法》賦予其的職權要求,對肅清職務犯罪毒瘤,凈化司法隊伍環(huán)境起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 檢察機關 職務犯罪 偵查權 法律監(jiān)督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監(jiān)察法》的頒布與監(jiān)察委員會的設立,原《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屬于檢察院的部分職權劃分至監(jiān)察委員會,如對貪污賄賂犯罪、瀆職犯罪的偵查權一并改由監(jiān)察委員會行使調查權。職權劃分勢必引起對檢察院偵查職權的限制,不過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仍然保留了檢察院對部分犯罪的偵查權。《刑事訴訟法》第19條第2款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jiān)督中發(fā)現(xiàn)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這從法律層面上為檢察院偵查權行使提供了必要依據(jù)。那么,這種保留下來的偵查權與監(jiān)察體制改革前的偵查權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這種偵查權與監(jiān)察委員會的調查權在職權行使上是否存在銜接或沖突的地方,偵查權的限制是否會影響《憲法》、《刑事訴訟法》所賦予檢察院的法律監(jiān)督職能。筆者擬通過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權的規(guī)定進行梳理,并由此來探討檢察院如何強化法律監(jiān)督職能,力圖避免類似孫小果案帶來的悲劇。
一、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的范圍與特征
(一)檢察院立案偵查的犯罪主體限于司法工作人員
人民檢察院對司法工作人員所實施的部分犯罪行為可以實施偵查權,這是《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guī)定[2]。此外,《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職務犯罪限于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虐待被監(jiān)管人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執(zhí)行判決、裁定失職罪、執(zhí)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私放在押人員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罪14項罪名。對于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而言,其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故司法工作人員構成此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若一般人和司法工作人員以外的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此罪,則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和監(jiān)察委員會行使調查權。而對于濫用職權罪、徇私枉法罪等此類犯罪,只能由特殊主體構成,司法工作人員觸犯此類罪名,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以外的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此罪,由監(jiān)察委員會行使調查權。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訴訟法》第19條規(guī)定司法工作人員構成此類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但不代表監(jiān)察委員會無權行使調查權,下文還會進行贅述。由以上敘述可知,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檢察院立案偵查的犯罪主體作出細化,表面上看限制其偵查權能,但卻強化了其對于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監(jiān)督職能,對打擊職務犯罪,履行訴訟監(jiān)督職能具有重要意義。
(二)檢察院偵查職能與法律監(jiān)督職能密切聯(lián)系
我國《憲法》第134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jiān)督”。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實行法律監(jiān)督,包括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zhí)行各個階段。對司法工作人員構成以上14罪名[3],人民檢察院依然實行法律監(jiān)督。不過,由于各罪之間性質,適用情況各不相同,檢察機關對其實施監(jiān)督的側重階段也就有所不同。一般來說,暴力取證、刑訊逼供發(fā)生于犯罪偵查階段,主要涉及查清案件事實,獲取證據(jù)材料等工作,所以人民檢察院對此罪名的監(jiān)督通常發(fā)生于偵查階段。對于徇私枉法罪,人民檢察院的監(jiān)督則涉及到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等各階段,而對于執(zhí)行判決、裁定失職罪此類發(fā)生于審判階段的犯罪,人民檢察院主要對其審判、執(zhí)行階段實行法律階段[4]。當然以上說法并不是絕對的,人民檢察院的監(jiān)督活動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只是側重階段有所不同而已。此外,對于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需要在監(jiān)獄或看守所執(zhí)行刑罰,監(jiān)獄或看守所內部通常會有派駐檢察官。派駐檢察官不僅是檢察院對監(jiān)獄刑罰執(zhí)行和監(jiān)管改造實行法律監(jiān)督的一個體現(xiàn),也是對監(jiān)獄公職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與合法性實行法律監(jiān)督的一個體現(xiàn)。
(三)檢察院偵查職能具有選擇性與讓與性
《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對于某些犯罪人民檢察院可以行使偵查權,在這里要注意可以二字。‘可以意味著人民檢察院對上述犯罪可以行使偵查權,也可以不行使偵查權,這從法律上賦予了人民檢察院一定的自由選擇空間。可能會有人疑惑,倘若檢察院可以自由選擇其職權行使,是否會給其不作為提供正當依據(jù)?筆者對此持否定意見,人民檢察院在考慮對一個案件是否行使偵查權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其是否與監(jiān)察委員會的職權發(fā)生沖突,如果監(jiān)察委員會對司法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已經(jīng)啟動了調查權,而檢察院還未對此案進行立案管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檢察權就無需再立案管轄,這與《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規(guī)定的“監(jiān)委為主”原則是一致的(下文還會進行贅述)。學界中還有一種觀點:‘可以一詞從表面理解是一種授權性規(guī)定,但實質上其義務性色彩更加濃厚。它在表示授予權力時,檢察院需積極履行職責,原則上不能輕易放棄。法律上的這種授權不只是一種職權,更是一種職責,而職責是不能輕易放棄的[5]。
二、職務犯罪偵查權在檢察院的內部配置
《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對檢察院在偵查職務犯罪時進行了明確的級別劃分,這對于配置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解釋如下:
(一)確定以地級市檢察院管轄為主的級別管轄配置模式
《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在級別管轄和偵查部門篇第一條第1款明確規(guī)定:“本規(guī)定所列犯罪案件,由設區(qū)的市級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基層人民檢察院發(fā)現(xiàn)犯罪線索的,應當報設區(qū)的市級人民檢察院決定立案偵查”。這里所稱的設區(qū)的市級人民檢察院,通常是指地級市人民檢察院或區(qū)級人民檢察院。不過《規(guī)定》并沒有完全剝奪基層檢察院的偵查權,其級別管轄和偵查部門篇第一條第2款規(guī)定:“設區(qū)的市級人民檢察院也可以將案件交由基層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或者由基層人民檢察院協(xié)助偵查”。如果由人民檢察院偵查更為適宜的,市級人民檢察院可以將案件交由基層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這對于基層人民檢察院的偵查權有所保留,只不過予以限制,使其起輔助作用。由此可以得出,我國目前確立了檢察院對職務犯罪“以地級市檢察院集中管轄為主,基層檢察院屬地管轄為輔”的管轄模式,這種管轄模式在司法實務中有一定的好處。第一,可以優(yōu)化配置司法資源,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在實踐中,上述14項罪名相比傳統(tǒng)的自然犯與法定犯而言,發(fā)生的概率會低很多,而司法人員觸犯以上罪名者,則少之又少。因此,如果在基層檢察院配置過多的偵查資源,很可能會出現(xiàn)無事可做的局面,造成資源的閑置與浪費。第二,可以避免干擾因素,促進公正司法。由于人民檢察院承擔著法律監(jiān)督的職責,所以基層人民檢察院必然要對基層公安、法院履行法律監(jiān)督,在監(jiān)督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工作上的交叉與聯(lián)系,如果再由基層檢察員對其司法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實施立案偵查,不敢保證會不會出現(xiàn)一個公正公平的結果,不利于公正處理案件。
(二)同一檢察院內部的不同配置模式
上述模式只能解決不同級別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沖突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檢察院內部各部門之間的沖突問題。《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在級別管轄和偵查部門篇第二條第1款規(guī)定:“本規(guī)定所列犯罪案件,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刑事檢察工作的專門部門負責偵查”。司法實務中,同一檢察院內部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可能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設置專門的職務犯罪偵查部門負責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另一種則是由不同階段承擔法律監(jiān)督職能的檢察官別承擔對應法律監(jiān)督活動中發(fā)現(xiàn)職務犯罪的偵查職能。第二種模式意味著任何承擔訴訟監(jiān)督職能的部門及檢察官都有權對司法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行使偵查權。相比較這兩種模式,筆者更加支持第一種模式。與第一種模式相比較而言,第二種模式看似更加便捷,但不同部門在行使偵查權時是否會出現(xiàn)職權上的沖突?就徇私枉法罪而言,檢察院監(jiān)督涉及到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各階段,檢察院在以上各階段行使法律監(jiān)督權的同時,均可行使偵查權,這樣勢必會造成偵查職能的重復與混亂,妨礙偵查效能。
三、檢察機關偵查職能轉變對監(jiān)督職能的啟示
通說認為,檢察院偵查職能的行使,強化了其法律監(jiān)督職能。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檢察機關的偵查權予以限縮后,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會弱化其監(jiān)督職能。監(jiān)察委員會設立以后,原本屬于檢察院的大量司法人員轉至監(jiān)察委員會,這也削弱了檢察院的人員力量。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現(xiàn)有的監(jiān)察體制下,在檢察院偵查職能予以限制的情境下,保障其法律監(jiān)督職能的正常運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踐行起訴為主的法律監(jiān)督模式
在我國的的刑事訴訟運行模式下,檢察院盡管也承擔部分偵察職能,但其主要職能依然是對犯罪嫌疑人履行起訴職能,通過對案件事實和證據(jù)的梳理,向法院進行陳述,尋求對犯罪嫌疑人相應的處罰,實現(xiàn)對違法犯罪的法律監(jiān)督。以起訴為核心的法律監(jiān)督模式現(xiàn)在已經(jīng)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實踐。例如《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人民檢察院可以對符合相關情形的案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這其實就是強化檢察院法律監(jiān)督職能的重要體現(xiàn)。在刑事案件中,對于確有錯誤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法院提起抗訴,從而引起二審或者再審程序,這同樣是檢察院進行法律監(jiān)督的體現(xiàn)。檢察機關偵查職能的限制和轉變,對其法律監(jiān)督職能不僅不會阻礙,相反還會起到強化作用。
(二)強化程序審查的法律監(jiān)督模式。
這就要求檢察院在行使職權過程中,要加強程序審查的力度,堅決維護程序正義。對于辦案人員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jù),應當依法予以排除并對違法行為基于制裁,這是實現(xiàn)法律監(jiān)督職責的重要途徑。
(三)保障監(jiān)督權行使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對于法律監(jiān)督而言,它是一種主動行為,要求監(jiān)督主體積極行使監(jiān)督權。而監(jiān)督權的行使是需要監(jiān)督主體的知情權和調查權為保障的[6]。但從司法實務中看,檢察機關的知情權和調查權還不夠充分。在一個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主要是通過對一個案件進行審查,進而發(fā)現(xiàn)犯罪線索。但是對于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案件,其移送審查起訴時,相應的證據(jù)材料已經(jīng)經(jīng)過加工處理,從而天然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即便其反應的是案件真實情況,那也往往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真實情況。對于受害人而言,現(xiàn)階段受害人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還比較薄弱,一個確有錯誤的生效判決與裁定,如果過了上訴期,有多少人能夠去積極申訴或者向檢察院提請抗訴,這個數(shù)字不會太樂觀。因此檢察院通過這個途徑獲取的信息更少。因此,檢察院在依法行使法律監(jiān)督的同時,更應積極主動履行法律所賦予的監(jiān)督職權,不僅應關注刑事領域,還要關注民事、行政領域。不僅對于自偵案件積極監(jiān)督,對于公安機關、監(jiān)察委員會管轄的案件也要積極監(jiān)督,不能將一項主動職權變?yōu)楸粍勇殭啵@是至為重要的。
結 語
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偵查權的保留,一方面反映了其對于自偵案件行使偵查權,查證犯罪線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其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積極行使監(jiān)督權的重要體現(xiàn)。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訴訟法》對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線索,可能會導致其監(jiān)督職能有所削弱,檢察機關不能僅依據(jù)此項職權來行使監(jiān)督權,而應當另辟蹊徑,積極尋求其他合法路徑,來強化其法律監(jiān)督職能。
【注 釋】
[1] 參見林維:《從孫小果涉案司法人員被查處談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效能》,載《檢察日報》2019年10月15日第002版。
[2] 《刑事訴訟法》第19條第2款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jiān)督中發(fā)現(xiàn)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3] 《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規(guī)定14罪名 。
[4] 參見謝登輝:《我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嬗變與反思》,載《警學研究》2019年10月第5期。
[5] 對于“可以”的解讀,學界存在不同觀點,“可以”一詞在公法上表示對公權力機關授權時,原則上不能輕易地將其解釋為自由裁量權,因為對于公權力機關而言,法律的授權既是職權也是職責,而職責是不能任意放棄的。詳見陳衛(wèi)東主編:《刑事訴訟法學》2017年版,第107頁、第108頁。
[6] 參加:秦前紅,石澤華:《新時代法律監(jiān)督理念:邏輯展開與內涵闡釋》,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年第06期。
【參考文獻】
[1] 林維.《從孫小果涉案司法人員被查處談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效能》[J].檢察日報,2019,(4).
[2] 謝登輝.《我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嬗變與反思》[M].警學研究,2019,(5).
[3] 孫謙,童建明.論檢察機關偵查的性質地位和作用[J].檢察理論研究,1993,(4).
[4] 朱孝清.國家監(jiān)察體制改革后檢察制度的鞏固與發(fā)展[J].法學研究,2018,(4).
[5] 秦前紅,石澤華.《新時代法律監(jiān)督理念:邏輯展開與內涵闡釋》[J].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6).
[6] 陳衛(wèi)東.《嚴格排除非法證據(jù)規(guī)定》下的檢察發(fā)展新機遇[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7,(4).
作者簡介:張鵬(1995年-),男,漢族,山東鄒平人,碩士研究生在讀,單位:天津商業(yè)大學,研究方向:法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