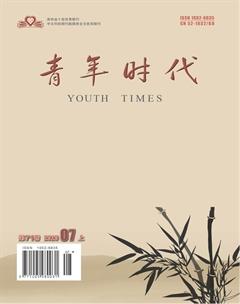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法學碩士模式探索
楊媛
摘 要: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呼喚新型法學人才。因此突破傳統的法學教學模式,探索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法學碩士的新模式,培養法學碩士在特定情景下解決現實問題的實踐能力便成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題中之意。因此,本文從高校與實務部門協同互動的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打造兩者協同培養法學碩士的新模式。
關鍵詞:高校;實務部門;法學碩士;聯合培養
一、引言
2012年為積極推動協同創新,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經濟、文化的有機結合,教育部、財政部聯合提出“關于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的意見”(簡稱2011計劃),為21世紀的法學教育理念注入了新的內容。伴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研究生規模以及社會需求的不斷擴大,重新定位法學研究生培養目標、轉變法學研究生培養模式、調整和優化法學研究生培養結構,把法律碩士(法學)研究生培養成為學術與應用并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的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成為中國法學教育改革的關鍵。
法學是一門應用性社會科學,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需要在實踐中通過解決具體問題得以體現。而在現行的法學研究生培養體系中,普遍存在著重視理論知識的掌握而忽視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的現象,法學教育與社會實踐嚴重脫節。隨著國家與社會發展以及高校擴招的需要,我國的法學研究生培養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這些問題日益凸顯。
從法學教育性質的實踐性和法學研究生近年來的就業情況來看,盡管法律碩士(法學)研究生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儲備,但是與其具備的實踐操作能力并不是成正比的。特別是法學學科本身所固有的實踐性、應用性等特點,決定了法學碩士生必須理論聯系實際,擺脫純粹性理論知識講授和單純性課堂傳授的局面。因此,研究高校與實務部門協同培養法律碩士(法學)研究生的教育模式,通過協同和聯合的形式搭建協同培養平臺和機制,有效解決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突出問題,在實踐中找到符合國情和學校實際的發展路徑,進而推動高校與實務部門的互動,實現人才培養質量和科學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對于培養法學碩士的理論對接實際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立足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要求,以法律碩士(法學)研究生為視角,探索加強高校與法律實務部門合作與聯系的途徑,創新法學研究生培養模式,提升法學研究生運用法律知識的實踐能力,從而推動法學教育質量的全面提升。
二、研究現狀
國外大學,無論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極為重視對法學專業研究生進行職業訓練、職業技能培養、職業素養的提升。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法學教育以培養律師為主要目標,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而這有別于中國傳統的以培養法學碩士為目標的法學教育模式[1]。
我國的法學研究生教育包括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和法律碩士研究生教育。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制度設置的初衷是為法學教育和科研機構培養學術型人才,它所預期的畢業生是學術型法律人。因此,在培養過程中較少與實務部門聯系和交流。設置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的初衷是為改變我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嚴重脫節的現狀,致力培養實務型法律人,在培養過程中與實務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系和深層次的交流。為了緩解應屆法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同時也是為了克服現行法學研究生培養機制實務教育方面的不足,教育部要求具有法律碩士培養資格的高校面向應屆法學本科畢業生招收法律碩士研究生,從而催生了繼法學碩士研究生、法律碩士研究生(非法學)之外的第三類法科碩士研究生,即法律碩士(法學)研究生。此類法學研究生實行兩年學制,不分專業,重在實務培養。
目前,很多高校非常注重與實務部門的合作,但重點是聯合培養法律碩士(非法學)實務能力,協同培養法律碩士(法學)研究生的案例較少,無論是非法本法碩,抑或是法本法碩都存在著缺乏實務導師引導的境況[1]。劉宇[3]指出我國法律碩士的培養目標其核心在于高層次應用人型、專門型或復合型人才[3],這造成了其他類型的法律人才培養目標的趨同化,因此應該著重提升法律碩士人才的專業化程度。知識來源于實踐又復歸于實踐,尤其是法律碩士的實踐性較強,因此法律碩士和實務部門的結合便成為法學碩士培養的一大關鍵。楊武松和潘弘[4]指出現代法學教育要兼顧法學碩士生法治精神的培養和其實際解決法律問題的應用能力,同時也要探索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法學碩士的培養機制。黨日紅[5]指出在法學碩士的培養過程中,要推進深度實踐教學,構建逐步深化的實踐課程教育體系,將法學碩士的課堂理論與校外實踐結合起來,形成“走出去,請進來”式的教學模式。馬思潔[6]則指出中國的法學教育要注重在實踐教學中重點突出應用型和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機制,突出學生的實踐教學、創新專業實踐、社會實踐以及校園實踐,突出高校與實務部門的合作培養模式,使法學學生的培養能夠扎根于實踐,進而強化法學學生在特定情景下實際應用知識的能力。科技的發展為法學碩士教育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法學碩士培養模式在人工智能時代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與途徑。谷永超[7]則以獨立學院為例探討了協同育人時域下法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指出要協同社會力量,選聘法治實務部門專家走進課堂,進而實現法學碩士培養的“雙導師”制。季連帥和何穎[8]指出智能時代的到來正在深刻改變法學高等教育的內容、模式和體系,法學高等教育的變革應該更加注重通過科技的應用加強高校與實務部門之間的協作。王樹海等同樣以獨立學院為例,探討了應用型法學人才的培養模式,指出法學碩士教育應該形成獨具特色的法學專業實踐環節教學體系。
三、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法學碩士模式探索
探索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法學碩士的模式與機制,首先要突破傳統的培養模式,改變學生扎根理論而實踐不足的現狀。注重高校與實務部門在法學人才培養方面的實質性合作,實行法學研究生的“雙師計劃”,根據學生自身的特質并結合社會法學需求現狀,實現校內外導師共同制定培養方案。探索高校與實務部門共享教育實踐基地資源的機制,并創新課堂教學方式、方法,著重培養法學碩士的實踐應用能力。
(一)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意識
不同于歐美國家的教學體系,中國的教學模式普遍存在著注重理論而忽視實踐的傾向,這造成了中國學生,包括法學專業的學生實際運用知識的能力較弱。相較于對理論要求較高的專業,法學教育的實踐性更強,因而對學生在特定情景下運用所學知識處理現實問題的要求也更加嚴苛。因此在法學碩士的培養過程中要首先樹立學生兼顧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意識,鼓勵學生主動走出校門,進入實務部門增強自身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
(二)創新課堂教學方式、方法,擴大課堂實踐教育
創新課堂教學方式、方法,擴大課堂實踐教育,增強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傳統的法學課堂教學和考核模式偏向于對導師對法律理論的闡釋和學生對法條的機械記憶,往往忽視了對于學生實踐應用知識能力的培養。因此,要改變傳統的法學碩士培養機制,增加課堂實踐教學和案例教學的比重,并將學生的實踐能力納入到考核機制,形成“課堂實踐教學+實踐考核”的新模式。有條件的可以爭取做到對實務部門的“每周一訪問”或“每月一訪問”,通過讓學生親臨現場并參與其中提升學生對現實問題的了解程度及深度,尤其可以借助信息技術打通高校與實務部門之間的通道,探索通過視頻教學的形式讓學生“親臨一線”,并加大實踐討論的課堂教學環節,培養學生在特定情景下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三)探索實行法學碩士的“雙師計劃”,實現校內外導師共同制定培養方案
傳統高校教師往往在理論方面根基較深而實踐不足。而校外實務部門的專家往往在實踐層面有更多的經驗積累,因此可以探索法學碩士培養的“雙師計劃”,即聘請實務部門的專家進入課堂,打造高校導師與實務部門專家共同培養法學碩士的體系,并根據學生自身的特點實現校內外導師共同制定培養方案。法學碩士培養的“雙導師計劃”要協調好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對于法學碩士培養的不同側重點,其中校內導師主要負責學生法學理論的指導,校外導師主要負責提升學生在特定情景或者特定案例下實際運用知識的能力。
(四)探索打造高校與實務部門共享教育實踐基地資源的機制
高校與實務部門各自的優勢在于,高校往往是知識生產的基地,其優勢在于掌握的知識資源,而實務部門的優勢則在于對于現實問題和前沿問題的了解,同時也掌握著更多的案例資源、設備資源以及空間資源等高校難以全面掌握的資源。因此高校可以協同實務部門打造共享式的教育實踐基地,打通兩者合作的通道,共享各自的優勢資源,從實現“非零和”博弈。高校與實務部門共享教育實踐基地資源可以形成法學碩士培養的正向反饋機制,從而為法學碩士的培養注入新的活力。
四、結語
法學碩士的培養要突破傳統法學教育的困境,探索新的法學碩士培養模式,提升法學碩士的實踐能力和對于現實問題的洞察能力。因此高校與實務部門發揮各自優勢資源,現實協同合作對于法學碩士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努力探索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互動的新模式,培養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型法學人才。
參考文獻:
[1]常安,孫森森.法律碩士(法學)培養模式探析[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4,26(7):72-78.
[2]劉宇.法律碩士教育培養目標的反思與完善路徑[J].河北農業大學學報(農林教育版),2018,20(4):46-50.
[3]付健,陳志文.論構建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的影響因素[J].梧州學院學報,2019(5):92-95.
[4]楊武松,潘弘.法學碩士研究生課堂實踐教學的進階路徑[J].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15(8):75-79.
[5]黨日紅.高校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J].勞動保障世界,2019(33):51.
[6]馬思潔.民族高校卓越法律人才培養實踐教學研究——評《民族高校卓越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教育發展研究,2020(4):2.
[7]谷永超.協同育人視域下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究——以獨立學院為例[J].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9(6):71-73.
[8]季連帥,何穎.人工智能時代法學高等教育的變革與應對[J].黑龍江社會科學,2020(1):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