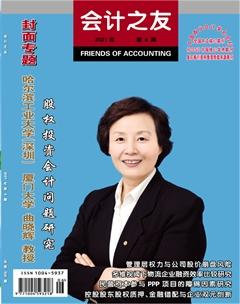股權投資會計問題研究
【摘 要】 股權投資對資本市場、新興行業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甚至增強國際競爭力都非常重要。股權投資是會計計量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充滿爭議的領域,突出表現在股權投資取得成本的會計處理、股權投資的期末再計量與列報和商譽的期末重評價。文章聚焦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方法和股權投資會計處理與財務列報及其問題,探討股權投資及其走勢、股權投資會計處理與決策的關系、股權投資相關會計計量與問題和商譽確認與計量及問題,對股權投資研究進行了簡要概括和展望,并分析了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關于企業合并準則對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會計處理方法的最新立場。文章就股權投資及其連帶的商譽減值或攤銷會計處理的分析,對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和企業財務報告編制者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關鍵詞】 股權投資; 商譽計量; 企業并購; 會計準則; 公允價值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1)06-0002-07
投資是會計與財務研究的熱點領域,也是資本運營的重要方面,股權投資尤其令人矚目。與債權投資不同,“股權投資不具有直接的返還性,并且產生的收益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1 ]。一方面,股權投資需要承擔企業經營的最終風險且所承擔的企業經營風險往往具有長期性;另一方面,由于股權投資方享有企業的最終收益以致股權投資在投資領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此,股權投資在公司戰略、市場分割、納稅服從、投資決策、會計計量、財務報告與披露、財務管理、風險控制和公司治理等領域都非常重要。本文主要討論股權投資的會計計量與列報問題。
一、股權投資及其走勢
股權投資是指為了資本增值或獲得其他利益而取得被投資企業所有者權益所持有的資產,具體表現為參股、取得控制股權或全資擁有被投資公司[ 1 ]。在投資實務中,雖然存在以自有資金或舉債進行股權投資的情形,但就長期股權投資而言,并購則是更為普遍的方式。通過并購取得控制股權,為主并企業在獲取先進技術和市場份額、實現上下游產業融通、稅收籌劃、資金融通等方面贏得優勢,從而形成以小博大、和平擴張、優勢互補和協同效應。
從國際來看,近年來,企業并購可謂風起云涌,并購交易筆數和交易金額以及單筆交易金額之大令人瞠目。根據穆迪(Moody)旗下的分析公司畢威迪(Bureau van Dijk)②《2020年上半年畢威迪全球并購回顧》的統計,即使在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嚴重影響的2020年上半年,并購交易活動的數量和價值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可觀的[ 2 ]。2020年上半年,全球共宣布了43 596筆并購交易,交易筆數比2019年下半年簽署的54 136筆減少19%,同比下降18%;交易總價值達17 466億美元,比2019年下半年減少24%,同比下降31%。在2020年上半年處于審查狀態的已宣布交易中,最大價值的單筆并購交易是英國電信巨頭維珍媒體和歐洲電信公司(o2 UK)(Virgin Media Ltd;Telefonica Europe plc)的合并,總價值達387.14億美元,排名第二的是怡安(Aon)以300.28億美元收購總部位于愛爾蘭的韋萊韜悅(Willis Towers Watson),前九名的并購交易都突破了100億美元大關。
根據《2020年上半年畢威迪全球并購回顧》,在2020年上半年,從數量和價值看,全球并購排在前三的是美國、中國和英國。2020年上半年,中國公司被作為并購標的收購交易達7 271筆,總價值3 225.23億美元,與2019年下半年相比,交易筆數下降27%,交易金額下降12%;與2019年上半年相比,交易筆數下降12%,交易金額上升1%。2020年上半年,英國的這一數字分別為3 364筆和1 317.36億美元③。從中英經濟體量來看,我國并購交易顯然不夠活躍。筆者認為,考慮到疫情之后全球產業分工和經濟復蘇在區域和行業方面都將發生很大變化,以致積極主并的公司和需要被并的公司數量都會十分可觀,全球新一輪并購浪潮及其規模和特點值得密切關注。
從國內來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的三大引擎之一,“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主導社會經濟資源流向的重要經濟活動”[ 1 ]。在我國,股權投資最近三十年來得到迅猛發展。通過股權投資,特別是企業并購,以股權為紐帶的典型意義的企業集團得以迅速組建、擴張,與此同時也對企業跨界發展和技術進步形成了強有力的支持,一些超大型企業集團得以形成,一些技術領先企業和新經濟新業態新平臺企業得以迅速擴張。
二、股權投資會計與決策
股權投資雖然有長短期之分,但長期股權投資與短期股權投資在財務報表上的列報主要取決于企業管理者的意圖及其調整,或者說基于公司發展戰略。關于這一點,投資者和債權人在做公司財務報表分析和投資標的盡調時,資產的流動性水平在長短期股權投資項目的財務報告日節點的操控往往被忽視。
股權投資的支付手段往往涉及融資或換股,更多是通過并購取得控制股權,很少有投資者以全額現金進行長期股權投資。這又涉及取得股權投資的并購方式及其會計處理方法問題。
并購是企業快速發展的手段,并且是資本市場重要的資源配置方式之一[ 3 ]。從業務拓展、價值聚集、技術獲取和行業整合來說,出于取得控制股權考慮而進行并購,隨著時間的推移,并購案的數量、規模和個體體量都在擴充,可謂方興未艾。然而,隨之而來的便是企業合并會計處理方法20年來的變革和商譽會計處理方法的順應改變帶來的諸多困惑,還有原則導向的會計準則制定規則導致的商譽會計計量與再計量的職業判斷失誤甚至是惡意操縱。
并購往往導致商譽在股權取得日的計量和財務報表日的再計量。商譽的計量極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利益關系人(stakeholders)的經濟決策。如果投資者、債權人、審計師等中介機構和監管機構等企業利益關系人不能看穿(see through)公司財務報告中商譽的真實價值和隱含的市場風險,就極有可能被誤導。這種情形一旦發生,投資方將遭受重創,資本市場的公平與效率勢必受到損害。如果這種情形在資本市場上比較常見,則勢必成為資本市場的重大隱患。
按照中外會計慣例,自創商譽不能確認入賬。并購形成的商譽的再計量究竟應該繼續當前的減值測試抑或回歸以前的分期攤銷,近年來在學術界和實務界的爭議很多,實務中也確實存在濫用商譽減值測試方法的情形,因此確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在會計上,股權投資和商譽都存在初始計量和期末再計量。商譽的計量,受制于股權投資初始計量。商譽的期末再計量,在目前的會計準則規范下,涉及是否以及如何確認商譽減值。這個領域,近年來異象叢生。我國部分上市公司在2018年報中進行商譽減值“洗大澡”(take big bath),就深刻地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三、股權投資相關會計計量與問題
這里主要討論企業合并和股權投資的會計處理方法與問題。
(一)企業合并會計處理方法與問題
歷史上,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方法有購買法和權益結合法。作為一項會計政策,二者之間的選擇在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環節是極易被操縱的,其后續影響直至股權取得日之后若干期合并報表的編報。
盡管從理論上來講,購買法和權益結合法適合于不同的合并方式,即購買法適合于投資企業主要以現金或其他資產取得被投資企業的股權,而權益結合法適合于投資企業主要以發行股票的方式來交換被投資企業的股權。但是,在權益結合法下并購企業對被并企業的投資是按較低的賬面價值計價,既不確認被投資企業可辨認資產的增值,也不確認商譽,而在購買法下則是按照被投資企業可辨認凈資產的公允價值來對股權投資進行計價并確認商譽。這樣,采用購買法進行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在合并以后年度,由于要對資產的增值進行轉銷或攤銷和對商譽進行攤銷或減值處理,母公司和集團報表中列示的成本費用要高于權益結合法,收益相應會少,從而使股價管理變得困難,且易于觸發資本市場退市條件。權益結合法將被并企業整個年度的收益都并入并購企業以及集團當年的損益表,而且不確認被投資企業可辨認資產的增值和商譽,一般會使并購企業和集團在合并當年和之后若干年的收益高于購買法。采用權益結合法,按賬面價值而不是按收購成本計價長期股權投資,一般會形成秘密準備,加之較低的折舊以及無須攤銷商譽和轉銷可辨認資產的增值,會為企業帶來較高的報告收益。
購買法與權益結合法會計處理影響的不同,不可避免地誘使一些企業通過業務重構或與被并企業股東進行桌下交易,制造采用權益結合法的條件,將本應采用購買法進行會計處理的企業合并打扮成符合條件的適用權益結合法的企業合并,以做高合并收益和維持股價高位。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盡管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原本設有權益結合法12項苛刻的應用條件,但權益結合法在美國仍然被長期嚴重濫用,成為合并企業及其集團操縱財務報告的一種手段。因此,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于2001年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41號——企業合并》(SFAS 141 Business Combinations)[ 4 ],規定企業并購的會計處理只能采用購買法,禁止使用權益結合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與之對等的準則是2008年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并》(IFRS 3 Business Combinations)[ 5 ],這是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會計準則趨同項目的一項成果。該準則規定,收購方以所支付對價的公允價值計量收購成本,以公允價值為基礎將該成本分配至取得的可辨認資產和負債,將剩余成本分攤至商譽。IFRS 3準則只規范了購買法的會計計量,并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報告同一集團內公司之間企業合并的交易。IASB認為,這種交易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很常見。但由于在IFRS 3準則中未對這種交易的報告做出規范,以致公司以不同的方式報告類似的企業合并。IASB發現: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提供關于收購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在其他情況下他們提供賬面價值信息。而且,在實務中往往是以各種方式提供賬面價值信息。此外,公司關于這些并購往往提供極少的信息。這種多樣性在實踐中使投資者很難理解這些交易對進行此類交易的公司的影響,以及難以在那些類似交易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
因此,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于2020年11月30日發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討論稿——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IFRSR Standards Discussion Paper Business Combinations under Common Control)[ 6 ],就同一控制下的同一集團的企業合并中,對可能的新會計要求開展公眾咨詢,征詢意見將于2021年9月1日截止。《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討論稿——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 6 ],提出了IASB關于如何補充IFRS 3準則的初步觀點。理事會的目標是在實踐中減少多樣性,提高報告這些交易的透明度和可比性。理事會的初步觀點是,當對投資者提供信息的利益大于成本時,公司應該提供類似的企業合并信息。具體地說,理事會建議在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對集團之外的股東形成影響時,應該提供公允價值的信息。這個建議與IFRS 3對用于不相關公司之間的并購的現有要求一致。在所有其他情況下,理事會建議應提供一種基于IFRS準則的單一方法的賬面價值信息。
在我國,按賬面價值確認長期股權投資的會計處理方法,在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依然在使用。換言之,我國會計準則針對企業合并業務的會計處理并沒有完全采用購買法。對于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采用賬面價值確認長期股權投資的方法,本身在邏輯上具有合理性,在實務上對于企業擴張來說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別是對高新技術企業和新經濟新業態平臺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沒有在會計準則上形成掣肘。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 7 ],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合并方應當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在最終控制方合并財務報表中賬面價值的份額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與支付對價賬面價值(或發行權益性證券面值總額)的差額,應當調整資本公積,資本公積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收益。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 8 ],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合并方取得的資產和負債,應當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賬面價值計量,合并方取得的凈資產賬面價值與支付的合并對價賬面價值(或發行股份面值總額)的差額,應當調整資本公積,資本公積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收益。
在我國,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方法,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一致,即采用購買法。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 8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購買方在購買日應當按照確定的合并成本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成本。購買方在購買日對作為企業合并對價付出的資產、發生或承擔的負債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購買方對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應當確認為商譽。初始確認后的商譽,在以后的會計期間,應當以其成本扣除累計減值準備后的金額計量。
很顯然,在我國,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計量,是按賬面價值入賬,實際上采用的是權益結合法,因此并不產生商譽。盡管如此,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仍然是大量的。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 8 ],其會計處理則只能采用購買法,由此才會形成商譽。
(二)股權投資會計處理方法與問題
股權投資的會計處理方法主要是成本法和權益法。二者對企業的損益影響不同,因此其適用條件就很重要。采用權益法會按持股比例將被投資企業的報告損益計入投資企業,因而會影響投資企業的資產和收益的報告金額。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 7 ],投資方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長期股權投資采用權益法核算。也就是說,權益法核算適用于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方對被投資方的長期股權投資持股比例可能因為公司戰略、財務或經營的需要增加或減少,從而使投資關系在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響或非前述三種之間變化,因此是否符合適用權益法的條件便可以在投資業務環節進行操縱性選擇。第一,是否對被投資企業形成重大影響的判斷取決于管理層意圖。雖然《第18號意見書:普通股投資會計核算的權益法》提出以直接或間接持股20%作為“重大影響”的判斷標準,但近年來對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響和重要性不給定具體比重的做法已經成為通行的會計慣例。實踐中,“重大影響”難免受管理層主觀判斷的影響。有研究表明,企業可以通過借助“重大影響”的判斷,選擇或變更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方法[ 9 ],因此,準則的進一步細化和規范尤為重要。第二,是否對被投資企業形成實質上控制、共同控制,需要職業判斷。“實質上控制”是一個難以量化的標準,因此被濫用的情況時有發生,從而為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盈余操縱提供了空間。另外,濫用實質重于形式的會計原則,也表現在合并財務報表合并范圍確定環節,實務中也確實有一些企業在股權投資入賬環節或股權投資存續期間以操縱利潤為目的來選擇或變更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方法。總的來說,現有會計準則仍然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和探討的部分,不斷地更新和細化準則與規范是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更是時代發展的趨勢和要求。與此同時,對企業管理層意圖的準確把握,也是反觀相關企業長期股權投資會計處理方法是否正確的一把鑰匙。至于企業管理層在財務報表日將原本列為長期資產——長期股權投資的部分或全部金額改為列在流動資產,既可能存在操縱流動比的動機,也可能完全是出于戰略或經營考慮。由于公司適用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所處經營環境以及市場競爭的突發性變化,或僅僅出于公司戰略或經營考慮,即使在下一報告期將轉為流動資產的長期股權投資轉回也無可厚非。
四、商譽及其確認與計量
商譽及其確認與計量,不但在企業估值方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且直接影響財務報告的質量、審計和內控的相關風險,甚至公司治理的成敗,因而是管理層監管、資本市場管制和投資者等其他企業利益關系人相關決策需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因素。
(一)商譽及其確認
學術界關于商譽內涵的爭議不斷,相繼衍生出好感價值觀[ 10 ]、超額盈利觀[ 11 ]、總計價賬戶觀[ 12 ]、協同效應觀[ 13 ]等多種觀點。而人們對商譽本質觀點的不統一,又引發了商譽確認及計量的一系列爭議。
確認,是指將交易或事項計入財務報表的過程。商譽的會計確認是非常魔幻的存在。根據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 8 ],購買方對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應當確認為商譽。如前所述,只有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采用購買法,才會在母公司賬表和集團合并報表中體現商譽。按照中外會計慣例,自創商譽不予確認,即不能入賬、計入財務報表或用財務報表附注披露。因此,一般的情形很可能是一個企業經過很長期間的成功經營,形成諸多優勢,諸如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產品不斷創新、引領行業發展、市場占有率高、管理先進、總部經濟環境優越、購貨商長期穩定、供貨商優質誠信,這樣的企業雖然賬上看不到商譽,但確實具有長期獲取未來超額收益的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只要這家企業的股權沒有售賣,確認商譽就無從談起。于是,商譽的確認,是且僅是企業并購的產物。
商譽金額的計算,理論上有多種方法,但共識是所并購股權的買價與所并購企業可辨認凈資產被并份額公允價值之差,或者說是并購溢價。并購取得的股權,可能存在由于調研局限或經辦人員舞弊而高價買入的情形,也可能存在并購方具有超凡的談判能力,或被并購方生產經營及財務遭遇極大困難,抑或并購形成的協同效應可以帶給被并方超常發展機遇而低價買入的情形。因此,商譽資產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未來獲得超額收益的能力,但也應該看到通過并購形成的股權投資初始成本和商譽的初始確認金額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和不可證實性。
即使并購的買價不是問題,確定所并購企業股權份額的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是因為,確定這一金額,需要對應收款項可收回額與應付款項公允價值互抵的凈額、存貨在股權取得日的可實現凈值、固定資產重置成本的折余價值和無形資產公允價值的攤余價值等予以辨認,這不僅需要掌握不同類別資產和負債估值的技術,而且需要估值人員對被并購企業所在行業、產品、技術和服務有與時俱進的了解,并且具有較高的職業操守和敬業精神。隨著幾十年來會計準則國際協調乃至最近20年的全球趨同,會計處理方法的可選擇性正在逐步削減,準則制定更多的采取原則導向,由此使得日常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過程存在更多的職業判斷,使得商譽很可能被過分高估而為企業并購埋下風險隱患[ 14 ]。同時,所并購企業可辨認凈資產對應的資產負債的賬面價值本身也有可能存在很多問題,更毋庸諱言企業經營宏微觀環境變化和管理問題導致的資產及負債賬面余額本身背離其價值的情形。
總的來說,作為基于并購買價倒擠出來的商譽金額確定的過程本身,充滿了不確定性和職業判斷所帶來的操縱機會,由此導致會計信息質量的降低,必將有損資本市場的公平與效率。目前,人們也許無法為商譽的確認提供更為科學有效的規范指導和監督,但商譽確認過程所衍生的不確定和風險并非無從應對,例如高水平的會計穩健性、較高比重的機構投資者和管理層持股比例,以及較多的分析師關注等對商譽資產蘊含風險的控制作用[ 15-16 ]。因此,充分發揮會計監督功能以及加強公司內外部治理未嘗不是解決商譽確認問題的一個可行方案。
(二)商譽的計量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作為一項共同努力分別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42號[ 17 ]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5 ]中,將合并商譽由直線攤銷法改為減值測試法,旨在提高商譽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借鑒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做法,根據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 18 ]規定,因企業合并所形成的商譽,無論是否存在減值跡象,每年都應當進行減值測試。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第142號準則《商譽和其他無形資產》[ 17 ]發布實施之前,商譽在美國應不少于40年攤銷完畢。第142號準則將商譽攤銷改為減值測試,這是對141號準則《企業合并》[ 4 ]取消企業合并權益結合法的對應改變。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商譽減值測試的處理方法,在實行過程中不斷顯現出其弊端。商譽減值測試取決于公司對未來盈利情況的預期,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出于股價管理、融資約束或監管紅線的種種考慮,很多企業盡可能避免對商譽進行減值處理,以致理論界和實務界越來越關注由于商譽減值未能及時足額確認而引發財務和市場風險的問題,從而恢復商譽攤銷會計處理的呼聲不斷加大。另外,商譽減值需要基于對公允價值的確認,但在不存在活躍交易的市場價格的情況下,公允價值無法得到證實,管理層披露商譽的機會主義動機增加,以致商譽資產成為盈余操縱的工具[ 19 ]。
(三)商譽的市場風險
商譽的計量情況究竟如何呢?根據Wind數據庫,截至2018年底,2 048家上市公司商譽余額為13 082.5億元(已計提減值)。2018年885家上市公司共計提了1 667.64億元商譽減值損失,分別是2017年的4.5倍,2016年的14.6倍,2015年的21.2倍,2014年的62.8倍。
再看看2018年報涉及商譽的審計意見的分布情況。根據北京興華會計師事務所網站《2018年上市公司商譽審計分析》[ 20 ],就涉及財務報表商譽余額而言,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達12 130.7億元,占比92.7%;無保留意見帶解釋性說明段審計報告達515.2億元,占比3.9%;保留意見審計報告360.7億元,占比2.8%;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75.9億元,占比0.6%。四種審計意見中,后三種總計占比7.3%。由此可見,審計師對2018年嚴重奇高的商譽攤銷并未顯示對應的職業謹慎。
《2018年上市公司商譽審計分析》[ 20 ]表明,在關鍵審計事項中,商譽減值為1 075項,占比14.5%。這一占比是標準無保留意見之外的審計報告涉及商譽金額占比7.3%的一倍。該分析認為,注冊會計師將商譽減值確定為關鍵審計事項的原因主要為:商譽對財務報表整體具有重要性;商譽減值測試及其使用的參數涉及管理層的重大會計估計和判斷,這些判斷存在固有不確定性并可能受到管理層偏向的影響。顯然,商譽減值蘊含的風險比表面數字大得多。
由于近年來企業并購業務發展迅猛,上市公司累積了大量的商譽,而且被并企業完成對賭協議之后出現業績下滑趨勢是常態,以致現存巨額商譽隱含的風險極易爆發。關于目前實行的商譽減值測試的會計處理,業界一直存在憂慮。一旦商譽的會計處理由減值測試改為攤銷,商譽余額對企業凈資產占比較大甚至超越凈資產總額的企業,ST或退市顯然只是時間問題。這種情形,在傳媒、休閑服務、計算機、醫藥生物、家用電器這些商譽超過凈資產50%甚至100%的行業來說,問題尤為嚴重。
(四)商譽會計相關制度分析
資本市場參與者尤其是上市公司,往往高度關注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和證券監管機構的政策動向。在美國,最受矚目的是美國證監會(SEC)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中國是中國證監會和財政部。
2018年11月,證監會會計部發布《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 21 ],對上市公司2018年報商譽減值行為進行規范,詳細規范了上市公司、審計師、資產評估師的責任。證監會的上述風險提示引起業界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國際上對商譽減值測試會計政策的弊端也多有討論。2019年1月4日,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官網發布了《企業會計準則動態(2018年第9期)》[ 22 ],報道財政部會計司針對會計準則咨詢論壇的“商譽及其減值”議題文件征求了會計準則咨詢委員的意見,大部分咨詢委員認為,相較于商譽減值,商譽攤銷能夠更好地實現將商譽賬面價值減記至零的目標,因為商譽攤銷能夠更加及時、恰當地反映商譽的消耗過程,并且該方法成本低,便于操作,有利于投資者理解,可增強企業之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并建議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就如何確定商譽的攤銷方法及使用壽命給予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咨詢委員的上述意見,被外界理解為財政部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支持“商譽攤銷”,而非現有的“商譽減值測試”。商譽攤銷一旦取代減值測試,大量上市公司將受到波及,由此輿論嘩然。2019年1月8日,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布《關于咨詢委員就商譽會計處理研討意見的說明》予以澄清,解釋“商譽及其減值”反饋意見的觀點僅是咨詢委員們針對有關會議文件發表的專家研討意見,請各有關單位和企業按照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現行要求對商譽做好相關會計處理。
即便如此,商譽減值風險一直是監管層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例如,財政部監督監察局2019年3月29日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商譽減值監管的通知(財監便〔2019〕23號)》[ 23 ]。2019年,證監會及各地證監局懲處文件涉及12個商譽減值測試評估項目,這些監管案例中關于商譽減值測試評估提出以下問題:(1)商譽相關資產組辨識及核查驗證問題;(2)評估方法及參數指標前后期一致性問題;(3)包含商譽資產組賬面價值與預計現金流一致性問題;(4)預計未來現金流量評估依據核查驗證問題;(5)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模型計算錯誤問題;(6)預計未來現金流量預測依據不充分問題[ 24 ]。
根據我國現行會計處理規定,企業合并所形成的商譽,至少應當在每年年度終了時進行減值測試,減值一經確認則不得轉回。而《企業會計準則》(2006)在2007年1月1日實施之前,我國的商譽會計處理采用直線攤銷法,攤銷年限一般不超過10年。從前述商譽相關數據不難看出,一旦商譽會計處理方法由減值測試回歸直線攤銷,對商譽金額和占比大的公司來說,必將帶來巨大的風險。
我國上市公司2018年報出現的商譽減值“洗大澡”浪潮,從現象上看是由資本市場上關于商譽的種種討論和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所引發,從實質上看則是源自企業并購爆發式增長和諸多溢價并購行為的長期累積。從監管部門來說,需要進一步完善包括并購定價和對賭協議條款在內的相關制度。從投資者和債權人來說,應該高度關注商譽對凈資產占比過高的公司和長期未做減值處理的公司,盡可能避免買入相關股份或對所持股份擇時減持。對上市公司來說,應當誠信穩健經營,堅守公平交易底線,及時客觀地確認商譽減值,堅持相關財務信息的公允列報。從會計穩健性的優良傳統和資本市場公平與效率的原則來說,商譽期末重評價的會計處理方法應該由減值測試改回直線攤銷。考慮到近年來信息技術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產業結構持續調整、技術迅速迭代、國內外產品和服務市場的激烈競爭、消費偏好的迅速變化,將商譽期末重評價改回直線攤銷法,應該是時候了。
五、股權投資研究述評及展望
股權投資現行會計處理方法缺陷帶來的操縱空間和會計信息質量的降低,可能導致投資者決策失誤和觸發資本市場風險,值得高度關注和深入研究。然而,目前大部分相關研究聚焦于私募股權投資對公司治理和企業價值等方面的影響[ 25-27 ],鮮少有文獻探討現行股權投資會計計量和列報的問題及其潛在危害,學術界和實務界對相關會計準則實施情況的調研及系統深入的研究更是很難見到。導致這種研究現狀的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股權投資會計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和對策研究門檻。股權投資會計是一種相對而言比較復雜的業務,研究股權投資會計計量及列報的缺陷和風險,要求研究者對股權投資會計準則和相關理論及實務具備較為深刻的理解,以及對公司財務全局和細節的敏銳洞察力。第二,確定股權投資價值在理論上和實務上都存在較大困難。
因此,股權投資會計問題的研究,有必要采用規范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法實現理論上的突破,從更長時期和更為廣闊的視角研究股權投資相關會計準則及其變遷的內在邏輯和原理,研究公司價值創造和股權價值形成的機制及路徑,特別是應該將大樣本分析與案例研究、實地調查和訪談相結合,了解企業經營管理和相關準則執行的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案。企業合并、長期股權投資和商譽的確認與計量特別是期末重評價,是值得長期研究的領域。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金融工具準則的出臺和實施,使得企業的財務報告編制者、審計師、監管機構面臨以公允價值計量和列報股權投資在技術、成本、審計及監管上的嚴峻挑戰,由此成為目前迫切需要集中投入和系統深入研究的領域。
公允價值的引入進一步增加了確定股權投資期末余額的主觀判斷和評估程序及難度,因此人們很難借助報表數據了解長期股權投資的真實情況及其蘊含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基于企業財務及非財務信息、企業微觀和行業中觀以及國家乃至國際宏觀政策和形勢合理估計長期股權投資的真實價值,便成為一個重要且迫切的科學問題,值得后續研究加以著力拓展。
【參考文獻】
[1] 曲曉輝.股權投資管理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2-3.
[2] Bureau van Dijk - A Moody's Analytics Company. Global M&A Review H1 2020[EB/OL].https://www.bvdinfo.com/en-gb/.
[3] 盧煜,曲曉輝.商譽減值與高管薪酬:來自中國A股市場的經驗證據[J].當代會計評論,2017(1):70-88.
[4]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141.Business Combinations [EB/OL]. June 2001.
[5]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No.3 Business Combinations [EB/OL].January,2008.
[6]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IFRSR Standards Discussion Paper Business Combinations under Common Control.[EB/OL].30 November,2020.
[7] 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EB/OL].2014.
[8] 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EB/OL].2006.
[9] COMISKEY E E, MULFORD C W.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the equity accounting standard[J].The Accounting Review,1986,61(3):519-525.
[10] 楊汝梅.無形資產論[M].施仁夫,譯.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9.
[11] 葛家澍.當前財務會計的幾個問題:衍生金融工具、自創商譽和不確定性[J].會計研究,1996(1):3-8.
[12] 馮衛東.基于知識經濟的商譽會計:理論研究與準則改進[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5.
[13] 鄧小洋.商譽會計論[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1.
[14] 傅超,王靖懿,傅代國.從無到有,并購商譽是否夸大其實?——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經濟問題,2016(6):109-123.
[15] 王文姣,傅超,傅代國.并購商譽是否為股價崩盤的事前信號?——基于會計功能和金融安全視角[J].財經研究,2017(9):76-87.
[16] 魏志華,朱彩云.超額商譽是否成為企業經營負擔:基于產品市場競爭能力視角的解釋[J].中國工業經濟, 2019(11):174-192.
[17]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142. 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s [EB/OL].2001.
[18] 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EB/OL].2006.
[19] RAMANNA? K. The? implications? of? unverifiable fair-value accounting:Evidence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odwill accoun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8,45(2):253-281.
[20] 北京興華會計師事務所.2018年上市公司商譽審計分析[EB/OL].http://www.xhcpas.com/xwdt/xyxw/2019 0716/310.html,2019.
[21]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EB/OL].http://www.csrc. gov.cn/ pub/ newsite/ kjb/kjbzcgf/xsjzj/sjpgjggz/01811/ t201811 16_346845.html,2018.
[22] 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咨詢委員對IFRS會計準則咨詢論壇“商譽及其減值”議題文件的反饋意見[EB/OL].2019年1月4日財政部會計司《企業會計準則動態》(2018年第9期),http://www.casc.org.cn/2019/0104/184671.shtml.
[23] 財政部監督監察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商譽減值監管的通知(財監便〔2019〕23號)[EB/OL]. [2019-03-29]https://www.sohu.com/a/304962030_99913655.
[24] 北京資產評估協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研究報告2019年第二期——商譽減值測試評估[EB/OL].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771541065422.html,2019.
[25] KATZ S P.Earnings auality and ownership structure:the role of private equity sponsor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84(3):623-658.
[26] 王會娟,張然.私募股權投資與被投資企業高管薪酬契約:基于公司治理視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2(9):156-167.
[27] 李九斤,王福勝,徐暢.私募股權投資特征對被投資企業價值的影響:基于2008—2012年IPO企業經驗數據的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5(5):15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