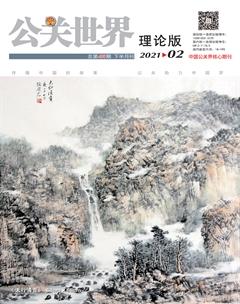走出內卷化:韓國教育熱的冷思考
熊作勇
摘要:韓國教育是韓國成功故事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分享其榮光的同時,也內蘊著韓國現代轉型過程中未曾化解的一系列深刻矛盾。在韓國教育熱諸種怪相的背后,是民族振興激發起來的全民教育熱情,是教育公平與選拔性人才培養、社會流動與精英塑造這些兩難之間的拉鋸。而走出內卷化的兩條路徑——一場重新定義幸福以及社會成功標準的文化變革,以及擺脫“高收入陷阱”——看起來都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韓國 教育熱 思考
韓國教育歷來享有盛譽。它與韓國的經濟崛起相伴而生。在經濟起飛前夜的1950年代,韓國人口普遍文盲狀態,短短兩代人之后,就已發展到成人識字率近98%,大學人口比率和經合組織國家大致相當——這樣的飛速發展,即使以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創下的教育發展記錄來衡量,也是驚人的。可以說,教育是韓國從經濟廢墟中崛起的決定性因素。用狂熱來形容韓國人對教育的態度并不為過。實際上,這也正是美國政治學家Michael J. Seth為其二戰后韓國教育發展史而擬的書名(Education Fever: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Pursuit of Schooling in South Korea)。
“教育熱”很好地抓住了教育在韓國社會的地位。正如美國《時代》周刊所說,沒有對教育的癡迷,韓國不可能成為今天的經濟強國。但與此同時,韓國教育也有陰暗的一面。它尤其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而飽受詬病。韓國教育在助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讓全社會承受了極其高昂的成本。
在一些觀察者看來,當下的韓國社會,教育早就已經脫離了它的本質,處于一種異化的狀態。教育領域呈現出諸多的悖論與不合情理之處。與同樣注重教育的幾個北歐國家相比,韓國教育的投入與其產出嚴重不成比例。為了滿足社會大眾對于教育的渴求,韓國教育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與經濟體系嚴重脫節。教育系統每年輸出眾多大學畢業生,經濟體系卻不能提供相應的就業崗位。教育政策以注重社會公平為圭臬,為此不惜在很大程度上犧牲創新性人才的培養和選拔,但與此同時,正規教育體系以外的課外補習班卻又異常發達。
一直以來,私人教育機構膨脹及其治理都是韓國教育的熱點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今日韓國日益激烈的升學競爭中,以提供均等化教育為目標的公立教育遠遠滿足不了實際的社會需求,私立教育機構應運而生,蓬勃發展起來。反過來,韓國社會存在的高學歷人力過剩的問題又進一步助長了私人教育機構的膨脹。如今,韓國的中小學生白天在公立學校上學,放學后到各類私人教育機構學習。私人教育在韓國已經成了體量巨大的產業。《紐約時報》甚至稱這些“企業化規模”的補習班為“韓國教育體系的支柱”。私人教育機構膨脹的背后是韓國式的教育軍備競賽和“拼爹”:因為學位對于一個學生的未來至關重要,是成功的跳板,于是富裕家庭開始砸錢在各種課外補習班上,以提高子女入讀名牌大學的機會,經濟條件一般的家庭尚能勉力支撐,而下層的貧困家庭就只能望洋興嘆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表明,韓國是家庭在教育上花費最多的國家。教育開支已成為許多家庭除了房貸以外的沉重負擔。
教育問題早已溢出了社會領域,成為左右韓國政治輿論和選舉舞臺上的一個焦點話題。在現代社會,教育可以說是社會流動和人才選拔機制的核心環節,教育于是成為社會各階層爭奪稀缺資源和支配權的戰場。處于不同社會集團較量的夾縫之中,韓國政府左支右拙,希望可以同時解決人才培養質量和教育公平這兩大天字號難題。教育政策領域所有過往的經歷證明,這近乎是一個永遠無解的博弈論困境。慣常的模式是,教育官僚部門發現良好的新政與始料未及的社會反饋之間反復幾輪互動,矛盾往往又回到了原點,且更為嚴重。比如,政府試圖在考試和招生政策中引入多樣化,然而,應試方式的多樣化又讓家長和考生們不知如何應對,其結果是課外教育熱不僅沒能退潮,反而催生出了“應試策略輔導”等五花八門的新服務,私人課外教育的花樣反而越玩越多。總之,在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的情況下,家長和考生為了保險起見,只能更加依賴私人課外教育。私人教育機構成為“打不死的小強”,越治理越泛濫,只能說明韓國教育有著一些更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教育社會學上長期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研究傾向,整合論者認為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通道,有助于社會凝聚,而沖突論者則將教育看作是階級階層沖突的另一種形式,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鞏固既有的利益格局和階層分化。圍繞韓國教育產生的大量爭議,堪稱教育社會學研討班上的絕佳討論個案。
對韓國教育熱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后果,人們嘗試從多種角度加以理解。有人認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教育熱的產生不是一種孤立現象,而是多種社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關于教育熱背后的家長的教育信念和支援行為,就有著眾多的個案研究。還有些人試圖從愈演愈烈的教育熱潮的歷史根源入手,追溯韓國教育問題的癥結源頭。代表者如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日本人中村修二。在獲獎后的一次記者會上,中村認為,當下韓國教育熱的癥結,還在于整個東亞的教育體系受到普魯士模式和傳統儒家科舉制度的影響過于深重。
中村的論證邏輯大致如下:18世紀的普魯士最先實施了一套后來成為現代化模板的大眾普及教育體系,其重心在于塑造易于管理、近乎整齊劃一的國民。這個體系恰好與工業化時代對于教育體系的需求無縫對接,為工業化起飛階段提供大量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但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創造力。而源自中國儒家的科舉制度,則是以公開競爭性考試為工具,為文官系統選拔人才。這種教育體系在促進社會流動的同時,同樣有著巨大的流弊,尤其會讓學生過度強化復習,投入過多的精力在重復性知識上,而僅僅為了在考試中更少出錯。東亞國家作為追趕型的落后國家,以一種后來者特有的追趕心態,強化了這套教育體系。相比之下,在工業化的起源地西方世界,不管經濟還是教育,都有比較緩和而自然的發展期,呈現出一種市場經濟加創新型教育的雙元組合。而被裹挾進入現代社會的東亞國家則沒有這樣的歷史余裕,出于自我防衛和追趕超越的需要,只能采取國家主導的計劃發展。具體到教育上,就是為了適應工業化的海量人才需求,采用了一種類似工廠流水線的、瘋狂追求效率的大眾教育模式。
另一個觀點則認為,韓國教育熱只是一個更為根本問題的表征。教育熱的存在,表明韓國社會陷入了某種內卷化而不能自拔。內卷化原是人類學家格爾茨在考察上世紀六十年代印尼農業發展時使用的一個概念,他注意到印度尼西亞許多世紀以來稻作文化的強化產生的結果更多是社會的復雜性(勞動生產率維持不變甚至下降),而非技術突破。后來,人們將這一概念泛化,用于描述那種長期停留在一種簡單層面的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復,而沒有發展的增長。內卷化現象廣泛出現在各個領域中,比如家族發展的自我重復、行業發展長期停留在一種簡單重復勞作等等。對韓國而言,在實現經濟起飛,一舉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躋身高收入國家之后(現人均約三萬美元),它已觸碰到某種隱形的天花板。韓國的外部內部發展空間,都存在著結構性局限,很難輕易打破。就外部而言,是韓國特殊的國際地位。戰后韓國加入了美國戰略軌道,是美國東亞秩序的“小伙伴”,外交安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監護,通過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成功實現了經濟現代化。但在美國體系下成長的代價之一就是,韓國必須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在美國資本支配下承擔價值鏈分工的某一環節。比如,韓國的“國家冠軍”公司三星,實際上就是由華爾街資本持股甚至控股的。就內部而言,是韓國的財閥壟斷格局。而在韓國內部,數十家大型財閥家族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大半江山。據統計,居于頂端的十大財團占據韓國75%以上的GDP,觸角深入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財閥集團壟斷了最賺錢的行業,卻只雇傭了全國3%左右的員工數。有人分析,在韓國,財閥長期雇員和公務員、教師、金融業者、律師一起,成為新時代的金飯碗,分化為韓國中產里面的上層中產階級。韓國教育熱的實質,就是整個社會,不分貧富,都希望躋身這個嚴格受限的專屬俱樂部。而在現代社會唯一合法的的社會晉升獨木橋,就是教育。
某種意義上,韓國的教育熱就是一個競逐游戲。在這個舞臺上,充斥著太多的追求者,戰利品卻又太少。除非想辦法分流一部分競逐者,或者有效地擴大戰利品,否則韓國的教育熱將持續受困于內卷化而無法解脫。
英國和德國分別代表了分流的兩種模式。在英國,孩子要在11歲時接受選拔性測驗(類似中國的小升初考試)。在考試中表現出卓越學術潛質的孩子將升入文法中學(相當于國內的重點中學),成為若干所頂級大學和社會精英的候選者,而測試成績一般的孩子則分流到普通中學。在普通中學完成中等教育的孩子,無論是社會期待還是在自我期望中,都不準備升入大學,或者只滿足于考取一般大學。毫無疑問,這套分流體制能夠運轉的的關鍵,在于英國存在著一套較為固定化的階級分層及其階級觀念。正如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如何繼承父業》這一經典研究中所揭示的,英國歷史上工人階級、藍領出身的孩子大多會承襲父輩的一套階級觀念,在主流文化教育機構中往往表現疏離,習慣以各種形式的消極反抗,比如逃學、男子化的粗魯言行來確認自身的階級認同,從而在實質上退出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德國的做法則是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提前分流相當比例的年輕人。德國模式的成功秘訣在于,在其經濟發展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以后,并沒有簡單地“去工業化”,而仍然維持了一個龐大的且擁有超級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能夠為技校畢業生提供大量就業崗位且薪資優厚。如此一來,大量的工業人口無需加入選拔性高等教育入門考試,教育體系中偏重精英教育的一端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自然就會減輕。
與有著刻板階級差異的英國相比,韓國是高度平等主義取向的社會,社會流動期望和晉升欲望更為強烈。對于優質教育資源及其所代表的高收入和高地位,每個社會階層都不甘人后,都認為自己有權去爭取。而藍領所從事的體力勞作和非熟練工作崗位,則普遍遭到鄙視。藍領工作不僅收入微薄,社會評價也非常低下,幾乎是失敗的代名詞。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英國模式的階級分層,還是德國模式的技術分流,韓國都很難簡單仿照。韓國唯一的內部出路,也許在于一場文化變革,整個社會需要重新定義幸福、成功以及社會地位的標準。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長期的經濟繁榮之后,西方國家一度進入“充裕社會”,隨即在價值觀領域出現了一場“后物質主義”轉向,人們尤其是年青一代的關注領域向更多的物質以外的領域延伸,比如政治、生活和社會環境的質量。或許可以期待,韓國也會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而出現一場類似的價值領域的變革,一些社會成員意識到不參與這場競逐游戲,日后也能擁有社會體面和相對不錯的前程。這個前景當然是一個社會系統共同努力的結果。
分流不易實現,“擴大戰利品”也是任重道遠。所謂擴大戰利品就是做大蛋糕,進一步擴展韓國的社會活力和國際空間。就內部而言,必須凝聚強有力的政治意志,以結構性改革,松動財閥壟斷的經濟格局,釋放出被壓抑的社會活力;就外部關系而言,韓國必須決心沖破現有的國際分工格局,占領價值鏈中更多的高端領域。只有這樣,才有增量資源的注入,才能打破內卷化的惡性循環。韓國的教育熱才能適度降溫,教育體系才能回歸正常角色,既滿足一個平等主義取向社會對于社會流動的合理期望,又能適應韓國邁向世界前沿國家所需要的大量創造型人才的培養需求。
參考文獻:
[1]樸光星,《透視韓國“課外教育過熱”現象》,《光明日報》(.2018年08月15日.
[2]趙同友,李鍾玨,《韓國教育熱的社會文化密碼——從文化建構與解碼的角度分析》,《外國教育研究》,2012年第六期.
[3]劉巧云,《從歷史文化視角看中韓教育熱現象》,《科教文匯》,2020年3月(下).
[4]趙偉偉,《論韓國的高等教育熱》,《高等教育》,2012年第六期.
[5][美]蘭德爾·柯林斯,《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6][英].保羅·威利斯,《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如何繼承父業》,.譯林出版社,2013年.
[7][美].安妮特·拉魯,《不平等的童年:階層、種族和家庭生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8]鄭也夫,《吾國教育之病理》,中信出版社,2013年.
[9]艾宏歌,《當代韓國教育政策與改革動向》,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
[10]Bok-Rae,.Kim,.‘The.English.Fever.in.South.Korea:.Focusing.on.the.Problem.of.Early.English.Education,.Journal.of.Education.&.Social.Policy,.Vol..2,.No..2;.June.2015
[11]Michael.J..Seth,.Education.Fever:.Society,.Politics,.and.the.Pursuit.of.Schooling.in.South.Korea,.University.of.Hawaii.Press.(September.3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