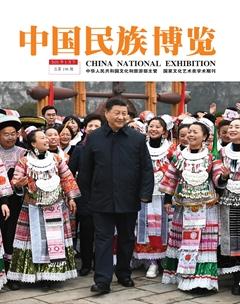清代青州駐防的歷史變遷與民族文化融合
【摘要】清代青州駐防從設立到衰落,經歷了最初設法避免旗人“沾染漢俗”而實行“旗民隔離”政策,到后期逐漸打破人為的隔絕局面,最終走向民族融合的歷程。在這一演進過程中,八旗生計問題是導致駐防解體的重要因素,同時,駐防解體極大地促進了滿漢民族文化融合。
【關鍵詞】清代青州駐防;歷史變遷;民族文化融合;民族變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2-102-03
【本文著錄格式】黃淵紅.清代青州駐防的歷史變遷與民族文化融合[J].中國民族博覽,2021,01(02):102-104.
基金項目:山東省藝術科學重點課題“清代山東駐防八旗歷史文化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ZD201906438)。
一、青州八旗駐防的設立
青州自古為“九州”之一,“東方之重鎮”,是膠東半島與濟南府之間的連接要道,地處海陸交接地帶,北臨渤海,南接運河區域,對山東甚至華東地區的海防都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
世宗原擬于山東登、萊兩府的沿海仿照天津設立滿洲水師營,而時任河東總督的田文鏡經查勘登萊膠州一帶后奏其不便。雍正七年(1729),議政大臣等議復,田文鏡上奏:“山東青州府,為適中要地,內陸與陸路各營聲勢聯絡,外與沿海營汛呼吸相通,設立滿洲兵駐防,可以資彈壓而重保障。”于是,清廷決定設青州駐防。為了避免旗人“沾染漢俗”,失去監視綠營之功效,同時方便駐防旗人日常操練和生活,將青州駐防地選定在青州府北5里的平坦之地,地勢高,便于防守。隨后,清廷派湖南進士田敬山監督,令青州知府廣壽指揮建造青州旗城。
歷時三載,一座規模恢宏、布局嚴整的旗城竣工。“雍正十年,設駐防于縣境,樓櫓壯麗,士馬飽騰,遂屹然為東方巨鎮焉。”[1]青州駐防是雍正朝設置的規模最大的永久性駐防之一。據《飲定八旗通志》記載:“設滿城一座,四門城樓,四座大城,月城共門八座,出水閘三座,周圍長一千零四十九丈,四門外防河石橋四座”,其中設有公衙門和將軍、副都統等各類衙署,以及兵丁、將役的營房,共計4000多個房間;離城三里設有教場一座,計一百六十丈;在城外建有普恵寺、福應廟。因地理位置與青州府南北遙相呼應,故稱之為“北城”,青州府為“南城”。
雍正九年(1731)清廷擬設將軍和副都于青州駐防,最高軍事長官為將軍,“調江南江寧將軍鄂密達為山東青州將軍……升江寧協領阿爾胡禪為山東青州副都統。”[2]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派將軍鄂密達和副都統阿爾胡禪,以及八旗滿洲騎兵2000人,步兵400人,協領四員,佐領、防御和驍騎校各十六員,理事同知一員,隨印筆帖式三員,駐青州。隨軍帶有兵工、鐵匠等,旗兵家眷也陸陸續續隨遷而來,進駐旗城的人員4700戶,達10000多人,自此開啟了滿洲八旗在青州駐防的序幕。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裁青州將軍獨設副都統,副都統直接聽從中央調遣。清政府裁青州將軍后,則剩職官50 員,即副都統 1 員、協領兼佐領 4員、佐領 12員、防御 16員、驍騎校 16員、筆帖式 2員。
某一駐防職官并非永久駐守在某一個駐防地,而是因種種原因根據需要經常調動。據孫菲菲(2012)[3]整理《青州八旗將軍及副都統表》知,自設立之初雍正九年(1731)到民國十八年(1929)青州駐防旗兵團與八旗組織解體,期間曾任命十四名將軍、四十八名副都統。
雍正朝以后,清廷再三強調“滿洲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青州亦首重騎射,軍隊訓練也以騎射為主。青州駐防旗兵訓練有素,具有很強的戰斗力,不僅加強了海防力量,控制了整個山東,對鞏固清王朝對全國的統治亦至關重要,確實達到了“無事則壁壘森嚴,收猛虎在山之勢;有事則整師從出,無援不及時之虞”[4]的目的,曾在臨清、曹州之戰中成為八方馳援、越野摧堅的勁旅。鴉片戰爭時期,青州八旗駐防官兵渡過長江扼守江防要地鎮江,阻擋了英國侵略軍的侵略步伐。出兵太平天國捻軍運動,表現出不俗的戰斗力,受到清政府的獎賞。
二、青州八旗駐防由盛而衰的轉折
清軍入關前出則為兵、入則為農。入關后,為保持八旗武力,清前期歷代君主對駐防旗人采取種種限制措施,禁止旗人從事工農商,實行餉兵制度,由國家供其俸餉,故習武作戰是八旗子弟的唯一出路。“凡兵丁等、承應官差,養贍家口,專于糧餉是賴。”[5]旗人完全依靠國家供養,不從事生產活動,亦不得從工商,“今之扼腕八旗生計者,輒曰國有四民功令,獨旗人不得經商逐利”,[6]賴餉而食是清代旗人的基本特征。糧餉制有效地保證了清政權從地方性政權向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的轉變,但是為清后期的“八旗生計”問題埋下了隱患。[7]生計問題也成為了青州八旗駐防走向衰落直至解體的重要因素。
青州旗城俗語道:“一厘一毫,悉出圣主”,青州駐防官兵依靠朝廷兵餉為生計。“青州新設駐防官兵,其官兵俸餉口糧馬匹草料,悉照各省駐防之例,十年議準。青州駐防官兵,粟米全行折給,每米一斗折銀一錢,均于該年地糧銀內動支。”[8]
雍正、乾隆時期,清政府為了保持駐防旗兵“滿語騎射”的特色,禁止駐防旗兵學習漢學,旗人子弟亦不得在駐防當地參加科舉考試。
清初八旗官兵兵餉相當優厚,但是兵有定數、餉有定額,隨著駐防兵丁人數的不斷增加,清政府無法負擔繁衍越來越快的八旗人口,加上八旗兵久不征戰,生活逐漸腐化,生計問題成為了八旗官兵特有的問題。
雍正朝以前,青州駐防兵丁最初多為孤身一人,后來不少人回京城贍養父母,也有年老無子女而回京的,生計問題沒有表現出來,而到乾隆時期問題卻日益顯現。乾隆十五年(1750),青州駐防將軍羅善病故卻無錢辦喪事。嘉慶時期,青州駐防財政緊張,已無多余錢財負擔戰馬喂養。嘉慶、道光年間,農民起義風起云涌,青州駐防兵丁常被派往各處參與鎮壓,沉重的兵役使生計更加艱難。咸豐十一年(1861),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恩夔奏:“青州旗營糧餉,久未支領,官兵養贍無資。”[9]
為了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發放賞賜銀與旗人,“康熙帝曾從國庫拿出銀錢5415000余兩,但無濟于事,很快旗人將其揮霍得蕩然無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發庫銀6554000余兩,也同先前一樣,旗人很快將其揮霍一空。” [10]另外,采取了必要的體恤政策。雍正元年,發內庫銀80萬兩,90萬兩分給各旗,作為官兵婚喪嫁娶的費用,臨時性的生活補助,或令旗人以此為本,開展營運生息。雍正七年(1729年),以外省駐防賞銀生息所得息銀救濟兵丁。種種措施,雖耗巨資,卻只能解決旗人暫時的貧困,并不能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雍正五年(1727)開始,清政府發給青州將軍的年養廉銀為1500 兩。乾隆三十二年(1767),青州副都統的養廉銀每年700 兩,乾隆三十五年(1770)改為500兩,養廉銀也是逐步遞減。
清政府又采取增加兵額、試行井田、增設養育兵、清理開戶人、出旗為民等項措施,試圖解決旗人生計問題。雍正帝于二年(1724年)正月向八旗都統發布了設立養育兵的諭旨:“今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內,共選取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訓練藝業。所選人等、每月給予錢糧三兩。”[11]嘉慶七年(1802)青州駐防增設養育兵100名。嘉慶二十年(1815)“于駐防八旗閑散壯丁內,擇其材堪造就者二百四十名,作為余兵。與甲兵一體操練,每名每月支給銀一兩,以資養贍。” [12]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青州駐防閑散兵丁的生計問題。
清政府采取的各種臨時調節辦法,治標不治本,對八旗制度本身的弱點絲毫沒有觸及,無法扭轉駐防八旗走向崩潰解體的命運,也預示著依靠這種經濟、政治體制維系的滿城高墻將旗人隔絕于世的時代該結束了。[13]
同治二年(1863),恩夔奏:“青州旗營,餉米缺乏,請飭山東巡撫寬為籌撥一折。據稱該營官兵,因糧餉缺乏已將所有對象變賣糊口,現在無可折變。衣敝履穿形同乞丐。該處地近海濱,入冬以后,男婦赴鄉乞食,死者甚多。”[14]同治七年(1868),軍機大臣等恩夔奏:“兵米改發折色,不敷糊口,……青州駐防兵丁,久形苦累。”[15]青州駐防官兵的生活日益艱難。
道光以后,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入侵,農民起義不斷,國力日衰,財政窘迫,青州駐防的兵額有減無增,餉糧層層苛扣,生活更為艱難,有的全靠賒借和變賣家當度日。光緒十一年(1885)到宣統元年(1909),山東巡撫多次上奏:“青州滿營兵米不敷支放”[16]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不得不要求八旗駐防“另謀生計,各食其力”。
自辛亥革命(1911)至1925年,青州駐防八旗的馬步聯軍的編制雖未動,但糧餉出現了嚴重困難。1925年,青州駐防旗兵糧餉斷絕,由地方補給,各派軍閥爭權奪利,青州駐防營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919年,青州駐防騎兵團在地方各派勢力的爭權奪利中瓦解,八旗行政組織徹底解體,經歷199年風風雨雨的青州八旗駐防宣告幻滅。
三、青州八旗駐防民族文化融合
清廷對八旗駐防實行“旗民隔離”,避免旗人“沾染漢俗”,設立滿城,通過各種禁錮措施隔絕八旗駐防兵丁與周邊民人交往,阻礙了民族間的交往和文化發展,但民族間的悄然融合從未間斷,也無法阻擋。
在駐防滿城內部,存在不同的民族成分,有滿族、蒙古族、漢族等,其中的漢族,除了八旗漢軍,還有購買的奴仆,或者是發配為奴的罪犯或戰俘,或者是被抱養、雇傭的漢人,融入到駐防旗人中,從內部打破了旗民畛域的局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八旗的非旗人成員,以個人身份置于旗人家庭之內,有著更多與滿人接觸的機會,他們更容易接受滿族影響而滿族化,同時也把大量漢俗帶入到八旗之內,成為八旗滿族與其他民族交往的紐帶,促進了民族間文化的融合。
隨著青州駐防旗營的解體,旗民之間再無“滿城”隔離,也無各種禁錮措施的限制,可以自由來往,進行商業貿易,甚至雜居、通婚等,使滿漢文化相互滲透,開始走向全面融合。
駐防旗人與當地人之間存在必要的經濟來往。駐防旗人不可從事農工商等,生活物資需要依賴于當地人,與當地人的經濟往來是必然的,因此,貿易方面的交往也會對清廷的隔離政策造成沖擊。雍正十一年(1733)規定:“準許四鄉漢人進行經商貿易,并于城內四街閑處鋪面坊400余間,加原蓋匠役房32間,租與商人,年收入租銀700余兩,作為獎賞祭祀、寺廟香火開支及歲修費用”。[17]次年(1734)又“奏準由山東潘庫撥銀6000兩,在旗城開設典鋪、米局。”[18]
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允許八旗駐防“另謀生計,各食其力”。辛亥革命后,青州駐防軍隊俸餉經費改為地方自籌解決,總額大大縮減,因而生活更加困難,不得不發動兵民生產自救,開設工藝局,從事鐵工、木工、養蠶、紡布、藤編等手工業,于北城、車站成立了一個市場,并向外批發、零售,另設有專賣部一處。清末開始,部分旗人通過考學、經商、外出務工等方式離開駐防城,也有許多上層旗人開始移居青州城,有的退休官員到青州城里購置房產定居。駐防旗人與民人之間的經濟貿易,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交流。
通婚向來是民族融合最有效地渠道,但清廷禁止滿漢通婚,特別是嚴格禁止滿族婦女嫁與漢人,但旗人男子可以娶民人女為妻、為妾,這些嫁入旗內的漢族婦女成為駐防旗人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勢必受到旗人風俗習慣的影響,同時也會將漢族的風俗習慣和思想文化帶到旗人內部,這種民族文化的交融是點點滴滴、無聲無息的,而且持久深刻。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式宣布滿漢可以通婚,更是促進了滿漢民族大融合。
參考文獻:
[1][4](清)光緒.益都縣圖志[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2][5][11]佚名.世宗憲皇帝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孫菲菲.清代山東八旗駐防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2012.
[6](清)王慶云.石渠余紀[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7] 潘洪鋼.清代八旗住房族群的社會變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佚名.清會典事例[Z].北京:中華書局,1991.
[9][14][15]佚名.穆宗毅皇帝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0]梅朝榮.大改革家雍正[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12]佚名.仁宗睿皇帝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定宜莊.清代八旗駐防研究[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16]佚名.德宗景皇帝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清實錄[C].第五十六冊,1985,314頁.
[17][18]李鳳琪,唐玉民,李葵.青州旗城[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黃淵紅(1982-),女,土家族,湖南,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為漢語詞匯、語法、清代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