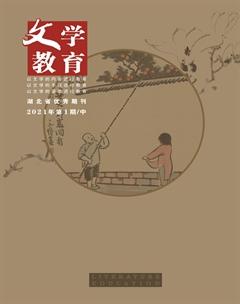淺析《陸犯焉識》中陸焉識的形象特征
潘玉梅
內(nèi)容摘要:《陸犯焉識》是嚴歌苓在201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與其以往的作品相比,《陸犯焉識》中,作者不僅把寫作角度更多的放在了男性的刻畫上,而且還是以20世紀中國這樣獨特的歷史年代來思考知識分子的命運。本文著重探討作品主人公陸焉識的形象特征。
關鍵詞:《陸犯焉識》 陸焉識 形象
嚴歌苓在以往小說中,對男性形象著墨不多,而2014年出版的《陸犯焉識》,就是以她祖父為原型的長篇小說。作者不僅把寫作角度更多的放在了男性的刻畫上,而且還是以20世紀中國這樣獨特的歷史年代來思考知識分子的命運。這部小說“是嚴歌苓第一次將深刻的目光轉(zhuǎn)向了自身家族史,特別是轉(zhuǎn)向了祖父這一代知識分子。”[1]
小說中的主人公陸焉識,大高個、一頭卷發(fā)。一塊歐米茄、一件英國毛呢大衣、一個藍寶石的領帶結,是他的標配。然而這樣的陸焉識到底有著怎樣的性格特征呢?
一.憐憫善良的陸焉識
陸焉識,一個大戶人家的長子,在其十四歲時父親去世,在看到恩娘,也就是嫁給父親才八個月的馮儀芳,因為要被退回到娘家哭得像個淚人似的。他最見不得女人流淚了,因此十四歲的他堅定地對恩娘說,不會把恩娘送回去的,他會賺錢來養(yǎng)活恩娘的。這就是陸焉識骨子里的善良,對他人有憐憫之心。憐憫一個孤苦女人,憐憫一個被命運擺弄了的女人。
陸焉識十八歲時,恩娘又帶來了她的侄女馮婉喻,陸焉識和婉喻的第一次見面看到的就是一個小恩娘,當他知道那個馮婉喻是恩娘要剝奪他愛情的自由,而強加給他的妻子時,焉識的內(nèi)心非常痛苦,那么和婉喻的交流自然只能是敷衍。當恩娘開始說自己為他、為這個家有多辛苦的時候,陸焉識感到不耐煩,因為恩娘總是會將自己的貢獻擴大,讓你覺得你已經(jīng)欠了她很多。因此焉識為了擺脫這個局面,說要出國留學。這是陸焉識將了恩娘一軍,但是陸焉識又憐憫女人,陸焉識對女人的憐憫是他的致命傷。當陸焉識一說完去美國留學,恩娘那落淚而變形的臉,讓他一陣悲憐:恩娘好可憐,已經(jīng)被父親擺布了,現(xiàn)在想做媒婆也只是想少受一點擺布。女人的可憐也讓他這樣的男子沒有出息。最后陸焉識做了讓步,同意和婉喻結婚,這也是基于對恩娘的同情。陸焉識雖然妥協(xié),但是又不甘心,不愿將一個男人僅有的一次愛情自由拱手讓出,所以不與婉喻同房,他認為可以犧牲自己,其實這種犧牲原本可以避免,但因為他的善良和他對女人的憐憫,讓他無法做出避免這種事情發(fā)生的舉動。這也體現(xiàn)出他的教養(yǎng),陸焉識是大戶人家的公子哥,受過高等教育,這樣的背景也不容他忤逆長輩。
在他成為陸犯之后,在大西北的荒漠上依然沒有流失自己的悲憫善良情懷,在大饑荒時代,不僅犯人吃不飽,就連看管的人,也是一個個餓得臉上浮腫。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時候,看到梁葫蘆——他的一個少年殺人犯獄友,被加工隊長“加工”掉半邊腦袋,他把自己每天的定量食品分一半給躺病床上的梁葫蘆,并且把自己藏下來的稀有的糖精片也搭進去了,親自喂給梁葫蘆。在被教管干部鄧指惱怒地拿著手槍逼問他自己的妻子到底去沒去過畢隊長那里的時候,陸焉識在嚇掉半條命的情況下做了偽證,保全了鄧指妻子的性命,陸焉識這樣做既是對女人的憐憫,也是內(nèi)心的善良所致。在貧瘠的大荒漠上,陸焉識沒有貧瘠掉內(nèi)心的善良,依然保持著善良和憐憫的情懷。
二.慷慨大度的陸焉識
陸焉識確實是個非常慷慨的人,但和其他人的慷慨有不同,他是那種真正的對錢不在乎,拿學費給近視的大衛(wèi)·韋買了一副昂貴的眼鏡,在國外留學期間,更是呼風喚雨的請客吃飯,幫助別人,給所有熟人買醉,不介意自己的吃虧,也不介意任何人向他索取。大衛(wèi)·韋就是每周都會來他住的地方,讓他請客吃飯,他反而還挺喜歡大衛(wèi)·韋的到來。陸焉識的慷慨不僅表現(xiàn)在對朋友們仗義疏財、大方接濟上,還表現(xiàn)在對恩娘和婉喻的善待。陸焉識在留學期間享受了五年的自由而放浪的生活,回國后見到了恩娘與婉喻,回想自己的生活,再想想恩娘和婉喻,又從心中憐憫起她們來。而這種憐憫,正是慷慨所驅(qū)使的,他同情弱者,見不得人家可憐。于是以一種同情并施舍的姿態(tài)與婉喻圓房,即使是施舍,也是因為陸焉識內(nèi)心的慷慨大度。
陸焉識的慷慨還表現(xiàn)在,他無法坐視別人的窘境。在回國后,大衛(wèi)·韋也回國了,卻是困窘不堪,連妻兒的溫飽也不能照顧。陸焉識在看到大衛(wèi)·韋如此落魄后,想到的就是要接濟他們,盡管那時的他家境不如從前,還是很慷慨的、真誠的去做這件事。所以那個晚上,他就親自去了大衛(wèi)·韋家,雖然撲了空,沒做成,可這份慷慨的心意已經(jīng)表露出來了。盡管后來的大衛(wèi)·韋恩將仇報,他也沒有去恨大衛(wèi)·韋,反而同情他。這就是慷慨大度的陸焉識。嚴歌苓在小說中描寫道“從他記事開始,他就為了不讓別人為難,常常做別人為難他的事,做別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別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隨和大度、‘與世無爭的評語,甚至大咧咧、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滿足的。”[2]也許這就是陸焉識的慷慨大度的原因了。
三.清高孤傲的陸焉識
當大衛(wèi)·韋被辭退回國后,窮困潦倒,找到陸焉識讓他借篇論文給他,好讓他在國內(nèi)謀份教授的職業(yè),好養(yǎng)家糊口,這時的陸焉識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很同情大衛(wèi)·韋的處境,但論文不能借,因為他認為論文造假是可恥的行為,而且他陸焉識就剩下書里學問這么一快福地了,怎么能就這么給糟蹋了呢?當大衛(wèi)·韋斥責他變了,不像以前那樣慷慨了,陸焉識只能再次誠懇道歉,他可以再給他買昂貴的眼鏡,買多少副都可以,但是論文真的不借。這正是他骨子里清高的體現(xiàn),他是陸焉識,是知識分子陸焉識,所以他做不出弄虛作假的事,也不愿做這種可恥的事,學問就是學問。也正因為這份清高孤傲給他日后帶來了禍患。
后來因為陸焉識的一篇文章提到日本語言的發(fā)展,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提到日本的語言,無疑撞到槍口上。這也是他的清高惹的禍,展示才學卻不考慮時局。因此陸焉識被罵成“漢奸”,而在背后罵他的人正是大衛(wèi)·韋。這時的陸焉識依然沒有與之對罵,而是心平氣和地解釋:語言就是語言,就算打世界大戰(zhàn),人類的語言還是妙趣橫生。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清高。然而這樣文縐縐的對答,讓對手更加找到了證據(jù)。其實,語言從來就是一些人奴化另一些人的手段。就這樣,陸焉識不管是在學校里還是會館里,已經(jīng)不招人待見了。當一個好心人告訴他要有自己的群眾,要善于投靠對手的對立面,還要拉對手的對手做朋友,并給他留下了一家雜志社的地址電話和幾個人名。然而陸焉識不是立刻去找到自己的“朋友”,而是研究起這家雜志社來,認為雜志社有些罵手罵的比較風度翩翩,不罵人時,小說、詩、論文寫得也挺不錯。因此,他并沒有立即去找對手的對手。
1945年底陸焉識從重慶一無所有的回到上海,陸家因為戰(zhàn)爭已經(jīng)開始敗落了。陸焉識不得不再謀份教職的工作,當聽到要考核時,陸焉識就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因為考核的是他在重慶時坐過牢的政治污點,雖然說考核是為了證明他的忠誠,但卻抵消了他自認為應該堅持的東西,那就是作為一個文人知識分子的學術自由。因此強烈的自尊心迫使他放棄了這個考核,轉(zhuǎn)而去找凌博士幫忙。然而作為一個清高而孤傲的陸焉識,其文人氣息很濃,就連送禮都變得局促不安。雖然說這場戰(zhàn)爭讓他有了一些改變,不是那個“為任何事也不會求人”的陸焉識了。但文人骨子里的清高和孤傲是不會因為戰(zhàn)爭而被磨滅,盡管他很有才學,善良而且慷慨,可是在鉆營的生活中,在亂世中,卻始終只是個沒用場的人。追溯起來,“在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缺乏自覺獨立的群體意識。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政統(tǒng)要求學統(tǒng)為其服務,從而使學統(tǒng)依附于政統(tǒng)或是最根本點。”[3]也正因為陸焉識的清高孤傲,才讓他這樣的文人知識分子沒用場。
通觀陸焉識的一生,我們不難看出,陸焉識的性格特征微妙的體現(xiàn)在他的行為舉止中。他就是一個清高、慷慨、瀟灑但又不失善良和憐憫之心的知識分子。他的遭遇讓我們明白了個人在時代里的渺小與無奈,也深刻體會到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困頓。而這,恰恰也是作品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丁揚.嚴歌苓:以“家族史”寫作折射知識分子命運[J].中華讀書報,2011,9:21.
[2]嚴歌苓.陸犯焉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43.267.
[3]湯一介.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的前途[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43.
(作者單位:巢湖學院文學傳媒與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