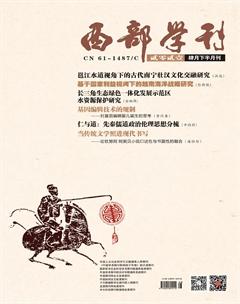從傳統到現代:新型互助養老的主要形式
辛穎 何曄
摘要:中國長久以來形成的傳統養老模式主要包括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其中,家庭養老成為傳統養老模式的主要支撐,但目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源模式提供的贍養動力不足。養老模式應該在發揮多個主體作用的基礎上趨于多元化,基于不同受助者的需求加以區分,力求最大化滿足老人養老需求。因此,互助資源的挖掘與利用是推動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方向。新型互助養老模式包括共享互助、交換互助、空間互助、鏈式互助等形式。每一種形式都有優缺點和適用范圍,通過鏈接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專業人員、老人子女共同的力量,打破傳統養老模式主體間配合少、缺乏合作意識的現狀,充分調動各個主體參與老年群體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中國的養老模式與養老服務真正在質量上有所提升。
關鍵詞:互助資源;互助養老;養老服務
中圖分類號:C91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8-0060-03
引言
當今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人口結構的迅速老齡化,傳統的“孝道”隨著現代化進程的迅速推進受到猛烈沖擊。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和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統計資料顯示:至2019年末,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5388萬人,占人口總數18.1%;65歲以上人口總數是1760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高達12.6%。相比于2018年末60歲以上的24949萬老年人口,65歲以上的16658萬老年人口,增比分別約為1.76%和5.67%。“銀發浪潮”正迅速席卷中國,費孝通歸納的中國的傳統的供養模式——“反饋模式”養老,即父母撫育子女,子女對父母承擔贍養義務的傳統模式[1]顯然已不能滿足現代化背景下老齡人口迅速擴張的需要。
由此不難得出,未來我國老齡人口將會在長久的時間內持續、高速擴張,老年人口的急速擴充必定會使養老服務需求迅速累積。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以及城鎮化進程帶來人口流速加快,進而導致傳統養老觀念的轉變及家庭結構的松散化、小型化,“空巢老人”現象日益增多。“十三五”和“十二五”綱要中對建設養老服務體系的重點轉變,反映出了我國養老政策和養老模式建構的新轉向以及新的結構導向,需要探索更符合老年群體的高質量養老需求的新型養老模式。在傳統社會當中,各種各樣的互助組織在基層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互助”這一古老的社會支持方式在當下養老服務當中仍有利用價值,充分挖掘各種互助資源、創新互助形式是完善養老服務供給模式的重要面向。
一、傳統養老模式及問題分析
從養老資源的提供者或支持力來源的角度看,人類只存在家庭養老、社會養老、自我養老三種基本的養老方式和模式[2]。中國長久發展形成的宗法制度,使家庭養老成為傳統養老模式的主要支撐,但目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源模式所提供的贍養動力不足。
(一)家庭養老
家庭養老是基于血緣、宗族理念為紐帶復合發展而成的養老模式。子女對父母的照顧通常是先賦角色和情感角色的統一,養老機構服務人員往往是功利角色和理性角色的統一[3]。然而傳統“孝道”觀念對子女的控制機制在今天因地域間隔受到了削弱。農村子女職業的非農化使得子女經濟貢獻增多而家庭地位提升而這導致老年人掌握的權威性資源貶值[4]。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隨著人口流動、代際思維觀念差異等正遭受到沖擊。如果不輔以相關制度對子女養老責任、意識加以強化和約束,家庭養老很難像以往那樣產生強有力的支撐作用。
(二)社區養老
相比于機構養老,社區養老更具地緣及人際優勢,但社區養老更多依賴社區規劃、社區服務人員對待養老的態度,具有間斷性、不穩定性。目前我國老齡化存在城鄉倒置問題[5],農村老齡人口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城鎮區域,但農村子女的流動性強于城鎮子女。在城鄉二元制結構背景下,社區養老模式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大中型城市地區較為普遍,而社區養老模式很難在農村地區扎根。
(三)機構養老
機構養老主要分為公辦、民營兩種性質。公辦機構設施齊全、收費低,但往往優先服務于特殊困難群體,以致“一床難求”。民辦養老機構定位不清、功能混亂、缺乏層次性、專業性、針對性。純粹的機構照料如果不和面廣量大的居家老人聯系,就難以發揮機構養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6]。國家統計局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指出2019年年末提供住宿養老機構3.4萬個,養老服務床位761.4萬張,而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5388萬人。老年人口與養老機構所提供的床位之間有巨大的差額缺口,僅依靠養老機構難以保障養老需求。
二、新型互助養老的主要形式
傳統的家庭結構以及緊密程度受到現代化發展的影響,傳統的養老模式已不能提供高質量的養老服務,因為高質量養老服務不僅涉及保障老年群體日常吃穿需求,還涉及精神慰藉以及身心愉悅的需要。為了發展高質量助老服務模式,養老模式應該在發揮多個主體作用的基礎上趨于多元化,基于不同受助者的需求加以區分,最大化滿足老人養老需求。基于此,亟待對現存養老模式進行改革與創新,在“保基本、多樣化、多元化”理念的指導下,努力突破當前養老模式驅動力不足的困局。
(一)共享互助,釋放子女養老壓力
共享互助依托“共享經濟”發展理念被提出,意在將老人、子女視為一種可以被共享的資源,將各個家庭中的老人、子女進行整合,協調老人與子女的關系,減輕子女因照顧老人而使就業時間和方式受到限制的壓力。共享互助模式可以作為打破老年群體大多僅依靠血親養老局限的重要抓手和依托性力量,并在釋放子女養老壓力上將發揮明顯作用。由一部分責任感強,具有奉獻精神、吃苦耐勞品質的老年人子女留守家中照顧老人,另一部分子女從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中“解放”,并將從事工作的部分收入用于補貼養老費用。共享互助模式解放了部分勞動力,使得一些子女可以從事勞動,改變因照顧老人無法從事全日制工作而只能從事閑散化、工資收入水平較低的工作現狀。共享互助將各個面臨同樣養老問題的家庭聯系起來,通過老人子女間的合作分工,緩解子女尤其是獨生子女壓力。因為是子女進行養老服務,更能從老人需求角度出發,除進行日常基本生活的照料外,更能考量到老人的情感需求。
(二)交換互助,帶動子女走向專業化
吸引剩余勞動力,尤其是因為照顧老人無法外出務工導致生活陷入困難的青壯年勞動力,成為專職化養老群體,為解決子女因養老而生活陷入困境提供新想法、新路徑。政府通過設置養老工作崗位來轉變子女身份,將照顧老人作為專門化的崗位,解決了因照顧老人沒有專門職業的子女就業問題,同時通過政策補貼解決該類家庭收入單一且不足的狀況,緩解家庭壓力。對于社區來說,也緩解了人才缺乏困境。政府可以通過專門的職業技能培訓來提升子女照顧老人的專業度,提升子女的職業意識、專業素養及服務意識,鼓勵該群體考取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證。通過提供職業技術培訓以及政策補貼的方式,確保技能培訓經費穩定投入。在實際操作中轉換待業在家、照顧老人的子女身份,建立社區工作和子女養老之間的聯動機制,解決就業問題以及養老問題。
(三)空間互助,提高現有資源利用率
空間互助分為兩種互助養老模式,分別基于“三社聯動”①模式及“共享經濟”理念而提出。借鑒“三社聯動”模式發揮社區人緣及地緣優勢,鏈接各個主體,提升各個主體在社區養老活動中的參與度。
布勞認為個體之間的交往得益于交換雙方都從相互交往中獲取到了所需,互相提供報酬將維持相互吸引與繼續交往[7]。空間互助屬于直接協商式交換,是一種直接、雙向的交換,帶有即時回報的特征。在社會交換論指導下,提高現有閑置資源的利用率,可以依托空間讓渡換取高質量的養老服務,以保障社區老年群體的養老水平。
1.閑置社區空間舉辦養老活動
僅依靠社區的力量難以負荷多樣化的特定老年群體的養老需要,鏈接社會組織的力量為社區中的老年群體提供多彩的養老服務是必要的。譬如,社區提供空間供社會組織定期舉辦養老活動和養老項目來滿足社區老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非活動期間將空間的使用權交給社會組織運營其他項目,彌合老年活動的運營成本缺口,調動、激發社會組織積極性。社會組織對于鏈接的社區免收或少收運營費,以減輕鏈接社區的資金壓力。政府在社區、社會組織聯動的基礎上給予政策性幫扶和傾斜,提高社區鏈接社會組織養老扶持力度。社區、社會組織之間形成互相監督的考評機制,定期反饋活動、舉辦成效,通過問卷、當面訪談、調查走訪等形式了解老年群體對活動舉辦的滿意度及工作成效。社區鏈接社會組織的模式打破傳統社區養老局限,在政府政策導向和資金扶持下,綜合社區、社會組織的力量,提升社區養老專業度程度,可以有效緩解社區養老活動內容、項目單一等問題。社區也可以在此基礎上考量和醫療及心理保健機構洽談合作的事項,保障社區老年人擁有健康的體魄及心理,避免老年人因心理空虛、情感孤獨而產生厭世感,在豐富老年人娛樂生活提供精神慰藉的基礎上,保障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生活。
2.剩余住宅空間換取養老服務
提供住宅剩余空間是指將空巢獨居老人閑置、冗余住房空間的使用權暫時性讓渡給租客,換取租戶對老人日常生活的照料的模式。老人免除租戶租金,而租戶對老人形成一種暫時性的贍養關系。將老人住房中的閑置房間拿出來易換養老服務,不會對老人的私人利益造成實質性傷害。同時,住房使用權的暫時讓渡可以幫助那些收入不穩定、收入難以滿足自己日常需要的青壯年群體減輕生活壓力。租客為老人提供養老服務作為抵扣房租的途徑,老人獲得養老服務,老人與租客間各取所需,建立良性互動關系。基于信息化的基礎,結合線上平臺和社區力量,建立健全租客申請以及誠信評價體系,以及受幫扶老人的電子及紙質檔案,檔案應包含受益老年人的個人信息及健康情況,防止老人和租客之間的產生沖突,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和租客權益。社區定期走訪調查,確定老人與租客間的匹配程度,明確申請人的責任和義務。當地政府也要加強管控,建立健全監督機制,明確處罰措施,分級、分層提供管理服務,保障老人安全和權益,形成老人、租戶之間的良性互動、互助關系。
(四)鏈式互助,輻射子女成為志愿者
演發“n+N”輻射模式,即社區志愿者+老年人后代協作模式,n指社區志愿者,N為老年人后代。該模式重點在于增強社區志愿者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擴大愿意參與幫扶老年人的老年人子女基數。發揮志愿者服務老人的示范性作用,將老年人子女納入志愿者服務團隊中,踐行“自我養老、互助養老”理念。大部分老人由于受傳統觀念和宗族觀念的影響,不愿意去敬老院居住而選擇居住在社區,但子女工作忙碌無暇整日照顧老人。社區派志愿者在子女忙碌時照顧老人,一些子女受到影響選擇成為志愿者,呈現出“愛的傳遞”現象。子女可以轉變為志愿者身份,被救助者轉變為救助者,通過輻射性互助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決子女工作繁忙無法一直陪伴在老人身邊的現狀。對于社區來說,也有效緩解了社區工作人員不足、資金緊張的局面。通過“輻射性影響”,形成鏈式互助模式,帶動更多子女在抽空照顧自己父母的同時,轉變身份,提升社區養老參與度,同時幫助解決其他家庭養老問題,進一步構建“和諧互助、互助自助”的鏈形輻射式結構。志愿者成員間在服務老人的過程中也更易鏈接出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通過互動衍生出信任和配合的默契程度,在滿足老人情感需要的同時,實現了自己的社會價值,對于社會凝聚力的增強也大有裨益。
結語
目前我國社會急劇變革,轉型升級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探索新型養老模式符合社會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人口流動加快導致的“空巢老人”占比提升的需要;受到“共商共享共建”理念以及“共享經濟”模式的啟發,在政府政策支持,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工作即“三社聯動”的原有基礎模式上,也進一步加強了家庭與政府組織、“三社”之間的聯動關系,有利于增強各個主體間的合作意識,在減輕政府壓力的基礎上,激發了各個主體的活力和積極性。
“互助”是有積極價值的優秀傳統資源,在當今社會治理和養老服務供給方面都有重要意義。共享互助、交換互助、空間互助、鏈式互助四種新型養老模式的提出是對現有傳統養老模式的有益的增量補充,通過鏈接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專業人員、老人子女共同的力量,打破傳統養老模式主體間配合少、缺乏合作意識的現狀,充分調動各個主體參與老年群體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也要求社會各個主體之間需加強信息溝通和交流,在踐行“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基礎上,滿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的需要,使中國的養老模式與養老服務真正形成“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及老有所醫”的全面化、多層次、多樣化形式。但對于各個運營主體如何根據所處環境探尋出最適合的養老模式以及具體的操作流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索。此外,這四種新型養老模式更多聚焦于城鎮養老,對其模式的補充完善與科學建構仍需思考與再設計。
注 釋:
①三社聯動,目前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并無一致看法。一種說法是,三社聯動指的是在政府主導下,在社區治理中,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
參考文獻:
[1]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3).
[2]穆光宗.中國傳統養老方式的變革和展望[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5).
[3]成偉,張燦賢,牛喜霞.中國傳統養老模式面臨的挑戰及多元化養老方式探索,2012(3).
[4]賀聰志,葉敬忠.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響研究[J].農業經紀問題,2010(3).
[5]李文管,鄧旭杰.我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養老困境及解決對策[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6(1).
[6]童星.發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以應對老齡化[J].探索與爭鳴,2015(8).
[7]彼得·M·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M].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作者簡介:辛穎(1997—),女,漢族,安徽淮北人,單位為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
何曄(1981—),女,漢族,江蘇大豐人,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與社會治理。
(責任編輯:易衡)
基金項目:本文系安徽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明清徽州鄉村治理的運行樣態與現代轉換研究”(編號:SK2019A028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