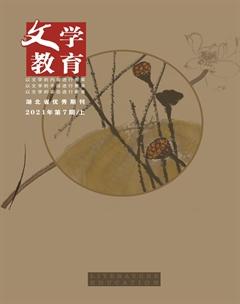論生命哲學視域下嵇康與尼采的審美內在異同
胡文慧
內容摘要:嵇康與尼采,一位是魏晉時期竹林玄學的翹楚,一位是西方非理性主義的先啟。兩人分別是中西兩種文化背景下特定文學歷史時期的代表,卻在藝術才學上存在著有趣的相似性,且在個體生命意識與生命存在的終極思考上也存在著相似性。嵇康與尼采均認識到了人生悲劇,但又以自身實踐人生價值,主張在人生悲劇中超越自身,探尋個體精神的無限和永恒,在審美中超越現實尋找精神的彼岸。
關鍵詞:生命意識 審美意識 酒神精神 任自然
嵇康和尼采雖處于不同的時空維度,但在時代環境、思想淵源、人物性格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相似性,同時在人生哲學問題的探求上也存在著明顯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以往的文章多集中在尼采思想與魏晉風度的比較研究上,對于尼采與嵇康的比較研究多集中在哲學思想、音樂理論等整體比較上,或是以“酒”為主題的共性研究。本文意從生命哲學視角切入,試探討嵇康與尼采在個體生命意識、個體超越意識方面的共性追求以及在餞行人生哲學上的審美方式差異。
一.個體生命意識思考
《顏氏家訓·養生篇》評曰:“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1]嵇康自謂“內負宿心”,從《答難養生論》可以看出他對生命的重視,“無執無為,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2]在現實中獨善其身,修養心性。但嵇康剛直的性格使他不能一味的做個隱士,最終作廣陵絕唱,從容赴死。嵇康認識到,人終將會死,與其恐懼死亡何時會到來,不如坦然面對生命的最后期限,活出生的意義和死的價值。嵇康清醒地感受到外界可以影響人的生存與否,但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自由地決定接受死亡的方式和價值。他感于生命的可貴,在有限的生命里跳脫政治的泥潭,追求生命才性的真實和自由,以清逸、輕靈的審美胸襟,任心靈暢游在自然山水之間。同時嵇康心懷仁心義膽,面對強權政治的死亡威脅也毫不退讓,嵇康所看待的死亡不僅是指舍生取義,更是一種為“道”而死,體現了孟子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氣,也實現了孟子所說的圣賢之死。對于嵇康而言,生的可貴與死的價值并不沖突,選擇遵循本性而赴死是更深層次的精神超越,為道而死又有何懼!
《悲劇的誕生》是尼采的早期作品,理論淵源主要來自于叔本華悲觀理論的批判。尼采在書中借用希臘藝術中以阿波羅為代表的日神精神和以狄俄尼索斯為代表的酒神精神為其悲劇的出發點,在他看來,希臘人早早地認識到了生命的短暫和空虛,但他們并沒有因此而悲觀,并沒有否認生命存在的意義,而是借用悲劇在藝術審美中體驗快感,在痛苦中感知最高的歡樂。“酒神精神”的提出,就是讓人們肯定生命存在的意義,并在人生痛苦之中持有積極的態度并踐行。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有這樣一段話: “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異樣最艱難的問題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我稱之為酒神精神,我把這看做通往悲劇詩人心理的橋梁”。[3]人生中的苦難無法避免,但決定以何種態度去面對才是人們能夠緊緊握在手中的。做自己現實生活中的超人,意志力的強大足以在痛苦與犧牲中碰撞出燦爛的火花,人們在酒神精神的世界中感知到自身的偉大。尼采認為,強大的生命意志正是在這種短暫痛苦的結束中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使得人們能夠在悲劇人生中尋求自由和完滿。陳鼓應言:“希臘人深切地了解到人被投入世界后,生命充滿著荊棘,短暫而可悲,最后終不免于一死。但他們卻能挺起心胸,怡然忍受。復于飽嘗人生痛苦之中,積健為雄,且持雄奇悲壯的氣概,馳騁人世。”[4]酒神精神的提出是讓人們直面自己的人生悲劇,如希臘人一樣在痛苦中感知精神的至高快樂,體念到超脫自身的蓬勃的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向上擴張的力量早已超脫了俗世的羈絆,升華至更為自由的天地。
尼采的人生哲學與悲劇緊密聯系,同時強調高度的權力意志。他相信個體的精神正是在人生的痛苦中迸發出敢于與世界較量的強大能量,古希臘人早就了解存在的可怕性質,但并沒有因此而悲觀,而是用戲劇來娛樂自己,于是一種樂觀的人生態度和積極的精神力量悄然產生。嵇康深感到了時代的悲劇,人生的痛苦,但對于“生死”的思考,折射出的是個體生命“在”的本體價值意義的光輝。二者都認識到了人生的有限和悲劇結局,但積極肯定了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他們不拘泥于現實世界的物質得失,更為關注自身精神世界的充盈,清醒的認識到生命的有限和超越生命的無限永恒,肯定生,不懼死,他們用自己的方法實現了對于有限與無限的統一,尋找到超脫物外的精神永恒。
二.追求精神境界異同
嵇康和尼采在時代環境、思想淵源和人物性格等方面存在著相似性。嵇康所處的年代政權混亂,經學自身早已走向了思想僵化,剛毅率真的嵇康在這種現實與精神的雙重壓抑中放棄仕途,摒棄了經學轉向老莊學說思想。尼采所處的年代德國戰敗,社會整體彌漫著悲觀的氛圍,基督教義讓人民變成了順民庸眾,孤傲的尼采完全的批判基督教條,他深深感知到了時代的痛苦,試圖掀起一場精神革命。也許正是相似的現實背景、相似的人物性格使得嵇康與尼采更加關注于自身與時代的精神痛苦,開始思考人的生存問題。尼采認為人就是在悲劇中度過,嵇康在亂世中也看到了個體難以逃脫的悲劇命運。他們都在用自己方式積極尋找解決人的生存意義這一問題的答案,最后都指向將個體歸于宇宙,在有限中尋找無限的歸宿。尼采的宇宙認識和嵇康的任自然,雖說法上不同,但他們所探索的整體是一致的。
嵇康反思和繼承了前人的宇宙觀,但區別于前人對宇宙的認識,破除了迷信色彩,而是發展成較客觀的自然觀,認為自然界的一切變化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加以解釋。對于個人與宇宙自然的關系,嵇康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是對老莊、阮籍關于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觀點的繼承和發展。嵇康在《釋私論》中說道:“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明任心,故是非無措也。”[5]“越名任心”即虛靜心透過悟道的提升作用,能超越世俗名分的貴賤利害對心的挾制,使人的心靈沖破一切外在虛矯的矩度所帶來的拘束和不自然,而復歸于道心的自然狀態。[1]嵇康認為要達到“任自然”的境界就要擺脫物欲的控制,收斂自己的外在情感,回歸自己的內心,舍棄外在規范或身份的壓力,看清自己的真實情感,發揮自身主體的內在活力,實現心靈的完全自由,尋求更為純粹的、真實的人性,體念自然,將個體生命與自然相互滲透,達到共融共存。
尼采借用宇宙認識,跳脫出人自身的限制,以更為宏大的視角來感知無限,人在此時化為渺小的一粒,生存的永恒歸于宏大中去。作為完全的非理性主義者,尼采同樣拋開了倫理、社會規則、秩序等現實的理性枷鎖,主張直觀地看待痛苦和痛苦背后的人生樂趣。他揭開了人性的丑陋,看到了個體本性中的自私,接受了人的陰暗面,只有在這種過程中才能剖析出人的真實和真誠,在與自身現實痛苦的斗爭過程中獲得幸福。“我們在短促的瞬間真的成為原始生靈本身,感覺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樂。”[3]尼采對于個人生存的思考也是更為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充盈。正視生命的痛苦和衰亡,就如在酒頌之時的舞蹈和歡歌,酒神藝術讓人們相信并體驗到了生命存在的永恒樂趣。正是借用了藝術的力量,人們才能夠以看戲者的身份實現對生命和世界的體驗。在“醉”的世界中,個體的隔閡被打破,人們突破了理性的桎梏,放縱自己去感知那集體無意識的狂歡,人與萬物融為一體,回歸到生命本源。“此時,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人不但感覺到自己與鄰人團結了,和解了,融合了,而且是萬眾心”。[3]
總之,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嵇康“任自然”的哲學思想是殊途同歸的,都是超越個體人生的有限性,尋求精神的永恒。他們都采用將人生藝術化的方式實現,用審美的眼光看待自身及周邊萬物,最終超脫自身,到達精神的彼岸。嵇康對于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老莊哲學,但他強調人作為個體,通過內在修煉,把自己置身于宇宙的某一點,自覺地與宇宙對話,走向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最終歸于自然心志到達玄妙境界。尼采論悲劇通過“縱酒”和音樂的途徑實現身與物化,歸于宇宙無限的統一。這更像是他走出自我,從局外人的角度把現實生活看作一種藝術形式。
三.個體審美維度差異
嵇康與尼采都有對個體生命的探索,都有對精神和心靈的關懷,他們的思想是非理性的且具有明顯的超越性。尼采主張藝術的形而上學,認為對生活的審美態度就是拋開物質欲望的束縛,追隨人內心最深處的本能,這是一種非功利的、非理性的向上的生活態度。嵇康承襲老莊玄學的主張,“越名任心”,為追求自然就要排除感性層和社會外界的干擾,“寶性全真”,這樣才能超越自身,到達無限的彼岸。然而,他們雖然都主張一種形而上的審美理解和實踐,但方式卻不盡相同。
羅光總主教在其《生命哲學》一書中有段話說道:“心靈的生命在發展的歷程中,常一面表達自己的美,一面接受其他物體的美。接受美為欣賞美,欣賞美為美和美相應。生命和生命相融洽,表達美為心靈生命的發揚”。[1]嵇康善寫四言詩,與五言的格律嚴肅來說,四言詩更能體現出嵇康所表達的卓熒高潔的精神氣質和高潔志向。例如《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之十四:“息徙蘭圃,秣馬華山。流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簽。鄧人逝矣,誰可盡言?”[5]徒步蘭圃,放馬華山,在原野放逐,在江畔聆聽,大自然的美景讓自己的心靈也變得開闊了起來。嵇康在夕陽美景下彈琴垂釣,早已忘記了時間的流失,心靈早已游覽在玄妙的空間里,悠然自得。嵇康在俯仰之間體驗到了心靈與自然的交融,任由心靈在自然中馳騁,體驗片刻間的人生至樂。這時嵇康已經忘記了現實中個體的自我,而是升華到一種無我的超自然境界,體驗到了寧靜和純粹,這必然是快樂的享受的。嵇康這種審美方式是一種由物及我和由我及物的雙向的動態過程,至樂的體驗是美的物勾起了個體心靈的美好感受,個體再將這種審美體驗向自然的太玄境界無限靠近,這一過程中物與個體的是平等的,人在天地中真正地實現了萬物一體。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強調說明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統一的,是兩個維度上的意義,而不是由外及里的關系。在日神精神中,造型可以看作是一種夢的合規范化,而尼采的酒神精神則打破了外在的和諧,呈現出混沌無序的狀態。尼采悲劇理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叔本華思想理論的影響,他理論最開始就是在叔本華悲觀主義的思想上建構起來的,但后期又否定了叔本華的思想理論。尼采生活在基督教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時代,教條思想讓人們變成了愚鈍的附庸物,而尼采試圖改變人們被壓抑精神的現狀,在尼采的思想中人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尼采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它讓人們將痛苦作為生命的養料,人們在“醉酒”中體驗生命是在痛苦和犧牲之中獲得快感和幸福。他反思了叔本華將世界看作意志和觀念兩部分,認為人的意志本身就是十分強大且豐富的,同時深深根植在人的內心深處,本能的具有不斷向外向上擴大的欲望。就如希臘人在“醉酒”中狂歡、迷狂,世界在這時仿佛也無法撼動人們的存在和生命。尼采認為醉是一切審美活動的生理前提,它的本質是“力的過剩”,是“力的提高”。[3]從此處看,對比嵇康的審美人生方式,尼采的顯現的更為強力和張狂。他將自己置身在物外,外在世界本是無情的,是人們的強大精神賦予了外物色彩。尼采的審美方式更像是單向的我及物的這樣一種過程,只不過在這一過程中,個體精神的抒發有著不同的路徑,一個是日神精神的美感是個體對外界的體驗又投射到或說創作出新的外物,而酒神精神的悲劇性愉悅則是人在與痛苦和災難作斗爭中所表現出的強大生命力和勝利感。
綜上所述,嵇康和尼采雖然處于不同的時空維度,但是他們對個體生命哲學的思考存在著相似之處。嵇康與尼采均意識到了生命的悲劇,但他們以自己對生命價值的實踐,主張在痛苦中超越自我,探尋個體精神的無限和永恒,在審美中超越現實尋找精神的彼岸。只不過他們審美方式存在著不同。一位是將自身放歸于自然,實現心靈與自然的契合,心靈體驗得以超脫,超越現實體驗;一位是將現實生存看做審美對象,在生命的痛苦和犧牲中獲得瞬間的強大精神力量,這種歡愉狂傲的力量在瞬間超脫了現實。但不可否認的是,嵇康與尼采的生命哲學都是在混亂時代中的積極的反抗和探索,在精神的荒原上開辟了一片廣闊的希望之地。
注 釋
[1]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88,83,84.
[2]夏明釗.嵇康集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65.
[3]尼采.悲劇的誕生[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4,326,71,312,6.
[4]陳鼓應.悲劇哲學家尼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
[5]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M].合肥:黃山書社,1986,231,12.
參考文獻
[1]童強.嵇康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胡泓.論尼采《悲劇的誕生》中的“生命形而上學”[D].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9.
[4]魏斌宏.復歸藝術 叩問生命——尼采《悲劇的誕生》美學內核探析[J].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09,29(03):85-88.
[5]劉偉安.論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學命題中的生命意蘊[J].中原文化研究,2016,4(06):38-43.
[6]張向雅.尼采和嵇康思想之比較[J].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06(02):21-23.
[7]白忠睿.淺析“酒神精神”與“魏晉風度”的共鳴[J].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16(01):41-43.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