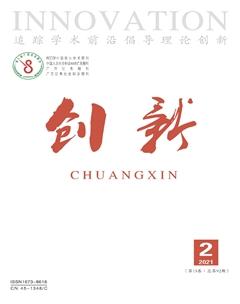中國民族聲樂藝術之審美
[摘 要] 中國民族聲樂藝術之韻味,是中國人在演唱藝術中所追求的深遠意味,是民族聲樂藝術魅力之所在,更是中華民族整體精神風貌的體現,其美學標準建立在中國戲曲、曲藝、地方民歌等傳統和民間的音樂藝術審美追求基礎之上。中國民族聲樂中氣息技巧、吐字行腔和抒情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審美特點——韻味,可從氣韻、聲韻和情韻三方面進行解讀,其蘊含的聲學、美學、哲學知識豐富,對當今流行音樂的發展仍有深遠影響。
[關鍵詞] 民族聲樂藝術;審美;韻味
[中圖分類號] J60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616(2021)02-0092-09
我國的民族聲樂藝術,“從廣義上來講,主要包括傳統的戲曲演唱、曲藝說唱和民族民間歌曲的演唱三大類民族演唱藝術,也包括新民歌、新歌劇的演唱和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演唱等”[1]。回顧中國聲樂藝術發展的數千年歷史,從遠古時期先民唱的“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的彈歌,到梨園、戲臺、劇場的演唱,中國聲樂藝術經過了歷朝歷代幾千年的發展、演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國家,具有民族特色的聲樂藝術審美特色——韻味。這些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味”,是民族聲樂藝術的魅力之核心,更是中華民族整體精神風貌的體現。
一、韻味在聲樂藝術中的美學解釋
韻味作為中國傳統的美學概念,最初是廣泛運用在詩詞、山水畫等文藝創作中,指的是藝術作品必須達到某種審美風貌和意境[2]257,是美學的中心。后來“韻味”這個詞也被大量運用于由文人參與的中國戲曲、曲藝的創作中,意指曲文既講究文辭、格律,又講究音韻和意境。而在傳統的戲曲表演藝術中,“味”的解釋是“劇種旋律、戲曲化的發聲(行當音色、表現音色)、吐字(噴口力度、字音反切)、樂匯音型語音化(上、下滑音)、音符群(大、小顫音,上、下顫音,裝飾音)以及喉阻音(虛阻音與實阻音)、立音等多種多樣的用嗓技巧”[3]90-91。如果用記譜的方法將美妙動聽的戲曲唱腔中的聲音滑動進行記錄,再機械地照譜宣唱,唱出來必然是缺乏生氣、呆板沒味兒的。幾百年來,民族聲腔藝術口傳心授、代代繁衍的特點,使得這種韻味蘊藏在旋律的語音化中,蘊藏在用嗓、行腔、發聲吐字的藝術技巧中。在藝術實踐的過程中和歷代文藝家們的總結提煉下,積累并形成了一整套民族傳統聲樂有關咬字行腔的美學原則和方法技巧,韻味從中得以窺見一斑。從各種戲曲、曲藝、民歌唱法的用腔來看,各種調整字音聲韻、帶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潤腔,以及為表現人物性格特色而進行的力度和表情處理,都對詞曲和諧暢達、曲情表現的完美統一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在民族聲樂藝術中,韻味是一種從內外部技巧到情感體驗創造都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審美的要求;在吐字、行腔、用聲和抒情方面,都表現出了約定俗成的美學原則的藝術效果。這是評判聲樂藝術作品是否具有審美價值的重要標準,更是中國民族聲樂歌唱家、聲樂教育家畢生追求的美學理想。
二、中國民族聲樂藝術韻味的解讀
(一)氣韻
在中華民族傳統審美經驗中,“氣韻”是中國古代藝術美學領域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也是歷代藝術家和批評家評價藝術品的重要話語。“氣韻”原不是一個詞語,最早“氣”是在古代生命哲學中為中國古代哲人所重視。古代先哲認為生命現象產生于氣,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氣韻”作為一個詞出現在藝術美學理論的范疇,最早是在繪畫領域,魏晉南北朝的謝赫在《古畫品錄》論“六法”中提出,“氣韻生動”居于“六法”的首位[4]7。其中,“氣韻”指的是繪畫表現出的人物的人性氣質、精神風度,是對顧愷之的“傳神論”觀點的發展和升華,“氣韻生動,乃顧愷之的所謂傳神的更明確的敘述,凡當時(指魏晉時期)人倫鑒識中的所謂精神、風神、神氣、神情、風情,都是傳神這一觀念的源泉、根據,也是形成‘氣韻生動一語的源泉、根據”[5]。五代畫家荊浩繼其后提出,“山水畫的‘六要(氣、韻、思、景、筆、墨),其核心是強調要在‘形似的基礎上表達出自然對象的生命”,“認為外在的形似并不等于真實,真實就是要表達出內在的氣質韻味”[2]279,“氣韻”被認為是藝術作品的靈魂,此后也成為整個中國畫的美學特色,被作為中國繪畫藝術所追求的最高標準。而在書法藝術中,同樣也非常重視藝術作品的神采風韻。唐代書法家張懷瓘云:“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6]宋代書法家蔡襄在《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十四論書道:“學書之要,惟取精神為佳。若摹象體勢,隨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之所為耳。”[7]從戰國時期《列子·湯問》中鐘子期對伯牙琴聲的評價“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8]到明代朱權在《善歌之士》中對歌者演唱的評價“一聲唱到融神處,毛骨蕭然六月寒”[9]可以得知,不管是在繪畫和書法藝術領域,還是在音樂藝術領域,氣質和神韻都是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品評音樂作品的重要標準。只有抓住表現對象的氣質神韻的音樂作品,才能使作者和聽者在情感上產生共鳴。與西方的寫實主義不同,中國人更注重把握藝術作品的精神靈魂。“在中國古代美學體系中,‘氣韻生動的命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們可以說,不把握‘氣韻生動就不可能把握中國古典美學體系。”[10]
中國民族聲樂藝術中的“氣韻”,氣為韻之本,韻為聲之魂。在聲樂藝術中,沒有氣就沒有聲,更沒有所要表現的一切事物的精神風韻。氣是聲樂表演藝術的基礎,氣息的運用是聲樂表演藝術家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術,而唯有靈活掌握氣息,賦予氣息以作品的思想和情感,才能產生韻味,使聲樂作品生動和鮮活起來。在古代聲樂論著中,氣息技巧作為發聲技巧的基礎,地位無可替代。唐代段安節在《樂府雜錄》中說:“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云響谷之妙也。”[11]294清代陳彥衡在《說譚》中說:“夫氣者音之帥也,氣粗則音浮,氣弱則音薄,氣濁則音滯,氣散則音弱。”[12]氣主宰著音和韻,決定了作品的格調。
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論》中談及歌之格調:“抑揚頓挫;頂疊垛換;縈紆牽結;敦拖嗚咽;推題丸轉;捶欠遏透。”[13]16其格調無不是運用氣息技巧所致。不同的氣息技巧會產生不一樣的藝術效果。例如,表現水面或草原的寬廣,山川或河流的蜿蜒起伏,氣息是一貫到底、連綿不絕的縈紆,如長調風格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和反映赫哲族人民勞動生活的《烏蘇里船歌》的引子部分,就是通過控制腹肌的力量,使氣息平穩均勻地支持聲音,來營造一種舒展寬廣、安靜寧謐的畫面和煙波浩渺的韻味。例如,表現悲憤激烈或高昂激揚的情緒,氣息是噴薄而出,依靠腹肌的爆發力、有力收腹的頂氣,從而使氣息力量集中支持聲音奔涌而出,造成一種如虹的氣勢,如評彈《蝶戀花·答李淑一》的最后一句“淚飛頓作傾盆雨”[4]28,在短暫休止后的“傾”字與前面“作”的音構成了八度的大跳音程,噴氣的技巧非常有感染力地表達痛失親人,猶如五雷轟頂般痛徹心扉的感情。還有表現歡欣鼓舞的氣氛、活潑熱烈的情緒情感時,氣息的支持是飽滿積極富有彈性的,在樂曲速度較快、樂句較長的情況下,還要使用偷氣、搶氣等技巧來獲得響遏行云、高亢婉轉的聲音,從而營造出歡快熱烈的氣氛。
在聲樂藝術中,“氣韻生動”一方面指演唱者運用不同的氣息技巧產生不一樣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指“反映客體作品和表演主體的生命活力的氣勢”[14],即演唱者在詮釋聲樂作品時所賦予作品的氣質和生命力。例如,女高音歌唱家吳碧霞演唱歌曲《梅花引》時,對首句“一枝梅花踏雪來”[15]的“踏雪”二字間做聲斷氣不斷的十六分休止的處理,賦予了梅花靈氣和生命力,把梅花似仙子一樣踏雪而來,傲然挺立在白雪天地間的形象鮮活地表現出來。又如,男高音歌唱家郭頌的經歷使得他的歌聲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這都是歌唱家本身的審美喜好和二度創作所給予音樂作品的氣質。因此,聲樂作品的氣韻不能脫離演唱者而單獨存在,它深受演唱者自身的氣質風度和藝術追求的影響。
(二)聲韻
最早記錄我國音樂美學思想的著作《樂記》中有言:“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6]語言是歌唱抒發情感的載體。我國民族聲樂藝術中的語言,以聲(五音)、韻(四呼)、調(四聲)為特點的漢語語音體系為主。漢語的這些特點形成了我國民族聲樂講究咬字吐字的傳統,形成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特有的民族韻味。
1.聲之韻,在于字頭腹尾之運化
在聲樂藝術中,“詞”是“情”的主導。吐字藝術是韻味的構成因素,在以聲傳情的藝術實踐中擔負著重要的角色。明代魏良輔在《曲律》中提出:“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11]495他將“字清”作為聲樂藝術審美的首要標準。清代的王德暉、徐沅澂在《顧誤錄》中說:“唯腔與板兩工,唱得出字真,行腔圓,歸韻清,收音準,節奏細體乎曲情,清濁立判于字面,久之嫻熟,則四聲不召而自來,七音啟口而即是,洗盡世俗之陋,傳出古人之神,方為上乘。”[17]用“真、圓、清、準”幾個字點出了傳統聲樂美學中對字、腔、音、韻的審美追求。傳統聲樂理論把歌唱的吐字歸納為“出字”“引長”“收聲”的過程。清代著名的戲曲家、小說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提出聲音韻味的奧妙就體現在字頭腹尾的處理上,他認為吐字最難的、又必不可少的是要把握“出口”和“收音”兩個訣竅,唱一個字要把握三個部分,字頭“以備出口之用”,字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為余音,以備煞板之用”,但是字頭、字尾和余音又不能太刻意,必須自然而然,渾然天成,“字頭、字尾及余音,皆須隱而不現,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并無其字,始稱善用頭尾者”[13]144。
(1)字頭韻
中國民族聲樂中歌唱發聲的字頭指的是字的聲母。即使是沒有聲母的字,也很重視從靜止到韻母的發聲過程。在傳統民族聲樂理論中,字頭對表現歌曲的情緒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聲母發音的準確、有力、夸張能更深刻地表達歌曲的情感。戲諺:“咬字千斤重,聽者自動容。”[3]112唇、舌、齒、牙、喉“五音”,其發音部位不同,聲母阻氣與出字破阻之間摩擦發出的音,就形成了塞音、擦音、塞擦音、邊音、鼻音等不同的聲音效果,既增強了歌曲的表現力,也給歌曲帶來了不一樣的韻味。
20世紀80年代家喻戶曉的電視劇《西游記》的片尾曲《敢問路在何方》,因其富含人生哲理的歌詞、通俗易唱的旋律以及富有民族韻味的演唱,一直傳唱了30多年而經久不衰,深受老百姓的喜愛。這首歌最初由張暴默演唱,但她唱的版本太抒情和柔美,導演認為不大符合整部劇給人的形象感受,于是最后換成了蔣大為的民族男高音版本。歌唱家蔣大為在談對這首歌曲的二度創作時,一直強調要順應語言的味道去唱歌,他認為把握語言就是歌唱成功的第一關鍵因素。他說,在拿到這首歌曲時,他反復地朗讀歌詞,到唱歌時,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一些處理,使得歌唱更富有韻味。比如,他在“一番番”和“一場場”的字頭上加入了下滑音的處理。下滑音的運用使字頭更有力量,增長和強調了“番”字頭在唇與齒和“場”字頭在舌與齒部位間摩擦的時值。這樣的處理使字頭更帶勁兒,充分表現出了奮進中飽含的辛酸,使得歌曲在高亢中又帶著蒼涼,讓人不禁聯想到取經路途的艱難和唐僧師徒4人百折不回的精神,從而受到鼓舞。
(2)字腹韻
咬住字頭,緊接著要向韻母過渡。韻母又有頭、腹、尾三個成分。其中,字腹是韻母的主要母音,在歌唱中有吐字引長的作用。因此,在民族聲樂理論中又把字腹稱為“引長”。無論是單韻母還是復韻母,對字腹的演唱要求是在音值引長延伸時,字不變形,并且要根據歌曲情感表達的需要調節氣息的強弱和共鳴腔的空間大小。“橄欖腔”是我國最古老的戲曲劇種——昆曲中非常重要的演唱技巧,這個技巧的運用使情感表達更含蓄、更細膩。它的要領主要是在一個字的字腹上用功。通過控制氣息,使字腹的音量由輕而重,再由重轉輕,像橄欖一樣兩頭小中間大,從而使歌聲聽起來深情動人,情感細膩深邃,如臨帖一樣筆筆勾勒,字字講究,耐人尋味。例如,昆曲《牡丹亭·游園·醉扶歸》的旋律有一字多音的特點,橄欖腔的技法就把昆曲在一個字上迂回婉轉用功的細膩講究的“水磨調”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如“裊晴絲吹來閑庭院”[18]9的“閑”字,出字后要在韻母“i”音上拖完三拍,在1、2、3三個音上分別做橄欖腔后,在最后一拍的后半拍才歸韻到“an”,不急不躁,穩穩地唱好每個音,才能準確地表現出杜麗娘端莊持重、挪步暗生香的閨秀氣質。又如由漢樂府詩中的《上邪》改編而成的藝術歌曲《長相知》,表現了一位女子對愛情忠貞不渝的態度。許多歌唱家在演唱這首歌曲時,在“上邪”的“邪”和“我欲與君長相知”[19]的“知”字等一字多音的韻母上都做了橄欖腔的演唱處理,充分表現了古代女子表白時內心的情感由羞澀到渴望,轉而壓抑控制的“由收到放再收”的含蓄的內心變化過程。橄欖腔的字腹韻腔處理,也表現出我們較之西方,在表達激情的習慣、方式上不同的含蓄的民族性格特點。
(3)字尾韻
傳統民族聲樂理論中非常重視字的收音。如果字尾收音不分明或不準確,就會影響詞義的表達。字尾的收音又稱為“歸韻”。傳統聲樂藝術演唱的歸韻,按照相同或相近的韻母分類為“十三轍”。合轍押韻后就會產生不同的韻味特點。如“-n”和“-ng”二者雖然都是收歸鼻子音韻尾,但前者是收前鼻音,后者收后鼻音,若歸韻不準確,不僅韻味受影響,意思的表達也會受影響。南宋張炎在《詞源·謳曲旨要》中道出了以字成韻的奧秘:“腔平字側莫參商,先須道字后還腔。字少聲多難過去,助以余音始繞梁。”[20]他指出,遇到歌詞少、拖腔長的情況,如果在出字后運用歸韻和裝飾音的方法進行處理,就能使聲腔更婉轉,形成余音繞梁的效果。
20世紀40年代后,我國出現了一大批民族聲樂藝術家,如王昆、郭蘭英、常香玉、李谷一等,她們的演唱技藝構筑在中國傳統曲藝、戲曲、民歌的基礎之上,她們有的以傳統戲曲為基底并向民歌學習,有的根植于民歌的土壤再借鑒戲曲的唱功。在民族聲樂藝術領域,她們對韻味的追求和創造一刻也沒有停止。曾被《人民日報》評價為“為我國聲樂藝術的發展做出突出貢獻并載入我國音樂藝術發展的史冊”的歌唱家李谷一,她的聲音中有著“一種得益于傳統戲曲和曲藝的熟稔”[21]。她演唱的《鄉戀》,因富有個性的聲音和獨特的民族韻味而曾風靡了整個中國。開頭幾句“你的身影,你的歌聲,永遠印在我的心中”,她對切分節奏進行了換氣處理,在“你”與“的”、“永”與“遠”、“我”與“的”之間造成了一種停頓的感覺,又把“身影”“歌聲”“印在”“心中”的“身”“歌”“印”“心”四字的韻母,分別是“en”“e”“in”和“in”,都在其小節最后一拍的兩個余音上做了韻尾歸韻的韻腔處理。這個處理非常巧妙,漫不經心地聽會覺得與眾不同,細細品味則感到意蘊生動、余音繞梁,不僅突出了“身影歌聲印在心中”的歌曲主題思想,也把歌曲的藝術形象展現得惟妙惟肖。帶有京韻大鼓風格的歌曲《故鄉是北京》,如果嚴格按照譜子唱,很難體現出京韻的味道。而李谷一在演唱時,對旋律進行了特殊處理,在字尾的歸韻上大做文章。例如,“靜靜地想一想”的第二個“想”字,她巧妙地加入了休止,把“想”字的字頭和字尾歸韻分開,出字即停,轉而用后鼻音韻母“ang”在兩個音上強調并延長,不僅表現出了人在沉思時的狀態,也把以鼻腔歸韻為主的京韻特點瞬間凸顯出來。
2.聲之味,在于豐富多彩的潤腔技巧
“潤腔”是情感表達的民族化、藝術化,是聲音在歌唱抒情技巧里的藝術升華,是使沒有生命的音符變得生動傳神,從而使聲樂藝術作品透過表象,成功實現意象的表達的重要技巧。在我國傳統聲樂藝術和民族民間音樂中,韻味常藏于潤腔之中。不論是傳統戲曲,還是民族民間歌曲,在傳統民族聲樂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都積累了豐富的潤腔裝飾技巧。這些腔調大多與所唱字音的四聲調值密切相關,又或者是一個民族在歷史變遷發展過程中的民族文化和情感的印記。
(1)為順應字音的四聲調值而用的潤腔
為順應字音的四聲調值而使用的潤腔,不是旋律結構中的音,而是演唱者結合了所唱的字的四聲陰陽的調值,對歌曲旋律所做的增加音符的特殊處理。昆曲中常用的潤腔裝飾細分起來有16種之多,幾乎都是為了調整腔與字音之間的關系而存在的。例如:在一些音調向上的旋律中,對于歌詞中的某些字音來說,中間相差一個音,這時候為避免曲調不順,就在中間添加一個音,這個音就是“墊腔”,如《牡丹亭·游園·皂羅袍》中“誰家院”[18]11的“誰”字,腔格為“[62] ”,在這兩個音中間加了一個“l”音,這個“l”音就是“墊腔”。“墊腔”這種潤腔技巧更適用于纏綿悱惻的曲詞,它的運用可以使曲子更婉轉多情。歌唱家在對一首民族風格的歌曲進行演唱的二度創作時,通常先對歌曲的一字一句進行認真分析,在歌曲旋律與字音不是非常貼合的情況下,會在不貼合字音的旋律音上加入前倚音或后倚音等裝飾音,使旋律更符合字的音調。加入裝飾音也是潤腔技巧的一種。例如:歌曲《十五的月亮》,“十”在普通話中的音調是陽平,調值是由中升到高,旋律中只有一個音“5”就立即過渡到“五”字上了,如果按照譜子的旋律唱,唱出來就是“失”的陰平調,聽起來字義會有誤。因此,歌唱家演唱這首歌時,會在“十”字的“5”音上加入一個下方小二度的前倚音“#4”,使字更符合由中升到高的音調特點,聽起來更朗朗上口,親切動人。
(2)鐫刻著民族文化和情感印記的潤腔
這種潤腔方式大多存在于民間歌手的演唱中,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生存環境息息相關。例如,生活在高原、高山等地區的民族民間歌手所唱的民歌中,會較多的存在拖腔和滑音等潤腔裝飾。苗族民歌手在唱“飛歌”時,句內的滑音和句尾的甩音是他們慣用的潤腔方式,這既充分表現了他們所生活的大山地勢險峻的特點,也表現了苗族人民性格中的豪放張揚。又如,瑤族、京族、納西族等在生活方式上有遷徙或游牧特點的民族歌手,其歌聲中自帶有“顫音”這種獨具特色的潤腔方式。用聲樂理論來分析,“顫音是在一種‘氣與‘力的配合中產生的,是在氣息的沖擊下,聲帶在向下拉緊和向上放松之間快速變換,使喉頭呈現縱向顫動的結果。”[22]這種帶有技術難度的顫音,聽起來像是民間歌手刻意追求的藝術表現手段,但當問及他們為什么這么唱時,瑤族人民回答“習慣用這種聲音”[23]。這種潤腔方式是遷徙民族艱難遷徙歷程的印記,能讓人感受到這個民族在長期遷徙歷程中所經歷的艱辛與磨難。
這些鐫刻著民族文化和情感印記的潤腔,能穿越時空,直抵人心,不僅讓人陶醉于聲音中所蘊含的自然與人文情態、民族情懷,更讓人驚嘆中華多民族文化的多彩魅力。
3.聲之妙,在于頓挫得法、抑揚有道
“頓挫”一詞出自《后漢書·孔融傳贊》,以評價聲調的抑揚和停頓轉折。詩文和繪畫、書法藝術中以“筆法頓挫”來形容內容的跌宕起伏、回旋轉折。戲曲昆腔中有“頓挫腔”一說,意思是在第一個音符出口后稍停頓一下,之后再用虛聲唱出另一音符,用虛聲唱的音符稱為“挫”,前后頓挫的兩個音則呈現出實虛的音色對比之美。清代聲樂理論家徐大椿認為:“唱曲之妙,全在頓挫,必一唱而形神畢出,隔垣聽之,其人之裝束形容,顏色氣象,及舉止瞻顧,宛然如見,方是曲之盡境。”[11]618“頓挫”的用聲技巧出神入化地表現了曲子的神韻和情感,“頓挫得款,則其中之神理自出,如喜悅之處,一頓挫而和樂出;傷感之處,一頓挫而悲恨出;風月之場,一頓挫而艷情出;威武之人,一頓挫而英氣出;此曲情之所最重也”[11]618。如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在《誰說女子不如男》唱段末句“這女子們,哪一點兒不如兒男?”中“男”字的拖腔后運用了頓挫技法,把花木蘭的巾幗英氣生動地展現了出來。在戲曲聲情藝術實踐經驗里,有一句話叫作“輕、重、抑、揚出感情”[3]120。這句話正是對頓挫技法的補充說明。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對字的抑揚頓挫之道也有所總結,他認為:“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襯字。每遇正字,必聲高而氣長,若遇襯字,則聲低氣短而疾忙帶過。”[13]158演唱中的抑揚頓挫能使音樂這種聽覺藝術呈現出明暗虛實對比的視覺效果,給人無限的遐想,同時也展現了中國傳統藝術注重虛實結合、起伏跌宕的線條美的審美特點。
(三)情韻
聲為情之形,情為聲之本。無論是將激情蘊含于旋律意境,用含蓄的方式表現在板路腔調上的昆曲、京劇藝術,還是將激情形之于聲音旋律,以更生活化接地氣的音樂形象來感人的評劇、豫劇等地方戲曲和民間小調,情韻始終是聲樂藝術作品表現追求的終極目標。我國民族聲樂藝術自古以來都注重聲情結合,以情動人。正是因為有了情韻,它的音樂語言才成為人民的音樂語言,它的激情才能動人,含蓄而富有魅力。
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聲情并茂。清代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有終日唱此曲,終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無曲;此所謂無情之曲,與蒙童背書,同一勉強而非自然者也。雖腔板極正,喉舌齒牙極清,終是第二第三等詞曲,非登峰造極之技也。”[11]593歌者必須先用心感悟曲中之情,心有所感,有感而發,歌聲才能牽動聽者的心。歌者的聲情要與曲情相合,曲情與心意相通,情與景相融。只有心口同唱,聲情并茂,歌唱技藝才能登峰造極。晉代張華的《博物志》中記載了春秋時期一個名叫韓娥的民間女歌手,她的歌聲極富感染力,人們能從她的歌聲中感受到她的情緒,并被其深深打動,因她的歌聲歡快而開心、悲愁而泣涕。她要到齊國(今山東省大部)去,因為沒有旅費,便轉往雍門(今陜西咸陽)借歌唱謀食。她住在旅店中,有人用言語羞辱她,她便曼聲哀哭,用歌聲盡情表達她的悲傷。當地的人們聽了,便整日沉浸在悲傷的情緒中不能自拔,只能請她改用柔婉的聲調再唱首歡樂的歌,人們這才從悲傷的情緒中解脫出來,被她的歌聲感染而又歡欣鼓舞[13]2。由此,足見感情濃郁的歌聲有著多么神妙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一位歌者,其演唱的歌聲必須發自真心,真情流露,才能將歌中之情傳達出來,與聽眾產生共鳴。任半塘在《唐聲詩》中講道:“歌者不可輕于啟喉,必待自己之真情既發,而后再有聲辭之吐;能先觸發自己之真情者,自能宣達聲與辭中之歌情,以度予聽者。”[24]我國著名的歌唱家郭蘭英在回憶自己演唱歌劇《白毛女》時說,當時她是一個字一個動作地去揣摩人物的內心,務必要做到真實。青年歌唱家雷佳在回憶復排歌劇《白毛女》的經歷時說,郭蘭英老師在指導她演唱和表演時一直強調要真實。讓她最為感動的是郭老師在示范喜兒哭爹那場戲時,完全不顧90歲的高齡,親身示范,毫無保留。郭老師當時“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讓所有人都驚到了,一聲“爹”更是瞬間把大家的眼淚給喊出來了。劇情和曲情中的情韻就是通過歌者的真誠感悟,飽含在歌曲的一字一句中,使聽者動容。
情之韻味,既宣達于詞與聲中,又蘊含于心中之真情,只有設身處地,力求將曲中之意形之于聲音,才能使聲音技巧與情感表達合二為一,達到聲情并茂的最高藝術境界。
三、結語
我國民族聲樂藝術博大精深,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其中蘊含的聲學、美學、哲學知識豐富,對當代流行音樂的發展仍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流行音樂界被奉為傳奇的女歌手王菲曾說她的歌唱風格深受鄧麗君的影響,而被譽為“國際天王巨星”的鄧麗君自幼受到大家閨秀的母親的影響,愛聽黃梅戲、評戲等地方戲曲,耳濡目染,戲曲功底為她輝煌的流行歌唱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扎實的根基,使她歌唱的音色、咬字、氣息的運用都具有獨特的民族韻味。鄧麗君的歌聲牽動著海內外華人,至今仍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音樂人,這也正是民族聲樂藝術中所蘊含的氣韻、聲韻和情韻的深厚藝術魅力之體現。無獨有偶,曾深受老百姓喜歡的流行歌手屠洪剛是京劇演員出身;著名流行歌手韓紅一直都從民族聲樂中汲取養分,并在流行音樂界將其發揮到極致。這都是民族聲樂藝術之韻味賦予他們歌唱技藝不一樣的藝術魅力。曾經培養了韓紅、雷佳、龔琳娜、吳碧霞等當代著名歌唱家的民族聲樂教育家鄒文琴,在她幾十年的聲樂教育生涯中,最注重的就是繼承民族聲樂的優秀傳統。她認為要發展民族聲樂,既要借鑒西方演唱技法,更要從民族傳統中汲取養分。曾任天津音樂學院院長的音樂教育家石惟正,在《人民音樂》發表的文章中高度評價了鄒文琴在中西傳統聲樂的優勢契合上所做的努力。談到繼承傳統的重要性,他說:“我國20世紀初到現在的專業歌唱史就是一部繼承民族傳統和借鑒西方的中西碰撞、交流和優勢契合、出新的歷史。”[25]演唱者只有深深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將民族的演唱技巧和表現方式,融會貫通地運用于自己的演唱創作,才能使演唱富有深厚的底蘊和魅力,質樸中透出感人的力量。
參考文獻:
[1] 李曉貳.民族聲樂演唱藝術[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1:1.
[2] 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3] 陳幼韓.戲曲表演美學探索[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
[4] 王夏.聲樂表演藝術中的“氣”與“韻”[D].杭州:杭州師范大學,2009.
[5] 徐復觀.中國古代藝術精神[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134.
[6] 張彥遠.法書要錄[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152.
[7] 水賚佑.蔡襄書法史料集[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3:8.
[8] 列子[M].殷敬順,陳景元,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5-156.
[9] 朱權,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M].北京:中華書局,2010:151.
[10] 葉朗.中國美學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
[11] 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12] 陳彥衡.說譚·總論[J].中國戲劇,1995(11):56.
[13] 周貽白.戲曲演唱論著輯釋[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
[14] 楊易禾.音樂表演藝術原理與應用[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259.
[15] 蔡世賢.中國藝術歌曲選(1996—2003)下冊[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239.
[16] 禮記[M].胡平生,張萌,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760.
[17] 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M].北京:中國戲曲出版社,1959:159.
[18] 張衛東.張衛東演唱說戲牡丹亭[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0.
[19] 楊曙光.中國古典詩詞藝術歌曲賞析與演唱[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8:66.
[20] 張炎,沈義父.詞源注 樂府指迷箋釋[M].夏承燾,校注.蔡嵩云,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14-15.
[21] 李詩原.李谷一聲音的個性、魅力與價值[J].人民音樂,2020(3):4-11.
[22] 韋蕊.瑤族民歌唱腔特色及其文化內涵探究[J].百色學院學報,2018(5):82-90.
[23] 毛殊凡.瑤族歷史文化與現代化[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62.
[24] 任半塘.唐聲詩: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95.
[25] 石惟正.鄒文琴教學隨想[J].人民音樂,2010(1):58-59.
[責任編輯:丁浩芮]
The Charm of Music: Artistic Aesthe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Wei Rui
Abstract: The charm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is what Chinese people pursue in the art of singing and is the reason why national vocal music is so appealing. It also reflects the overall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aesthetic standards are based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folk songs such as Chinese operas, folk art forms and local folk songs. The charm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as shown in breath technique, enunciation and lyricism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breath, sound and lyricism. It contains rich knowledge of acoustics,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and still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p music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national vocal music; aesthetics; ch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