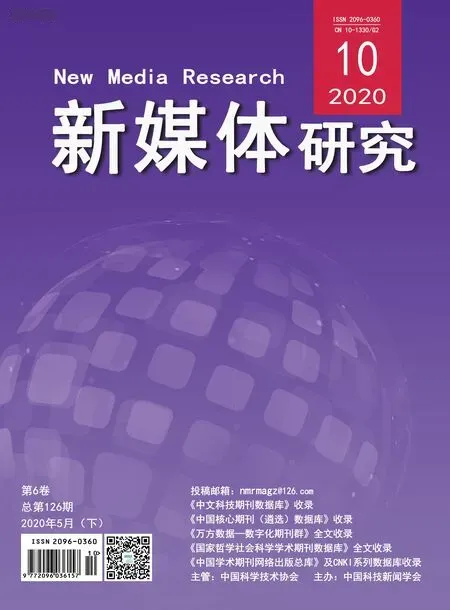我國傳播學研究中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應用
周彥宏
摘 要 近年來,我國學者應用社會網(wǎng)絡分析,在傳播學領域中對特殊的社交媒體用戶、突發(fā)性事件中的傳播節(jié)點及知識傳播、國際傳播、傳媒貿易等領域的有關主體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探索,并結合多種輔助分析方法對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應用進行拓展,通過實證數(shù)據(jù)展現(xiàn)傳播網(wǎng)絡的形態(tài)與其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以及傳播節(jié)點的作用。
關鍵詞 社會網(wǎng)絡分析;研究方法;傳播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0-0005-05
社會網(wǎng)絡分析是社會科學中對于社會網(wǎng)絡中的社會個體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的一種分析方法。它的核心依據(jù)是“社會由關系構成”,這表示由于個體所鏈接的各種關系,才使得個體的社會屬性得以塑造。因此,社會網(wǎng)絡分析著重描述個體間的互動關系。不同于對個體屬性的研究,社會網(wǎng)絡分析將研究對象置身于其所處的復雜關系網(wǎng)絡之中,并通過對這種關系進行精確定義和測量,展現(xiàn)研究對象的社會性背景[ 1 ]。
對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中所運用的結構性視角,經(jīng)典的傳播學理論中早有涉及,而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得以明顯地在傳播學研究中體現(xiàn)。根據(jù)學者楊春華的研究,自2011年,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才在我國傳播學研究中正式發(fā)展起來[2]。近年來,網(wǎng)絡與新媒體使社會關系帶來了巨大變革,意見交流的公共空間結構及媒體間、媒體與受眾間的信息傳播結構發(fā)生了改變。互動和關系成為媒體發(fā)展和傳播研究的重點關注領域,而計算機技術及統(tǒng)計方法在傳播學研究中的跨學科應用,也為社會網(wǎng)絡分析方法在傳播學領域的發(fā)展培育了基礎。
筆者根據(jù)CNKI的學科分類,以“新聞與傳媒”學科研究作為限定范圍,在CNKI文獻數(shù)據(jù)庫中以“社會網(wǎng)絡分析”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共得到2004年至2020年間中文文獻481篇,其中文獻發(fā)表高峰期集中于2013年—2015年,雖然自2016年文獻發(fā)表量有所回落,但文獻被引證數(shù)據(jù)卻自2014年進入高峰期。被引量代表著文獻被引用的次數(shù),是判斷文獻影響力的重要依據(jù)之一。因此,對高被引量文獻進行分析可以展現(xiàn)一定時間段內的學科領域中學者們的關注重點。
本文經(jīng)剔除不以社會網(wǎng)絡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獻和明顯偏離傳播學研究范疇的文獻后,選擇被引量前50篇的研究進行研讀分析,梳理我國傳播學研究中以社會網(wǎng)絡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研究文獻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具體應用。通過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一探社會網(wǎng)絡分析在近年我國傳播學領域研究中的應用與發(fā)展,及這些研究為我國傳播學領域知識和傳媒產業(yè)做出的貢獻。
1 不同的社會主體及其關系
應用社會網(wǎng)絡分析進行傳播學研究的文獻,以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為研究對象,并通過不同研究角度和具體分析方法對其進行展現(xiàn)。在這些研究的前提中,首先需要確定的就是社會網(wǎng)絡里的“點”“邊”及“網(wǎng)絡邊界”。“點”的選取則通過研究中的社會主體反映出來。在本文選取分析的研究文獻中,社會主體主要包括特殊社交媒體用戶、信息傳播節(jié)點、文本內容主體、合作學者、合作機構、國家和地區(qū)六類,其中以特殊社交媒體用戶、信息傳播節(jié)點、文本內容主體為主。
在本研究選取分析的高被引文獻中,以特殊社交媒體用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占比最高,以探究特殊社交媒體用戶之間的關系。對高校圖書館官方微博進行研究的有學者葛艷[ 3 ],對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微博研究的有學者許偉[ 4 ],這兩項研究分別從圖書館主體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具體工作服務出發(fā),探尋其媒體賬號之間的互動關系和服務影響力。對高校學校官方微博進行研究的有學者廖小琴等[5],該研究通過研究高校官博之間的關注關系,來描述這一網(wǎng)絡中,處于中心地位的高校官方微博。付永升等則選擇對大學生微信用戶進行研究[6]。學者趙英等為對企業(yè)內知識共享進行研究,選取了企業(yè)部門和部門成員作為節(jié)點,并在這項研究中展現(xiàn)了基于企業(yè)部門和部門成員的不同層次的與包括咨詢關系、情感關系、情報關系、信任關系的不同屬性的關系網(wǎng)絡[ 7 ]。學者陳遠和學者許鑫等則以科學網(wǎng)用戶為節(jié)點分別研究了科學網(wǎng)博主中的意見領袖和學術博客中的學科交互行為[8-9]。學者洪小娟等研究了食品安全傳播中新浪微博上的媒體微博[10];學者韋路等研究了Twitter上的主要媒體賬號[ 1 1 ];學者孫厚權等研究了政務微博中的意見領袖[12];學者侯筱蓉等則特別研究了某一城市中的醫(yī)院官方微博[ 1 3 ]。對于社交媒體用戶的研究還有學者陳遠等以騰訊“10萬+”粉絲用戶為節(jié)點,學者褚建勛等通過滾雪球抽樣以普通用戶為節(jié)點兩者分別對騰訊微博和新浪微博總體網(wǎng)絡進行的研究[14-15]。此外還有學者劉佩等以知乎用戶為節(jié)點對網(wǎng)絡問答社區(qū)用戶進行的研究[16],學者雷輝等以政府、企業(yè)、學校、微博名人用戶為節(jié)點,所做的不同特征主體網(wǎng)絡關系的比較[ 1 7 ]。
而通過信息傳播節(jié)點的選取,來對信息的社會網(wǎng)絡發(fā)展進行研究的學者也不在少數(shù)。其中在某一特定議題下進行信息傳播的節(jié)點分為兩類,這些參與話題且作為信息傳播節(jié)點的主體也都是社交網(wǎng)絡的用戶。一類是積極行動者,這一類用戶以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lián)盟動員行動下的行動者為代表,在研究者陳先紅等人的限定下,互動行為在三次以上的用戶被作為積極行動者節(jié)點[18]。在特定議題下進行信息傳播的還包括議題的討論參與者,這些討論參與者一般以轉發(fā)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而不同的學者又分別以評論、點贊、評論、發(fā)帖或回帖等行為作為節(jié)點選取的條件。
這些對于議題下信息傳播網(wǎng)絡的研究展現(xiàn)了不少特殊議題,除上述艾滋病患權益動員外,還有穹頂之下[19]、魏則西事件[20]、雅安地震[21]、溫嶺虐童事件[22]等突發(fā)性議題,危機公關[16]、轉基因食品[23]、食品安全謠言[24]、霧霾[25]等特殊話題。此外,對于信息傳播網(wǎng)絡的研究還包括對國際傳播的研究,和微信公眾號信息傳播網(wǎng)絡的研究。在對于國際傳播的研究中,學者吳瑛選取了主流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主要節(jié)點,這些主流媒體是來自16個國家的32份報紙,其選擇依據(jù)于“在主流議程中,網(wǎng)絡媒體依附于傳統(tǒng)媒體的議程設置”的前人研究[26]。學者徐寶達等對微信公眾號的信息傳播研究則結合了“微信公眾號”和“普通用戶”間的多邊關系,通過信息傳播網(wǎng)絡總結微信平臺內的信息傳播規(guī)律[27]。
文本內容之間的關系也是傳播學研究應用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其中文本內容主體主要包括自媒體和科學文獻。學者韓有業(yè)通過以10家新聞學院的具有學術取向的微信自媒體為節(jié)點,通過對核心詞和訂閱號組成的社會網(wǎng)絡進行分析,分析不同學院對學術資源的搶奪[28]。學者閔超等則通過建立圖書情報學和新聞傳播學CSSCI收錄文獻的關鍵詞集,在對關鍵詞進行交叉詞頻后得到核心關鍵詞,并將這些核心關鍵詞與其他關鍵詞組成社會分析網(wǎng)絡,從而得到交叉研究熱點及這些研究熱點與其他研究點的關系[29]。
在出現(xiàn)頻率較低的領域中還包括學者間的合作關系,機構間的合作關系,以及國家間的貿易關系研究。其中學者間的合作關系研究以學者邱均平等對知識管理領域學者合作關系研究為代表[30]。機構間合作則在學者張洋等對經(jīng)濟學領域機構合作的研究中展現(xiàn)了師承關系(有向非對稱)、互引關系(有向非對稱)、合著關系(有向對稱)三種不同的關系[ 3 1 ]。貿易關系則以學者李彪等的研究為代表,這項研究中展現(xiàn)了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電影貿易往來[32]。
2 不同的網(wǎng)絡關系層次與定義框架
針對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們在社會網(wǎng)絡關系的建立和描述中使用了不同的網(wǎng)絡層次和定義方法。在這里借鑒了學者楊春華總結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五個層次:個體層次、二元層次、三元層次、子群層次和總體層次[2]。本研究根據(jù)文獻的實際內容對層次分類進行調整,因缺少三元層次的文獻而將其去除,并依據(jù)文獻中對不同總體網(wǎng)絡進行對比的內容添加網(wǎng)絡間對比層次。因此,下述社會網(wǎng)絡分析方法的應用將從個體層次、二元層次、子群層次、總體層次及網(wǎng)絡間對比五個方面展開。
個體層次是對于節(jié)點的分析,主要用于考察個體在網(wǎng)絡中的地位。對于個體層次的主要描述方法和測量方法為中心性分析。中心性分析具體包括點度中心性(Point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其中點度中心性包含點入度和點出度,用于表示節(jié)點與其他節(jié)點的鏈接關系,最簡單的測量方法便是計算與該節(jié)點直接相連的其他節(jié)點的個數(shù),相對值越大,說明該節(jié)點在網(wǎng)絡中所處的地位越趨于中心。接近中心性則是基于網(wǎng)絡節(jié)點不受控制性而提出的測量指標,接近中心性越大則表明其在網(wǎng)絡中獨立性越低,與節(jié)點間的聯(lián)系易受影響。中介中心性測量的是該節(jié)點多大程度上位于圖中其他點的中心,展現(xiàn)控制其他節(jié)點之間聯(lián)系的能力,其值越大,說明在網(wǎng)絡中越重要[5]。因此,可以看出中心性分析的測量指標目的都是為了反映節(jié)點在網(wǎng)絡中的影響力,對于網(wǎng)絡關系的控制能力。在具體研究中,節(jié)點中心性的判定常和節(jié)點信息權利及傳播貢獻聯(lián)系起來。陳遠等在對騰訊用戶的研究中,通過測量節(jié)點中心性和節(jié)點信息貢獻量的數(shù)據(jù),將節(jié)點中心性的三個分析指標與節(jié)點信息貢獻量進行相關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中介中心性與節(jié)點信息傳播貢獻量的相關性更好更穩(wěn)定,更適合用于測量大規(guī)模網(wǎng)絡中節(jié)點對信息傳播的貢獻[ 1 4 ]。此外,對于個體層次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還有對于節(jié)點角色的分析,其中大多數(shù)通過結構洞的概念進行描述。侯筱蓉等在研究中對結構洞分析進行進一步闡述,將有效規(guī)模、效率、限制度和等級度作為表征網(wǎng)絡結構洞特征的指標[ 1 3 ]。趙金樓等則在研究中通過結構同型性分析對相似角色的節(jié)點進行判斷[21]。韋路等則以內節(jié)點數(shù)、外節(jié)點數(shù)、緊密中心度、間距中心度為指標對節(jié)點在網(wǎng)絡中的社會資本進行分析并用于展現(xiàn)節(jié)點特征[ 1 1 ]。
學者們對于二元結構的關注較少,分析方法也較為簡單。陳先紅等在研究中對于兩個節(jié)點間的等價結構性進行描述,用以展現(xiàn)該關系對于兩邊節(jié)點的同等重量[18]。韋路等的雙向鏈接關系則直接確認了有向網(wǎng)絡中兩節(jié)點的雙向相關[ 1 1 ]。
對于子群層次的關注一般表現(xiàn)為研究中對凝聚子群的描述,這一術語也在多個研究中被提及。葛艷則進一步關注子群間的關聯(lián)性[ 3 ];趙英等關注局部聚類系數(shù)和距離[ 7 ];洪小娟等則分析了子群間的連通性和穩(wěn)定性[24]。
在總體層次的分析中,最受關注的特征就是網(wǎng)絡密度,特征路徑長度則為比較常見的測量指標、此外還有凝聚力和群聚系數(shù)。如胡改麗等在對虐童事件的傳播網(wǎng)絡分析中就同時使用了這三項指標[22]。除密度外,網(wǎng)絡中心勢和核心-邊緣模型的分析概念也常被使用,分別以雷輝和張洋等的研究為代表[17,31]。陳先紅等還使用了等級度的概念[18],冪律分析也被劉佩等引入整體網(wǎng)絡的分析中,用于展現(xiàn)無標度網(wǎng)絡的不平等性[16]。
在網(wǎng)絡對比分析中有吳瑛、閔超、胡改麗三位學者從時間上縱向對比網(wǎng)絡,其中吳瑛等選擇了從2010年到2014年五個時間斷點[26],閔超等選取了2001年與2011年兩個時間斷點[29],胡改麗等將信息傳播網(wǎng)絡特征與熱點事件發(fā)展階段相結合[22]。而以許鑫為代表的學者則從社會主體上劃分,對由不同主體構建的總體網(wǎng)絡進行對比分析,其中許鑫等的研究中還包含了由不同關系建立的社會網(wǎng)絡的對比分析[9]。褚建勛等則從樣本范圍大小及社會網(wǎng)絡本身具有的結構特征等方面進行比較[15]。
3 數(shù)據(jù)收集方法與分析工具使用
在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研究中還少不了數(shù)據(jù)收集與分析工具的使用。筆者根據(jù)文獻中的研究內容將所選文獻中使用的數(shù)據(jù)收集方法分成了檔案記錄、內容分析法、觀察、抽樣、調查問卷五類。
由于所選文獻的研究主題大多有關社交媒體用戶和文本內容,所以基于社交平臺的用戶檢索、篩選、記錄,和基于文本內容的文本內容抓取和詞頻分析成為數(shù)據(jù)收集的主要方法。學者許偉對圖書館員的微博用戶數(shù)據(jù)收集就來源于社交網(wǎng)站平臺的直接搜索功能,通過不同關鍵詞搜索結果的擬合得到最終搜索結果[ 4 ]。馬寧等的研究中使用了AutoMap在開放資源中提取數(shù)據(jù)[ 3 3 ]。閔超等使用了Visual Studio 2008對文獻內容的關鍵詞數(shù)據(jù)進行抽取[29],王晰巍等則通過Java自編程序獲得全網(wǎng)新浪微博霧霾話題的相關輿情[25]。徐寶達等則通過微信授權下的搜狗搜索和微信啦,獲取研究所需的微信訂閱號內容與互動行為數(shù)據(jù)[27]。觀察法中則以陳先紅等使用的虛擬民族志為代表[18]。抽樣方法中則以滾雪球抽樣和排名順序抽樣為主,陳遠等所使用的三角擴散法則將強關系條件嵌入滾雪球類抽樣過程中[ 1 4 ]。對于明確的研究主體,問卷調查法也有幸在所選文獻中被使用,付永升等和趙英等直接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獲取社會主體間是否存在單向關注關系[6-7]。
在所選文獻中,社交網(wǎng)絡分析大多通過已有軟件完成,Ucinet在軟件的使用中占據(jù)主導優(yōu)勢,被使用比例約占76%。第二常見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工具為Gephi,Gephi所展現(xiàn)的分析結果以云圖為特色。韋路等在研究中使用的NodeXL可同時抓取數(shù)據(jù)和進行社會網(wǎng)絡分析[ 1 1 ]。其中還有馬寧等使用動態(tài)網(wǎng)絡分析方法對輿論傳播中的意見領袖進行識別,其中動態(tài)網(wǎng)絡分析所使用的工具為組織風險分析器(Organization Risk Analyzer,ORA)[ 3 3 ]。其他分析工具還包括北京大學微博可視化分析工具[18]、谷尼微輿情軟件[19]。
此外,在以社會網(wǎng)絡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前提下,許多學者的研究還將其他分析方法與社會網(wǎng)絡分析結合。鄰接矩陣在記錄“邊”關系時是必不可少的運用,而基于同一主體基礎的不同層次關系的分析,則需要建立元矩陣,其中以馬寧等的動態(tài)網(wǎng)絡分析為代表[ 3 3 ]。pearson雙變量相關被用來對兩變量的相關性進行檢驗,在研究中已被驗證的相關關系有官博中心性指標排名與學校排名相關[5];師資輸出中心度與學科排名高度相關、與機構發(fā)文數(shù)據(jù)低度相關[ 3 1 ];社會化媒體使用程度與社會資本之間正相關[ 1 1 ]。許鑫等的研究中則使用了參數(shù)T檢驗方法[9]。還有王旭等結合搜索指數(shù)變化與關注趨勢變化展現(xiàn)輿情生命周期特征[20],胡改麗等將其前階段研究中獲得的熱點話題傳播模式6階段融入了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發(fā)展分析中[22]。
4 討論與總結
通過上述對文獻內容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近年來我國學者對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在傳播學領域中應用進行了較為豐富的探索,為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在傳播學的適用性進行了肯定,特別是在一般網(wǎng)絡信息資源的核心優(yōu)勢評價的評價及意見領袖的識別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從所研究的社會網(wǎng)絡的社會主體來看,研究對象中的社會主體主要集中于社交媒體用戶,但這些社交媒體作為傳播領域中特殊重要角色,是線上信息流動的重要節(jié)點,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另外,社交媒體在當今傳播行為中所承擔的重要角色已被近年許多學者論述,并得到定性研究中的眾多認可,運用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這一結論的可靠性在實證數(shù)據(jù)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此外,對于信息傳播事件進行社會網(wǎng)絡研究的文獻也為我們展現(xiàn)了多個突發(fā)性事件,科學、環(huán)保、醫(yī)療等領域的重要議題的發(fā)展情況,為我國輿情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結構化的可靠的研究材料。熱點之外,國際傳播、傳媒貿易等傳播學領域的重要話題也在文獻中展現(xiàn),進一步展現(xiàn)了研究內容的豐富性。值得一提的是,知識傳播也在已選文獻中占據(jù)不可忽視的地位,隨對于知識傳播進行研究的學者大多數(shù)來源于情報科學領域,但知識傳播其因傳播內容的特殊性,也不能為傳播學領域學者忽視。
在研究方法上,我國學者也對社會網(wǎng)絡分析在我國傳播學領域中的應用進行了拓展,如不同網(wǎng)絡間的對比分析中,基于時間的縱向對比,展現(xiàn)了社會網(wǎng)絡在時間上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展現(xiàn)了一般社會網(wǎng)絡分析在時間切片下所不具有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這一方法的拓展可用于輿論傳播過程和特殊個體生長的研究中,對其進行更形象、更多維度的展現(xiàn)。社會網(wǎng)絡分析與相關性分析的結合則將社會網(wǎng)絡的特征因素與其他因素結合起來,檢驗了諸多影響社會網(wǎng)絡建立的因素,及社會網(wǎng)絡這一結構特征所帶來的影響。在解釋性的研究中,以上研究還對怎樣將輿情網(wǎng)絡結構特點運用于政府輿論控制引導,企業(yè)促進企業(yè)內社交媒體中的知識共享行為,怎樣有效疏通健康信息流通渠道提出了建議,也有直接針對網(wǎng)絡媒體平臺進行的研究對微信平臺信息傳播的有限性進行了解釋。最具前沿性的是學者馬寧使用的動態(tài)分析法,其研究展現(xiàn)了研究意見領袖身份在輿論主體、討論話題、態(tài)度傾向為邊的元矩陣構建的網(wǎng)絡層次中演變的動態(tài)過程。同時,該研究還利用ORA挖掘精英人物的測量指標將意見領袖分為焦點人物、傳播人物、活躍人物、潛在活躍人物、討論帖獨占人物和關鍵詞獨占人物六類,使得節(jié)點身份和連線關系更加多元,對意見領袖展現(xiàn)角度也變得更為豐 富[ 3 3 ]。該研究也體現(xiàn)了動態(tài)網(wǎng)絡分析法在我國網(wǎng)絡媒體平臺研究和意見領袖研究中的適用性,并從網(wǎng)絡層次的演變中解釋了不同意見領袖的構成原因。
綜上所述,近年來社會網(wǎng)絡分析方法在我國傳播學領域研究中的應用展現(xiàn)了我國傳播產業(yè)中的實際情況,為傳播產業(yè)發(fā)展和研究通過科學地系統(tǒng)地方法留下了寶貴的記錄資料。但其中也顯現(xiàn)了部分研究結果的同質化,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對于案例進行研究時未能很好地判定案例所代表的一般性領域,提煉該案例的比較特點,未能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更多的研究傾向于從傳者行為出發(fā)進行研究,雖然在網(wǎng)絡社交媒體的傳播者傳授雙方是相互的,但在以上研究中對于傳播研究只展現(xiàn)了信息傳達的概念,對于接收分析的研究少之又少。數(shù)據(jù)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對于社會主體與社會關系發(fā)展與生長過程的研究也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未來,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將在我國的研究中具有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值得傳播學學者對其進行學習利用。
參考文獻
[1]約翰·斯科特.社會網(wǎng)絡分析法[M].劉軍,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
[2]楊春華.社會網(wǎng)絡分析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J].當代傳播,2015(4):29-33.
[3]葛艷.UCINET軟件在高校圖書館微博關系研究中的應用[J].圖書情報導刊,2016,1(5):3-6.
[4]許偉.基于社會網(wǎng)絡的學科服務微博圈研究[J].情報科學,2015,33(2):59-62.
[5]廖小琴,孫建軍,鄭彥寧,等.高校微博互鏈網(wǎng)絡的核心-邊緣結構分析:鏈接結構和信息分布視角[J].情報科學,2014,32(1):119-123,149.
[6]付永升,鄔凱偉.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微信朋友圈實證研究:以華中農業(yè)大學信息1003班為例[J].情報探索,2015(1):21-25.
[7]趙英,楊閣,謝彩云.基于SNA社交媒體對企業(yè)知識共享的影響研究[J].財經(jīng)科學,2014(10):92-101.
[8]陳遠,劉欣宇.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意見領袖識別研究[J].情報科學,2015,33(4):13-19,92.
[9]許鑫,翟姍姍,姚占雷.學術博客的學科交互實證分析:以科學網(wǎng)博客為例[J].現(xiàn)代圖書情報技術,2015(Z1):13-23.
[10]洪小娟,姜楠,洪巍,等.媒體信息傳播網(wǎng)絡研究:以食品安全微博輿情為例[J].管理評論,2016,28(8):115-124.
[11]韋路,丁方舟.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全球傳播圖景:基于Twitter媒介機構賬號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5(6):91-105.
[12]孫厚權,王冬冬,張俊麗.政務微博的意見領袖分析[J].情報雜志,2014,33(1):124-127,166.
[13]侯筱蓉,余曉林.自媒體用戶關系結構對健康信息擴散的影響及案例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15,59(16):90-95.
[14]陳遠,李韞慧,張敏.基于節(jié)點度測度SNS用戶信息傳播貢獻的實證研究:以騰訊微博為例[J].情報雜志,2014,33(10):159-164.
[15]褚建勛,倪國香,魏燊.基于用戶網(wǎng)絡關系結構的微博社交功能研究[J].情報雜志,2014,33(2):128-131,154.
[16]劉佩,林如鵬.網(wǎng)絡問答社區(qū)“知乎”的知識分享與傳播行為研究[J].圖書情報知識,2015(6):109-119.
[17]雷輝,聶珊珊,黃小寶,等.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網(wǎng)絡傳播主體行為特征研究[J].情報雜志,2015,34(1):161-168.
[18]陳先紅,張凌.草根組織的虛擬動員結構:“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lián)盟”新浪微博個案研究[J].國際新聞界,2015,37(4):142-156.
[19]翁士洪,張云.公共議程設置中微博輿情互動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69(1):109-118.
[20]王旭,孫瑞英.基于SNA的突發(fā)事件網(wǎng)絡輿情傳播研究:以“魏則西事件”為例[J].情報科學,2017,35(3):87-92.
[21]趙金樓,成俊會.基于SNA的突發(fā)事件微博輿情傳播網(wǎng)絡結構分析:以“4.20四川雅安地震”為例[J].管理評論,2015,27(1):148-157.
[22]胡改麗,陳婷,陳福集.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網(wǎng)絡熱點事件傳播主體研究[J].情報雜志,2015,34(1):127-133.
[23]楊輝,尚智叢.微博科學傳播機制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以轉基因食品議題為例[J].科學學研究,2015,33(3):337-346.
[24]洪小娟,姜楠,夏進進.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網(wǎng)絡謠言研究:以食品安全微博謠言為例[J].情報雜志,2014,33(8):161-167.
[25]王晰巍,邢云菲,趙丹,等.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移動環(huán)境下網(wǎng)絡輿情信息傳播研究:以新浪微博“霧霾”話題為例[J].圖書情報工作,2015,59(7):14-22.
[26]吳瑛,李莉,宋韻雅.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中國與國際媒體互引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22(9):5-21,126.
[27]徐寶達,趙樹寬,張健.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微信公眾號信息傳播研究[J].情報雜志,2017,36(1):120-126.
[28]韓有業(yè),馬弋飛.關系視角下的新聞傳播類專業(yè)自媒體學術互動行為研究:基于10家新聞傳播學院微信官方訂閱號2016年內容數(shù)據(jù)分析[J].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6(2):114-121.
[29]閔超,孫建軍.基于關鍵詞交集的學科交叉研究熱點分析:以圖書情報學和新聞傳播學為例[J].情報雜志,2014,33(5):76-82.
[30]邱均平,劉國徽.基于社會網(wǎng)絡和關鍵詞分析的作者合作研究:以國內知識管理領域為例[J].情報科學,2014,32(6):3-7,13.
[31]張洋,謝齊.基于社會網(wǎng)絡分析的機構科研合作關系研究[J].圖書情報知識,2014(2):84-94.
[32]李彪,潘佳寶.再中心化:文化帝國主義視角下全球媒介產品貿易網(wǎng)絡研究:基于全球電影貿易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J].國際新聞界,2014,36(3):77-91.
[33]馬寧,田儒雅,劉怡君,等.基于動態(tài)網(wǎng)絡分析(DNA)的意見領袖識別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8):8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