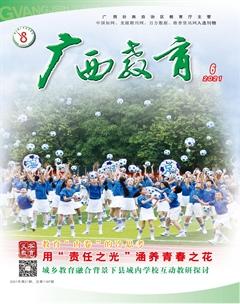“植樹問題”數學模型的廣泛應用研究
李織蘭 李春蓮 徐娟



【摘要】本文針對小學數學教師常把“植樹問題”教成普通的“數學應用題”的現狀,論述引導學生構建“植樹問題”數學模型并廣泛應用該模型的途徑,認為教師可以根據課本中的問題創設情境,滲透對應關系,引導學生構建“植樹問題”數學模型,讓學生經歷“實際情境—畫點線圖—觀察圖形—歸納規律”的過程,運用不同層次的練習,讓學生體驗數學模型的抽象性和廣泛應用性,培養學生的數學致善精神。
【關鍵詞】植樹問題 致善精神 數學建模 小學數學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21)21-0032-03
“植樹問題”因其具有較高教育價值和魅力而被編入幾乎所有版本的小學數學教材。但是,很多小學數學教師把這樣一個魅力無窮的問題教成了一道普通的“數學應用題”,單純引導學生解決“植樹問題”、得到答案,不能將“植樹問題”延伸和演繹,不能把“植樹問題”的解決方法類推到其他問題解決中,未能挖掘“植樹問題”蘊含的豐富的數學思想、數學文化和數學精神。
一、“植樹問題”的教學分析
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教師通常把“植樹問題”設計為等距離植樹,教學流程是把“小路”抽象成一條線段,把“樹”抽象成點,點把線段平均分成若干段(間隔),“探究”后發現“間隔數=路的總長÷間距”;三種不同植樹要求,分成三種情形找間隔數和點數(棵數)之間的數量關系——“點數=間隔數+1”(兩端都種)、“點數=間隔數-1”(兩端不種)、“點數=間隔數”(只種一端),并要求學生熟背這一規律,然后變化問題情境訓練解題技能,使學生面對類似的新情境時能不假思索地機械應用。實際教學效果不盡如人意,學生在解決“樓梯問題”“鋸木頭問題”等過程中屢屢出錯。學生分不清具體問題中的“樹”和“間隔”,不能把“植樹問題”的解決方法與生活中相似的現象進行知識鏈接,導致解題錯誤百出,同時也束縛了學生思維的發展,沒能更廣泛地將“植樹問題”應用在生活中。
經過對原有課堂教學的反思和對教學文獻的分析,解讀課標和小學數學教材,我們達成了以下幾點共識。
第一,重視“模式化”,讓學生弄清楚“樓梯問題”“鋸木頭問題”等都與“植樹問題”有相同的數學結構:“植樹問題”數學模型。以“植樹問題”的現實原型為背景,根據“樹”與“間隔”所呈現出來的內在規律,通過適當的教學手段幫助學生建立“點段關系模型”,這是本節課的關鍵。
第二,“植樹問題”的實質就是“點段關系模型”中的點與段的對應關系。在教學實踐中,強調并要求記憶“兩端都種”“只有一端種”“兩端不種”三種情況相應的計算法則。面對新的類似問題時,多數學生只會機械應用,不能完整無誤地寫出“植樹問題”三種類型的數量關系,部分學生弄反了數量關系中的棵數和段數。就“植樹問題”而言,是否真的就只有“兩端都種”“只種一端”“兩端都不種”這樣三種情況?也許還會存在“由于道路中間有一段是我們學校的大門,在學校大門前(某一段的若干個間隔)不需要種樹”等特殊情況。其實,所謂的三種情形相應的計算規律只是針對具體情況進行的適當變化,學生需要感悟“一一對應”的數學思想,并依據基本模式,通過適當變化以適應各種情況。因此,比有規律地機械應用更重要的是思維的靈活性。
第三,“100米的小路,每5米作為一小段,共有多少段”是小學階段常見的“平均分”模型的常見問題,我們在教學實踐中發現,這種簡單的計算對高年級的學生來說,通過一番“探究”得到“間隔數=路的總長÷間距”顯得多余,因此,我們沒有把它作為知識目標之一。“雙基”不應求全,而應求變。
第四,“植樹問題”不一定都是植樹的問題,建好的“植樹問題”模型要回歸到現實情境,“植樹問題”模型同樣適合于設置公交車站、大路兩旁安裝路燈、樓層與臺階、鐘樓大鐘敲鐘報時、鋸木頭、男女生間隔排列等問題,學生運用模型解決這類問題時,真正的困難是對同模結構的識別——把哪些對象看成“點”,哪些對象看成“段”。
基于此,我們的教學設計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尋找規律走向建構模型,第二階段是從應用模型走向培養致善精神。
二、從尋找規律走向建構模型
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可以描述為:根據建模的目的和掌握的信息(如數據、現象等),將實際問題翻譯成數學問題,用數學語言準確地表述出來。(如圖1)將現實對象的信息加以翻譯、歸納,用精準的數學語言表述對象的內在特征,建立數學模型;再經過求解、演繹,得到數學上的解答;然后經過翻譯再回到現實對象,給出分析、預報、決策、控制的結果;最后,這些結果必須經受實際的檢驗,完成“實踐—理論—實踐”這一循環。
學生在小學一年級學習過比多少,假設在桌面上有一些杯子和蓋子,如果想知道是杯子多還是蓋子多,常用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分別數出杯子和蓋子的數量,比較哪個數大就行了;另一種是將每個蓋子蓋在杯子上,然后看看是否有杯子缺蓋子,或者是否有蓋子剩余,或者剛好既沒有杯子缺蓋,也沒有蓋子剩余。由于第一種方法要數出元素的數目,這對很多情況來說是辦不到的,而第二種方法不計元素的數目也能進行比較,因此第二種方法更具普適性。在數學中,我們選擇第二種方法作為比較“多與少”的標準方法,這種方法蘊含“一一對應”的數學思想。只有讓學生理解了一一對應,他們才能真正明白“植樹問題”數量關系中的“+1”“-1”和“一樣多”的含義。
教師在教學“植樹問題”時,可以根據課本中的具體的問題(如圖2)創設情境,滲透對應關系,構建“植樹問題”模型,讓學生經歷“實際情境—畫點線圖—觀察圖形—歸納規律(點數與段數的數量關系)”,以及逐步加深認識的過程,進而使他們獲得一個清晰的“植樹問題”數學模型:點的個數與小段的段數之間的數量關系。
形式上的抽象性和應用上的廣泛性與是數學所具有的顯著特點,數學的抽象程度越高,數學的應用就越廣泛。正是追求更廣泛的應用,促成了數學的進一步抽象化。因此,我們在教學中將“線段”更一般化為“線”(不一定是線段,如圖3所示),線上的“點”也不一定是等分點。
三、從應用模型走向培養致善精神
教學中,教師首先要引導學生通過畫圖,抽象出實際問題對應的植樹問題模型中的“點”和“段”,再利用具體的“點”“段”的對應關系解決問題;變式練習的設計,要從“近”到“遠”、從低級到高級,不同層次的練習層層推進,增強學生對同模結構的識別能力,發展學生思維,培養學生的致善精神,讓學生體驗到數學模型的抽象性及其應用的廣泛性。
第一題組,教師可以安排一個完全同類的題組(如圖4所示)。第一題的情境不變,“樹”是真樹,只是改變了數量。第二題將“樹”變式成“公車站”。兩題與課本原型完全同模,旨在增強學生用“植樹問題”模型解決問題的熟練度。
第二個題組,充滿生活氣息。如圖5所示,第一題屬于可逆性變式,袋鼠每跳一下的距離是間隔的長度,腳印是“樹”,小路的全長是原型的條件,在這里成了問題。第二題屬于條件性擴展變式,道路的兩側常常被學生忽略。
第三個題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在“植樹問題”數學模型的廣泛應用中受到激勵。第一題是“敲鐘”問題(如圖6所示),我們把看不見卻能聽得見的鐘聲當成了“樹”,相鄰兩次敲響的鐘聲之間的時間成了“間隔”。
第二題是“鋸木頭問題”(如圖7所示):“樹”是鋸口處,這是不容易看見的“樹”;因為題目沒有要求把木頭分成一樣長的小段,所以“樹”不一定是等距離排列,間隔也不一定是相等的。題目還可以改編成:“我交代工人把一根木頭鋸成10段。我走出車間,聽到電鋸響了10次。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但是我已經知道這位工人鋸的木頭不符合我的要求,這是為什么?”以增強趣味性。
第三題的原題是:“一節課有40分鐘,老師擔心來不及講完所有內容,所以設置了手機提醒。上課鈴聲響后,老師的手機每隔5分鐘就振動一次,提醒老師要把握時間。一節課下來,手機要提醒老師幾次呢?”雖然它與課本上的原型類似,但是由于各教學環節所用的時間并不相等,所以這樣的提醒設置對老師沒什么用處。我們進行了如圖8的改編,“線”上的“點”不一定是等分點,也許會有更廣泛的應用。
第四題(如圖9所示)中,梧桐樹是“樹”,相鄰兩棵梧桐樹中間的銀杏樹就不是“樹”了,而是“植樹問題”模型中的“間隔”。因此,“間隔”未必就是“一段”,只是我們可以把它們“畫”成段。教師向學生明確,“植樹問題”不一定是要植樹的,“樹”不僅僅是樹,有時候不是樹卻可以看成“樹”,而有的時候真樹又可以看成“間隔”,這就是“植樹問題”的奇妙。
我們通過改變問題中的已知條件,體現一題多練,通過對比讓學生發現解決“植樹問題”不是簡單地“+1”或“-1”,而是要看清已知條件和所求的問題。
教師要讓學生感受“植樹問題”的無窮魅力,超越具體的感性的解題方法,上升到抽象的思想方法與策略,引領學生建構解決這類問題的數學模型,探究出解決此類問題的“通則”“通法”,激勵學生在日常生活和生產中更廣泛地運用數學模型,從而培養學生的數學致善精神。
【作者簡介】李織蘭(1967— ),女,廣西百色人,在職碩士,副高職稱,現就職于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研究方向為小學數學教育;李春蓮(1977— ),女,大學本科學歷,一級教師,現就職于桂林市臨桂區第三小學,研究方向為小學數學教育;徐娟(1978— ),女,廣西靈川人,大學本科學歷,一級教師,現就職于桂林市靈川縣第三小學,研究方向為小學數學教學。
(責編 秦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