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訴訟路徑下不動產登記的撤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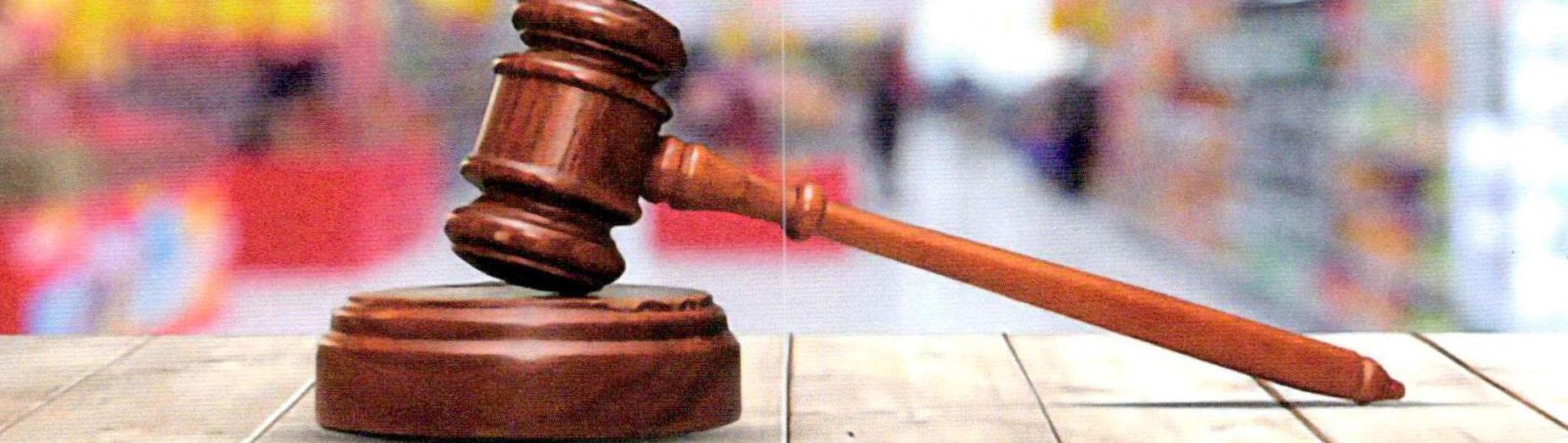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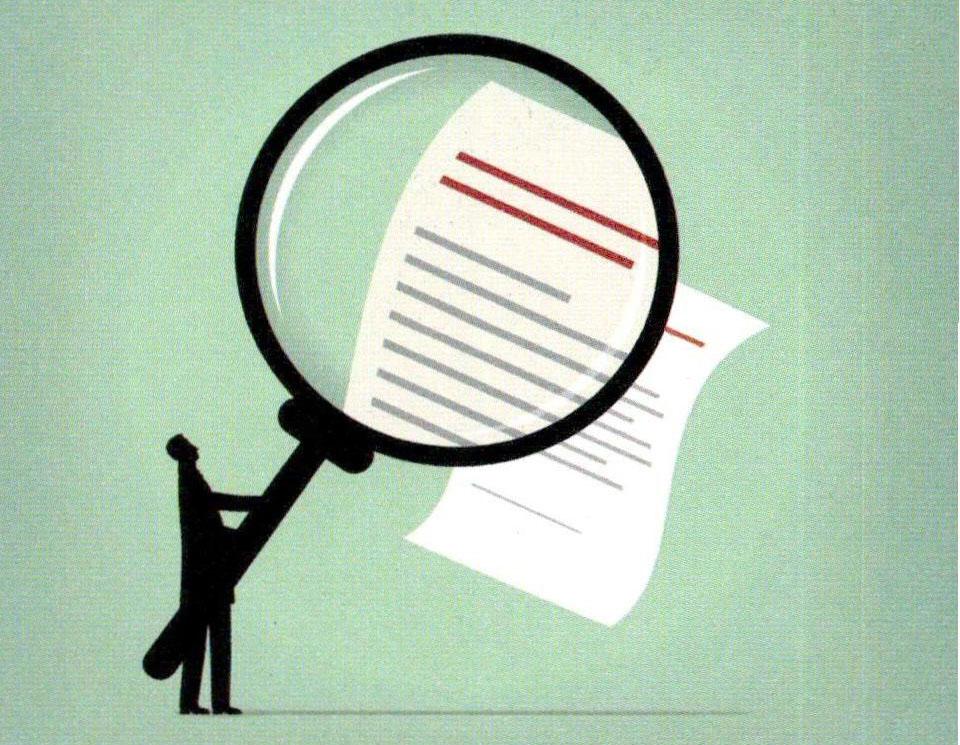
摘要:不動產登記撤銷的訴訟路徑分為“單一的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優先,行政訴訟后置”兩種模式。不同的訴訟路徑對不動產登記撤銷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在《民法典》施行、不動產登記類賠償訴訟突出的背景下,融合行政審判要素和民事審判要素成為大勢所趨。
關鍵詞:不動產登記;訴訟路徑;撤銷;過程有責性;結果違法性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1-9138-(2021)01-0037-41 收稿日期:2021-01-01
作者簡介:史意,南京市不動產登記中心。
1 不動產登記撤銷的不同訴訟路徑——以三個案件為例
申請人尋求司法救濟撤銷不動產登記時,可以直接就行政行為本身提起行政訴訟,也可以對登記行為所依賴的民事原因文件先行提起訴訟,而后再提起行政訴訟。兩種不同的訴訟路徑對不動產登記撤銷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下文即以三個案件為例展現不同訴訟路徑下不動產登記的撤銷。
1.1 單一的行政訴訟
案例一:A、B系夫妻,涉案不動產登記在雙方名下。A訴稱,B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找人冒充A辦理了涉案不動產抵押登記,故要求撤銷抵押登記。庭審過程中,B向法院說明,其找了一名女子假裝夫妻辦理登記,抵押權人C對此并不知情。A提交的鑒定報告亦顯示:“A”的簽名和指紋均不是A所簽所留。法院向A釋明:對作為房屋登記行為基礎的抵押合同效力有異議,應當先行解決民事爭議。A表示,C已就與A、B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提起了民事訴訟,故不再另行提起。
經審理,法院認為,登記機構留存的關于A的照片顯示,冒充A的女子與A在年齡、樣貌上相仿,且其持有A的身份證件,登記機構在依法審查的范圍內已經盡到了審查義務。在抵押合同、借款合同有效,沒有證據證明C取得抵押權屬于非善意取得的情況下,要求撤銷抵押登記依據不足,故駁回訴訟請求[參見江蘇省南京鐵路運輸法院(2017)蘇8602行初999號]。
1.2 民事訴訟優先,行政訴訟后置
案例二:涉案不動產原所有權人為A,B系A之女,C系A之孫。A將涉案不動產出賣給C并辦理了轉移登記。B得知此情況后,申請認定A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法院予以支持。據此,B起訴要求認定《買賣合同》無效并撤銷登記行為,法院支持該訴求,并要求C協助A將涉案不動產恢復登記至A名下。后A去世,B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過戶。執行過程中,C向法院提出:A及其配偶已于多年前辦理遺囑公證,將涉案不動產遺留給C個人所有,法院據此駁回了C的申請。
隨后,B起訴要求撤銷轉移登記及抵押登記。一審判決認為,登記機構已經盡到了合理的形式審查義務,故駁回訴訟請求。二審法院認為,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應作為行政訴訟案件的審理依據,在合同已被確認無效的情況下,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所確認的不動產物權轉讓行為失去了民事權利基礎,故對房屋轉移登記行為的違法性予以確認,但因抵押權人的抵押權構成善意取得,故確認轉移登記行為違法[參見江蘇省南京鐵路運輸法院(2018)蘇8602行初1147號、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蘇01行終272號]。
案例三:A、B系夫妻,涉案不動產登記在雙方名下。A因向C借款,將涉案不動產抵押給C并辦理了登記。B得知后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確認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無效。法院查明,B未與A、C共同至登記機構辦理抵押登記,合同中B的簽名和摁手印系他人所為,故抵押合同無效。在另案中,法院亦認定,他人冒用B的名義簽字并辦理抵押登記,C未盡到審查義務,自身有過錯,主張善意取得的理由不能成立。
隨后,B起訴登記機構要求撤銷抵押登記。法院判決認為:根據民事判決查明的事實,登記機構未對B是否到場進行審查,未充分履行法定職責。抵押登記基于的主要證據已被法院確認無效,合法性基礎已不存在,而C的抵押權亦不構成善意取得,故抵押登記應予撤銷[參見江蘇省南京鐵路運輸法院(2018)蘇8602行初190號]。
2 不同訴訟路徑下不動產登記撤銷的標準——“結果違法性”與“過程有責性”
2.1 “過程有責性”標準
“單一的行政訴訟”路徑采取的是“過程有責性”標準。即以行政機關提供證據的合法性為視角,著眼于登記機構受理、審核、登簿的過程,審查登記機構是否盡到了合理審慎審查的審查義務,如登記機構能夠證明已經盡責,則予以維持;反之,則對登記行為作出否定性評價,而無論登記過程中其他不能歸責于登記機構的明顯致錯因素。
如案例一中,即使能夠明確有人冒充真實權利人辦理登記,但是在民事基礎行為未被確認無效之前,法院仍從登記機構的角度,以常理化標準為要求判定其是否盡到應有的審慎審查義務。
2.2 “結果違法性”標準
“民事訴訟優先,行政訴訟后置”路徑則采取的是“結果違法性”標準。即以民事行為的有效性為前提來評判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一旦作為原因文件的民事行為無效,即認定登記結果有誤,并對登記行為作出否定性評價。至于登記機構是否盡到合理審慎審查的義務的問題,有的法院置之高閣、不予評價,有的則以民事行為的失效直接斷定登記機構未盡審查義務。
如在案例二中,一審法院即堅持“過程有責性”標準,而二審法院則堅持“結果違法性”標準,以登記行為所依賴的民事行為基礎喪失為由,對登記行為作出否定性評價。在案例三中,法院甚至沒有對登記機構的審查義務作具體分析,而是直接以民事行為的違法性否定登記行為的合法性,并認定登記機構未盡合理審慎的審查義務。
3 不同訴訟路徑導致不同審判標準的內在機理
“結果違法性”與“過程有責性”標準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直觀上的沖突,但仔細探究其內在機理,不同的審判標準彰顯了不同訴訟模式的特征以及登記行為的特殊法律地位。
3.1 行政訴訟的審判模式決定了“過程有責性”標準
在行政程序中,一方是擁有強大行政管理職權的行政機關,另一方是勢單力薄的行政相對人。正是由于行政程序的不平等性導致行政審判模式的刻意“矯正”:由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并由行政機關對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負舉證責任,簡單地說就是“審被告”。這意味著,在交織民事、刑事、行政等法律關系的案件中,法院解決的只能是行政糾紛,而民事、刑事糾紛恰恰要留待另外的程序解決。
在不動產登記撤銷案件中,法院與登記機關的審辯關系居于主導地位,其更多的是以登記程序是否履行為出發點,審查登記機構是否盡到合理審慎審查義務,而不論登記材料本身是否真實有效。
3.2 “矯正”行政訴訟模式的局限性為“結果違法性”標準創設條件
以合法性審查為核心的訴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就案論案”的弊端,與公眾的理解和期盼存在落差,使得行政訴訟仍然沒法像醫生處理一個身患多種疾病的病人一樣,讓糾紛得以徹底解決。上述“過程有責性”標準將關注點聚焦于登記機構是否盡到合理審慎的審查義務,容易造成登記程序合法性與結果正確性之間的錯位,與普通大眾關于“合法即正確”的直感相沖突。
正是為了回應行政訴訟模式的弊端,《最高院關于審理房屋登記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確定了民事爭議有限前置的規則、原《最高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條承認法院自由裁量限度內民行一并審理原則。由此可見,無論是分開審理還是合并審理,在審判內里上,均確定了“先民后行”的雛形,使得行政審判吸收參照民事審判結果,從形式正義轉向實質正義功能主義,由“過程有責性”轉向“結果違法性”標準。
3.3 債權形式主義下的不動產登記具有復合性
從各國的規定來看,物權變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義、物權形式主義和債權形式主義。
我國不承認物權無因性理論,而采取債權形式主義。根據《民法典》的相關規定,不動產物權需要“變動原因行為”與“登記”相結合,才能發生物權的效力。一旦原因行為無效,物權變動即喪失了合法性基礎。
當事人提起不動產登記撤銷訴訟,其實質往往是對引起物權變動原因行為的效力存有異議。因此,在民事訴訟解決了物權變動原因行為效力的情形下,行政訴訟即采用“結果違法性”標準。反之,則以“過程有責性”標準直接審理登記機構是否盡到合理審慎審查義務。
3.4 登記行為兼容公、私法性質
對于登記行為的性質,理論界眾說紛紜。有民事行為、行政確認行為、行政事實行為、公私性質混合之說等等。無論如何界定,都不能免除不動產登記公、私混合的特征。一方面,《民法典》第209條關注的重心在于確立物權變動效果和公示方式之間的一般規則,不動產登記是作為特定法律事實對物權狀態所產生的效果而存在的。不動產在法律上的效力取決于物權得喪變更的基礎民事法律關系。另一方面,根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的相關規定,不動產登記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規范登記機構的登記行為。
正是因為公、私法兼容的特性,使得不動產登記撤銷之訴中,“單一的行政訴訟”模式可以運用行政法監督登記行為的合法性;而“民事優先,行政后置”模式可以吸收民事行為的效果并對登記行為進行干預。
4 不同訴訟路徑下撤銷登記類案件審理模式再思考
雖然原《最高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顯現出原因行為與登記行為“一并審理”的法律圖景,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呈現散化特征,其中有民行獨立審理互不影響式、行政附帶民事式、民事附帶行政式等等。而這既無法應對《民法典》的要求,也無法與既有理論實踐相融合。
4.1 《民法典》對撤銷登記類訴訟路徑帶來新挑戰
《民法典》第153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基于此,衍生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型強制性規定的概念區分。
具體到不動產登記案件中,因無權處分而引起的原因文件效力糾紛,不屬于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范疇,并不會被法院直接認定無效。在“比例原則”的指引下,法院可以在承認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認定轉讓方不具有物權轉讓的資格,從而否定物權轉移的效力。但是,此種不發生物權轉移效力的認定究竟在哪一種訴訟模式下進行,《民法典》并未明確。也就是說,法院可能在民事訴訟中認定民事基礎行為有效,但對是否發生物權轉移的效力不予評價。這就為以往“民事先行”模式下的不動產登記撤銷案件帶來了巨大挑戰,更加凸顯出中民行交叉一并審理的迫切性。
4.2 抵押登記撤銷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已然勾滲透民事審理要素
在本登記及抵押登記撤銷同時訴諸法院,而本登記行為已被作出違法性評價時,根據《最高院關于審理房屋登記案件若干問題》第11條的規定,法院需對抵押權人是否善意取得作出相應的評價。雖然“善意取得”制度屬于民事規范的內容,但法律并未強制當事人通過民事訴訟對抵押權人加以評價,而是在行政訴訟中一并審查。此時,行政訴訟已不單單是吸收而是滲透了民事審判要素。
如在案例一中,法院以“沒有證據證明抵押權屬于非善意取得”對善意取得問題作出反向推斷;而在案例二中,直接適用原《物權法》第106條的規定,從“善意”“合理價款”“登記”三方面對抵押登記行為作出正向的、充分的評議,最終維持了抵押登記。
4.3 行政賠償案件亟需法院對登記行為的過錯及結果作出回應
根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的規定,國家賠償確立了“違法原則為主,無過錯原則為輔”或者“違法原則為主,結果原則為輔”的歸責原則體系。
在單一的行政訴訟模式下,“過錯有責性”標準明確了登記機構是否存在主觀過錯,但卻使登記結果處于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因為即使行政行為被維持,當事人仍然可以通過民事訴訟再行提起撤銷之訴。同樣,在先民后行的訴訟模式下,“結果違法性”標準雖然固定了行政行為的結果違法性,但卻忽視了對主觀過錯的回應或者簡單以原因行為的無效認定過錯的存在。此種差異并不利于后續不動產登記類行政賠償的確定與解決。因此,一方面,在先民后行模式下,登記機構迫切希望法院對登記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予以客觀審查和評價;另一方面,重新審視單一行政訴訟模式的局限性,從節約司法資源,回歸訴訟糾紛解決功能本位出發,給予登記結果一次性終極評價,成為回應行政登記類賠償案件的迫切要求。
5 小結
在不動產登記撤銷訴訟中,不同的訴訟路徑形成了不同的撤銷結果。國家機關應當回應實踐需要,融合不同模式下的審判標準,如此才能回應《民法典》的時代要求,真正做到“案結、事了”。
參考文獻:
1.何海波.行政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16
2.王洪亮.不動產物權立法研究.法律科學.
2002.02
3.楊偉東.不動產登記的公法思考.清華法律評論.2006.12
4.吳光榮.論不動產權屬確認的程序選擇——以不動產登記之法律性質為中心.行政法叢論.
2012.02
5.章劍生.行政不動產登記行為的性質及其效力.行政法學研究.2019.05
6.孫憲忠.不動產登記基本范疇解析.法學家.
2014.06
7.沈巋.國家賠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