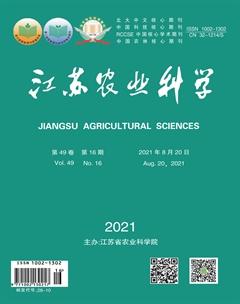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的技術集成及經濟效益分析
孫益豪 金濤 張家宏



摘要: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是一種高效利用稻田時間和空間開展黑斑蛙和泥鰍生態健康養殖的新型種養模式。闡述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的田間配套工程建設、綠色種養、綠色營養、綠色防控等技術措施,并運用投入-產出分析法,比較稻-蛙鰍共作與常規稻作的經濟效益以及投入的物質與服務費成本項(苗種投入、物料投入、租賃服務以及設施防護)。結果表明,稻-蛙鰍共作模式與常規稻作種植產投比分別為1.98、1.12,前者經濟效益較高;物質與服務費成本項中,雖然稻-蛙鰍共作投入較高,但化學農藥及化肥實現零投入,具有良好的生態效益。因此,推廣該綠色種養模式,對提高稻田資源利用率和農產品質量、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大有裨益。
關鍵詞: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效益分析;推廣
中圖分類號:S966.3;S964.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1)16-0088-05
我國稻漁綜合種養歷史悠久,江浙一帶稻田養魚歷史可追溯到2 000年前[1]。近年來,稻漁綜合種養模式已成為農業農村部首推的綠色生態發展、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內容。隨著我國生態農業的發展和人們對優質食品需求量的增加,稻田綜合種養已由“稻魚共生”發展成“稻蝦、稻蟹、稻鴨”等多種模式[2-6]。稻蛙、稻鰍2種模式也有過相關報道[7-8],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拓發展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該模式是將水稻種植與黑斑蛙和泥鰍有機結合,充分利用稻田資源進行縱向養殖,實現化學農藥和化肥零投入,耗水量減少,收獲稻、蛙、鰍農漁產品,達到“一田三收”的效果,進而使收益達到最大化。江蘇省高郵市界首鎮大昌村處于江蘇省里下河中部地區,境內江、河、湖、溝水系縱橫交錯,水資源極其豐富,種植業和養殖業發達[9]。依托里下河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發展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在稻田田間工程、水稻種植、蛙鰍飼養技術等方面經驗豐富,并取得顯著成效,以期為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推廣提供實踐與推廣依據。
1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田間工程
1.1 稻田選擇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宜選擇土質較好(土質疏松肥沃,土壤質地為保水、保肥性好的壤土和黏土、周邊無污染源)、水源充足且水質良好、排灌水系配套完善、交通方便的稻田。
1.2 稻田改造
稻-蛙鰍綜合種養生產基地應適合全程機械化操作,尤其是水稻耕作、插秧和收割等。每個種養單元約為0.667 hm2(圖1),一般長度為100 m,寬度為66.7 m,正中間開溝寬度為2 m,深度為 0.9 m,四周設置青蛙投餌平臺,寬度為1.5 m。
1.3 設置護網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生產基地應有4類網。一是基地上空設置天網,防止魚鷹、白鷺、夜鷺、池鷺等鳥類侵害捕食黑斑蛙和泥鰍。二是每個種養單元四周設置防逃網,防止黑斑蛙、泥鰍逃逸,或蛇、水老鼠等敵害生物入侵;稻田四周設置的防逃網網片顏色以淺色為宜[10]。三是基地四周設置防盜網,防止人為盜捕。四是進排水口設置金屬濾網,防止黑斑蛙和泥鰍外逃[11]以及天敵入侵。
2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三綠”生產技術體系
2.1 綠色種養
2.1.1 稻-蛙鰍綜合種養時空耦合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的水稻種植、黑斑蛙與泥鰍養殖的時空耦合見圖2。
2.1.2 蛙鰍苗投放技術
2.1.2.1 泥鰍品種選擇及投放選 泥鰍品種為臺灣泥鰍,生長速度快,抗病能力強,養殖周期短。養殖鰍苗為基地人工繁育鰍苗,繁苗時親鰍雌雄比例為10 ∶ 1。泥鰍苗投放時間一般選擇在6月中旬、秧苗栽插返青扎根后,于早晨或傍晚投放,盡量避開氣溫較高的正午。鰍苗投放密度約15萬尾/hm2,規格為4~5 cm,且體質健壯,無病無傷。投放鰍苗前應用3%~5%食鹽水浸浴3~5 min。
2.1.2.2 黑斑蛙品種選擇及蛙苗投放 選擇品質優、產量高、抗病能力強的黑斑蛙品種[12],將選擇經過馴食的黑斑蛙作為育苗的種蛙,雌雄比例為 1 ∶ 1。蛙卵到蝌蚪一般需要55 d左右,從蝌蚪到成蛙上岸一般需要60 d左右。蛙苗在6月下旬選擇晴天無風時投放[13],投放密度約為45萬只/hm2,并多點均勻投放。蛙苗應體質健壯,無病無傷。投放蛙苗前同樣使用3%~5%食鹽水浸洗3~5 min。
2.1.3 水稻種植技術
2.1.3.1 水稻品種選擇及種子處理 根據江淮地區的氣候特點,水稻品種應選擇優質、高產、抗逆性強、熟期適中且植株偏高的當地主推品種[14],如優質雜交秈稻豐優香占、粳稻品種南粳5718、金香玉1號等;播種前應進行水稻種子處理,主要是曬種和鹽水選種,然后用1%生石灰浸種消毒,避免把病菌帶入大田[15],也可以采用種子包衣劑進行包裹處理。
2.1.3.2 水稻育秧、栽插 采取水稻缽苗育秧栽培技術,通過精量播種、控水和化控技術,培育出有完整缽球、秧齡長、秧苗壯、抗逆性強、適宜稻-蛙鰍田大苗機插的缽苗[16-17];鰍苗、蛙苗投放之后進行水稻栽插。采用機插秧方式,水稻株行距控制在33 cm×23 cm,基本苗3~4株/穴,移栽密度約為11.85萬穴/hm2。寬行寬株有利于稻田通風透氣,便于蛙、鰍在稻田活動。
2.2 綠色營養
充分將稻-蛙鰍農田生態系統內的生物質、有機質、礦物質等內生資源進行循環利用,根據種養動植物的營養需求,合理投入適量飼料就能滿足稻-蛙鰍的營養問題,進而實現零化肥投入的目標。本研究的食物鏈為黑斑蛙捕食稻田中的螟蟲、稻螟蛉、蝗蟲、飛虱、蚜蟲等害蟲以及人工投喂的飼料;泥鰍以黑斑蛙的蛻皮、水體中的水蚯蚓、水虱、搖蚊、小型甲殼類動物、植物碎屑、有機物質[18]、稻花[19]等為食,以及部分人工投喂的飼料;黑斑蛙和泥鰍排泄的糞便以及殘飼成為水稻生長的有機肥料,同時黑斑蛙和泥鰍在稻田中穿行活動起到耘耥松土和除草的作用,有利于促進水稻健壯生長。
2.2.1 黑斑蛙投喂技術 黑斑蛙投喂堅持“四定”原則,要求定時、定位、定質、定量。一般每天 06:00、17:00各投喂1次[20],投放至投餌臺上,每天總投飼量以前1 d剛剛吃完的飼料量為參考值,并以晚上投飼為主,約占每天總投入量的70%,全生長期總投飼量為14 625 kg/hm2。選用40%蛋白的專用膨化配合飼料,每20 kg飼料中須添加多維 50 g、大蒜素50 g、三黃散80~100 g、護肝散50 g以促消化[21]。黑斑蛙養成規格一般應達24~26只/kg。
2.2.2 泥鰍投喂技術 稻-蛙鰍生產中原則上不投喂泥鰍專用飼料,但需每天將投餌臺上過剩的蛙飼料清掃至稻田中供泥鰍食用。泥鰍養成規格一般應達24~30條/kg。
2.2.3 水位調控 稻-蛙鰍綜合種養田中水稻的水位調控基本符合“淺—深—淺”的規律。前期培育25 d以上秧齡,株高30 cm左右的秧苗機插,插秧后稻田水位控制在10 cm左右,深水活棵控制雜草滋生。隨著秧苗返青并快速生長,田面水位應逐步增加。夏季7、8、9月水位控制在30~40 cm,其間須要換新水1次/周,每次換1/3,晚排晨灌,保持水質清新和水位相對穩定。同時,深水位也方便蛙、鰍在稻田中捕食生長。在水稻成熟期,稻田水位降至環溝內,對黑斑蛙、泥鰍進行集中捕撈。待田面瀝干硬實后,進行水稻機械收割。
2.3 綠色防控
2.3.1 水稻病蟲害綠色防控
2.3.1.1 農業防控 水稻選用抗蟲、抗病品種;采用機插秧方式,利用寬行、寬距的栽插特點,保證稻田通風透光;稻-蛙鰍田冬季休耕曬田。
2.3.1.2 物理防控 稻-蛙鰍綜合種養區域四面圍網,上方再加蓋天網防控鳥害,進水口、排水口安裝80目以上的鐵絲或尼龍濾網,防控水生敵害生物幼苗和卵粒隨水流進入稻田;安裝頻振式殺蟲燈,誘殺螟蟲和稻飛虱、稻蝗等遷飛性害蟲。4 hm2安裝3臺殺蟲燈,調節太陽能光控開關,一般燈亮7~8 h/晚;在田中放置黃色膠黏害蟲誘捕器(簡稱黃板),以此來誘殺稻薊馬、稻蚜、稻飛虱等多種害蟲。一般插置黃板300~450塊/hm2,將黃板懸掛于水稻上部15~20 cm處。
2.3.1.3 生物防控 構建稻-蛙鰍互利共生種養食物鏈系統,利用黑斑蛙捕食稻縱卷葉螟、二化螟、三化螟、稻螟蛉、稻飛虱、稻蝗等稻田害蟲和蛙鰍的耘耥踐踏以及取食除草。同時,黑斑蛙和泥鰍在田中跳躍和穿行游動,會震落稻株上的害蟲被蛙鰍取食。生物農藥防治則用32 000 IU/mg蘇云金桿菌可濕性粉劑1 500 g/hm2防治稻縱卷葉螟,用75%三環唑可濕性粉劑300 g/hm2+10%井岡·蠟芽菌(井岡霉素2%和800 000 IU/mg蠟樣芽孢桿菌)懸浮劑750 g/hm2防治稻瘟病、稻曲病、紋枯病等[14,17]。
2.3.1.4 生態防控 (1)性誘滅蟲。利用性誘劑誘殺或干擾害蟲交配。一般稻-蛙鰍田安插性誘捕器 45個/hm2,連片設置,誘芯15 d左右換1次,誘捕器距離地面約1 m[17]。(2)香誘滅蟲。香根草不僅具有水土保持、護坡作用,還是控草性植物。香根草體內能散發出獨特的香味,將稻螟雌成蟲吸引到草上產卵,螟蟲在香根草上的產卵量是水稻的4倍左右,且香根草分泌出活性物質對螟蟲的卵有毒殺作用,孵化出的幼蟲在香根草上不能完成生活史[22]。在栽種稻-蛙鰍田四周田埂上可有效防控害蟲。
2.3.2 蛙鰍病害綠色防控 對于蛙鰍病害的防控,要堅持“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蛙鰍養殖密度較大,應加強養殖溝內的水質管理,防止水質過肥。如發現泥鰍浮頭、受驚或日出后仍不下沉,應加注新水并做好消毒工作[20];正確使用鰍、蛙病害防控菌劑,如經常使用EM菌等生物菌劑調節水體菌相平衡,控制有害病原菌孳生;在飼料中添加用于內服的藥品如土霉素、嗯喹酸、磺胺嘧啶、磺胺甲唑等,有利于防治黑斑蛙紅腿病、偏頭病及肝膽病,以及泥鰍車輪蟲病、赤鰭病、爛鰭病、打印病、寄生蟲病等[21];還要清除池邊雜草,保持養殖環境衛生,及時打撈處理死亡的鰍、蛙等。
2.3.3 其他日常管理 每天堅持巡田,查看水稻、蛙鰍等生長狀況,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并采取應對措施;仔細巡察稻田四周圍網、防盜網以及架設的天網,對損壞部分及時修補,防止蛙鰍天敵入侵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和蛙鰍逃逸;在大雨天氣時重點做好防洪、防逃工作[23];黑斑蛙、泥鰍養成時用不同的地籠分別捕撈,并及時出售。
3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經濟效益分析
3.1 經濟效益對比分析
試驗地點位于江蘇省高郵市界首鎮大昌村生產示范基地。在稻田綜合種養中,水稻單作作為對照組,以1 hm2進行效益分析,稻、蛙、鰍的成本投入以及產出見表1。
在稻-蛙鰍共作與常規稻作的經濟效益比較中,成本投入項目包括物質與服務費、用工費、土地成本。稻-蛙鰍共作模式中,物質與服務費占總成本的86.0%,用工費占總成本的7.6%,土地成本占總成本的6.4%。在水稻單作中,土地成本占比最大,占總成本的58.9%;物質與服務費占總成本的32.4%,用工費占總成本的8.7%。稻-蛙鰍共作模式下,物質與服務費投入較高,約為水稻單作的25倍,屬于高投入。
在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下,5個月的養殖周期內投入蛋白為40%的人工配合飼料 14 625 kg/hm2,即可平均收獲水稻6 232.5 kg/hm2、黑斑蛙 11 293.5 kg/hm2 和泥鰍2 979 kg/hm2。而水稻單作種植可平均收獲水稻10 012.95 kg/hm2。按照市場價格普通稻谷售價為2.7元/kg;由于在稻-蛙鰍種養模式下水稻采用原生態種植,不使用化學農藥以及化肥,稻谷的市場價格售價為 6.5元/kg,青蛙的售價為31.0元/kg,泥鰍的價格為16.5元/kg。稻-蛙鰍種養模式下可獲利 217 259.55元/hm2,投入與產出比為1 ∶ 1.98;水稻單作模式下,水稻可獲利2 858.25元/hm2,投入與產出比為1 ∶ 1.12。稻-蛙鰍種養模式下產出稻谷、成蛙和泥鰍3種農漁產品,前期高投入、后期高產出,相比當地單一水稻種植收入增加且增收效果顯著。
3.2 物質與服務費成本項的比較
在稻-蛙鰍模式生產中,物質與服務費的成本項包括苗種投入、物料投入、租賃服務、設施防護。其中,物料投入中的漁藥費為鰍、蛙病害防治藥品的總費用;設施防護投入包括基礎設施費、稻田防治器具費。在基礎設施中,田間工程、防護網、投餌臺等設施費用按照5年(其中地籠按照2年)折舊費來計算成本投入,在稻田防治器具中有性誘劑、殺蟲燈、黃板,其中殺蟲燈設施同樣按照5年折舊費來計算成本投入。該種養模式下,物料投入開支最大,以飼料費最高,約占物質與服務費成本項的 1/2,其次是苗種費,以蛙苗費最高,約占物質與服務費成本項的三成,鰍苗費遠低于蛙苗費。水稻單作模式中,以物料投入和租賃服務的開支較高,物料投入中以化肥和農藥費為主,租賃服務又以育秧費及機插秧費為主,與之相比,稻-蛙鰍模式實現化肥零投入(表2)。
4 小結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中,對于溝坑占比等有明確的技術指標和要求,應嚴格按照標準建成較科學合理的稻-蛙鰍田。該模式田間工程的設計中,溝和投食臺累計占田塊總面積的近10.2%,符合國家稻漁綜合種養規范中提出10%的要求。在黑斑蛙、泥鰍2種水產生物養殖過程中,對于蛙、鰍飼料投喂、病害防控等技術要求較高,農戶對蛙、鰍養殖技術相對缺乏。稻-蛙鰍種養模式成功與否,技術是關鍵。該模式比水稻單作種植模式增收效益明顯,但在前期生產過程中飼料和蛙鰍苗費投入費用所占比重大。飼料方面,應改善黑斑蛙投喂技術,在滿足黑斑蛙食量基礎上盡可能節省飼料投喂量來降低成本;苗種方面,黑斑蛙、泥鰍市場的供不應求是導致苗種成本價格上升的主要原因。雖然該模式有一定的可復制性,但其他地區受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影響以及農戶經濟條件制約,須進一步研究在其他地區推廣的適應性。在大力推廣這種新型高效綠色種養模式下,應加強對農戶稻-蛙鰍種養技術專業知識的培訓,提高生產管理水平,打造稻-蛙鰍農漁產品特色品牌,以進一步提高農民的收入。
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效益顯著。一是經濟效益,稻-蛙鰍共作既可以有效利用土地資源,又做到“一水兩用”“一田三收”,本研究的凈利潤是水稻單作的數十倍以上,據有關文獻報道,是稻鰍共生模式的4.5~5倍[24]。二是生態效益,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生產中,化肥和化學農藥零投入,可以避免農業面源污染,使稻田生態環境得以修復,且生產出綠色健康的農漁產品可以滿足大眾消費需求,同時還可以保護野生泥鰍和黑斑蛙的種群繁衍,維護生態平衡。三是社會效益,稻-蛙鰍綜合種養模式用工量多、可復制性強。開展該綠色種養模式,能夠調動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吸引青壯年勞動力返鄉創業,帶動剩余勞動力就業,增產增收致富,促進鄉村振興。
參考文獻:
[1]游修齡. 稻田養魚——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典型之一[J]. 農業考古,2006(4):222-224.
[2]李昕升,王思明. 江蘇稻田養魚的發展歷史及生物多樣性分析[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139-144.
[3]Zhang J H,Bi J H,Zhu L Y,et al. Key techniques of an ecological pattern “planting rice in one season and breeding red swamp crawfish in three seasons” for green production in Lixiahe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J].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7,18(8):1406-1409.
[4]吳 俊,朱凌宇,張家宏,等. 江蘇里下河地區1稻2鴨共作模式生產技術[J]. 浙江農業科學,2017,58(9):1616-1617,1625.
[5]江 洋,汪金平,曹湊貴. 稻田種養綠色發展技術[J]. 作物雜志,2020(2):200-204.
[6]王強盛,余坤龍,李婷婷,等. 水稻-克氏原螯蝦共生綠色種養的效應分析[J]. 江蘇農業科學,2021,49(1):77-81.
[7]韓洪波,李星星,趙譜遠,等. 稻蛙綜合種養模式技術分析、存在問題與發展趨勢[J]. 中國水產,2018(3):83-84.
[8]李艷薔,晏 群. 稻鰍共生種養模式試驗研究[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8,39(5):54-60.
[9]張家宏,朱凌宇,王守紅,等. 江蘇里下河地區“四水”生態種養綠色生產技術[J]. 湖北農業科學,2018,57(1):24-26.
[10]陳 俞,陶賽峰,朱 梁. 蛙稻生態種養模式的實踐和探討[J]. 上海農業科技,2016(3):139-140.
[11]劉 靜. 稻蛙共生種養技術[J]. 湖南農業科學,2013(24):59-60.
[12]徐 曼,鄧正春,顧振華,等. 稻蛙綠色生態種養技術及效益分析[J]. 作物研究,2020,34(4):384-387.
[13]蔣 靜,郭水榮,陳 凡,等. 稻蛙共生高效生態種養技術[J]. 中國水產,2016(4):73-75.
[14]張家宏,葉 浩,朱凌宇,等. 江淮地區“一稻三蝦”綜合種養綠色生產技術[J]. 湖北農業科學,2019,58(8):110-113.
[15]魯艷紅,廖育林,聶 軍,等. 稻-蛙生態種養技術模式研究與展望[J]. 湖南農業科學,2017(3):74-76,80.
[16]郭小鷗,余聰華,薛曉波. 不同育秧方式對機插水稻生長發育及產量的影響[J]. 農業科技通訊,2019(9):68-70.
[17]張家宏,王桂良,黃維勤,等. 江蘇里下河地區稻田生態種養創新模式及關鍵技術[J]. 湖南農業科學,2017(3):77-80.
[18]張華東. 稻鰍立體種養 糧魚穩產增收[J]. 當代水產,2012(2):66-67.
[19]陳 豪,全堅宇,朱文榮,等. 稻鰍連作綜合種養生產技術探索[J]. 農業開發與裝備,2019(2):227-228.
[20]楊衛明,李建勛. 稻鰍生態種養技術[J]. 水產科技情報,2014,41(5):252-254.
[21]楊 萍,李 亮,李尚書,等. 稻田輕簡化高效生態立體種養——稻蛙鰍模式[J]. 農業開發與裝備,2019(1):182-183.
[22]魯艷輝,鄭許松,呂仲賢. 水稻螟蟲誘殺植物香根草的發現與應用[J]. 應用昆蟲學報,2018,55(6):1111-1117.
[23]馬本賀,王海華,左之良,等. 稻蛙鰍共作立體生態種養試驗[J]. 水產科技情報,2019,46(5):264-267.
[24]榮朝振,孫守旗,蘇鵬飛. 稻鰍綜合種養試驗[J]. 科學養魚,2019(7):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