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省的知名度“杠桿”是什么?
譚保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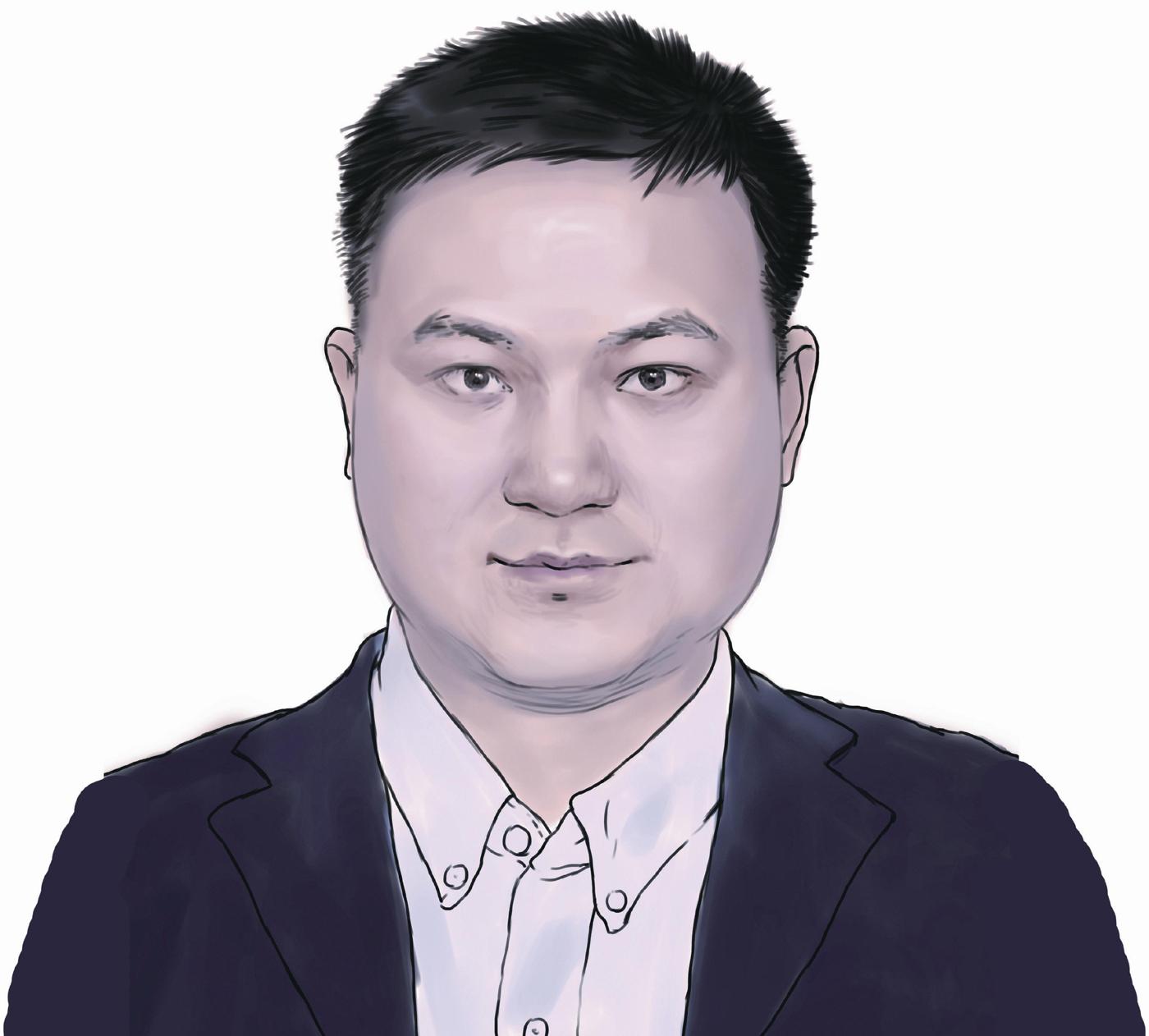
在中國的省級行政區中,有兩個“西”總是缺乏存在感,一是江西,二是山西。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鄰近的省份并不比兩個“西”的經濟要發達多少,但知名度卻要高很多。湖南就要比江西的辨識度大很多,你知道湖南人嗜辣如命,卻不知道江西人吃辣比湖南人還要厲害。此外,陜西、河南也要比山西的曝光率高很多。
為什么會有這種知名度差異?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人口的多寡和地域的大小,會影響知名度。在給定的一個“人均出新聞”的概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省份取相同的概率)之下,那么人口多的省份,自然曝光率就會高,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湖南人口為6600萬,而江西人口只有4500萬,差了不少。同樣,河南人口9900萬,陜西3900萬,而山西最少,只有3500萬。
地域面積的大小也差不多是這個道理。在“每平方公里出新聞”的同一個概率之下,面積大的省份,曝光度自然高。在這方面,江西和山西同樣吃了虧,它們地域面積都不算大。
第二個原因可能更重要,江西和山西都沒有“核心城市”,這讓它們缺乏吸引全國網民關注的重要支點。特別在重慶、成都和鄭州等一大批“網紅城市”不斷崛起的時代,把知名城市為支點,對提升一個區域的知名度和整體形象來說,太重要了。長沙之于湖南,西安之于陜西,鄭州之于河南,無不說明了這個道理。但江西和山西,暫時還沒有這種支點。
2020年,江西的第一大城市省會南昌,GDP只有5700億,而湖南第一大城市省會長沙有1.2萬億。再看山西,其第一大城市省會太原,GDP為4100億,而鄰省省會西安和鄭州分別達到了1萬億和1.2萬億的水平,差距不小。
地域知名度是一個經濟現象,也是文化現象,研究它,有利于理解我們中國人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再看人口,長沙、西安和鄭州早已破千萬,成為“特大城市”,而南昌和太原的人口分別是600多萬和500多萬,和前面幾個超級省會相比,存在“代差”。
不過,以上兩個“原因”很大程度已經是一種“結果”,因為人口多寡和城市對資源的集聚程度是由很多客觀條件決定的,比如自然條件,經濟地理的歷史變遷等。
從宋朝到明朝,江西都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之一,手工業非常發達,這里的景德鎮生產著世界上最富有美感的瓷器奢侈品。經濟發達的物質基礎,自然也哺育了眾多優秀人物,在唐宋八大家里,江西人就有曾鞏、歐陽修和王安石三個,有點半國才子都是江西人的感覺。
到了近代,海運興起,江西作為南北要沖,長江水運中心的優勢地位迅速下降。同時,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快速發展,以及武漢作為近代工業中心之一的崛起,開始對江西產生強大的虹吸。于是,江西輝煌不再,一些江西人自嘲“不東不西,不是東西”,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山西的輝煌歷史更加綿長久遠。戰國七雄里面,山西一個地方就產生了韓趙魏三個強國,盡管它們后來把都城和統治中心外遷,但山西是它們在文化和宗族上的龍興之地。在明清兩朝,晉商更成為一個奇跡。他們的興盛時間橫跨明初到晚清的六七百年時間,比徽商更有歷史的持久力。
然而,山西多山的地理條件,也決定這個地方無法像河南那樣形成大規模的農耕區,因此人口數量方面必然吃虧。同時,帶有晉商基因的山西人也并不排斥奔走四方,行商致富的生活方式,并不會固守在桑梓之地。種種條件,決定了山西不會有鄭州和西安這樣的超級中心城市。
地域知名度是一個經濟現象,也是文化現象,研究它,有利于理解我們中國人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