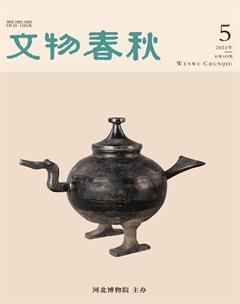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襲變化與商周族群的文化認同
雒有倉 黃端勝
【關鍵詞】金文族徽;西周;商周族群;文化認同
【摘要】通常認為,西周金文族徽是商代晚期族氏名號的沿襲,事實上,西周金文族徽還存在許多變化:一是族徽地域分布中心轉移,二是族徽銅器數量由增轉減,三是族徽種類減少,四是人名、地名、官名性族徽增加,五是族徽功能與性質有所變化。正確認識西周金文族徽的這些變化,對于深入認識當時周人銅器上出現殷商文化標記的族徽與日名,大量殷遺族氏分散遷移各地與周人族群融合,以及西周中晚期殷遺族徽、日名顯著減少與周文化的認同等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文族徽與商周族群認同研究”(批準號:17BZS038)研究成果
西周時期,金文族徽作為殷遺族氏和商文化的重要標記,在各階段的青銅器上長期存在,其間出現了一些明顯變化,深刻體現著商周族群的文化認同與融合。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學者們多側重于對殷遺的遷移、管理及身份地位等進行討論[1—4],少見對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襲變化與商周族群的文化認同的研討[5—8],本文不揣谫陋,試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這一問題略作分析,敬請專家學者教正。
一、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襲
從族徽銅器出土情況來看,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襲大致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殷商大族的族徽銅器出土地點較分散。如前述冉族的西周銅器分見于河南洛陽,陜西長安、寶雞、鳳翔,山東臨朐,湖北荊州等地;戈族的西周銅器分見于陜西涇陽、長安,河南洛陽,湖北隨州等地;子族的西周銅器分見于河南鹿邑、洛陽,山西曲沃,山東滕州等地;舉族的西周銅器分見于山東費縣、長清,陜西長安、扶風,北京房山等地。各地墓葬多見族徽銅器單獨出現,或族徽銅器在該墓地出土銅器中占據多數,說明西周時期的殷商大族成員多被分散遷移至不同地域。另一種情況是殷遺中小族氏的族徽銅器出土地點往往集中在某一個地區。如山東滕州前掌大墓地的商代晚期墓M17、M129、M213出土銘“史”銅器3件,而同墓地的西周早期墓M11、M13、M18、M21、M30、M34、M38、M40、M41、M45、M110、M120、M121共出銘“史”銅器60件[10]:208—333,說明史族不僅是從商代晚期延續至西周早期的族氏,而且一直居住在滕州前掌大附近未曾遷移。
從金文族徽的類型看,一些商代晚期常見的族徽形式在西周時期依然存在。以族徽“子”為例:
(1)“子”單獨出現或與父祖日名聯綴,見于商代銅器有子鼎(集成1042)、子觚(集成6525)、子爵(集成7316)、子卣(集成4732)以及子父丁鼎、子父戊簋、子父庚爵、子祖己卣、子祖癸觚、子祖辛爵(集成1596、3186、8584、4894、7085、8343)等,見于西周銅器有子鼎、子簋、子爵、子觶、子壺(新收549、1852,集成7320、6021,近出645)以及子父乙鼎、子父辛爵、子父丙觶、子父乙盉、子祖辛盉、子祖丁觶(集成1534、8593、6248、9340、9337,銘圖10396)等。
二、西周金文族徽的變化
西周初年,伴隨著舊王朝覆滅、新王朝建立,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結構發生了較大改變。首先,關中地區的豐鎬取代了安陽殷墟成為新的政治中心,關東地區的不少殷遺貴族因受周人統治者懷柔安撫,遷居岐周或宗周任職為官,服務于周王室。其次,周公東征之后營建洛邑,將參與“三監之亂”和懷有對抗意圖的殷頑民遷居成周,并駐守八師加以集中監管。再次,武庚叛亂平定后,周王室通過大規模分封構建地方統治體系,將大量殷遺族氏分散遷移至齊、魯、晉、宋、燕等地,成為各諸侯國統治土著居民的重要依靠力量,并在較大范圍內形成了周人與殷遺、土著“三結合”的族群結構,促進了不同血緣群體之間的政治融合。以上三方面政治環境的改變,不僅使得殷遺族氏長期居住一地的血緣聚居狀態有所改觀,而且促進了商周族群之間的融合,使西周金文族徽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
(一)族徽地域分布中心的轉移。從族徽銅器的出土地點看,商代晚期的金文族徽以安陽殷墟為中心,地域分布以今河南省為主,山東省也有較多分布,而西周早期的金文族徽則以成周、宗周、岐周三點一線為中心,地域分布主要見于成周所在地今河南洛陽地區,關中豐鎬遺址所在地今陜西長安縣,周原遺址所在地今陜西岐山、扶風縣乃至鳳翔、寶雞一帶(詳見拙稿《西周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與商周族群的政治認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待刊稿)。這種情況應是當時政治中心自東向西轉移,殷遺族氏大量西遷的結果。從近年考古發掘材料來看,西北地區的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發現有腰坑和殉狗的殷遺民墓葬以及“薛侯”等甲骨刻辭[13,14],而南方的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則出土19種徽識類青銅器[15]242,這些情況說明,西周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實際上不限于王畿附近地區,在王畿之外的四土之地也有廣泛分布,地域范圍比商代晚期進一步擴大。
(二)族徽銅器數量的變化。商代晚期族徽銅器十分常見,據我們統計,在已著錄的有銘銅器中,現存商代晚期族徽銅器約有5300余件,而西周的族徽銅器共有3300余件。這種情況說明,西周時期的殷遺族氏銅器數量少于商代晚期,總體上呈下降趨勢。然而,如果分階段觀察,就會發現有不同情況存在。據嚴志斌統計,殷墟三、四期共有族徽銅器1660例[16],這個數據即使加上不能分期斷代的1200余件族徽銅器,共計2860余器,仍略少于《銘圖》《銘續》《銘三》三書著錄的西周早期族徽銅器數量2950件。可見,與殷墟三、四期相比,西周早期的族徽銅器仍然呈繼續增長的趨勢。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與西周早期的殷遺族氏分散遷移,不斷促使族徽傳播地域擴大、使用人群增多有關。然而,自西周中期以降,族徽銅器數量明顯減少,見于《銘圖》《銘續》《銘三》著錄的西周中期族徽銅器僅285例,西周晚期族徽銅器的數量更少,僅存105例。可見,西周中晚期的族徽銅器數量急劇減少,漸趨消亡。這種情況當然并非是由于殷遺民滅亡,而是殷遺族氏因受周文化影響拋棄族徽不用,認同于周文化并融入周人族群的反映。
(三)族徽種類的變化。西周早期的金文族徽種類與商代晚期相比,雖然在數量上有所增減,但總體上變化不明顯,所見共1089種,約與商代晚期的族徽種類數量相當。然而自西周中期開始,許多殷遺族氏紛紛棄族徽不用,金文族徽種類明顯減少,所見僅110余種。到西周晚期,金文族徽已不常見,所見僅20多種。金文族徽種類的以上變化,是周文化后來居上的反映,也是殷遺民拋棄族徽不用而融入周人族群的體現。
(五)族徽功能與性質的變化。殷商時期,金文族徽除常見于青銅器外,也常見于甲骨文作人名、地名、族名[17],學界稱之為“三位一體”。這是因為族徽所代表的族氏不僅是一個血緣團體,而且由于長期居住一地,族氏名實際上已成為地域性血緣團體的代名詞,故有“胙土命氏”的政治含義。西周時期,由于商王朝統治秩序被推翻,殷遺族氏的地位普遍下降,族徽已不再具有“胙土命氏”的政治功能,而主要作為殷商族群表示同族血緣關系的符號而存在,從而與不用族徽的周人形成了較明顯的區別。因此,從性質上看,商代的金文族徽所代表的大多為血緣與地域相結合的政治集團,具有表示血緣關系與地緣政治的雙重含義。而西周時期,由于殷遺族氏大多被分散遷移各地,隸屬于封地諸侯等各級貴族,并按“周之宗盟,異姓為后”[18]原則納入了周人建立的宗法秩序,因而其金文族徽多屬單純表示血緣關系的父系家族名號,沒有“胙土命氏”的實質內涵,從而成為殷遺民表示血緣關系的文化符號。顯然,這種文化符號在西周時期的存在乃至消亡,實際上體現著殷遺民逐漸融合于周人族群并認同于周文化的一種歷史過程。
三、商周族群的融合與文化認同
西周時期,殷遺族氏與周文化的融合認同,較明顯地體現在金文族徽與日名使用等方面。關中西部的先周遺存及周初墓葬少見腰坑、殉人、殉牲,“絕少見到日名、族徽銅器”[19],說明周人原本不使用族徽與日名,而現存周人銅器銘文表明,“族徽文字是殷人的專利,周人則棄而不用”[20]。因此,通過對族徽與日名的考察,可以認識商周族群在西周時期相互融合與文化認同的情況。
西周早期,姬姓周人貴族使用族徽與日名較典型的例證,是近年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考古發掘出土的兩件西周早期銅器[15]220,114:一件是M27出土的伯生盉(銘圖14705),蓋、器同銘:“伯生作彝。曾”;另一件是M111出土的曾侯鼎(銘圖續121),蓋、器同銘:“曾侯作父乙寶尊彝”。前者“曾”位于銘尾,應為族徽,后者“父乙”之稱為日名。按曾姬壺、曾子原簠、曾侯輿殘鐘銘文中“曾”為姬姓,新見楚王鼎(隨仲嬭加鼎)和新出隨仲羋加編鐘以及同名匕、缶的銘文表明“曾”即“隨”,為漢東地區的姬姓諸侯封國[24]。另M111同出犺簋銘文有“南公”的記載,“南公應是南公適,曾國應是南宮適的封國,其族姓為姬姓”[25]。可見,前述伯生盉上的族徽“曾”和曾侯鼎上的日名“乙”,應是西周早期曾國姬姓貴族對于殷商文化初步認同與融合的表現。進一步來看,葉家山曾國墓地先后出土有19種族徽,說明當時有大量的殷遺民隨遷。而M1出土3件銅鼎銘“師作父癸”“師作父乙”,這類“師”之稱謂“除象師雍父這樣稱父號者外,大體上可視為殷代以來的舊族”[26],即為殷遺“以官為氏”的族徽,說明隨遷的殷遺民中有成周八師的成員。而姬姓曾公室貴族之所以使用族徽與日名,應是受隨遷殷遺和商文化影響的結果。從該墓地年代稍晚的M2、M28、M65出土的多件曾侯器上均無日名,亦不見將“曾”置于銘尾的族徽用法來看,姬姓曾公室對日名和族徽的使用僅限于最初受封的一段時期內,而這種暫時性的使用最終被姬姓周人貴族排斥和拒絕。這種情況的出現,顯然與商周文化此消彼長,周文化后來居上,占據主導地位有關。
與周人貴族個別、零星地使用族徽和日名不同,西周早期的殷遺貴族多見使用族徽與日名。例如:
臣高鼎(銘圖2020):“乙未,王賞臣高貝十朋,用作文父丁寶尊彝。子。”
從西周墓葬銅器來看,在禮制層面也有商周族群相互融合認同的明顯反映。例如西周早期的殷遺墓葬以河南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為代表,出土有盤、盉等器,已開西周盤盉固定配置的先河,但銅器的形制大多具有濃厚的商代遺風,禮器組合既有爵、觚、觶、尊等酒器48件,也有鼎、簋、鬲、甗等食器29件,銘文多見族徽與日名,既有濃厚的商文化特征,又有明顯的西周因素,發掘者從出土銅器所見酒器、食器所占比重出發,認為這種情況應屬“重酒重食的組合”[28],即為偏重于商禮重酒而又有周禮重食并存的體現。山東滕州前掌大M11、M18、M21、M38、M120[10]551—562及M308、M309、M312[29],北京房山琉璃河M50、M53[30],湖北安居羊子山M1、M4[31],以及陜西涇陽高家堡M4、M1[32],長安張家坡61M106[33]、67M87[34],寶雞竹園溝M7、M8[35]等墓葬,都有類似的情況存在。但在同時代的其他墓葬中往往又有食器比重超過了酒器的現象,這應當是重食的周代禮制在商周文化融合過程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的反映。從西周中期的墓葬來看,在一些有腰坑和殉犬的墓葬中,隨葬的銅器往往有族徽與日名,有些墓葬還出土數量相等的青銅酒器與食器,如1978年陜西扶風齊家村M19出土食器5件(鼎2簋2甗1)、酒器5件(爵2觶1尊1卣1)[36],1975年扶風莊白村墓葬出土食器6件(鼎3簋2甗1)、酒器6件(壺3爵2觶1)[37],可見當時的殷遺后裔仍遵行商代禮制,但同時已經接受了周代禮制。西周晚期,在能夠確定為殷遺后裔的墓葬中,有些銅器不見族徽,但出土有銅酒器,銅器組合以食器為主,如河南洛陽白馬寺M21出土食器3件(鼎1簋2)、酒器2件(壺2)[38],銅器組合中的食器數量超過了酒器;有些墓葬不見腰坑,出土銅器僅有食器,酒器多為仿銅陶器或明器,如1992年陜西長安馬王村M92出土青銅食器4件(鼎2簋2)和仿銅食器陶甗1件,酒器則為仿銅陶器5件(爵2觶2尊1)[39],器物組合具有明顯的重食特點。這些墓葬的規格都不是很高,墓主人都屬于中下層貴族,說明在西周晚期的殷遺中下層后裔中,代表商文化的飲酒器已經退出了禮制范疇,而代表周禮的食器的比例大幅提升,表明周文化最終得到了殷遺后裔族群的廣泛認同。
————————
[1]李宏,孫英民.從周初青銅器看殷商遺民的流遷[J].史學月刊,1999(6).
[2]杜正勝.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四分.臺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3]宮長為,徐義華.殷遺與殷鑒[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4]張禮艷.灃西地區殷遺民的社會地位及其變遷[J].考古與文物,2013(2).
[5]錢唯真.商周金文中族氏徽號的因襲與變化研究[D].臺中:東海大學,2007.
[6]張懋镕.試論商周之際字詞的演變: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一[G]//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227—244.
[7]張懋镕.商周之際女性地位的變遷: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二[G]//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245—269.
[8]張懋镕.金文所見商周之際諸兄地位的變遷: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三[G]//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270—274.
[9]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元年[M]//阮元校刻本影印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2134—2135.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1]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6—211.
[12]雒有倉.商周家族墓地所見族徽文字與族氏關系[J].考古,2013(8).
[13]李政.商周考古的重要發現: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發現西周早期諸侯級墓葬,鑄銅、制陶作坊等重要遺跡[N].中國文物報,2017-12-05(2).
[14]馬強.周王朝西北邊疆的新發現: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J].大眾考古,2020(2).
[15]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6]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分期斷代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82—83.
[17]雒有倉.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綜合研究[M].合肥:黃山書社,2017:67—91.
[18]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隱公十一年[M]//阮元校刻本影印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1735.
[19]張懋镕.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說的考古學證明[G]//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223—250.
[20]張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說[J].考古,1995(9).
[21]司馬遷.史記:周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6.
[22]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徐家橋郭家莊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69,71,81,35.
[23]楊寬.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8—130.
[24]張懋镕.李學勤與“曾國之謎”[J].江漢考古,2020(2).
[25]黃鳳春,胡剛.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J].江漢考古,2014(5).
[26]白川靜.西周史略[M].袁林,譯.徐喜辰,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79.
[27]張懋镕.試論商周之際字詞的演變: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之一[G]//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西部考古:第4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05.
[29]滕州市博物館.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發掘報告(1998—2001)[G]//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岱考古: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227—375.
[3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M]//蘇天鈞.北京考古集成:1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0,23.
[31]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青銅器[J].文物,2011(11).
[32]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國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5—31,69—106.
[33]趙永福.1961—62年灃西發掘簡報[J].考古,1984(9).
[3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1967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J].考古學報,1980(4).
[36]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J].文物,1979(11).
[38]張劍,蔡運章.洛陽白馬寺三座西周晚期墓[J].文物,1998(10).
[3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鎬隊.1992年灃西發掘簡報[J].考古,1994(11).
〔責任編輯:成彩虹〕
————————
①據王長豐統計,商周金文族徽共有2168種,見氏著《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9—636頁。這一統計數據包括同族徽的不同字形,實際上現存商周金文族徽共約1900多種。
②冉族銅器數量根據《銘圖》《銘續》《銘三》著錄統計,下文戈、舉、子族銅器統計依據相同,不一一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