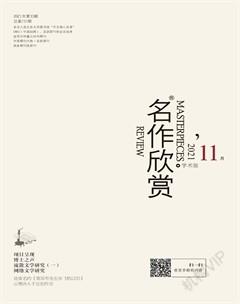精微寫作與暗示美學(xué)的內(nèi)涵與外延
摘 要:女性主義是本文的一大主題,通過暗示的美學(xué)等手法綜合展現(xiàn);通過分析場景營構(gòu)、人物結(jié)構(gòu)、情節(jié)細(xì)節(jié)等等,多角度探幽索微,從而將女性主義分解開、溶解在生活中;又一次提取并分析,在此過程中體驗(yàn)女性意識的覺醒,社會問題的深刻命題,以文學(xué)形態(tài)、美學(xué)體系,進(jìn)行多維度解讀。《雨中的貓》通過對貓、天氣、鏡子等多個(gè)意象的巧妙選取,在象征符號中傳達(dá)主題、營造文學(xué)藝術(shù)感;采用敘事性寫作結(jié)構(gòu),借助人物交互帶動小說節(jié)奏。“冰山原則”“零度寫作”,文本在虛幻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穿梭,始終充分展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語境下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關(guān)鍵詞:女性主義 場景 暗示 對比 審美
引言
海明威在時(shí)代女權(quán)主義批評的時(shí)代波瀾與視角下,著眼于女性這一群體,賦予了女性在社會中的符號意義。他不愿為妻子兒女所累,卻不得不關(guān)注到妻子的訴求之后,其內(nèi)心產(chǎn)生了震蕩。在自身親身經(jīng)歷與感受的基礎(chǔ)上,作為一個(gè)問題的關(guān)注者、故事的陳述者、后續(xù)的見證者,海明威用文學(xué)審美的特征獨(dú)特地展現(xiàn)一個(gè)來源于生活,融入文本,又高于社會生活與個(gè)人靈魂的審美境界。
一、場景設(shè)置與文本主線的契合
(一)關(guān)于貓的心理暗示
1.“貓”的概念
“Anyway, I want a cat,…I want a cat.I want a cat now.”顯然,“a cat”其實(shí)并沒有明確的所指,而是將“貓”概念化,成為一個(gè)廣泛意義上的能指。從貓的出現(xiàn)、對貓的尋找、最終戲劇化地失而復(fù)得,“貓”這一意象始終承擔(dān)了豐厚的意蘊(yùn)。太太要的真的是一只貓嗎?是那種生物學(xué)意義上、具有一定特征的生物嗎?也許并不是。而且,她最初要找尋的、消失在雨里的那只貓也并非店主送給太太的那一只。再換一個(gè)思路想,太太真的非貓不可嗎?這里,我們關(guān)注到了場景的觸發(fā)。
2.“貓”的觸發(fā)機(jī)制
文本的推進(jìn)與迭起需要一個(gè)運(yùn)作的觸發(fā)機(jī)制,一只貓,“蜷縮在一張?zhí)手晁木G色桌子下”,便一下子刺激感應(yīng)了太太心間幽微難言的心思。她產(chǎn)生了外界與自身的映照,自己與貓?jiān)谑篱g處境相通的一個(gè)點(diǎn)被觸發(fā),形成了一個(gè)由點(diǎn)及面、蔓延擴(kuò)散的結(jié)構(gòu)。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的態(tài)度令她心寒與無奈,妻子想要掙脫卻無所適從,同情那只蜷縮身子的小貓時(shí),一直以來的對自己生活境遇的憐憫也被觸發(fā)了。“想要貓”,成了一個(gè)磁場強(qiáng)烈的心理暗示,這種暗示漸漸像現(xiàn)實(shí)蔓延,成了有些不合邏輯卻無比真實(shí)的“一地雞毛”,將文本語言的增生推進(jìn)帶進(jìn)了另一個(gè)大場景,即現(xiàn)實(shí)生活。
暗示的審美哲學(xué),朦朧似夢的意境創(chuàng)造,回歸現(xiàn)實(shí)的必然,無一例外地彰顯了海明威小說中的美學(xué)特征。
(二)場景鏡頭式鋪排
1.大環(huán)境的營構(gòu)
開頭的一段場景描寫也是暗示的一種體現(xiàn)。第一句寫室內(nèi),十分簡練,“留宿的美國客人只有兩位”,將人物角色和范圍設(shè)定基本劃定。“丈夫”“太太”,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縮影,二元對立的基本劃分,精度濃縮,排除了寫作過程中的其他雜質(zhì)。“一路上碰到的人一個(gè)都不認(rèn)識”,文化排斥、個(gè)體在社會中各個(gè)場域必然存在遭遇的孤立現(xiàn)狀,映射出真實(shí)的心理。這前后兩句便很巧妙,濃縮的旅館場景,僅僅寫旅客的居住分布狀況,“小世界”基本定型,讓朦朧感有了一定的環(huán)境依托,不至于過于散亂而弱化了審美意味。接下來的描述中,滲透了文化身份認(rèn)同的問題,比如“意大利人老遠(yuǎn)趕來瞻仰戰(zhàn)爭紀(jì)念碑”“青銅制的”“在雨里閃閃發(fā)亮”——意大利人的文化歸屬感,融入了該地的自然風(fēng)光與旅游景色,不和諧中透露著深刻的合理性,為后面轉(zhuǎn)筆提供文本可能性。
2.點(diǎn)面結(jié)合與收束的美感
這時(shí)寫到一位“侍者”,在布局的側(cè)面落筆,作為一位“觀察者”,將整個(gè)場景收入眼中,即收入整個(gè)描寫的畫面構(gòu)造,收束全段,將一切象征意義整合而歸一。
作者的景物描寫轉(zhuǎn)向了紀(jì)念碑前的廣場,車輛已然開走,形成了空蕩蕩的場景布局。這一切意象都指向一個(gè)狀況——這一對夫婦來此游玩的不合時(shí)宜。這里有一種暗中的排斥感,不該出四人僅僅作為游客,而處于這樣的文本架構(gòu)中,存在的扭曲感與怪異感隱隱鋪墊,是作者潛意識流動而又故意為之的。虛幻的不安感受與似真似隱的話語場域,為后文的不和諧因素埋下了潛在筆觸。
有人說海明威對場景的寫作有如攝影,鏡頭轉(zhuǎn)換流暢又不失條理感,色彩調(diào)取忽為黑白單色、忽為靚麗彩色,布局構(gòu)造巧妙,點(diǎn)面結(jié)合得當(dāng),靜態(tài)中有動態(tài)元素活性,“攝影”式寫法強(qiáng)化藝術(shù)美感,象征意味隱而彌顯。
在文中結(jié)尾處,“廣場上已經(jīng)上燈了”,寓意為事情有了一定階段性的結(jié)束,文本已經(jīng)完成了情節(jié)上階段敘事的任務(wù),一切已然掃明了基本的軌跡;首尾交疊相生,喻感寫作自一而終。
(三)“雨”的意象之包容力
1.“雨”的意象傳統(tǒng)
進(jìn)而,突然出現(xiàn)了一個(gè)元素“雨”。在中外文學(xué)作品傳統(tǒng)中,“雨”一直是一個(gè)朦朧意味的意象,有著極大的審美包容性。不論是唯美的意境營造,還是在文中承擔(dān)文本角色,都有著豐富的情感內(nèi)涵和審美價(jià)值,即兼具描述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特征。比如中國古典詩詞之中,尤指柳永填詞,“雨霖鈴”訴盡相思離別之苦楚,在雨中執(zhí)手相看淚眼,催發(fā)蘭舟,細(xì)雨朦朧,更添前方不定、未來難許之惆悵之意。“細(xì)雨”“暴風(fēng)雨”僅僅作為意象本身特征而有不同色彩的意義,有著文學(xué)意味中的強(qiáng)弱明暗,并沒有其包容力大小的區(qū)分。正如《榮格與分析心理學(xué)》中榮格所說:“每一個(gè)意象都凝聚著一些人類心理和人類命運(yùn)的因素, 滲透著我們祖先歷史中大致按照同樣的方式無數(shù)次重復(fù)產(chǎn)生的歡樂和悲傷的殘留物。”在海明威另一部作品《永別了,武器》中,同樣出現(xiàn)了“雨”這個(gè)意象,充分含露了人類心理中的災(zāi)難與命運(yùn)意識,巧妙借用了個(gè)體對外界召喚感知的心理力量,賦予了其幸福、苦難、希望、重生等多重元素,自原始?xì)v史中獲取了暗示的情感審美與意義象征。
2.“雨”的節(jié)奏感
那么在《雨中的貓》一文中,“雨”帶動了情節(jié)發(fā)展的語言節(jié)奏,包蘊(yùn)了太太心中的迷茫悵惘、對現(xiàn)實(shí)的回避與痛苦、丈夫心知卻漠不關(guān)心……這一切正如貓兒在雨中的迷失匿跡,以致在結(jié)尾,似乎故事仍在隨著雨聲不歇,而給不出一個(gè)確切明白的最終一筆。
二、人物信息交互中的內(nèi)在與外延
(一)“太太”之女性總覽
在作者筆下,“妻子”這一人物有著剛?cè)嵯酀?jì)的性格特點(diǎn)。她一面輕聲細(xì)語地喃喃而道,一面又意愿強(qiáng)烈地想要得到“這只”貓。在海明威筆下的女性,總是有著相通的地方。但總體筆調(diào)依舊朦朧,沒有直接明確指向,重點(diǎn)放在了“話語場域”的營造,不斷通過文本的重復(fù)、暗示、模仿,形成作品集中分散又有序統(tǒng)一的審美秩序與文學(xué)規(guī)范。
比如在《在士麥那碼頭上》中,孩子們已經(jīng)死去,母親們卻只能在半夜發(fā)出一陣“亂叫亂嚷”——無法忍受的心理痛楚只能通過接近原始的方式、沒有邏輯的聲音來發(fā)泄。縱覽海明威在《在我們的時(shí)代里》所書寫的女性,本文中的女士已然是較為傳統(tǒng),對時(shí)代回應(yīng)較輕微的一位了。因此在本文中起筆,作者所打理的語言更為朦朧,也更加溫和地觸及生活。
(二)男性的對應(yīng)角色
1.“動”與“靜”
動,具有活脫性和生命力;靜,具有節(jié)奏感和明晰性。不同于景色畫卷形態(tài)的動靜對比的寫作,《雨中的貓》體現(xiàn)在兩個(gè)基本對立的主體身上,體現(xiàn)在言語與行動之中。并且兩個(gè)主體的動靜狀態(tài)趨于極端——太太從見到貓兒開始,就一直在布置的場景中行動,尋找、問詢;回到房間里依舊在絮絮不歇地說話、梳妝等等,大動態(tài)下細(xì)節(jié)也足夠到位。然而丈夫趨于“靜”的極端,在床上的位置沒有改變,最多的是看書、放下書、繼續(xù)看書,始終都是在床上讀書的狀態(tài)。盡管差異對立尖銳,不過其中流暢的敘事增強(qiáng)了二元對立的流動感,讀來更覺語韻的“和而不同”,以及兩個(gè)對立主體的“同而不和”。
2.“鏡子”旁的微交流
值得注意的有這樣一個(gè)情節(jié)——太太坐在梳妝臺鏡子前,以及與丈夫幾句簡短的對話。“鏡子”里,是太太美麗的容顏,鏡子里和鏡外的人和事,有著虛與實(shí)的象征意義(在下一部分中有相關(guān)分析)。丈夫夸贊了她的美貌,放下書去靜靜欣賞,然而妻子一提到貓,以及其他希望擁有的銀器、蠟燭、新衣服等等。在這里分析人物的心理,可以看到太太抓住了丈夫?qū)⒛抗饨K于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機(jī)會,在努力做著改變現(xiàn)狀的嘗試,最終還是失敗了,丈夫又回歸了書中的虛幻世界。丈夫的關(guān)注點(diǎn)象征了“二戰(zhàn)”之后人們精神空虛的現(xiàn)狀,只關(guān)注表面容顏的美麗,忽略精神實(shí)質(zhì)的東西。這是二人的語言互動以及眼神的短暫交互與傳遞,一切又遁入了寂靜與空虛。
3.疊踏的藝術(shù)美感
本篇小說中,事物選取后重復(fù)疊踏的藝術(shù)手法值得注意。“床”在文中出現(xiàn)了七次,“書”在文中出現(xiàn)了八次,這些是關(guān)于丈夫的;“貓”在文中出現(xiàn)了二十二次,是關(guān)于妻子以及與店長和侍女配角的互動的。在人物互動中,這幾個(gè)重復(fù)出現(xiàn)的意象依舊蘊(yùn)含著豐滿的意味,環(huán)繞緊隨著人物的動向與情節(jié)的迭生推動,象征與暗示隨著文本,更新著更多的要素。
(三)微妙的心理觸動
從女性心理來看,女性的心理感觸本就是細(xì)膩的,長期在丈夫的漠視與冷落中,太太的內(nèi)心便更為敏感。當(dāng)她見到老板“站起身,向她哈哈腰”時(shí),作者也是巧妙地將老板的人物設(shè)定為一位“老頭”,親切感進(jìn)一步拉深了。在筆者看來,這是一次親切心靈碰撞的過程,而并沒有逾越的成分。老板的人物設(shè)造本質(zhì)上的目的便是與丈夫形成反差。在這之后,太太對于老板有了更多細(xì)致微妙的心理感受和變化,比如再一次遇到時(shí),太太“剎那間覺得自己極其了不起”,這又是一次女性意識在心理狀態(tài)中的外現(xiàn)。這些便屬于人物心理的外延模式,延伸向更廣闊的意蘊(yùn)與主題。
(四)巧妙的敘事學(xué)架構(gòu)
在敘事學(xué)上,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利用“符號矩陣”解剖敘事文本中的人物深層關(guān)系和潛在主題意蘊(yùn),體現(xiàn)了對立與和諧的哲學(xué)觀念。行動和欲望相對立,逐漸生發(fā)出了非行動和非欲望,四個(gè)人物圍繞著這個(gè)符號模型展開了敘事。太太對現(xiàn)實(shí)幸福生活的精神訴求、關(guān)于貓的一系列行為活動,丈夫?qū)ΜF(xiàn)實(shí)的逃避、虛無的念想,老板友善的舉動與心靈世界,侍女的普通大眾化心理與行為,都在符號化敘事的框架中,彼此溝通流轉(zhuǎn),形成大事件本身與外延。
在人物的交互中,摻雜了暗示、象征、重疊、相通、相悖等各種元素,但每個(gè)人物的交集與個(gè)體外延都?xì)w屬于一個(gè)敘述框架與審美體系之中,有著“和而不同”的美學(xué)特征。
三、主題在文本中的明暗顯現(xiàn)
(一)“鏡子”意象之明暗意義
在《雨中的貓》里,突出了一種虛與實(shí)的寫法。我們且從文中細(xì)節(jié)處分析——鏡子這一意象的虛與實(shí)的象征義。太太在梳妝鏡前仔細(xì)端詳自己的后腦勺與脖子,抱怨自己的發(fā)型不好看,自己“厭膩透了”,而丈夫不支持她改變發(fā)型,并且膚淺庸俗地贊揚(yáng)她的美貌。當(dāng)妻子提出更多美好幸福生活設(shè)想后,他又躲回了書本后面的虛幻世界。在太太眼中,鏡子里的自己被生活的枯燥乏味打磨得粗糙不堪,都產(chǎn)生了厭膩?zhàn)约旱那榫w。迎合丈夫的審美令她不悅,男孩子一般粗短的發(fā)型,映照著男性的扭曲審美和女性的無奈與鏡中借以寄托的生活期許。
“鏡子里”和“鏡子外”有著生活本質(zhì)的哲學(xué)思考,在文學(xué)中增添了敘事環(huán)節(jié)描寫,因而有了文學(xué)型的樣態(tài)。
西方文學(xué)中鏡子這一意象有著獨(dú)特的含義,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著有關(guān)鏡子的比喻:“你拿一面鏡子四面八方地旋轉(zhuǎn),你馬上就會創(chuàng)造出太陽、月亮、大地等以及我國想要的一切。”在《雨中的貓》中,鏡子里是女性對自己內(nèi)心的發(fā)掘的鑰匙,一個(gè)自我意識潛在的入口,因此年輕的美國太太注視著鏡子里的自己,自我觀念慢慢氤氳而出,逐漸成形,又受多因素影響,不斷更新重生。
女性主義的主題在這里達(dá)到了高潮,可以理解為壓抑后的迸發(fā),盡管是以溫和的、生活化的方式。
(二)虛構(gòu)世界的濃縮
1.“看書”的背后
另外,虛幻的心理集中體現(xiàn)在丈夫身上,“看書”成了一種逃避的形態(tài),看到妻子的美貌后,在邊界處略有動搖,仍停留于表面;當(dāng)妻子一提及現(xiàn)實(shí)生活,小貓、蠟燭、新衣服……他又回到了靡然的生存狀態(tài),麻木、漠然,對外界的感知遲鈍而弱化。
在這種家庭環(huán)境下,更有利于女性自我意識的滋生與泛濫,男女權(quán)利問題回溯到了歷史傳統(tǒng)的位置。
2.虛幻與現(xiàn)實(shí)寫作
我們之前提到了海明威的“零度寫作”,語言成為一種“透明”的工具,不急于宣泄作者的真情實(shí)感,而是返回事件發(fā)生的原點(diǎn),讓筆下的人物以自然、最符合人性規(guī)律地走一遍故事的歷程。因此他的寫作才能做到貼近人與事物的本質(zhì),最真實(shí)地觸動到讀者的意志。
(三)“冰山”與“零度”
根據(jù)“冰山原則”(表現(xiàn)給讀者僅為很一小部分,而冰山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可見于海平面之上),海明威并不在意于鋪展開廣闊的描寫,而是選取起普通的一隅,傾注自己的思想,使之富于意義。不在于直露的言辭,而傾向于“零度”的寫作筆調(diào)。含蓄不露,溫和無言。作者也是在革新中尋道路,與現(xiàn)實(shí)相知,不愿涉身過多,這些也與作者自身的性格、經(jīng)歷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
在寫作過程中,通過兩人的互動,事情發(fā)展的過程,太太情緒的變化,配角、景物的出現(xiàn)與助推,環(huán)境的營構(gòu),使得主題在文中體現(xiàn)的力度明暗交錯(cuò),更加有抑揚(yáng)的節(jié)奏感,彰顯文學(xué)藝術(shù)性。
四、結(jié)語
根據(jù)艾布拉姆斯的“文學(xué)四要素”的理論,文學(xué)的四個(gè)要素分別為——作品、世界、作者和讀者。我們就這四要素加以總結(jié)。
海明威本身擁有矛盾的性格,在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時(shí),他面臨著妻子和一個(gè)新生生命的壓力,因而他的情感有著較為復(fù)雜微妙的變化,在文中妻子和旅店老板的互動和心理狀態(tài)中略微可見。
《雨中的貓》賦予了朦朧的美學(xué)元素和深刻的象征意義。將文學(xué)秩序有意地模糊化,暗示了逃避與追求、行動與欲望的異化文學(xué)空間。由于篇幅短小,暗示的細(xì)節(jié)分布較為密集。海明威在文中人物的刻畫較為溫和,純粹的合理敘事,沒有強(qiáng)烈批判的意愿展露,使得全篇合理地在生活場景中發(fā)生。
這篇文章中暗含著語論的傳播,在那個(gè)時(shí)代堅(jiān)定地踏下一個(gè)文學(xué)領(lǐng)域中女性主體意識的渴望和覺醒的印章,在文學(xué)意識流的催動和時(shí)代語境的變遷下,給予女性問題一個(gè)開放式的結(jié)尾,有意期待文本接受者給出自己的答案。作者給予了讀者一個(gè)開放性的結(jié)尾解說。這也正體現(xiàn)了作者試圖與讀者達(dá)成溝通的意愿。
在20世紀(jì)的美國,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硝煙給人民的心理帶來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人們借助膚淺浮華、刺激感官的方式排解著內(nèi)心的空虛和憂愁。也正是這樣一個(gè)多元共生的裂縫中,女性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渴望自由,追求主宰的現(xiàn)實(shí)的幸福生活;呼吁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鼓勵(lì)女性在話語上爭取自身權(quán)利,增強(qiáng)群體的競爭力。
文學(xué),正是要在時(shí)代與人性的裂縫中,尋求那些變與不變。
參考文獻(xiàn):
[1] 甘文平.“夢”的建構(gòu)、消解與幻滅——《白象似的群山》與《雨中的貓》的主題比較[J].四川外語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02 (3) :26-29.
[2] 姜淑芹, 嚴(yán)啟剛.雙重對立:生態(tài)女性主義視閾中的《雨中貓》[J].四川外語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 (5) :24-27.
[3] 海明威.雨中的貓[A].海明威短篇小說集[C].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4] 鳳翔.雨中的貓:女性境遇的一個(gè)重要隱喻[J]. 張家口師專學(xué)報(bào),2002 (4).
[5] 張龍海.海明威短篇小說的主題思想和美學(xué)價(jià)值[J].當(dāng)代外國文學(xué), 1998 (2).
作 者: 鄭軼文,陜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在讀本科生。
編 輯: 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