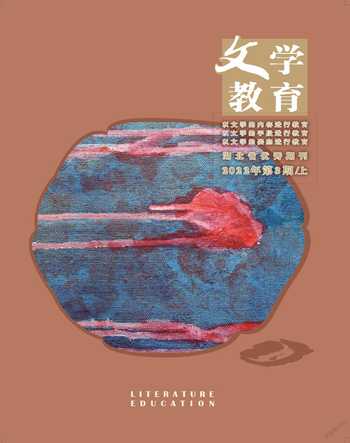霍夫曼童話中童年創傷主題分析
黃志杰
內容摘要:霍夫曼是德國著名浪漫主義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許多社會問題,其中童年創傷是霍夫曼作品中熱衷的主題。霍夫曼在他的作品中透露的對童年創傷的觀點和態度,在當代社會也有廣泛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擬運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論探析霍夫曼《胡桃夾子》和《沙人》兩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揭示主人公童年創傷形成的原因及暗恐心理的發展過程,并對比分析導致主人公毀滅性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欲以闡釋霍夫曼作品中暗含的克制暗恐心理的方法,剖析霍夫曼在作品中透露出的對待童年創傷的態度和觀點,為兒童心理創傷的治療給出建議。
關鍵詞:霍夫曼 童年創傷 暗恐 治療
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是19世紀德國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兼具浪漫與現實、塵俗與幻境、恐怖與和諧”(周芳、童真,2017:128)。
縱觀霍夫曼的作品,童年創傷一直是霍夫曼熱衷的主題,童年創傷會導致心理上的暗恐。暗恐是一種驚恐情緒,看似突如其來,但卻可以追溯到心理歷程史上的某個源頭。因此,不熟悉的其實是熟悉的,非家幻覺總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弗洛伊德在《暗恐》一文中闡述的“暗恐/非家幻覺”,是“壓抑的復現”(Freud,1970:246)的另一種表述,所謂“非家幻覺”是“家和世界位置對調時的陌生感”,或者說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開始時期的一種狀態”(趙一凡,2006,122)。熟悉的與不熟悉的并列、非家與家相關聯的這種二律背反,就構成心理分析意義上的暗恐(童明,2011:106)。當童年時期的某些恐怖記憶在現實生活中再次被喚醒時,就會再次出現恐懼心理。
一.故事設計的暗恐
霍夫曼在作品中構建童年創傷主題時設計了許多暗恐場景,營造出暗恐效果。弗洛伊德認為,作家是營造暗恐效果的專家;他給故事設置一在個現實的背景,假裝要給讀者真實,卻又在敘述過程中重現很多超現實的因素,通過這一設計產生并增強暗恐效果(Freud,1970:273)。霍夫曼就是這樣一個營造暗恐效果的專家,很多人認為霍夫曼的童話是“現實主義童話”(Thalmann,1952:475),就像《沙人》和《胡桃夾子》兩篇作品故事都是發生在普通的家庭之中,敘述的內容也大都是日常生活,但是在這兩篇童話中都存在著很多不真實的因素,正是這些不真實因素構成了文中的暗恐。
《胡桃夾子》整個故事限制在小女孩家的范圍之內,這種背景環境的設定讓讀者感覺故事貼近生活從而相信故事的真實性。但故事中胡桃夾子的出現給故事增添了童話色彩。圣誕夜晚上出現了七頭鼠王,胡桃夾子和鼠王進行激烈交戰,瑪麗把自己拖鞋扔向了鼠王,隨后昏厥。瑪麗醒來的時候媽媽正在床邊照料。故事這時一下子從童話拉回到了現實,“霍夫曼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多重人格,由于外部世界的巨大變化和不可信性,造成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在夢幻世界和現實生活之間的混亂”(李香,2012:305),這種“家”和“非家”情節、夢幻世界和現實生活的并列增強了全文的暗恐效果。
教父把胡桃夾子小人修好并且給瑪麗講了關于咬胡桃的小先生戰勝老鼠王后的童話故事,聽后瑪麗的病奇跡般的好了。而后幾天晚上作者又描寫了老鼠王步步緊逼欺負瑪麗的情景,整個敘述過程也是現實和幻想的交叉融合。最后胡桃夾子為保護瑪麗戰勝了老鼠王,并帶瑪麗去到了童話王國。整個故事的敘述都是熟悉和不熟悉、“家”和“非家”、夢幻和現實的并列,成功營造暗恐的效果。
《沙人》一文講述了大學生納撒內爾被暗恐心理支配的悲慘命運和毀滅性結局。故事中描述的納撒內爾暗恐心理的復現以及納撒內爾的瘋狂舉動給故事增添了暗恐效果。
納撒內爾第一次瘋狂是因為見到了一個名叫科佩拉的眼鏡經銷商,此人讓他回憶起童年時代的可怕經歷。陌生的不熟悉的人勾起了納撒內爾熟悉的恐怖回憶,這種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并列營造本文的暗恐效果。納撒內爾再一次瘋狂是看到心上人奧琳琵雅散落在地上的眼珠。故事中新出現的人、物或是事件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和過去有著相似性,這種陌生情節和熟悉情節的反復重合使本文籠罩在恐怖氛圍中。納撒內爾最后一次瘋狂是因為在塔頂觀光時看見了科佩留斯,這次瘋狂使納撒內爾徹底崩潰,最終跳樓自殺。
霍夫曼在作品中多次描寫熟悉與不熟悉、“家”和“非家”的人、物或者事件的并列重合,巧妙構建了恐怖場景,營造出暗恐效果。在那些熟悉的恐怖體驗中透露著主人公童年的創傷,童年的創傷體驗往往難以忘懷,以暗恐心理的形式壓抑于主人公無意識深處(Freud,1970:268),雖意識不到,但卻發揮巨大作用。
二.暗恐心理的根源
“霍夫曼作品經常表現一種瞬間感,以瞬間感知和迷狂,表達人暫時陷入的出離自我的非理性狀態。”(丁君君,2016:9)主人公為什么會一次次陷入“出離自我的非理性狀態”?都是因為主人公的暗恐心理。在暗恐心理支配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次次做出近乎瘋狂的舉動。
在《沙人》一文中,保姆給納撒內爾講述恐怖的沙人的故事是納撒內爾暗恐心理的根源。看被律師科佩留斯威脅挖掉眼睛時,又一次從深度及廣度上大大的加強了納撒內爾的暗恐心理。“《沙人》展現了一部眼睛的進化史。”(丁君君,2006:23)在對《沙人》的著名闡釋中,弗洛伊德將眼睛解讀為一種對陽具的轉喻,對眼睛被竊的恐懼意味著面對閹割的恐懼(Freud,1970:255)。
當和科佩留斯有著相似名字的眼鏡經銷商科佩拉出現在納撒內爾生活中時,納撒內爾陷入了瘋狂,因為納撒內爾把沙人、科佩留斯、科佩拉三者形象重合了。孩提時期有關科佩留斯的恐怖經歷經歷已經成了納撒內爾“感受世界的基本模式:原本尋常的并可以預見的事物轉眼之間會變成陌生的和充滿敵意的東西, 這讓他驚恐不已”(馮亞琳,2006:37)。
當親眼看到心上人奧琳琵雅眼睛被拉扯出來時,納撒內爾的瘋狂不可控制。操控眼睛、眼睛經銷商科佩拉、失去眼睛,這些因素促使了暗恐心理的復現,導致納撒內爾的瘋狂。
在《胡桃夾子》中,小女孩瑪麗經歷了第一晚的見到老鼠的恐怖經歷后,故事中瑪麗的家人也想了各種辦法來捕捉老鼠,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之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捕捉不到真正的老鼠,是因為老鼠根本不存在,老鼠只存在于瑪麗的幻想之中。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曾指出,人之前來自生活中的記憶可以以夢的形式出現(Freud,1982:142-143)。童話世界中老鼠國王變本加厲索取的過程其實表征著瑪麗內心深處恐懼心理的加深,瑪麗心中的恐懼心理其實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暗恐心理。
在暗恐心理支配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次次做出各種瘋狂的舉動。這些舉動都是暗恐心理復現所導致的。暗恐心理被深深壓抑在主人公的潛意識深處,一旦出現暗恐場景中相似的人、物或是事件時,不熟悉的和熟悉的重合,家和非家的重合,會激發壓抑的暗恐心理,對主人公產生巨大影響。
縱觀兩部作品,主人公的暗恐心理的起源都是是童年的創傷經歷。在兩部作品中對創傷經歷和創傷體驗的描述具有相似性。首先,創傷經歷都發生在主人公的童年時代,童年時代的創傷經歷像一顆不定時炸彈影響著主人公后續的生活。第二,創傷體驗相似,在經歷創傷事件都主人公都有昏厥、生病、神志不清、焦慮等狀況。焦慮是創傷體驗和暗恐心理中一個及其重要的因素,在經歷童年創傷以及后期暗恐心理復現時,主人公都伴有不同程度上的焦慮心理。
三.暗恐心理的治療
兩部作品雖然都有童年創傷主題,但童年創傷所導致的主人公的結局,即暗恐心理支配下主人公的結局卻是截然不同的。《沙人》中納撒內爾最終走向了跳樓自殺的道路,而《胡桃夾子》中瑪麗在胡桃夾子的幫助下最終戰勝了心中的恐懼,和朵謝梅小先生進入了童話王國。
對比兩部作品中主人公童年創傷和暗恐心理的發展軌跡,我們可以發現兩部作品中主人公都采取了多種方式治療自己的童年創傷、平撫自己的暗恐心理。
《沙人》一文中納撒內爾經歷了多次治療愈合階段,母親、未婚妻克拉拉以及克拉拉哥哥洛薩的陪伴以及引導曾多次使納撒內爾恢復正常狀態。《胡桃夾子》一文中瑪麗同樣也有用多種方式克服自己的暗恐心理。總的來說,兩部作品中主人公治療暗恐的方式無非以下幾種:一,自我治療(自救);二,他人的理性的引導(他救);三,他人的陪伴和理解(他救)。
兩部作品中治療暗恐的方式看似相同,但在具體的實施上有著一些差異,正是這些差異導致了兩個主人公截然不同的結局,對比兩部作品中主人公治療暗恐所采取的的方式以及各種治療方式具體的實施方法,可以發現《沙人》和《胡桃夾子》的主人公都有過自我治療,只不過納撒內爾選擇的是自我平撫,而瑪麗選擇的是勇敢出擊,戰勝恐懼。在兩部作品中,主人公都有受到他人的理性指導,克拉拉和洛薩在信中通過理性分析幫助納撒內爾克服恐懼(成年后),而教父朵謝梅在發現瑪麗異常后通過童話故事幫助瑪麗樹立戰勝老鼠王的信心(童年時);兩部主人公也都有來自他人的陪伴,納撒內爾母親、克拉拉以及洛薩的陪伴,瑪麗有家人和教父的陪伴;但不同的是,瑪麗有教父和瑪麗哥哥的理解,而納撒內爾沒有。可以發現兩部作品中主人公治療暗恐心理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自我治療方式、接受他人理性指導的時間以及他人的理解三個層面。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接受理性教育的時間。理性教育對于兒童來說至關重要,理性教育開始的時間早晚也直接影響兒童心理的形成過程。《胡桃夾子》中教父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人,他最早發現了小姑娘瑪麗心理狀態的不正常,并且耐心的用兒童易于接受的童話的方式予以引導,可以說教父朵謝梅是瑪麗理性教育的啟蒙者(Kremer,1999:96)。《沙人》中納撒內爾的童年時期父親的角色是缺失的,也沒有一個類似教父朵謝梅角色的人出現在他童年時期予以理性的啟發。
其次,他人理解與否對于暗恐心理的治療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理解對于一系列心理疾病的治療至關重要,他人的不理解會增加患者的焦慮情緒,比如在《胡桃夾子》中瑪麗的父母對瑪麗恐怖經歷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并且否定瑪麗的想法,使女孩越來越孤獨和沮喪(Gillespie,2008:192)。《沙人》一文中雖然克拉拉和洛薩在努力的用理性的知識寬慰納撒內爾,但是他們對納撒內爾的心理狀態是不理解的。在《胡桃夾子》一文中,教父是唯一一個理解瑪麗的成年人(Gillespie,2008:192),教父及時的發現了小姑娘心理上的問題并且讓小姑娘感受到來自他人的理解,結合理性的引導堅定了瑪麗戰勝老鼠王的信心。除此之外,在最后胡桃夾子說要幫助瑪麗討伐老鼠王但是缺少一個佩劍時,瑪麗的哥哥從自己的玩具上取下一個劍給胡桃夾子配上,看似過家家般的情節卻給了瑪麗極大的信心,有了武器最終幫助瑪麗從心理上戰勝老鼠王。
“霍夫曼面對人類的精神困境,期望通過詩性的自救和神性的他救相結合來尋找一條救贖人類的道路,并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完滿的永恒世界。”(陳曉艷,2012:123)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窺探出霍夫曼在作品中表達出來的對于童年創傷的態度,作品中傳達的思想對于現代社會童年創傷的治療仍具有重要意義。
兒童的暗恐心理往往起源于童年時期的創傷經歷。創傷體驗以暗恐心理的方式埋藏在無意識中,當出現和創傷經歷相似的場景時,創傷心理就會復現并會產生巨大影響。若處理不好暗恐心理,往往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及時的理性啟迪和來自他人的理解對治療暗恐心理至關重要。研究結果啟示我們在對待兒童童年創傷時要予以及時的理性引導,并且要從兒童的視角出發理解兒童心理。這就是霍夫曼在他的現實主義童話中傳達給我們的對于童年創傷的應對辦法,因此時至今日霍夫曼童話仍有廣泛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Freud,S.Das Unheimliche[A]. In:Studienausgabe,Bd.IV:Psychologische Schriften[C],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1970.
[2]Freud,S.Die Traumdeutung [M]. 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2.
[3]Gillespie,G.&M.Engel & B. Dieterle.Romantic Prose Fic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8.
[4]Kremer,D.E.T.A.Hoffmann: Erzhlungen und Romane[M].Berlin: Erich Schmidt,1999.
[5]Thalmann,M.E.T.A.Hoffmanns Wir
klichkeitsmarchen[J].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 Philology,1952.
[6]陳曉艷.論霍夫曼小說《金罐》中的詩性自救與神性他救[J].文學教育,2012(8).
[7]丁君君.惡魔與想象——曼小說中的文學之“惡”[J].德語人文研究,2016(2).
[8]丁君君.瞳孔中的鏡像——論霍夫曼的小說《沙人》[J].外國文學,2006(5).
[9]馮亞琳.從《金罐》和《沙人》看霍夫曼二元對立的藝術觀[J].外語學院學報, 2006,22(1).
[10]李香.論E.T.A霍夫曼小說《沙人》中的人格分裂[J].商業文化,2012(3).
[11]童明.暗恐/非家幻覺[J].外國文學,2011(4).
[12]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13]周芳、童真.起步中的霍夫曼研究[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41).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外語學院德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