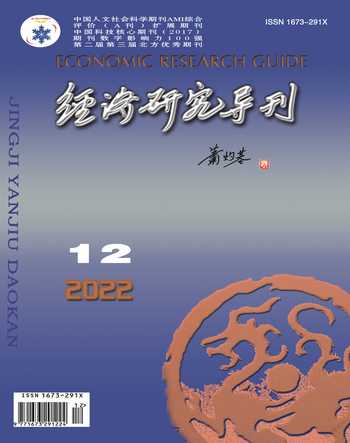法律治理視域下生活垃圾分類精細化管理探究
劉志 王雅
關鍵詞:垃圾分類;精細化管理;法律治理
中圖分類號:X705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12-0044-04
一、垃圾分類概況
(一)我國垃圾分類法律概況
我國關于垃圾分類管理立法主要包括《環境保護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這四部法律。同時,各地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的具體的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在其各自的生效地區內實行。
(二)西安市垃圾分類法律概況
2019年9月1日正式生效的《西安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分別從垃圾的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置等相關方面進行了規范,是真正意義上推進西安市垃圾分類的專門性法律。此外,政府出臺的政策中都貫徹了垃圾分類的精神,如《西安市“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的第17條、第20條及第22條分別強調要加強對生活垃圾分類、收運、處理的管理和督導、建立和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類體系、強化對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效率;2019年3月15日頒布并生效的《西安市促進全域旅游發展的實施意見》的第7部分“優化旅游環境”中,規定了要充分調動社會成員,推動城鄉生活垃圾的分類,鼓勵使用新型生活垃圾處理設施;《西安市老舊小區綜合改造工作升級方案》在第四部分“組織保障中就明確提出”市城管局在督導老舊小區違法建設拆除執法工作的同時,還要指導開展生活垃圾分類收集,保障小區的居住環境。
二、西安市生活垃圾分類精細化管理問題與困境分析
(一)欠缺垃圾分類管理的社會基礎
西安市正式推行垃圾分類僅一年多,公眾對于垃圾分類必要性認知并不充分,導致在實踐中存在彼此觀望、僥幸、不在意等心理,使垃圾分類的進程緩慢且成效差[1]。集體認同感、團結、意識和動員是集體行動的四個核心議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集體認同感[2]。因此,要想加快推進垃圾分類的進程,提高公眾的集體意識、個人責任感是必經之路。
(二)缺失垃圾分類管理配套法律的支撐
《固體污染物環境防治法》的第四章確定了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個方面規范垃圾分類,并由縣級以上地方政府進行統籌安排。《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條例》于2019年4月16日通過,其作為統籌西安市垃圾分類的法律,屬于地方政府規章,法律效力較低,且沒有頒布相應的實施細則。其次,西安市垃圾分類采取四分法,未對玻璃、大件家電、家具等大件廢棄物、餐飲垃圾的回收處理進行規定,垃圾收費制度、定時定點回收制度等形同虛設。最后,未細化垃圾分類處理系統。未詳細規定垃圾分類的回收、運輸、再利用,只是利用填埋與焚燒這兩種簡單粗暴的方式進行垃圾的處理,并沒有讓垃圾分類呈現出應有的促進資源再利用的目的。
(三)垃圾分類的責任主體不明
參與垃圾分類主要是政府、生產者、公眾、社會公益組織四類主體,但目前西安市的垃圾分類責任的劃分及其間的合作還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狀態。
1.《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辦法》第7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中規定了城市管理部門、生態環境行政管理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商務行政管理部門均有權對垃圾分類有管理權限。但是,法律并未明確哪一個部門主要承擔垃圾分類的監管責任,管理主體多,責任劃分不明,出現問題互相推諉。
2.生產者的責任鏈比較短。生產者的主要責任主要體現在其生產經營活動中要盡量減少垃圾及其他廢棄物的產生,對其產生的包裝具有回收的義務。但在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的過程中,生產者的生產行為并未受到實質的影響,未規定其所承擔的總量控制責任及其他社會責任,導致源頭垃圾量居高不下,垃圾分類的難度以及回收再利用的難度較大。
3.社會公益組織沒有履行職責。社會公益組織是政府、企業、居民間的重要“紐帶”和“潤滑劑”[3]。目前在西安主要有西安公益聯盟、西安市益行動環保公益中心、西安古城青年志愿者協會這三個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公益組織。西安公益聯盟成立于2006年,截至2012年,只有22場與垃圾分類及環保公益無關的活動[4],且自此之后未再組織活動;2017年成立的以“促進西安市垃圾分類”為目標的西安市益行動環保公益中心,其活動主要集中在2017年,至此之后再也沒有其他相關的活動;西安古城青年志愿者協會的活動也基本和垃圾分類無關。由此可見,這些公益組織的建立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垃圾分類或者是為了環境保護,但是這些組織的活動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四)監督機制不完善且執法效果差
先賢孟子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縱使有良法,也必須得善治才得以落到實處。西安市推進垃圾分類的過程中的治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在監督機制與執法機制上的問題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1.垃圾分類監督主體不明確。在《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辦法》的第7條的第2款和第3款分別規定了生態環境行政管理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管職責,其分別主管垃圾集中轉運設施及垃圾處理場所的污染物排放、督促物業開展垃圾分類。垃圾分類管理從分類投放到轉運及最終處理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卻將整個監督鏈條拆分開,導致各部門之間推諉,且會增加分揀成本。
2.監督員的設置沒有起到實際的監督效果。一方面,絕大多數小區都未設置專門的監督人員;另一方面,即使是有監督人員,其崗位的設置也是形式大于實質,居民會抱著僥幸心理將垃圾混裝混投,實際產生的分類效果較差。
3.執法效果較差。以曲江新城的執法活動為例,在2019年11月底集中一周調動214人進行119次執法檢查后,并未做出行政處罰等處罰措施,只是進行勸導教育,且對于教育之后違規行為是否改正未進行后續的跟進監督和指導。再者,開展此執法活動的時間較為集中,并未將其日常化、常規化。此外,西安市垃圾分類實施時間較短,面臨如何選擇合適的執法手段、執法方式及確定處罰的力度等問題。最后,要指導和監督居民垃圾分類及落實獎懲機制,面臨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各種因素的限制,執法行為受阻,執法效果較差。
(五)激勵與懲罰機制欠缺
《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辦法》第48條第一款規定可以對成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進行獎勵。只是單獨的條文規定了要進行獎勵,但具體標準缺失,欠缺可執行性。此外,在西安市其他有關垃圾分類的法律或者其他政府文件中,都沒有關于獎勵的具體標準、金額、方式的規定。
《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辦法》第45條、第46條、第47條分別規定了服務單位服務質量和信用等級進行評價并公開、個人拒絕垃圾分類而納入個人征信系統、投訴及救濟渠道,對單位、個人最高分別處三萬元、一千元的罰款,處罰的金額小,達不到威懾及懲罰的目的。此外,并未規定除直接的行政主管人員以外的其他有密切聯系的責任人的責任。
三、推進西安市生活垃圾分類精細化管理的法律治理
(一)借助法治宣傳平臺,增強公眾垃圾分類的個人責任意識
先賢荀子曾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那么從古人的智慧中可以看出,作為推行垃圾分類精細化管理的核心力量是公民,因此加強法治宣傳教育是推進垃圾分類精細化管理的重要一環。
1.需要借助法治宣傳平臺,增加垃圾分類信息的獲取渠道。在西安市政府官網首頁上設立垃圾分類法律專區,宣傳循環經濟思想,其核心內容就是資源減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環的3R原則[5],提高公眾的參與熱情與個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2.借助法治知識宣傳的平臺,設立趣味性的“垃圾節”[6]。將從垃圾里面挑選出來的物品作為展出的“展品”,將一些具有實用性地從垃圾里面分揀出來的物品,免費分發給在場的觀眾,由此加強公眾的垃圾分類的意識。
3.將垃圾分類知識的普及與學校教育平臺相結合。例如,開展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開設環境保護—垃圾分類的通識課,邀請市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人員做講座,或者開展垃圾分類知識競賽等方式。
此外,在推行垃圾分類的過程中,還要加強公眾彼此之間的信任,形成穩定的群眾基礎,形成穩定而牢固的信任關系,打破集體行動困境,推動垃圾分類的進程。
(二)提高法律的位階,為垃圾分類提供制度保障
垃圾分類是新時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是破解“垃圾圍城”之困的關鍵所在[7]。要完善西安市垃圾分類體系,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提升相關法律法規的效力位階。將《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辦法》提升為地方性法規,以西安市的管理經驗帶動周邊城市的垃圾分類的進程;將《西安市“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這一政府性文件上升為地方政府規章,將垃圾分類管理與節能減排相結合。
2.制定垃圾分類相應的實施細則,明確垃圾的分類標準、主體責任、收集、運輸處理及再利用等環節的實施細節,采用標準與標志并用的方式。
3.明確分類的垃圾種類目錄及其投放規則,并將其印制成冊,分發到戶。
4.根據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制定《西安市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實施方案》,明確生產者在垃圾分類中的責任與任務要求,建立生產者責任的延伸制度。
5.制定《西安市垃圾焚燒辦法》,改變目前主要是填埋的垃圾處理方式,推動垃圾資源化進程。
(三)精細垃圾分類機制,以政府促進強制分類
縱觀成功進行垃圾分類法律治理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強制推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西安市的垃圾分類的進程中,政府就必須發揮強制作用。
1.全面取消西安市內的公共垃圾桶,明確分類垃圾桶的顏色標識,增加垃圾桶的投放數量,增加廢玻璃、小家電、大件垃圾額外單獨設置回收點和回收桶,政府限制企業對商品的過度包裝。
2.生活垃圾回收收費并強制分類。政府制定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標準,實現分類計價、計量收費等差別化管理,征求公眾意見,將收費標準向社會公布,并將費用專項用于生活垃圾分類、收集、運輸及處理領域,嚴格專款專用。
3.嚴格執行生活垃圾定時定點收集。目前在西安市,在各大高校、小區的垃圾回收點都設置有垃圾分類警示牌,包括分類的標準、垃圾回收的時間點等,應嚴格執行垃圾定時定點收集制度。
4.政府需加大對垃圾運輸公司分類運輸、處理的監管力度。挑選專業的垃圾運輸公司,并建立專門的工作小組進行監管,規范垃圾分類運輸的流程,加大混裝運輸行為的懲罰力度。
(四)建立健全責任分配及責任延伸制度,建立四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
垃圾分類工作需要社會各個群體的合作與共同努力,劃分各主體的責任與義務范疇。如Hasegawa所指出的:“協同治理能夠為追求不同議程的不同派別創造機會,去提升對于彼此的信任感。只有各方有共同的愿望并承諾去實現共同目標,協作才能夠達成。”[8]
1.明確垃圾分類中政府責任主管部門及責任范疇。在德國,將垃圾分類處理事業定義為準公共事業,由政府和市場共同承擔責任[9]。那么在西安市的垃圾分類法律治理過程中,首先應確定西安市生態環境行政管理部門為垃圾分類管理的責任部門,并負責建立本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目標責任制和考核評價制度。其次,制定垃圾分類法律相應的實施細則并推動實施。最后,加大政府的執法力度,嚴格執法[10]。
2.明確生產者的責任,建立責任延伸制度。將生產者的責任延伸到源頭垃圾總量的控制上,鼓勵推行凈菜上市,禁止過度包裝,選擇耐用的、可循環使用的包裝材料,在包裝袋上明確分類標識;鼓勵生產者借助新興的物聯網技術、云計算、大數據平臺建立健全廢舊產品的回收體系等。
3.明確公眾的主要責任在于按照垃圾分類的標準進行分類,并配合垃圾分類回收。法律具有利導性,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分配利益,影響人們的動機和行為[11]。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鼓勵公眾減少一次性生活用品的使用、選擇環保購物袋等;在垃圾分類投放的過程中做到互相監督,強調公眾的個人責任感。
4.明確社會公益組織的責任,激發其活力,鼓勵其探索垃圾分類管理模式、手段和措施。政府應鼓勵其活動的開展,并為其提供必要的幫助,提高其地位與社會的認可度。
(五)完善激勵機制,提高違法成本,激發垃圾分類積極性
著名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認為,“只有一種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會驅使潛在集團中的理性個體采取有利于集團的行動。”[12]激勵政策的合理運用一定是正向激勵和負向激勵相結合的過程[13]。
對于負向激勵方面,《西安市垃圾分類管理辦法》的第49條至第53條規定的處罰,均是以罰款為主,且未對屢次違反規定的行為作出規定。因此,應加大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對屢次違規的主體要求其承擔一定的垃圾分揀責任。其次,建立社區垃圾分類的連帶責任,建立連坐制度。此措施的核心在于一人違規投放垃圾,其所在的整個小區都要受到懲罰。再次,建立“信用處罰”機制,將是否按照規定履行垃圾分類義務納入信用機制考評體系,將垃圾分類的情況與個人信用評分相聯系。
史波芬認為,激勵機制的目的就在于使得被激勵著認知到自己行為需要與制度規定相一致,要在認同制度的同時,做到知行合一[14]。傳統的激勵模式基本均是以命令的方式,與其命令居民被動接受,不如采取正向激勵機制讓居民主動積極參與垃圾分類的效果更為顯著。
建立正向激勵機制,緩解負向激勵可能會引發抵觸情緒,促進垃圾分類機制的良性循環。首先,參照德國設立“押金瓶”制度,實施塑料瓶、玻璃瓶押金返還的激勵措施。其次,開發微信生態賬號,創建社區衛生公開平臺。例如開發微信的小程序,將垃圾分類與二維碼掃碼識別垃圾相結合。最后,將垃圾分類處理廠與居民正確垃圾分類的程度與對其所在社區的公共福利相結合。例如,西安市首個全量接收生活垃圾的光大環保能源(藍田)有限公司,可以規定城六區中月垃圾分類水平前10名的小區會得到一筆可觀的現金獎勵,用于小區的供暖等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維修。
因此,在選擇正向激勵的手段時,應注重激勵的前提條件,要將承諾的利益可視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得到居民的信任,使其能夠主動地去進行垃圾分類,這才是采取激勵措施的最終意義與目的。正如奧爾森所說:“選擇性的正向激勵對個人的偏好的價值要大于個人承擔集體物品成本的份額,而價值較小的制裁或者獎勵都不足以動員一個潛在的集團。”
參考文獻:
[1] ?郭施宏,陸健.城市環境治理共治機制構建——以垃圾分類為例[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20,(Z1):132-141.
[2] ?杜歡政,樊亞男.以全產業鏈思維布局垃圾治理體系——以上海為例[J].宏觀經濟管理,2020,(11):72-77+84.
[3] ?西安公益聯盟網頁,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安公益聯盟/9008409?fr=Aladdin.
[4] ?劉娟,王東旭.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問題的法律規制研究[J].法制與社會,2021,(5):121-122.
[5] ?李冠群.科學處理垃圾 建設美麗城市——國外城市精細化管理系列研究之一[J].當代世界,2018,(8):76-78.
[6] ?夏蕓蕓.武漢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治理法治化研究[J].長江論壇,2020,(5):51-56.
[7] ?張萍,張波.石家莊市生活垃圾分類法律問題研究[J].河北環境工程學院學報,2020,(3):72-75+81.
[8] ?Hasegawa,Koichi.“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ism in Japan.”Civic Engagement in Contemporary Japan:Established and Emerging Repertoires,99-85.New York,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Springer,2001.
[9] ?曾玉竹.德國垃圾分類管理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經濟研究導刊,2018,(30):159-160.
[10] ?張競宇.日本垃圾分類管理經驗及其對天津市的啟示[J].低碳世界,2019,(8):320-321.
[11] ?孫笑俠.法理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12]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13] ?錢世超.激勵機制在居民生活垃圾分類中的問題與對策分析[J].經貿實踐,2018,(18):245.
[14] ?史波芬.淺說激勵機制在國內劇名生活垃圾分類中的問題與對策[J].廣東化工,2018,(11):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