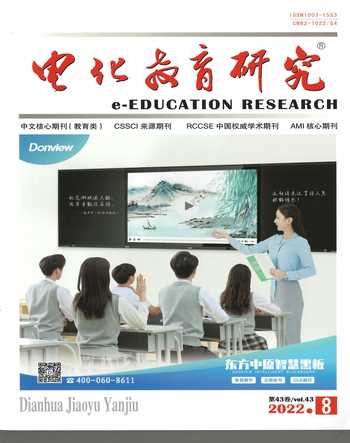促進還是抑制:哪些因素影響校長的在線教學持續意愿?
趙曉偉 王維昊 沈書生



[摘? ?要] 在線教學作為線下教學的有益補充,是促進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能否合理并持續推進在線教學,有賴于校長的遠見卓識。文章基于“認知—行為”視角形成影響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分析框架,對17名中小學校長進行深度訪談,通過內容分析與定性比較分析,識別出促進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四條路徑,分別是理念先行型路徑、文化浸潤型路徑、愿景牽引型路徑、綜合施策型路徑,同時也發現了一條抑制持續意愿的路徑,即權宜執行型路徑。文章對每種路徑結合典型案例進行詳細刻畫,進而提出提升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建議,以期為在線教學的持續推進提供參考,并為校長教學領導力研究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 教學領導力; 在線教學; 領導行為; 定性比較分析
[中圖分類號] G434? ? ? ? ? ?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趙曉偉(1995—),女,山東莒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信息化教學設計、信息化領導力研究。E-mail:zxw1995925@qq.com。
一、問題的提出
在線教學從早期在學校教育中若隱若現,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面鋪開,再到后新冠肺炎疫情時期趨于常態應用,已然成為無法抗拒的現實。研判在線教學的實施成效,促進應急式在線教學轉化為混合常態教學,是推進信息技術與教學深度融合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然而,這一理想對于基礎教育現實而言還有多遠,如何幫助中小學校有效適應混合學習新常態?一系列問題尚需深入研究。對諸如此類問題的回應,論者并不鮮見。早期學者從師生在線教與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大規模在線教學后,長遠布局未來學校教學形態,探索教育改革混合動力,還需從管理者層面系統考量。
校長對在線教學的整體研判將影響學校未來的教學規劃與路徑選擇。然而,筆者團隊前期調研發現,后新冠肺炎疫情時期53.1%的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不高,近40%的校長僅將在線教學作為線下學習的附加項[1]。既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所有校長均組織在線教學,為何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存有差異,哪些關鍵因素起促進或抑制作用,如何引導校長從被動應對向持續推進轉變?由于校長的在線教學持續意愿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為了解促進或抑制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組合因素,本研究嘗試采用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從校長大規模在線教學中已形成的認知與行為的現實因素出發進行溯因,以期為不愿開展、不知如何推進在線教學的校長提供借鑒。
二、研究基礎與框架
(一)研究基礎:在線教學持續意愿
持續意愿最早由Bhattacherjee提出,被理解為個體初次采納后繼續使用技術的主觀傾向[2]。在線教學持續意愿是指個體認為自身在未來繼續以純在線或混合形式組織在線教學的程度,以往研究通過技術接受模型、計劃行為理論、自我決定理論等探究關鍵影響因素[3-5]。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在線教學史無前例,部分研究者擴展技術接受模型、環境匹配理論,探索師生緊急在線教學后的持續意愿[6-7],為混合新常態背景下課堂教學變革提供新思路。
既有研究主要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或結構方程模型等方式,對不同影響因素與持續意愿間的關系展開探討,這種方式對自變量之間潛在互動關系關注不足,默認變量之間的獨立性而忽視協同效應。此外,已有研究對因果對稱分析邏輯的關注也導致應對持續意愿的復雜誘因方面略顯困難[8]。由于實踐中校長的在線教學持續意愿往往受多因素協同影響,同一結果可能由不同因素的組合效應所導致。因此,本研究采用QCA方法,對多案例中校長的認知與行為進行組態分析,探究哪些因素促進或抑制了校長的在線教學持續意愿。
(二)分析框架:“認知—行為”視角
個體認知是個體與外部世界交往過程中持續建構對外部世界認識的過程,是個體行為選擇和后續行為意愿的前提[9]。管理者的認知包括管理者識別與解釋外部變化、調整原有認知結構并影響行動和后續意愿的過程[9]。不同管理者對不同情境的認知可能不同,進而產生差異化的行動策略。管理者的先前認知,會隨著他們所遭遇的情境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伴隨行為改變促進認知調整并形成后期認知,這種認知會影響管理者的決策,并通過后續行為表現出來;當管理者能夠通過行為過程強化新的認知后,這種認知又會不斷作用于他們的持續行為,從而形成“認知—行為”的雙向強化,最終體現到他們的行為持續意愿當中。
對于校長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組織開展在線教學實屬“無奈之舉”(個體對在線教學的認知未發生改變),隨著對在線教學實施的效果評價,校長建立起對在線教學的感性認知與價值考量,并通過認知調整與行為變化實現初始教學領導行為躍遷,逐步形成新的教學領導行為,并影響后續的行為意愿。因此,可以從“認知—行為”的視角構建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影響模型(如圖1所示),該模型包括認知層與行為層。其中,認知層是校長組織在線教學過程中對外部變化的持續理解與思考,參考解構計劃行為理論,從對在線教學的認知、對社會影響的認知兩個方面思考[10];行為層關注校長實際的在線教學領導行為,參考Hallinger等人提出的教學領導行為框架[11],并融入在線要素,從規劃在線教學愿景、協調在線教學進度、構建網絡學習空間、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創設在線育人氛圍五個方面進行理解。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訪談、內容分析和QCA三種方法。前兩種方法用于了解校長在線教學實施情況與持續意愿,第三種方法用于對編碼取值后的數據校準與組態分析。QCA源于1987年Ragin出版的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12]一書,目前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管理學、教育學等領域,其中,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聚焦于教師數字技術采納行為研究[8]、數據素養的影響因素[13]等方面。作為一種整合定性(案例導向)與定量(變量導向)研究的方法與工具集,它不同于定量研究的還原論視角,而是以整體論視角,借助集合思想和布爾邏輯表達因果模式,揭示產生復雜社會現象可能的必要、充分及其延伸條件。其假設:若所有案例的結果中均出現某個條件,則該條件可能必要;若某個條件導致特定結果出現,則該條件可能充分,但可能還有其他條件導致相同結果,即存在多個充分條件[14]。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多重并發因素,根據前因條件與案例情況,采用fsQCA研究認知與領導行為的組合效應及其與結果間的多重關聯。
(二)案例選擇
研究依據QCA對案例數量的要求,結合目的性抽樣與開放性抽樣,遵循信息飽和度原則,將南京市7個區17名中小學校長作為訪談對象,受訪者平均任職7年,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組織在線教學,訪談時已返校復學。訪談以面對面半結構化方式進行,訪談內容以時間線方式展開,引導校長通過敘述事件豐富答案。訪談聚焦三個主題: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前對在線教學的態度以及技術融合實踐的情況,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線教學的實施方式、效果及自身認知的變化,三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對在線教學融入日常教學的態度與擔憂。持續時間為90~120分鐘。最終獲得錄音資料35小時,轉錄文本資料19萬余字。個案編碼以“順序—所在位置(D:市區;S:城郊;R:鄉村)”命名。
(三)變量賦值
QCA對前因條件選擇的方法有問題導向、研究框架、理論視角、文獻歸納和現象總結五種。研究借鑒已有文獻,從“認知—行為”維度將條件變量劃分為7個條件變量、19個細化指標,見表1,條件變量的得分為細化指標得分的均值;結果變量聚焦校長是否愿意持續推進在線教學,包括積極與消極兩種傾向,以0~3進行賦值,分值越大表示態度越積極。編碼工作由2名熟悉編碼表和編碼方式的研究者背對背進行,編碼結果具有較好的一致性(Kappa為0.869)。
(四)數據校準
數據校準是考慮案例間類別與程度差異,將條件與結果變量賦予可解釋的集合意義的過程[12]。研究將條件變量的完全隸屬、交叉點及完全不隸屬三個錨點設定為[5,2.5,0],將結果變量的三個錨點設定為[3,1.5,0],統一校準后的值介于0~1之間。
四、數據分析與討論
借助fsQCA3.0軟件,研究將影響因素與持續意愿間的因果關系概念化為必要性與充分性的關系,必要性指所有結果均出現某一條件,充分性表示所有具有特定條件的情況都導致某結果的出現。研究選取7個條件變量,邏輯上可能的組合為128(27)個,由于部分組合不會在樣本中表示或與事實相悖,因此,需要進行閾值限定,將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設定為0.7,將案例閾值設定為1[16],識別出促進或抑制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條件組合,且該組合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一)必要條件分析
必要條件分析的重要指標是一致性水平,若超過0.9,表明該條件變量是影響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12]。研究發現,促進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條件變量一致性介于0.356~0.843之間,均未超過0.9,不構成必要條件;盡管抑制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條件變量有6項的一致性超過0.9,但覆蓋度均未超過0.8,也不構成必要條件,表明任一獨立條件變量均無法構成解釋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
(二)條件組態分析
當單個條件變量不能達到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時,需探究不同條件變量對結果的充分條件。QCA為條件組態分析提供了簡約解、中等解和復雜解,若某一前因變量出現于簡約解和中間解中,即為核心條件,若僅出現于中間解中,則為輔助條件。為便于歸納分析,研究將核心條件相同的不同解視為同一路徑的不同組態,形成影響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11個組態(或稱為11個解),見表2。促進校長持續意愿的10個組態一致性均達到0.9以上,抑制校長持續意愿的1個組態一致性達到0.9,說明條件組態對每個結果的解釋力均為90%以上。此外,促進與抑制持續意愿的組態分布能夠解釋約74%、84%的案例,具有較高的解釋性。由于QCA的解仍具有“黑箱”特性,研究以典型案例作為“手電筒”來窺探組態細節與整體邏輯。
1. 促進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路徑分析
促進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路徑包括以POfz為核心條件的H1路徑、以CAfz 為核心條件的H2路徑、以PVfz 為核心條件的H3路徑以及以“POfz×CAfz×PVfz”為核心條件的H123路徑。
(1)“適應—創新”的理念先行型路徑(H1)
H1路徑由H1a~H1d組態構成,表示對在線教學具有積極認知的校長,領導行為是輔助要素,即使力有不逮,對在線教學仍心向往之且不受他人影響。代表案例是四個市區校校長,前兩條路徑對應的校長,新冠肺炎疫情前均開展了在線教學。根據技術接受理論,個體對技術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越高,對技術態度越積極,技術持續意愿越高[3]。部分校長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前未組織過在線教學實踐,但具有創新性認知,可能受先前經驗或專業背景影響[J校長具有教育技術學科背景,期望引入智能平臺診斷學生知識點掌握情況 (14-D)],也可能由于認識到在線教學有助于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支持[“之前信息化教學偏形式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線教學以‘直播+練習+答疑為主,教師能夠提供個性化指導”(9-D)],因而也具有較高的在線教學持續意愿。
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前開展過在線教學實踐的校長是早期采納者,他們積極適應在線教學趨勢,一是利用學習空間創新混合學習形態,探索出自帶設備的個性化學習模式(15-D)、“二維碼+導學單”的翻轉學習模式(16-D),形成集中同步、分散異步型混合學習方式。二是利用在線平臺將教師專業學習與教學應用相聯系,如D校長自2014年組織教師在節假日基于在線平臺開展教研組備課活動、直播答疑活動,培養出一批“網紅教師”(16-D)。基于適應性創新探索,兩所學校皆獲批首批智慧校園示范校并吸引系列經費投入,成為在線教學的受益者,虹吸效應明顯,因而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較高。
(2)“平臺—利用”的文化浸潤型路徑(H2)
H2路徑由組態H2a~H2c組成,表明以學校育人理念為引領推進在線教學的校長,即使尚未建立對在線教學的積極認知,但通過鼓勵教師協調教學進度或密切家校合作,對在線教學的隱含價值充滿期待。代表案例是三個城郊校校長,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均部署了在線教學平臺,尚未有融合的實質性探索。教育文化發生在教育的原點,并與教育活動共始終[17]。作為一種新的活動形式,在線教學的推進需要從文化建設角度思考網絡學習空間對立德樹人的時空拓寬,可以從實踐活動與課程教學方面發揮協同育人的有效舉措。
第一,發揮現有平臺的功能性與趣味性,以校園文化理念引領推進育人實踐活動,實現家校協同。如依托主題學習活動網站開展“創新校園防疫”“學校吉祥物征集”等主題活動,家長對各類活動都很支持,且參與度很高(3-S)。第二,發揮平臺資源的可加工性,基于次生文化形態創新教學方式,實現師生協同。如L校長立足學校育人理念關注兩類次生文化形態:一類是課程文化形態,設計了統整式、階梯式的“穿石課程群”,以時間線為邏輯橫向組合了學科同類知識,合并后的新主題涉及自我管理、生命教育、家國責任等內容,并對原有課程剩余部分進行組裝,縱向銜接了1~6年級不同階段的課程內容;另一類是課堂文化形態,設計基于“潤學單”的遞進式學習模式,即從真實情境的問題引導出發(順學),提供學習資源和潤學單引導學生自主探究(助學),并通過脫離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實現學科育人(利學)(4-S)。
(3)“規劃—調整”的愿景牽引型路徑(H3)
H3路徑表明,系統謀劃、定期監測在線教學實施進展的校長,即使尚未看到在線教學的實質影響,但通過調整教學組織形式、支持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期望持續引領在線教學共同愿景的落地。代表案例是一個市區學校校長,其在受訪校長中任職年限最長(18年)。目標設定理論表明,明確且具有挑戰性的目標對于指導個人行動、激勵個人實現績效目標具有重要價值,獲取目標進展的反饋有助于調節目標與行為間的關系[18]。
對于校長而言,設定明確在線教學愿景并引領不同主體與愿景同向而行至關重要,借助智能平臺持續監測學生數據,據此作出調整與決策同樣不可忽視。如R校長建立學校、年級、班級的三層在線教學目標,強調用數據說話,引導教師結合數據診斷學習質量并協調教學進度。為達成目標,校長推進在線教學經歷“直播教學”“年級組授課+個性化指導”“班級授課+個性化指導”三階段,此過程中,教師每日獲取學生學習表現曲線,診斷薄弱知識點并進行個性化輔導;年級組每周查看班級間的差距,協同教研為薄弱班級的教師提供教學法支持;校長每兩周查看年級與班級報告,根據班級進度與學習表現調整教學方案(11-D)。當學校利用數據開展規劃、推動在線教學變革、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與績效評估時,有助于在線教學效能的顯著提升[19]。
(4)“變革—迭代”的綜合施策型路徑(H123)
H123路徑由組態H123a和H123b組成,表明對在線教學有積極認知、能夠傳遞在線教學愿景并創設育人文化的校長,若能協調教學進度或支持教師發展,即使未重新部署在線平臺,未受他人影響,也可能具有積極的持續意愿。代表案例是兩個市區校校長,均在疫情前開展過在線教學。這一現象可用適應性結構理論解釋,由于技術結構與組織行為存在遞歸關系且相互迭代塑造,當技術精神與組織精神一致時,有望以合規方式使用技術并形成組織文化[20]。當校長的技術認知與在線教學本身的價值相一致,能夠認同在線教學的價值、理解在線教學對線下教學的優化與變革時,有助于校長忠實地采納在線教學,并隨時間推移迭代形成穩定的行為結構。
這類校長首先確立了規劃育人為本的在線教學變革愿景,掌握在線教學入場的主導權。如J校長具備“承上啟下”的理念,關注線上的核心并抓準線下的變化,反思線上與線下教學目標的異同(17-D)。其次,利用現有在線平臺與資源,促進教師技術應用或開展數據啟發的教學改進,為在線教學持續運行帶來積極示范效應,推進智力資本積累。此外,借助在線平臺開展主題育人活動,記錄學生成長過程、發展狀態并提供干預。B校長利用現有學生成長平臺記錄學生混合學習中的學業能力、日常行為表現、綜合創新能力、體質健康情況數據,并引導教師為薄弱項的學生提供補償教學或身心健康支持等(12-D)。一旦校長能夠自發地借助在線平臺促進學生參與并賦權學生時,在線教學將持續推進與迭代,變革的影響和規模將是持久深遠的[21]。
2. 抑制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路徑分析
該路徑由缺乏三個核心條件(POfz、SDfz、CAfz)的NH路徑表示,表現為對在線教學態度較保守且缺乏能動性、未能借助在線平臺創設育人文化與支持教師發展的校長,具有消極持續意愿,形成“應付—規避”的權宜執行路徑。代表案例是一個鄉村校校長,目前該校正部署智慧校園建設。由于校長受已有認知的局限,導致對在線教學的有限應用和規避心理。有限應用反映為個體有限理性下的決策并非追求最優方案,而是發現滿意方案即可,滿意程度取決于校長經驗、觀念與期望水平,往往沿用過去的應用模式或決策偏好選擇保守、低成本的應用方案,盡管能夠降低決策成本,但資源與服務難以滿足學生差異化需求,自上而下的供給與自下而上的訴求存在錯位。規避心理是校長對在線教學潛在風險采取選擇性規避的心理傾向,傾向于放大在線教學導致的負面影響而未思考如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很多學生未能跟上在線教學進度、家長不能及時監督,導致學生兩級分化嚴重,復學后以線下學習為主(5-R)]。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采用溯因邏輯,通過半結構化訪談、內容分析和QCA方法,有效識別促進和抑制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條件組態,促進路徑包括綜合施策、理念先行、文化浸潤和愿景牽引,抑制路徑體現為權宜執行。這一結果與沈書生教授歸納的四類校長(活力進取、主動探索、彷徨觀望、消極應付)有異曲同工之處[22]。結合該研究,本研究以“認知取向—行為方式”為二維坐標,刻畫校長在線教學持續意愿的影響機制(如圖2所示)。
綜合施策與理念先行組態對應活力進取型校長,這類校長對在線教學具有積極認知,能夠引領在線教學變革,或依托在線平臺協調教學進度、發掘育人文化的浸潤作用(育人導向),或整合現有平臺促進教師研修與改進教學(管理導向);文化浸潤組態對應主動探索型校長,這類校長認同在線教學的未來趨勢和功能價值,利用在線平臺促進育人活動與學科課程的交叉滲透;愿景牽引組態對應持續觀望型校長,這類校長周圍充斥在線教學的探索與應用,崗位使然進行了信息化投入,深思熟慮在線教學的組織方式并基于數據持續調整,嘗試挖掘在線教學的實質價值(管理導向);權宜執行組態對應消極應付型校長,這類校長盡管也經歷了在線教學實踐,但對在線教學存有消極認知與規避心理,多質疑而少建構,在線教學與已有教學實踐的互促程度有限,導致在線教學效果不佳,強化了自身對在線教學的消極認知。
(二)研究建議
基于研究結論,不同認知與行為方式皆可促進在線教學的持續意愿,且這些條件組態既有技術樂觀主義的探索創新,也有技術中立主義的漸進調整。本研究從影響持續意愿的核心條件出發形成可選方案,以期回應“引導校長從被動應對向持續推進轉變”這一命題。
1. 組織主體間實用對話,優先建立在線教學的理性認知
對在線教學的積極或消極認知反映不同主體的技術價值判斷與選擇,并依據在線教學效果而強化或淡化。當線上線下教學產生碰撞時,由于教學組織的若干方面并非總是必然相互支持,其效果具有不確定性,容易引發不同管理者的主觀解讀并產生崇拜或恐懼心理。然而,僅憑當下可見的效果妄下結論難免草率,在線教學的真正價值需隨時間推移持續探索。Thompson指出,對于后果不確定的技術,可采用實用對話的方式建立主體間關于技術價值的共識[23]。主體間通過對話表達對在線教學價值的認可或懷疑,既可能建立對在線教學的價值共識,形成主體間關注在線教學價值判斷和選擇的通約性,也可能仍然存在局部沖突,此時可以作為建立在共識基礎上的反證。
主體間對話重在尋找不同主體對在線教學認知的分歧點,建立主體的認知沖突并調整原有認知結構。對話的情境和主體是廣泛的,可以出現在能力提升研修中,由培訓者作為主持人,邀請參培校長以敘事的方式分享在線教學實施舉措,拋出在線教學實施中的現實困境,引導其他校長分享解決該問題的思路與經驗,此活動可以以輪轉的方式開展。也可以出現在校內研修會議中,通過設計結構化協議(如調優協議),組織管理層與一線教師開展富有成效的對話,對話內容需引發參與主體的審辨反思,反思主題可以是:若在線教學效果不佳,可能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改進;若效果超出預期,可能原因是什么,下一步如何做等。通過對話、反思引導校長及教師重新認識在線教學的價值,建立對在線教學的集體理解并推動學校改進。
2. 嘗試漸進性領導變革,以在線教學承載育人愿景落地
主體間的實用對話一定程度上能夠給予偏見者更新自我認知的機會。若校長仍難以認同在線教學的實質價值,可通過漸進性領導行為變化不斷探索。由于在線教學變革的本質是“育人”而非“制器”,任何教育改革如未真正融入學校并觸及教學,都難以真正惠及學生[24],校長可先懸置對在線教學的認知偏見,發揮在線教學推進的主導權與控制權,在技術滲透中彰顯育人之本。
將在線教學融入育人文化可經歷三個階段[24]:一是體現工具思維的顯性階段,以替代任務或輔助應用拓寬育人的時空向度,以物化制品為載體提高育人活動的趣味性、效率與覆蓋面,發揮在線教學促進育人理念實現的技術工具性;二是體現整合思維的調適階段,將在線教學滲透至教學、課程等次生文化形態,優化重組資源供給方式與內容排列形式,設計體現育人理念的單元或跨學科課程體系,發揮在線教學的工具實在性;三是體現變革思維的隱性階段,將在線教學作為育人文化的內生要素培育學生主體責任,引導學生為達成學習目標而選擇、加工、處理認識對象,引導教師基于數據提供學習決策支持[25],發揮在線教學的育人價值。
3. 開展參與性行動研究,以持續迭代挖掘在線教學價值
在線教學從外在主義的工具性到內在主義的價值性融入的過程,需要校長的整體規劃與漸進調整。參與性行動研究在基于數據的規劃變革與協同反思方面具有系統性,為在線教學的持續變革提供較好的行動范式[26]。作為行動研究的一種,它要求校長建立實踐共同體,以數據驅動的方式研究、評估和改進學校變革中的特定問題,形成新知識并持續解決實踐中的問題。
針對在線教學推進項目的參與性行動研究,校長需要經歷四個階段的循環過程[26]:診斷階段始于校長與共同體的反思,需要基于已有數據(學業表現、訪談、反思日記等)反思學校在線教學的實施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列出可能需要改進的關鍵問題集,協同確定優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了解理論研究與實踐中的做法,提出假設并思考可收集的定性與定量數據;行動階段需要根據研究假設,協同設計并實施在線或混合教學行動方案;測量階段要求校長采用形成性評價的方式衡量行動產生的短期結果,對結果的測量需要與研究問題和假設保持一致;反思階段則要求共同體成員反思已形成的行動方式、收獲及下一輪需研究或改進的問題,并進入新問題的診斷階段。這種迭代過程有助于幫助校長在推進在線教學過程中,批判反思自身教學領導力,創設積極變革的學校文化,促進實踐共同體的專業成長,并縮小教學愿景與現實成效間的距離。
[參考文獻]
[1] 趙曉偉,邵宏宇,沈書生.從應對危機到適應變化:不同類型校長在線教學領導行為特征分析——江蘇省中小學在線教學調查研究報告之四[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2,40(4):61-76.
[2] BHATTACHERJEE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inuance: an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J]. MIS quarterly, 2001,25(3):351-370.
[3] VENKATESH V, DAVIS F D.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J].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46(2): 186-204.
[4] CHEON J, LEE S, CROOKS S M,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readi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2, 59(3): 1054-1064.
[5] S?準REB?準 ?準, HALVARI H, GULLI V F, et al. The rol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 explaining teachers' motivation to continue to use e-learning technology[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09, 53(4): 1177-1187.
[6] 覃紅霞,李政,周建華.不同學科在線教學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愿——基于技術接受模型(TAM)的實證分析[J].教育研究,2020,41(11):91-103.
[7] CHOU H L, CHOU C. A multigroup analysis of factors underlying teachers' technostress and their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ward online teaching[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21, 175: 104335.
[8] 蔡建東,楊小鋒.組態視域下學前教師數字技術采納行為意向誘發機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較分析(fsQCA)[J].電化教育研究,2022,43(4):116-124.
[9] YANG D, WANG A X, ZHOU K Z, et al. Environmental strategy, institutional force,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a manager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9(4): 1147-1161.
[10] TAYLOR S, TODD P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 6(2): 144-176.
[11] HALLINGER P, MURPHY J. Assessing the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behavior of principals[J].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985, 86(2): 217-247.
[12] RAGIN C 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3] FARRELL C C, MARSH J A. Contributing condition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achers' instructional responses to data[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6, 60: 398-412.
[14]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J]. Social forces, 2009, 88(4): 1936-1938.
[15] 景玉慧,沈書生.理解學習空間:概念內涵、本質屬性與結構要素[J].電化教育研究,2021,42(4):5-11.
[16] GRECKHAMER T, FURNARI S, FISS P C, et al. Studying configurations wit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st practices i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J].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18, 16(4): 482-495.
[17] 宋志臣.教育文化論[J].教育研究,2012,33(10):4-11,33.
[18] LOCKE E A, LATHAM G P. A theory of goal setting & task performance[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0.
[19] HARRIS A, CHAPMAN C, MUIJS D, et al. Improving schools in challenging contexts: exploring the possible[J].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2006, 17(4): 409-424.
[20] DESANCTIS G, POOLE M S. Capturing the complexity in advanced technology use: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2): 121-147.
[21] 趙曉偉,沈書生.學校管理者信息化領導力的內涵演變與構建策略[J].電化教育研究,2019,40(11):34-40.
[22] 沈書生.中小學校長信息化領導力的構建[J].電化教育研究,2014,35(12):29-33.
[23] THOMPSON P B. Food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 ethical perspective[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0.
[24] 邱相彬,李藝,沈書生.信息技術作用下的課程文化變革思維[J].教育研究,2017,38(9):92-98.
[25] 沈書生.聚焦學習決策:指向認知發生的數據及其應用[J].電化教育研究,2021,42(11):13-19.
[26] JAMES E A, MILENKIEWICZ M T, BUCKNAM 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using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to improve schools[M]. California: Sage, 2008.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Principal's Continuous Intention of Online Teaching?
ZHAO Xiaowei,? WANG Weihao,? SHEN Shus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Online teaching, a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offline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Whether online teaching can be rationally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depends on the vision of the principal. Based on the "cognitive-behavior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orm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principals' continuous inten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nd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7 school principal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identifies four paths which would promote principals' continuous intention of online teaching, namely, idea-first path, culture-infused path,vision-driven path and synthesized-measure path, and also finds a path that inhibits the continuous intention called the expedient implementation path. This study provides a detailed portrayal of each path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and then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principals' continuous inten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Keyword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Online Teaching; Leadership Behavi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2019年度國家一般課題“適應性學習空間支持下的學習范式研究”(課題編號:BCA190081);2021年南京師范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選題資助計劃(課題編號:YXXT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