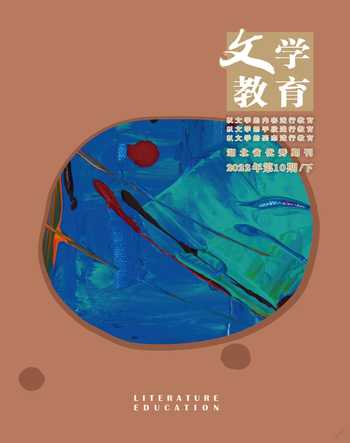電視劇《陳情令》中人物的創傷與療愈
胡夢蝶 楊芳
內容摘要:本文主要運用西方創傷理論,輔以心理學、權力、悲劇、解構等學說,從教育的視角探究《陳情令》中多位人物的不幸命運,如出身低微之恥,家庭教育之失,雙親缺席之殤等,以及由此引發的身份焦慮,產生的心理創傷,以及創傷的療愈方式,結合當前國內中產階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慮現狀,為“雙減”政策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提供現實思考。
關鍵詞:《陳情令》 《魔道祖師》 家庭教育 身份認同
《陳情令》是近年口碑尚佳的國劇,播放前已憑借原著小說《魔道祖師》的熱度備受關注,收官時沖上頂流,成為當年亞洲電視劇收視率之王,一舉囊括各項大獎。該劇2019年一上映便引起學界關注,次年發文量達峰值,雖近兩年熱度有所下降,但因問世不足三年,故尚有研究空間。既有研究集中傳媒和文化研究領域等外部視角,針對劇外內容較多,為數不多的劇集內部研究多是綜合分析多重要素(如情節改編、人物刻畫、服化道造型、音樂藝術等)從中探尋劇集獲得成功的原因,對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不夠深入。本文認為,《陳情令》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劇中人物的復雜性體現。他們的苦難人生,無論是出身低微之恥,家庭教育之失,還是雙親缺席之殤,都給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導致了身份認同危機,促使他們找尋心靈療愈之路。基于此,本文立足劇情,聚焦劇中人物的不幸命運,從教育的角度分析其身份焦慮、創傷成因及療愈方式,以期為當今“雙減”政策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提供現實思考。
一.出身低微之恥
《陳情令》中,金光瑤和薛洋為人不齒,主要由于他們不體面的出身;江楓眠雖傾慕藏色卻終另娶虞氏,乃因虞夫人家門顯赫,金子軒起初羞于聯姻江氏,也是出于懸殊的世家地位。魏無羨和藍忘機同樣出類拔萃,但前者的傲氣被看作年少輕狂,后者的高冷卻被視為雅正之風,其原因莫過于名門出身給藍湛做了有力背書,而魏嬰一介家仆之子,理當任人貶損污蔑。可見,整劇劇情預設了一個底層邏輯——森嚴的階級觀。
低微出身給魏無羨造成了巨大困擾。事實上,他的少年生活未必像他所述那般美好:在內,主母虞夫人因與魏嬰母親藏色曾是情敵,故對他心懷嫌惡,把丈夫的冷落遷怒于無辜的魏嬰,常冷嘲熱諷,罰跪祠堂。如果虞夫人是顯性霸凌,那么少主江澄則是隱性欺壓。江雖聲稱與魏情同手足,但他言語間帶著居高臨下,多次不顧外人在場訓斥師兄。在外,魏嬰畢竟不是江宗主血脈,卻享受了正統世家公子待遇,這將他的身份懸置在公子和野夫之間,免不了人前背后遭到閑言碎語。早期流浪經歷,使魏嬰倍加珍惜云夢的現世安穩,加之感念江家之恩,種種委屈他只得隱忍,這造成了他的心理創傷。他對外桀驁不馴,口出狂言,正是他滿腹怨氣的外化。
為了尋找身份定位,治愈心靈,魏嬰首先通過記憶修正的方式療愈。既然記憶是“主體站在當下立場對于過去的建構”(Newman,338),那么記憶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可靠性和自我虛幻性。他對藍湛描述的童年回憶更多是經記憶粉飾過、改寫過的的版本,這既是善良的他對云夢江氏世家體面的維護,更是他對抗卑微自我、保護自我的方式。他的不可靠敘述具有自我防御屬性。通過記憶改寫,他期望創造一個想象中的完美童年,消弭真實經歷中的不快,填補自我心理缺失的滿足,重建自我與欲望的同一性關系。如果改寫記憶比較消極,那么魏嬰還積極地見賢思齊,激勵自我成為“超人”。他用自己的卓爾不群成功地贏得了世家楷模藍忘機的欽佩:劍尚未出鞘,便和持劍的藍湛打成平手。考慮到藍湛日日勤勉,魏嬰玩世不恭的治學態度,魏嬰的武學天資遠在藍湛之上。而且魏嬰聰慧機智,天馬行空地想到化怨氣為己用,雖遭來斥責,但他射日之爭一戰成名,風光無限,用行動證明了自己想法的可行性,打臉了遷腐的權威藍老先生。聽學結束放天燈時,魏嬰立志“鋤強扶弱,無愧于心”,令藍湛對他刮目相看。他之后竭力救助溫氏無辜,也踐行了這一諾言,影響了藍湛的人生走向。總之,魏嬰的優秀、正直和善良,洗白了他的卑賤出身,使他超越了階級局限,升華成一代宗師。
和魏嬰境遇類似,三位反派金光瑤、薛洋和蘇涉也都受低微出身所累遭遇了太多侮辱和輕賤。這些負能量的堆積,激發了他們對權力歇斯底里地追求,對社會的變本加厲地報復。值得一提的是,故事把反派作惡幾乎全部歸因于出身:娼妓之子,私生子、底層草根等,暴露出編劇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當前,階級固化日益尖銳,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可能會導致一系列不和諧的社會現象。因此,應打開階級壁壘,緩和階級差異,擯棄出身決定論的偏見,對低階但才華出眾的“鳳凰男女”正向引導,使他們也成為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
二.家庭教育之失
在福柯的經典權力模式中,君主權力指使用暴力鎮壓否定,強調統治的絕對中心,而規訓權力則采用空間隔離的方式,按照一定紀律將規訓對象改造成符合權力意愿的客體。劇中,江澄和藍湛的非正常家庭教育與這兩種權力有著指向性關聯。
1.君主權力模式——“虎媽”式壓制教育
作為云夢江氏唯一繼承人,江澄本應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但是他暴躁易怒、好強善妒,躁動不安,與他天之驕子的身份極其不符。江澄的創傷,一部分歸結于父親的冷暴力,更重要的是來自虎媽虞夫人君主權力驅使下的壓制教育。她恨鐵不成鋼,常譏諷挖苦兒子不成器。江澄不停被比較,被打壓被批判,心理不斷失衡,極度缺乏安全感。
虞夫人的打壓教育造成了江澄功利主義人生觀,導致江澄篤信成王敗寇,只在乎個人名利,家族安危,與魏嬰奉行“鋤強扶弱”的大義格格不入。雖然虞夫人和江澄或明或暗的施壓常讓魏嬰深感委屈、無助和孤獨,但江叔叔和師姐無私的愛照亮了他心中陰暗的角落,補償了他的心靈失衡。江宗主不顧夫人反對,毅然抱養了小魏嬰,待他甚至比親生子江澄更親近,師姐江厭離也一直把他看作親弟弟,給了他母親般的疼愛和寵溺。百鳳山圍獵場,面對強勢的未來大舅子金子勛對魏無美的無理指責,師姐不卑不亢,以退為進,堅持要求對方道歉。所以魏嬰本質上善良仗義、有責任心和道義感,沒有心懷歹念,淪為惡人。反觀江澄不止一次抱怨魏嬰的“英雄病”,不識時務行俠仗義。江澄明知溫情姐弟是無辜的株連者,也明知對方有恩于己,但面對眾家聲討和刁難,為逃避社交壓力,他還是勸魏嬰看清形勢,違心從眾。可見,江澄心中權力才是正義,趨炎附勢才是生存之道。不同的人生觀使魏江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
江澄的高壓家庭教育最嚴重的后果是,江澄把母親打壓諷刺的教育模式如法炮制給了外甥金凌,使金凌呈現出和他相似的性格缺陷:驕矜自傲、暴躁易怒、敏感自卑。好在重生的魏嬰帶他和其他小輩一起夜獵,給他補了輕快放縱的一課。這種快樂教育得到了金凌的認可,金凌不再視他為殺父仇人,觀音廟主動為他趕走愛犬,還鼓勵江澄找他和解。雖然江澄最終未能找尋到彌合創傷療愈方式,但他的外甥金凌在含光君和夷陵老祖的共同教育下,在與玄門同伴的交往中矯正不足,成為了心靈健全的少年。
2.規訓權力模式——壓抑式的家規教育
陳情首席男神藍忘機“皎皎君子,澤世明珠”,連一向自恃甚高的魏無羨都對這位知識有廣度、思想有深度、靈魂有溫度的仙門名士另眼相看。實際上藍湛絕非完美偶像,他的創傷源于姑蘇藍氏清教式的規訓教育。嚴苛的《藍氏家規》形塑了世家涵養和良好家教的同時,也極度摧殘了人性。藍湛自小禁閉在云深不知處,受訓于三千條家規,過早成為權力規訓的對象,泯滅了兒童天真爛漫、不諳世事的本真,雅正到近乎古板,顯示出與年齡嚴重不符的老成持重,活成正統價值觀的大寫的文化符號。
人前,藍忘機是高山仰止的含光君,私下他卻忍受著高處不勝寒的孤獨,直到魏嬰一張笑臉一把劍點亮了藍湛暮鼓晨鐘的生命。藍湛內心深處,何嘗不想成為那個明媚跳脫、活力四射、愛憎分明、瀟灑無羈的魏嬰式少年呢?魏嬰的“劣跡斑斑”釋放了藍湛心中被壓抑的欲望。魏嬰的離經叛道,在藍湛眼里處處彰顯著人性的光輝:聽學期間質疑學術大咖藍啟仁老先生的權威、金陵臺上叫板第一家族蘭陵金氏、窮奇道拯救沒落家族溫氏殘余……魏嬰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正是藍湛想做不敢做的“本我”。
魏嬰放天燈的誓愿激起了藍湛的深深共鳴,征服了他孤傲的心。“鋤強扶弱”既是忘羨情的出發點,也是終極歸宿,是他們兩世的契約,維系了他們恒久的知己情。窮奇道是藍湛人生重要的轉折點。滂沱大雨使兩人形成鏡像關系——魏嬰就像一面鏡子,照出藍湛榜樣形象背后是可笑的膽怯和顧慮。藍湛欣賞魏嬰鮮明的是非感和強烈的責任感,欣賞他不畏強權的膽識。旁人眼中大逆不道的魏嬰活成了藍湛的偶像。忘羨情,與其說是小我的兒女情長,不如說是對“鋤強扶弱”的認可和堅守。藍湛對魏嬰逐步接納的過程,也是他看清本真,回歸真正自我的成長歷程。一場大雨如同一場神圣的宗教洗禮,給了他天啟般的頓悟,使他脫胎換骨。云深不知處漫天遍野的白兔既象征著忘羨知己情,又喻指了他們共同人生抱負。佛經所載,兔子用自焚的肉身供養了修行人,佛祖以兔子自況,強調舍生取義的犧牲。若魏嬰為保護溫氏無辜做了英勇就義的兔子,那么藍湛為保護魏嬰代表的家國情懷,也毅然犧牲“景行含光”的聲譽,徹底拋開腐朽的家規戒律,為維護魏嬰,維護理想自我,維護心中的正義。三十三條戒鞭打死了昔日刻板嚴正的“楷模”,也涅槃了無畏強權,堅持正義的真我。正因心懷天下,藍湛最終甚至放下了與魏嬰的個人情愫,毅然決定擔負起仙督的職責。
從江澄和藍湛失敗的家庭教育中或許能夠管窺兒童教育的一個原則:對于有心靈創傷的孩子來說,教育不應用權威自上而下地去壓制,或用規訓權力去壓抑。目前全民陷入了激娃內卷的怪圈,各種天價培訓班市場亂象,國家及時出臺“雙減”政策,向繁重的學習負擔說不,將學生從權力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減輕了家長的教育焦慮,還學生一個健康的校園氛圍。
三.雙親缺席之殤
藍湛對魏嬰的知己情,除了魏嬰的優秀和嚴苛家教誘導外,也源于藍湛早年的戀母情結。他的兄長藍曦臣曾提過,他們父母雖一見鐘情,但因母親錯殺了丈夫青蘅君的恩師,夫婦相愛卻不能廝守。父親常年閉關,在藍氏雙壁的成長過程中幾乎缺席,母親被藍氏幽禁,每月方得一見子嗣,且尤其喜歡逗忘機。父母一個抑郁早逝,一個看破紅塵,婚姻中充滿了遺憾。失恃之痛,父母的缺席,是藍湛終身的陰影,導致他性格冷漠自閉,沉默寡言。
青蘅夫人英勇中透著魯莽,英氣里含著頑皮,快意恩仇,敢愛敢恨,活脫脫一個女版魏嬰。所以藍湛對魏嬰的感情,參雜著對母親的愧疚。兒時的他能力有限,未能保護飽受禁足之苦的母親,未能彌合父母的嫌隙,未能消弭家族對母親的仇視。他對魏嬰的袒護,是以一種曲折的方式向母親贖罪。知己死后,他固執問靈十三載,如同當年母親病逝,他固執立于門外,等母親歸來為他開門一般。
進一步說,藍湛的創傷復現了姑蘇藍氏的“代際間幽靈”(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即“家族隱秘的創傷在后代的心理空間中重復表演, 形成作為創傷間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陶家俊,120)。如果內斂不逾矩的藍湛象征著希臘悲劇的日神精神,那么劍走偏鋒的魏嬰便是酒神的化身。無獨有偶,可以挖掘出姑蘇藍氏“日神一酒神”的群像:如果青蘅夫人是酒神魏嬰的翻版,那么年少成名的青蘅君應如日神藍湛一般俊美克制;如果滿腹經綸、迂腐板正的藍啟仁象征日神,那么他頑劣調皮的學友藏色便是與他對立的酒神。可惜,藍氏首代“日神一酒神”只是初會,未能真正融合,但為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的想象。到了藍魏這一代,日神—酒神交鋒之巔是窮奇道雨夜。大雨激發了藍湛心中酒神的一面,讓藍湛放下古板的條條框框,不再將家規奉為圭臬,亦不再追問孰正孰邪,而以“鋤強扶弱”的大義為終極人生意義。魏嬰重生后,藍湛也不再規訓不羈的酒神,對他多了理解和寬容,同時,獻舍重生的魏嬰也少了輕佻沖動,多了份日神的沉穩和自控。至此,日神—酒神沖破重重阻擾,為了共同的信念,穿越生死,堅定地站在一起。到了下一輩,姑蘇藍氏既培養得出板正的日神藍思追,也容得下不羈的酒神藍景儀。景儀心直口快,懟天懟地,不似藍氏子弟,反像夷陵老祖。他能夠安然存于姑蘇,背后是藍湛的縱容和默許。思追和景儀同氣連枝,毫無嫌隙。日神和酒神的完美交融打破了藍氏悲劇的詛咒,從此不再有飲恨終生的怨侶,也不再有心靈創傷的子弟。
縱觀整部劇,多位人物都有雙親缺席的經歷,或父母早逝,或父母基本不在場,如藍氏雙璧、魏無羨、金光瑤、薛洋、金凌、聶氏兄弟、思追景儀、雙道長等等。聯系現實,有些父母過分迷信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忽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逃避父母的責任。實際上,兒童的性格形塑遠早于學前,家長的缺席極易造成兒童的心理創傷。所以父母應盡早投身到家庭教育的角色中,使子女得到正向教化和溫暖激勵,即使有創傷也能及時療愈,避免悲劇命運。
《陳情令》通過懸念環環推進,節奏緊湊且張弛有度,細節處理細膩,人物形象飽滿。忘羨之間惺惺相惜的默契,義無反顧的仗義,克制隱忍的對視,感動著無數觀眾。整劇既彰顯了中華的器物文化和儒釋道精神,也弘揚了“鋤奸扶弱”的俠之大義,不僅得到了大眾媒體的贊譽,也贏得了新華社等官媒的高度肯定。本文從教育角度出發,考察劇中人物心理創傷的成因、身份認同的找尋及創傷療愈的過程,以期為“雙減”政策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提供現實思考。
參考文獻
[1]Newman,Birgtt.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Memory[C]//Astrid Erll and Ansgar Nunning.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10.
[2]陶家俊.創傷[J].外國文學,2011(04):117-125+159-160.DOI:10.16430/j.cnki.fl.2011.04.022.
本文系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使女的故事》中極權政治書寫研究”(編號:2021SJA2260)階段性成果,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學院科研項目“文化符號學視域下英語電影片名翻譯研究”(編號:njpj2021-2-1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