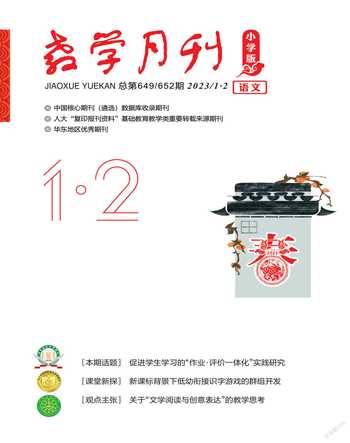關于“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教學思考
周一貫
【摘 ? 要】從學生自幼接觸文學作品的現實出發,認識“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這一學習任務群的基本內涵,厘清文學的“思想性”“真實性”和“典型性”,并提出“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相關教學策略:充分理解文學作品是教材選文的主旋律;正確認識科普作品中的文學嫁接;深入感受紅色經典課文中的文學色彩;在沉浸式審美和文學滋養下學習創意表達;在范文引領下進行多種文學體裁的習作嘗試。以此解答教師在這方面的疑問。
【關鍵詞】文學;文學閱讀;創意表達
不少一線教師認為,“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看起來似乎比“實用性閱讀與交流”的教學難度更高。其實不然。對學生和教師來說,接受“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并不會比接受“實用性閱讀與交流”困難許多。可以這樣說,孩子出生后,就生活在一個文學的環境里。他們最早聽到的催眠歌謠就是文學作品,不久后看到的花花綠綠的圖畫書也是文學作品。他們聽慣了的大人們講的故事,更是不折不扣的文學作品。至于教師,誰都有過接受文學的童稚時代,當時接觸的語文教材中有極大部分課文屬于文學作品,自然更具有對文學的親近之情。一句話,大家生活在一個文學的世界里。而且,文學似乎更切合孩子的認知特點和心靈世界。
小學階段的“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與小學生的年齡特征和接受能力十分切合。對此,《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以下簡稱“2022年版課標”)就明確指出了具體要求與操作方向:“旨在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活動中,通過整體感知、聯想想象,感受文學語言和形象的獨特魅力,獲得個性化的審美體驗;了解文學作品的基本特點,欣賞和評價語言文字作品,提高審美品位;觀察、感受自然與社會,表達自己獨特的體驗與思考,嘗試創作文學作品。”[1]26這里所涉及的要求與范圍,都指向小學生現實存在的學習活動。可以說,“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是兒童生命成長和發展中的應有之義。
一、“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內涵解讀
雖然學生自幼接觸文學作品,但是接觸文學作品與了解文學不完全是一回事。什么是“文學”?現代專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藝術,所以也稱“語言藝術”。文學通過作家的想象活動把經過選擇的生活經驗體現在一定的語言結構之中,以表達人對某種生存方式的發現和體驗。[2]如前所述,孩子出生后不僅生存在一個現實世界里,也生活在一個文學世界里。從某種角度說,兒童對文學并不陌生,而且他們的思想和言說,往往更多地會帶著文學的色彩。但是教師指導學生閱讀文學作品卻并不簡單,需要基于更多的了解和素養。
從歷史來看,“文學”一詞的意蘊是有所變化和發展的。先秦時期,“文學”曾泛指包括哲學、歷史、政治等在內的一切學術和文化方面的書面著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將文學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現代則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多種體裁,在各類體裁中又有多種多樣的形式。[3]這樣,就會出現因文本(通常指應用文、記敘文、說明文和議論文)與文學作品(通常分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類)相互融合而產生中介性的新文體。如果從“實用性閱讀與交流”這一學習任務群的角度分析,并不缺少有關“如何說明”的啟示;如果從“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視角思考,也有相當豐富的教學機遇。所以,在教學實踐活動中不宜作決然的割裂。對此,2022年版課標在“課程內容”部分,針對“內容組織與呈現方式”,明確指出:“語文學習任務群由相互關聯的系列學習任務組成,共同指向學生的核心素養發展,具有情境性、實踐性、綜合性。”[1]19這說明各學習任務群之間不是截然分割,而是“相互關聯”的,只有“相互關聯”,方能“共同指向學生的核心素養發展”。
根據馬克思主義對文學藝術起源的解釋,最初的文學藝術是原始人在生產勞動中創造的:或是勞動經驗的介紹,如原始洞穴壁畫;或是勞動生產的美化,如原始舞蹈;或是組織協調勞動動作的手段,如原始歌謠;或是以幻想征服自然,爭取豐收的理想,如神話。當然,受生產發展水平的影響,原始人的文學藝術多為音樂、詩歌、舞蹈這三類,并以勞動的節奏為共同紐帶。這說明,文學不是遠離生活的尊貴殿堂,而是人們勞動中的產物。當然,對于“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基本內涵,還應有以下一些方面的認識。
一是文學的思想性。所謂“思想性”是指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所顯示出來的全部思想意義和認知價值,通常是指進步的、革命的思想。對于思想錯誤或反動的作品,一般不用這個概念。作品的思想性,是題材的客觀意義和作者的主觀思想情感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其中,作者的主觀思想情感居于主導地位。它既影響到作品題材的選擇,又關系到對題材的評價與開掘。所以,作品的思想性取決于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當然,許多具體的、產生于各個歷史時期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質,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具有進步性,又或多或少對生活作了某些不正確的甚至是歪曲的描寫,流露出一些消極的思想情緒。對于這種瑜瑕共存的狀態,我們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去區別對待,有批判地吸收。
二是文學的真實性。這里指的是文學作品反映生活、揭示生活所達到的真實與深刻的程度。所謂的真實,指符合生活的本質及規律,體現了歷史發展的方向,而不是指具體的真人真事。這就與作者的三觀、生活經驗、藝術修養密切相關。文學因為采用了集中概括的手段表現主旨,所以可以比生活更真實。
三是文學的典型性。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是自然存在的,也往往是粗糙的、分散的,有的只體現了本質的某一方面,有的只體現了本質的非主要方面。但文學作品通過藝術形象所顯示的必須是社會生活的某種本質和規律。它以真實生活為基礎,又比實際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普遍性。這就是文學作品既源于生活而又能高于生活的關鍵所在。因此,文學作品的典型性總是與藝術塑造的方法聯系在一起,它表現的可以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可以是生活中可能有或應該有的人和事。由于各種藝術方法的特點不同,藝術的典型性和真實性往往會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如:現實主義要求作品中所表現的生活與客觀的實際生活,從外在現象到內在本質都相近,雖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但卻能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子來表現生活;浪漫主義則可以在合乎情理與生活邏輯的前提下,采用幻想、夸張、擬人化等手法虛構人物和故事,即改變生活的外在形式來表現生活,以揭示生活本質。
在指導學生閱讀文學作品時,教師雖然無須把這些文學相關的基本理論直白地告訴學生,但應當在教學過程中相機滲透和點撥,特別是在學生質疑問難時相機誘導,幫助他們提高閱讀文學作品和創意表達所需的能力。如統編教材三年級下冊第二單元的首頁配了《鷸蚌相爭》的插畫,在教師作單元導讀時,學生提出:“從畫上看,鷸把蚌啄住了,而蚌又把鷸的嘴牢牢鉗住,怎么它們還會說話?”教師就讓學生反思“如果蚌有嘴,那么它們的眼睛、鼻子又在哪里”,從而使學生進一步理解,這只是用擬人的方法講故事,以便說明某種道理。正如2022年版課標對“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所強調的,本學習任務群不求學生對文學理論進行系統的學習,而是“旨在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活動中”,通過“整體感知、聯想想象,感受文學語言和形象的獨特魅力”,并從中“獲得個性化的審美體驗”。當然,也要從中“了解文學作品的基本特點”,但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學生要在不斷“觀察、感受自然與社會”的過程中“表達自己獨特的體驗與思考”,甚至“嘗試創作文學作品”。顯然,這樣的過程和要求,無疑能讓學生長期受到熏陶和感染,并逐步獲得提升。
二、“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實施要則
在教學實踐中,針對“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有哪些注意事項?
(一)充分理解文學作品是教材選文的主旋律
應當看到,小學語文教材的選文主體是文學作品。這是因為文學作品的生動形象源于對生活的藝術創造,其形式活潑多樣,故事富于想象,語言優美生動,特別適合兒童閱讀。
從統編教材看,一年級上冊編排了大量的兒歌、童詩和韻文,如起始教育《我上學了》中的《上學歌》,識字單元的《金木水火土》《對韻歌》以及寫雪花的詩謎,拼音單元中的《輕輕跳》《說話》《在一起》《繞口令》《剪窗花》《歡迎臺灣小朋友》《家》,課文單元中的《小小的船》《青蛙寫詩》《雪地里的小畫家》……入選的古詩也有好幾首,如《江南》。就一年級下冊來說,課文多了,歌謠、兒童詩雖然相對少了些,但仍然占著主體位置。課本第一單元是“識字”,第1~4課全部是韻文。《誰和誰好》《一個接一個》《怎么都快樂》等兒童詩和入選的古詩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還以專題形式出現了讀讀童謠和兒歌的“快樂讀書吧”。
從二年級上冊開始,課文主體由“兒童歌謠”轉變為“童話故事”。二年級上冊以“兒童故事”為重點,三年級下冊則比較多地編排了“寓言”,讓兒童感受“小故事大道理”的睿智。接著便是四年級上冊的“神話”和四年級下冊的“科學小品文”。第三學段(五、六年級)更多涉足小說,不僅有長篇小說的節選,還有白話小說(中國四大古典名著)和小小說(如《橋》)。同時涉及戲劇(如《京劇趣談》《藏戲》)和外國著名文學作品(如《魯濱遜漂流記(節選)》《騎鵝旅行記(節選)》和《湯姆·索亞歷險記(節選)》。
正因為文學作品是教材選文的主旋律,而且從一年級開始就以兒歌、童話吸引學生,自然十分有利于“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這一學習任務群在教學實踐中的落實。
(二)正確認識科普作品中的文學嫁接
作者提筆為文,因其內容和形式特點的不同而呈千姿百態。人們把內容和形式特點相近的作品歸為一類。然而,文學作品是歷史的產物,有著時代的印記。“世道既變,文亦因之”,文體也與萬事萬物一樣,處在不斷的變化中。盡管我們強調作者揮筆為文前要有文體意識,但畢竟寫作是作者個性化的表達,驅遣文字時更多的是“跟著感覺走”,寫著寫著,有時會很自然地超越文體的藩籬,有了客觀上的“跨界”之舉。這樣的跨界多了,就會形成一種介乎兩種體裁之間的新文體。
如科普作品是講科學知識的,本來與文學并不搭界,但為了將抽象枯燥的科學知識講得生動,就必須借助某些文學的魅力,久而久之,便慢慢形成了一種結合科學知識內容與文學樣式的新體裁,名為“科普文藝”,包括科學隨筆、科學小品文、科學雜文、科學童話、科學詩等等。又因為小學語文課在落實語言文字的積累和運用的同時,又承擔著知識傳授的責任,所以,為了有最好的閱讀效果,傳授知識類的課文應當力避枯燥和單調。科普內容與文學樣式的結合,自然成了最理想的方式。于是,課本選編了大量有這類體裁特點的課文。如一年級上冊的《小蝸牛》、二年級下冊的《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三年級上冊的《在牛肚子里旅行》、三年級下冊的《花鐘》、四年級上冊的《夜間飛行的秘密》、四年級下冊的《琥珀》、五年級上冊的《太陽》、五年級下冊的《金字塔》、六年級上冊的《宇宙生命之謎》等。由于這些課文均采用了某種文學表現手法來傳遞科學知識,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要讓學生讀懂它的知識內核,同時也要接受它的文學樣式,獲得審美的陶冶,且這兩者應該和諧融合、自成一體。
(三)深入感受紅色經典課文中的文學色彩
語文教學的根本理念之一在于“立足學生核心素養發展”“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充分發揮其獨特的育人功能和奠基作用”[1]2。顯然,紅色經典課文的教學,無疑是十分重要的部分。紅色經典課文的主體是中國革命斗爭的光輝史實,敘寫的是真人真事,它們是“記人敘事的優秀文本”。同時,這類課文又有很強的文學性。因此,在小學各學段都是“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重要內容。如第一學段要求“閱讀并學習講述革命領袖、革命英雄、愛國志士的童年故事,表達敬仰之情和向他們學習的愿望”。第二學段則提出“閱讀并講述革命故事、愛國故事、歷史人物故事,感受幸福生活來之不易,表達自己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對革命英雄、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第三學段的要求更高:“閱讀、欣賞革命領袖、革命先烈創作的文學作品,以及表現他們事跡的詩歌、小說、影視作品等,感受革命領袖、革命先烈偉大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認識生命的價值;運用講述、評析等方式,交流自己的情感體驗。”[1]27所以,在這類課文中真實性與文學性是同時并存的,在教學中應兩者兼顧,不可偏廢。如統編教材二年級上冊的《八角樓上》,講述了革命領袖毛主席在艱苦的革命斗爭環境中日夜操勞、忘我工作,領導中國革命在艱難困苦中走向勝利的故事。在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課件進行補充,使學生對課文反映的背景有所了解,同時讓學生以“學講革命故事”為載體識字學詞,厘清課文結構,實行多元整合。“講故事”的過程就是感受革命領袖偉大精神的過程。可采用“巧設情境”的“三步實踐法”,即第一步“初讀課文,理解詞語,抓住要素,有條理地講故事”,第二步“抓細節要素,具體地講故事”,第三步“悟精神要素,生動地講故事”,真正做到真實性與文學性有機結合。
(四)在沉浸式審美和文學滋養下學習創意表達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源于人類的勞動生活,為人們所喜聞樂見。所以,小學進行“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的訓練,正當其時。
學生從口頭表達轉向書面表達,其產生、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程:先由學生的生活萌發表達動機,再由表達動機強化為寫作行為。如果這個過程是由學生自發推動的,其中必定會充滿創意。如果這種表達是由教師嚴格授意,并要求學生去努力“達標”的,那么“類同表達”會從根本上銷蝕本來所有的創意,而扭曲成為千篇一律的“雷同文”。這是學生自由表達遭到不適當干預所帶來的結果。綜觀統編教材對學生習作的要求,不難發現,其關注的正是表達中的創意。以三年級上冊的單元習作為例,第一次是《猜猜他是誰》,創意就在于“用幾句話或一段話寫一寫他”,不能在文中出現他的名字,但是要讓別人讀了內容后,能猜出寫的是誰。這顯然是學生愛玩的游戲,各人的創意就在其中。第二次是《寫日記》。寫什么?創意全在“說說你有什么發現”上。第三次和第四次分別是《我來編童話》《續寫故事》,“編”和“續”無疑是最有創意的。第五次、第六次分別是《我們眼中的繽紛世界》和《這兒真美》,都需要學生自己去發現值得書寫的內容。第七次是《我有一個想法》,童年是“想法”最多的一段生命歷程,也是“創意”最多的一個生命階段。最后一次習作是《那次玩得真高興》,玩得“真高興”總是與花樣出新相關,創意就在其中。由此可見,在文學滋養下進行創意表達,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的習作回歸自我、回歸生活、回歸真實。應當說,這是最容易做到,也往往是最有創意的。
(五)在范文引領下進行多種文學體裁的習作嘗試
2022年版課標對“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這一學習任務群提出了“嘗試創作文學作品”的要求。這里的“文學作品”指的當然是采用了某種文學體裁的學生習作。這不僅需要,而且可行。其實,這一要求已體現在統編教材之中,如三年級上冊第三單元習作便是《我來編童話》。其所在單元是童話單元,要讓學生“乘著想象的翅膀,游歷奇妙的童話王國,看花兒跳舞,聽星星歌唱”“感受童話豐富的想象”,然后才順理成章地提出“試著自己編童話,寫童話”的要求。而且,教材還提出了三組關鍵詞作為引領:一是“國王”“啄木鳥”“玫瑰花”;二是“黃昏”“冬天”“星期天”;三是“廚房”“森林超市”“小河邊”。三組關鍵詞分別提示了故事的主人公、時間和地點,而主人公又分別是“人”“動物”和“植物”。在如此精心的鋪墊和引領下,讓學生嘗試寫童話,不僅可行,還饒有童趣。此外,四年級下冊第三單元的“綜合性學習活動”是“輕叩詩歌大門”,與寫詩歌相聯系;第五單元的習作《游 ? ? ? ? ?》嘗試寫游記類散文;第八單元的習作《故事新編》是嘗試創作故事。六年級下冊第五單元的習作《插上科學的翅膀飛》是撰寫科幻故事……可以說,結合相關文學體裁的寫作嘗試,機會有很多,因為這是學生在大量閱讀了文學作品之后自然產生的一種讀寫聯動。
文學與童年有著一種合乎天道的契合。兒童生活在富于想象的文學世界里,他們當然也成了文學特別是兒童文學的最大讀者群,而從讀中學寫,更是由讀過渡到寫的自然進階方式。小學階段的兒童可塑性最強,且最易接受形象化的教育。文學作品的閱讀與創意表達會極大地影響他們的性格、氣質、志趣和理想的形成,提升其審美水平。因此,“文學閱讀與創意表達”對于落實好“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的時代新人”的培養要求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2]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七版)[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3]孫家富,張廣明.文學詞典[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浙江省紹興市魯迅小學教育集團和暢堂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