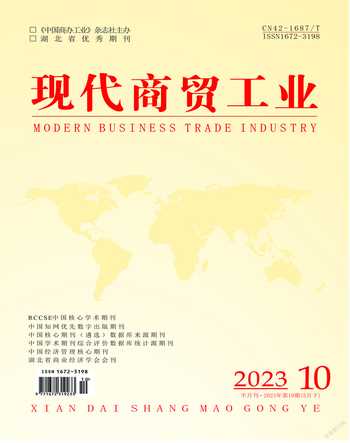關于法治思維及其分層的探析
楊凱
摘?要:法治思維是人理解法治運行的方式,它包含對人、法和自由三個層面的認識。人是社會規定性的結果,自由只存在于社會規定性中。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自身、法、自由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決定了人的法治思維的層次。通過對三者關系本質的理解,人的法治思維可分成遞升的三個層次,第一層:實然的法治;第二層:應然的法治;第三層:實踐的法治。人通過不斷地揚棄舊識,達到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辯證統一。
關鍵詞:法治思維;法治思維分層;實踐;法治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0.056
對于法治思維的含義的理解,比較流行的觀點基本或者是從法的價值思維來對法治思維進行概括,或是從現代法治內涵——實質法治和形式法治——來對法治思維進行分析,這些概括和分析都以不同的角度對法治思維進行了辨析。但是,這些辨析的結果,正如陳金釗教授所言:“就世界范圍法學研究的現狀看,盡管思想家們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人們所揭示的法治,仍然是一個家族相似的概念,并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
法治思維本質上說是屬于思維的范疇,而思維的主體是人。因此,對法治思維的分析,可以以人為出發點,考察人與法治的關系。進一步看,關于法治思維的討論無外乎是法的規定在何種程度上處理與人的自由的關系以及人在何種程度上考察自身、法與自由三者之間的關系。準此而言,當我們論及法治思維,或者更進一步論及這樣的法治思維是否在思維中具備一定分層,則首先一步是要對人、法與自由這三者進行辨析。
1?關于人、法及自由的理解
人之所以為人而不為他物,這一分別是通過規定性來完成的,也正是這樣的規定性給予了人的本質。決定人本質的規定性是什么?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其自身的規定性,規定性下事物均各得其所,是為此物而不為他物。但是,為了維持一般的自然實體,事物都有著共同的一般規定性。與此不同,人在已有的事物的一般規定性上更進一步,通過勞動下的社會實踐逐步建構了社會規定性,“當人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個體時,他顯然無法被視為本來意義上的人;唯有融入包含多方面的社會實踐過程,不斷確證其內在本質,個體才能走向真正的人。”這個實踐的過程就是人賦予自身社會規定性的過程。人是人作為生物意義上的個體通過實踐形成規定性的結果,“人”就是人的本質,當我們討論“人”時,我們實際上討論的就是人的社會規定性。人的歷史是人社會實踐活動的總和,是人的知與行的統一,從這一層面上說,人是人的歷史的存在與存在的歷史,自身開展歷史并通過歷史進一步展開自身。在這開展與展開的社會實踐過程中,作為原因和結果的社會規定性不斷豐富和完善。社會規定性也就是人的社會實現和人的社會現實,是決定人本質的規定性。
在人通過社會實踐形成社會規定性的過程中,法作為社會規定性的表現形式誕生了。法是人的歷史開展的一項結果,它總是伴隨著社會實踐的豐富而豐富、系統而系統、目的而目的。自古以來,無論任何社會以何種形式立法,對于法的證成本質上就是人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對于自身社會規定性的確認(比如統治階級的法根本上是處于統治地位的人將自己的階級性質通過法的形式加以確認,并以法要求他人對自己的階級性質加以確認)。
如果說,社會規定性通過法的形式賦予人以規定,那么另一方面看,這又必然涉及到另一在表征上似乎是對立的概念——自由。自由與法,共同構成了法治沖突表征的兩個方向。
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古以來,人不斷追問自由從何而來,立足于何地,又向處發展?對此,長期有這樣一種觀點,人的自由首先應該是與規定人的法是兩個相互排斥的東西。自由的存在就是反對法對人的規定性。黑格爾探討過這樣的觀點,他將這種將自由抽象化并與現實相分離的反思方式,稱之為反思的知性,即“指一種從事抽離和分裂,并且堅持其分裂狀態的知性。……理性限于僅僅認識主觀的真理,僅僅認識現象,僅僅認識某種不符于事物本身的本性的東西;知識已經墮落為意見。”這里,反思的知性作為外部反思,只是“表現為一種或此或彼的推理能力”,僅僅知道把一般抽象原則運用到自由的內容中去,教條主義或者形式主義地去理解自由,用自由一般的抽象原則閹割了自由的內容,“遮蔽了作為內容本身的現實”。
那么自由被遮蔽的作為內容本身的現實是什么呢?首先是,人的自由只存在于社會規定性中或只在于人的社會現實,或進一步說,正是因為社會規定性或人的社會現實,人的自由才有了自由于“人”的意義,自由跟法一樣也是社會規定性的表現形式,是社會規定性展開的結果;其次是,既然法是社會規定性的表現形式,社會規定性通過法來闡述,處于社會現實中的自由也只能通過法的形式展開。以上兩點也就是說:一方面,自由是在人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生成的,不該先驗地置于人的實踐之上,它不是人實踐的原因,而是人實踐的過程和結果,是人通過社會實踐對自身社會規定性的確證,雖然自由的概念在其認知發展過程中逐漸獲得了某種獨立性的外觀,但是它依然根本上的完全從屬于社會現實,沒有人的社會實現和人的社會現實,人的自由就失去了于“人”的意義;另一方面,自由從屬于社會現實的形式就是法本身,自由是法中的自由,法是自由中的法。馬克思對此有很精辟的表述:“只是當人的實際行為表明人不在服從自由的自然規律時,這種表現為國家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規律才強制人成為自由的人。”
2?人的法治思維的三個層次的界定
準前文所述,當我們論及法治思維,也就是法的治理的思維方式,首先就應該從人自身、法與自由三者的內在關系來考察。法治思維不是一個僵化的、籠統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法治思維具有層次性,并且層次本身是靈活的、具體的、變化的。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自身、法、自由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決定了人的法治思維的層次。根據對三者關系的理解,以下,將其區分為三個遞升的層次。
2.1?法治思維第一層:實然的法治
這一層法治思維中,人看到了人、法及自由的各自的規定性。認為:首先,人與法是分離的——法是外在于人的東西,法是永恒不變的、完善的、理性的存在;而人是善變的、有缺陷的、感性的存在。人與法分處兩個部分,人只能感性地認識和感受法。其次,追求自由被認為是人的天性,無法的規定的人即自由的人。而法無時無刻不在規定著人,準此,自由也只能是外在于人的。既然法是將規定性加之于人,那么法實施過程就是規定人的過程,而自由就是將這些規定性從人之中剝離,也就是去規定化的過程。因而,自由與法就處在一種相互排斥、割裂的關系中。
這種關系下,法使人壓制動物的本能而不至于無節制的互相爭奪,自由則使人成全自我而不至于無節制地利他來損害自身。因此,人在法的規定化與自由的去規定化中定位自身:通過接受規定來保證群體,通過爭取自由來保證個人。
這一層法治思維實際上是將法與自由看成相互獨立的兩個部分,而人似乎在其中完成一個中介——將法的一部分轉化為自身,又將自身的一部分轉化為自由。但法與自由之間本身是沒有聯系的。也就是說,人的自我意識主導著規定性的呈現:人靠對法的感性認識理解法,產生對法的知識,進而制定法律,完成自我規定;同時,人靠對自由感性認識理解自由,產生對自由的知識,進而不斷通過排斥法律來解除自身的規定性,進而達到自由。此時的法治思維是不考慮法的實質的,它只考慮法治的實然狀態。由于法與自由是通過人拉鋸式地開展,使得法不存在對于自由的妥協,排除了自由的價值。同樣,自由也排除了法的價值。因此人只能在法與自由的形式中尋找衡平,或者說正當性。這樣的法治思維的本質即導向強調形式法治,關注法的形式價值,排斥法的實體價值,即“排除法的正義性思考,限于語言邏輯分析,把法律肢解為純形式化的東西”。
2.2?法治思維第二層:應然的法治
第二層法治思維中,人認識到法與自由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互聯系,且這一聯系是在兩者同為一個整體的對立中實現的。
認為:法與自由是無法分割的。法是規定化,自由是去規定化,法與自由在對立中相互聯系、相互轉化。從聯系上看,法是規定了的自由,自由是去規定的法,法與自由通過否定彼此來實現對自身的確證。從轉化上看,法向自由及自由向法是不間斷的過程,這種轉化不需要其他存在(包括人)進行中介,而是基于它們自身。準此,法與自由共同構成了一個對立著的運動變化的整體,這一整體自在且自為存在著。
正如法與自由的狀態,人相對于法與自由組成的整體也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同樣不是割裂的:前者必須通過后者的規定性來完成自我規定。人對于法的認識和對于自由的認識,都來自對于這一整體對人的規定:對法的認識來自這一整體中規定性的一面,對于自由的認識來自去規定性的一面。對法的認識繼而形成了法律,而對自由的認識變成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說,人設法律和人本身的自由意志均來自這一整體。準此,法與自由的這個整體與人又構成了新的整體。
這一層法治思維中,人進而相信存在著一個自我運動又總體超然不動、普遍理性的整體,它在自由與法的變動中理性地維持著純粹的正義。這個整體一般被稱之為自然法。自然法是存在于人設法律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準則,它是法與自由的合集,是人設法律與人的自由意志的終極目的。秉持這一認識的人認為真正的法律必須是與自然法相符合的,法律以接近自然法的程度作為判斷自身正義性的標準。同樣,真正的自由也必須是與自然法相吻合,以接近自然法的程度作為實現自由意志的衡量。因此,這一層的法治思維只考慮法治的應然狀態,只相信和追求那個終極目的,不關心法治的實然狀態,極力排斥法治的形式價值,將法律僅僅看作是一種靠近絕對自然法的實用工具,這種狀態下法治本身就與法律對立起來了。
2.3?法治思維第三層:實踐的法治
在第一層法治思維中,人對法治的認識局限于分離地理解人、法與自由,將法與自由看作是獨立于人的外部的東西,它以外部反思的方式將人作為轉化的中介,好似提高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能動作用,實際上則是將人對于法與自由的認識完全割裂,人無法完整的認識法和自由,人只能在自己轉化的部分有限的認識法與自由的沖突,因此這樣的認識必然造成人的法治思維的形式化,法律被肢解成純粹形式,法治也只留下工具化的意義。
第二層法治思維認識到人和法與自由雖然是彼此對立的,但這對立不是分離的割裂,而是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整體。但是它把三者的概念理解為自在自為的運動,實際上是通過對三者的抽象把概念神秘化為現實運動的主體。真正的法治社會的現實事物仿佛不存在了,或者說,成了這概念自在自為的外部表現。法治思維成了沒有現實所依托的純思維,法律只剩空洞的概念表述,法治也就成了無本之木。
惟其如此,第三層法治思維必然是對兩者的揚棄。認為:正如前文人與法關系的探究得出的結論——一方面,人是社會規定性的結果,是歷史的存在與存在的歷史,自身開展歷史并通過歷史進一步展開自身,從這一意義上看,社會規定性也就是人的社會實現和人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自由和法同樣是社會規定性展開的結果,自由是法中的自由,而法是自由中的法,自由與法是社會現實的一體兩面,互為表里。因此,本質上看,人、法、與自由具有同一性。這樣的同一性立于什么之上呢?社會實踐的過程。人通過社會實踐產生社會規定性,從而產生自身。人是人的本質,而實踐是人通往人的本質的途徑。
這一層法治思維批判地繼承了前兩層法治思維,進而超越性地認識到法治實際上是形式價值和實質價值地辯證的統一,統一于人這一命題之中。法治的狀態既不能是純粹強調形式,也不能是純粹強調實質,或者說,不是單方面的過程。人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遵循應然的規定而得出實然的結果,人在法的維度下與自由達成和解,在自由的維度下與法達成共識。人在人的現實中確證了法即自由,自由即法,自身即自由與法的統一。法治既是人達成法的目的手段,也是人追求自由的結果,更是人實現自身意義的方式,就這一意義來看,法治本身就不再是形式法治思維下撇開正義性而規定人的規范,也不再是實質法治思維下維護正義而只有實用價值的工具。
3?結語
綜上,法治思維的這三個層次是遞進關系,后者的進展是建立在靠跨越前者的基礎上的,后者是對前者的揚棄。當人停留在任一法治思維的層次上,這樣的思維就會影響人對于自身、法與自由的總體認識和判斷,進而產生差異性的法治觀念和法治實踐。總之,當人通過不斷揚棄舊識,在思維上,從實然的法治層次出發,經過應然的法治層次,終于進入法治思維的第三個層次——從社會實踐上認識法治,才可以說真正對法治乃至法治思維本身都形成了具有原則高度的把握。
參考文獻
[1]陳金釗.對“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詮釋[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21(2).
[2]楊國榮.倫理與存在:道德哲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6.
[3][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4.
[4][德]黑格爾.黑格爾著作集:第5卷邏輯學Ⅰ[M].先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324.
[5]吳曉明.論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G].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7.
[6][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7]劉平.法治與法治思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