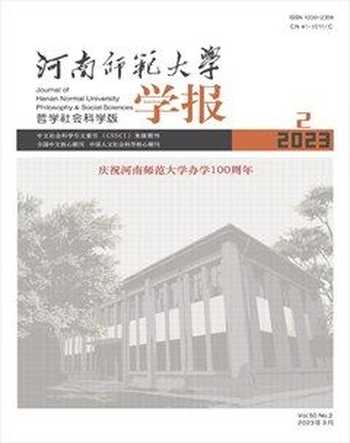由主客二分到主體間性:網(wǎng)絡(luò)治理模式的演進邏輯
廖和平 邢碩
摘 要:網(wǎng)絡(luò)治理模式由網(wǎng)絡(luò)管控發(fā)展到網(wǎng)絡(luò)共治,體現(xiàn)了由主客二分轉(zhuǎn)向主體間性的邏輯演進過程。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的理論根據(jù)在于對主客體進行二元預(yù)設(shè),并將二者對立錯置,技術(shù)與權(quán)力被異化為主體,個體受到技術(shù)異化和權(quán)力異化的宰制而淪為客體,并受到來自技術(shù)與權(quán)力的雙重管控。要實現(xiàn)對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從主體到模式的全面變革,需要從底層邏輯上重置主客體、重申社會性和重建認同來共同完成對技術(shù)異化、權(quán)力異化及人和社會異化的糾偏。網(wǎng)絡(luò)共治模式得以構(gòu)建依賴開放的權(quán)力系統(tǒng),并將從根本上否定并扭轉(zhuǎn)基于主客體分化導(dǎo)致的異化現(xiàn)象,進而摒除技術(shù)理性的統(tǒng)治缺陷,催生出基于主體間性而形成的權(quán)力共治主體。多元權(quán)力主體通過交往行動、平等參與和對話協(xié)商,最終達成基于合作的尊重理解與交往共識,以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實現(xiàn)對技術(shù)理性的揚棄,落實以主體間性為根基的合作共治。
關(guān)鍵詞:主客二分;主體間性;網(wǎng)絡(luò)管控;網(wǎng)絡(luò)共治
作者簡介:廖和平(1963—),女,湖南寧鄉(xiāng)人,湖南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行政學(xué)理論與實踐等相關(guān)研究;邢碩(1991—),男,河南長垣人,湖南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博士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相關(guān)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18BKS126);湖南省黨建理論研究基地一般項目(19DJYJY09)
中圖分類號:D035-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359(2023)02-0023-07
收稿日期:2022-05-06
網(wǎng)絡(luò)產(chǎn)生了日益凸顯的網(wǎng)絡(luò)社會問題。各國對待網(wǎng)絡(luò)的態(tài)度也經(jīng)由無政府主義式的網(wǎng)絡(luò)自治轉(zhuǎn)向網(wǎng)絡(luò)控制。而為了滿足網(wǎng)絡(luò)參與者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需要,則要對這種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作出合理的調(diào)整,落實網(wǎng)絡(luò)管控走向網(wǎng)絡(luò)共治的治理理念。網(wǎng)絡(luò)治理模式經(jīng)由網(wǎng)絡(luò)管控走向網(wǎng)絡(luò)共治,其演進邏輯在于扭轉(zhuǎn)以主客二分為基礎(chǔ)的技術(shù)理性的全面統(tǒng)攝,并對建基于主客二元對立的技術(shù)、權(quán)力和人的異化進行全面糾偏,完成主客體關(guān)系與管理模式的雙重變革,最終實現(xiàn)以主體間性為根基的合作共治。
一、技術(shù)嵌入: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的理論預(yù)設(shè)
管理模式涉及管理主體和管理對象,就管控而言,一般將政府作為管控主體,將政府外的組織、群體和個體作為管控對象。有學(xué)者認為,網(wǎng)絡(luò)管控是以政府為主體、由行政機構(gòu)制定并實施的干預(yù)互聯(lián)網(wǎng)提供商的一般或特殊行為[ 鄒衛(wèi)中:《自由與控制:網(wǎng)絡(luò)民主困境及其新路》,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230頁。]。實際上,網(wǎng)絡(luò)管控的情況更為復(fù)雜,作為一種伴隨新的科技革命而出現(xiàn)并廣泛應(yīng)用于人們生活中的信息技術(shù),它兼具技術(shù)性與社會性雙重屬性,也兼具主體與客體雙重身份。網(wǎng)絡(luò)管控是在主客二元對立為基礎(chǔ)的技術(shù)理性[ 技術(shù)理性也可稱工具理性,是把世界及其構(gòu)成要素看做達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不產(chǎn)生價值和意義,其實質(zhì)是實用主義。]指導(dǎo)下,將技術(shù)及占有技術(shù)的權(quán)力者作為主體,將其他網(wǎng)絡(luò)參與者作為客體,主體對客體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及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進行全方位的滲透和掌控。因此,對網(wǎng)絡(luò)管控的分析,要以其技術(shù)性為起點展開。
(一)主客體錯置:技術(shù)的異化
技術(shù)性是網(wǎng)絡(luò)的根本屬性和網(wǎng)絡(luò)社會生成的底層邏輯。網(wǎng)絡(luò)具有數(shù)字化特征,各種內(nèi)容在網(wǎng)絡(luò)上以編碼形式出現(xiàn),甚至網(wǎng)絡(luò)的參與主體也需要網(wǎng)絡(luò)對身份進行數(shù)字化演繹;網(wǎng)絡(luò)具有信息化特征,網(wǎng)絡(luò)傳播的內(nèi)容是信息,網(wǎng)絡(luò)本身也是網(wǎng)絡(luò)和現(xiàn)實社會之間信息勾連和傳播的信息中介;網(wǎng)絡(luò)具有連接性特征,能夠通過分享信息將網(wǎng)絡(luò)參與主體連接起來,從而使時空脫域活動成為可能。基于以上三種特征,網(wǎng)絡(luò)表現(xiàn)出其工具性的特點,人們利用網(wǎng)絡(luò)獲取海量信息,依托網(wǎng)絡(luò)實現(xiàn)跨時空的不在場交往,借助網(wǎng)絡(luò)滿足各類生活需要。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實現(xiàn)了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全面變革,可以說,只要技術(shù)允許,“線下”活動可以完美投射到“線上”。
可見,網(wǎng)絡(luò)的普及對人類生活世界產(chǎn)生的影響已經(jīng)到了無法忽視的程度,這個過程正如計算機倫理學(xué)先驅(qū)詹姆士·摩爾所說:“計算機革命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技術(shù)引入階段。在這一階段,開發(fā)和改進計算機技術(shù)……第二個階段——工業(yè)化國家剛剛進入的階段——是‘技術(shù)滲透階段。在這一階段,技術(shù)滲透到了人們?nèi)粘;顒雍蜕鐣ㄖ疲淖兞嘶靖拍畹囊饬x,如金錢、教育、工作和公平選舉。”[ 詹姆士·摩爾:《計算機倫理學(xué)中的理性、相對性與責(zé)任》,正萍譯,《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6年第5期。]網(wǎng)絡(luò)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內(nèi)容,但網(wǎng)絡(luò)也是一把雙刃劍,當(dāng)它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時,其在社會生活、信息傳播、意識形態(tài)方面表現(xiàn)出的統(tǒng)治力量反而形成了對人的宰制。
法蘭克福學(xué)派以反思的自覺對科學(xué)技術(shù)展開理論批判,認為科學(xué)技術(shù)具有兩重性——既是一種重要的生產(chǎn)力,以巨大的力量推動社會生產(chǎn)力提高,又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變體,以意識形態(tài)的形式壓抑人、操縱人,從而導(dǎo)致人由主體淪落為被奴役的客體,其批判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理性在法蘭克福學(xué)派社會批判理論中具有哲學(xué)根基地位,理性的發(fā)展與主體性的生成和主體地位的確立是同一的,它既表征目的本身,又是對目的的展現(xiàn)。然而,隨著技術(shù)對生活世界愈加滲透,社會生活和社會行動逐漸被技術(shù)主導(dǎo)。
人們看似有了更多的自由選擇機會和更豐富的生活內(nèi)容,但實際上技術(shù)理性已悄然將人退化為技術(shù)的附庸,實現(xiàn)了技術(shù)和規(guī)則對人的統(tǒng)治。技術(shù)理性主張效率至上,基于實用主義立場追求功利,行動受功利驅(qū)使,借助技術(shù)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達到預(yù)期目的,并在此過程中表現(xiàn)出對人的全方位控制。網(wǎng)絡(luò)社會是網(wǎng)絡(luò)的技術(shù)性與社會性的結(jié)合,是建基于技術(shù)之上的社會空間。照此邏輯,網(wǎng)絡(luò)社會是否首先要符合技術(shù)的統(tǒng)治需求?是否要遵循技術(shù)理性的管理邏輯來對待網(wǎng)絡(luò)社會?馬爾庫塞曾提出“技術(shù)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轉(zhuǎn)而成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43頁。],人們出于利益追求,自愿加入技術(shù)系統(tǒng)當(dāng)中,技術(shù)由解放的工具異化為奴役人和束縛人的工具,人自身成為無差別的同化物。人不再通過自身的意志來掌握和利用技術(shù),相反,成為技術(shù)體系的組成要素,淪為技術(shù)的奴隸和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消費的奴隸,最終處在生活世界中的人淪為客體,置于技術(shù)控制之下,失去了人之為人的主體地位。
(二)占有技術(shù)的權(quán)力:權(quán)力的異化
技術(shù)作為管控主體,是一種異化了的技術(shù),對技術(shù)的占有生成的管控權(quán)力是一種異化了的權(quán)力。權(quán)力的異化在管控模式演變過程中體現(xiàn)為其自身的異化和技術(shù)引入后導(dǎo)致的管控效能的異化。傳統(tǒng)的管控模式依據(jù)階級身份的差別和對資本、軍隊力量的占有,以暴力的形式和強制的手段實現(xiàn)對人們的控制和統(tǒng)治,人們能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服從的是基于何種權(quán)力基礎(chǔ)的“暴政”。然而現(xiàn)代技術(shù)已經(jīng)逐漸取代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依托資本,技術(shù)完全可以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工具,以此達成統(tǒng)治階級權(quán)力的集中,形成一種以技術(shù)為底層邏輯、以資本為保障、以權(quán)威為主導(dǎo)的集權(quán)形式。異化的技術(shù)在成為網(wǎng)絡(luò)管控發(fā)揮權(quán)力效力手段的同時,也嵌入了基于技術(shù)自身發(fā)展所帶來的未知和不確定性影響。
對待異化的技術(shù)和異化的權(quán)力顯然不應(yīng)持價值中立的立場,這似乎與“科技造福于人”的觀點相沖突。實際上,說科技造福于人類,是指科技滿足人類需要的層面,這恰恰也是占有技術(shù)的權(quán)力與技術(shù)相結(jié)合,從而導(dǎo)致權(quán)力被異化,進而緩慢入侵人的生活領(lǐng)域和意識領(lǐng)域。馬爾庫塞區(qū)分了人類的“真實需要”和“虛假需要”,認為人們最基礎(chǔ)的需要是滿足衣食住行的生存需要,但隨著社會發(fā)展,人們對需要的標準逐漸提高,“需要”的內(nèi)涵也逐漸豐富。需求的變化反映了人們的社會屬性,社會屬性的滿足則依賴于社會制度的實現(xiàn)。
因此,管控之所以能夠發(fā)揮作用,就在于統(tǒng)治階級有意識地錯置了人們的“真實需要”,利用了“虛假需要”。在統(tǒng)治階級看來,占有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資料而獲得物質(zhì)產(chǎn)品的需要是一種真實需要,而諸如思想、文化等對人和社會的發(fā)展具有創(chuàng)造性作用的需要則是一種虛假需要,這是對人這一需要的錯置。當(dāng)人們認為獲得了“需要”的滿足而沉醉其中時,實際上只是對給定的“虛假需要”的順從。“真實需要”是人在自由狀態(tài)下提出的需要,是體現(xiàn)了人的本性的自主性需要。當(dāng)人們把順從當(dāng)作幸福,把所受到的支配當(dāng)作舒適的生活方式加以認可時,就永恒地接受了管控的內(nèi)在邏輯,成為統(tǒng)治權(quán)力之下被異化的個體。技術(shù)與權(quán)力的聯(lián)袂,也最終達成了對社會的整體管控。
(三)形式認同:人和社會的異化
人在技術(shù)和占有技術(shù)的權(quán)力的雙重管控下,被異化為服從于意識形態(tài)的簡單個體,社會被異化為受制于意識形態(tài)的單一形式。異化下的人和社會與技術(shù)和權(quán)力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形式上的認同”(同化)關(guān)系,這鞏固了統(tǒng)治階級的管控根基,但實際上是對人和社會發(fā)展革新的桎梏。
社會控制的現(xiàn)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shù)的形式[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0頁。]。馬爾庫塞指出:“技術(shù)設(shè)施在維系并改善各個個人生活的同時,又使他們服從于設(shè)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統(tǒng)治集團與該社會融為一體。”[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49頁。]就此而言,“統(tǒng)治不僅通過技術(shù)而且作為技術(shù)來自我鞏固和擴大,而作為技術(shù)就為擴展統(tǒng)治權(quán)力提供了足夠的合法性。”[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42頁。]在信息化的社會,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鉗制了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如人們雖然可以利用網(wǎng)絡(luò)精準、快速得到想要獲得的信息,但是反過來,通過技術(shù)算法,網(wǎng)絡(luò)可以按照用戶搜索習(xí)慣形成信息繭房,這種“自由選擇”實際上是技術(shù)宰制下單一化信息的獲取和對其他信息的剝奪,個體由此處于形式認同下的異化狀態(tài)。
誠然,人在滿足了“虛假需要”的前提下,與技術(shù)和權(quán)力產(chǎn)生了普遍的、隱秘的對抗關(guān)系。“虛假需要”基礎(chǔ)上的意識統(tǒng)一導(dǎo)致經(jīng)濟、文化與政治生活被全面鉗制。“就形式認同與異化的關(guān)系而言,同化機能越是強大,被同化的主體越是感到異化,因而,同化理論揭示了同化對于異化的根源性和實質(zhì)性。”[ 楊樂強:《工具理性的起源及其同化機能:早期法蘭克福學(xué)派同化理論探析》,《江漢論壇》,1998年第7期。]這充分表明,技術(shù)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附庸,為統(tǒng)治階級的管控提供辯護。統(tǒng)治階級作為意識形態(tài)主導(dǎo)的一方,合理性調(diào)控、制衡和統(tǒng)攝個體成員,個體成員合理性認同、確信和依托于前者,從而形成一種共時態(tài)的或結(jié)構(gòu)性的包容認同關(guān)系[ 楊樂強:《工具理性的起源及其同化機能:早期法蘭克福學(xué)派同化理論探析》,《江漢論壇》,1998年第7期。]。然而后者對前者的認同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認同,前者通過“合理化”控制達到對人的主體地位的否定和對其能動性的剝奪,個體的人則出賣和轉(zhuǎn)讓個體性以實現(xiàn)一種片面自足的生存,這是技術(shù)理性指導(dǎo)下統(tǒng)治階級對個體成員造成的同化。
同化造成了同質(zhì)化的個人和板結(jié)化的社會。人的靈魂被同化到技術(shù)規(guī)則之中,人們接受標準化的文化產(chǎn)品,個人錯誤地將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當(dāng)作其觀念世界,以采納統(tǒng)治階級發(fā)布的“指令”來代替主動與他人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成為單面化的個人。個人意識消解的實質(zhì)是個體被控制和操縱所內(nèi)化,是以一種潛化、模仿的形式來取代認同,進而達到與整個社會的“一致化”。在生活世界中,形式認同內(nèi)含了對經(jīng)濟、文化、政治等諸多領(lǐng)域消解對立、消除否定的意義,以此來保證社會制度和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實現(xiàn)對生活世界的全面支配和對社會的全面管控,最終消解社會進步和改革的可能。
二、技術(shù)悖論: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建構(gòu)邏輯的反思與批駁
法蘭克福學(xué)派在對科學(xué)技術(shù)批判的過程中,逐漸理順了技術(shù)和權(quán)力控制人的演化路徑:在主客二元對立被錯置的前提下,技術(shù)以其理性效率原則將人們卷入了技術(shù)規(guī)則的洪流,依托資本,統(tǒng)治階級與技術(shù)聯(lián)袂,使技術(shù)成為權(quán)力的附庸,實現(xiàn)了從物性支配到對人的行為方式、意識領(lǐng)域的全面占據(jù)和掌控,參與主體淪為同質(zhì)化的客體,社會淪為板結(jié)化的社會,最終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要實現(xiàn)對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的革新,關(guān)鍵在于恢復(fù)網(wǎng)絡(luò)參與者的主體地位,限制管控權(quán)力效用的發(fā)生,重建人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明確作為治理主體的網(wǎng)絡(luò)參與者所具有的共治權(quán)力。
(一)重置主客體:對技術(shù)異化的規(guī)制
對技術(shù)異化的規(guī)制關(guān)鍵在于恢復(fù)人的主體性,主體性蘊含著事實與價值的雙重意蘊,從事實與價值來看,人具有最大的內(nèi)在構(gòu)成性價值,其本身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主體性的工具性價值體現(xiàn)為他是維持社會活力的最深層根源,能夠直觀地催生人的行為,進而為社會發(fā)展提供動力;又能夠極大地指導(dǎo)和提升個人行為的效率,有助于形成對個體價值的尊重與保護。主體性的雙重意蘊還意味著,處在社會關(guān)系中個人的主體性狀態(tài)與該社會對主體的權(quán)力賦予和保障狀況密切相關(guān)。個體作為社會的參與者、行動的承擔(dān)者和接受損益的利益相關(guān)者,不能被視為非人格化的機械式客體,而是具有獨立人格尊嚴、自由意識,具有理性與自主性,既守規(guī)則也會犯錯的人格化主體。總是像客體一樣受他人支配和安排,聽命于絕對統(tǒng)治的受制狀態(tài),都是個體主體性沒有受到尊重的表現(xiàn)[ 余向華:《主體性與社會秩序的人本建構(gòu):轉(zhuǎn)型變遷透視下的經(jīng)濟人假說》,經(jīng)濟科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58頁。]。
關(guān)于人主體地位的確立一向是人本主義關(guān)注的問題。自古希臘羅馬時期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到啟蒙運動對人性、人的道德性的考量,人們逐漸發(fā)展出了關(guān)于“人”的一個基本共識,即將人作為尺度,肯定人的價值,高揚人的利益,滿足人的需求。之所以強調(diào)網(wǎng)絡(luò)參與者的主體地位,是由于只有當(dāng)個體從被數(shù)字化、符號化了的原子式客體變?yōu)樘幱诮煌鶎υ捴械闹黧w時,對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才能構(gòu)成網(wǎng)絡(luò)社會中形成共識的條件。網(wǎng)絡(luò)參與者只有作為主體而發(fā)生交互關(guān)系時,才能構(gòu)筑網(wǎng)絡(luò)共治的堅實基礎(chǔ),從而促進網(wǎng)絡(luò)社會的長足發(fā)展。但由于主客體的錯置,使得技術(shù)和基于技術(shù)的權(quán)力成為管控主體,本應(yīng)具有主體性的人卻成了被認識和管控的客體對象。人們囿于自身的有限性,一方面受到技術(shù)理性的桎梏,另一方面又渴望獲得價值意義。因此,要改變管控現(xiàn)實,變革管控模式,首先就要扭轉(zhuǎn)被錯置的主客體地位,用以主體人為中心的人本管理邏輯取代技術(shù)理性的管理邏輯,形成網(wǎng)絡(luò)共治模式。
但是僅僅恢復(fù)人的主體性對于變革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來說遠遠不夠。一方面,不加限制的主體性最終將陷于自我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泥淖,另一方面,基于網(wǎng)絡(luò)的雙重屬性,技術(shù)性扭曲了人的主體性,社會性反而為人們發(fā)揮主體性提供了條件。
(二)重申社會性:對權(quán)力異化的糾偏
網(wǎng)絡(luò)承載著網(wǎng)絡(luò)參與者開展各項活動、進行信息交流的社會空間,這使得異化的權(quán)力失去了發(fā)揮效力的場所,并為其他主體賦權(quán)提供了條件。因而,網(wǎng)絡(luò)的社會空間屬性及其所承載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互構(gòu)關(guān)系是限制管控權(quán)力、糾正權(quán)力異化的重要路徑。
從網(wǎng)絡(luò)的社會空間屬性來看,“互聯(lián)網(wǎng)的全球性、多節(jié)點、高速度,使得它獲得了無限的生機和敏感,這是政府所難以控制和把握的。政府管理互聯(lián)網(wǎng)的原則應(yīng)當(dāng)是有限管理,保證互聯(lián)網(wǎng)有足夠的發(fā)展空間是駕馭這種新媒介最好的辦法”[ 丁未:《網(wǎng)絡(luò)空間的民主與自由》,《現(xiàn)代傳播》,2000年第6期。]。開放共享的網(wǎng)絡(luò)空間因其橫向扁平化的結(jié)構(gòu),扭轉(zhuǎn)了管控模式所對應(yīng)的中心——邊緣形態(tài)的由上至下發(fā)揮權(quán)力效力的社會結(jié)構(gòu),從而破除了權(quán)力、地位、資本、種族等現(xiàn)實交往中的限制,“事實上更有益于民主協(xié)商,因為它顛覆了當(dāng)面討論中的禮儀束縛”[ 安德魯·查德威克:《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學(xué):國家、公民與新傳播技術(shù)》,任孟山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第146頁。],更加彰顯了網(wǎng)絡(luò)參與主體交往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擺脫了對管控權(quán)力邏輯的信奉。基于網(wǎng)絡(luò)的社會空間屬性對權(quán)力進行限制,首先要堅定去中心化的呈現(xiàn)形態(tài),滿足網(wǎng)絡(luò)參與主體間的溝通需求和地位維護,規(guī)避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的一元權(quán)力主體現(xiàn)象,促進多元主體模式的良性發(fā)展;其次要維護扁平化的發(fā)展結(jié)構(gòu),穩(wěn)定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的橫向發(fā)展態(tài)勢,防止出現(xiàn)“金字塔”型結(jié)構(gòu)衍生出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
從網(wǎng)絡(luò)的互構(gòu)關(guān)系屬性來看,網(wǎng)絡(luò)的社會性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一是體現(xiàn)在人與人的關(guān)系上。在關(guān)系視角下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自我與他人可以通過社會交往以主體和主體之間的形式實現(xiàn)共存。尤其在交互的網(wǎng)絡(luò)社會當(dāng)中,信息傳播者同時也是信息接收者,這將傳統(tǒng)的由主體到客體的社會活動轉(zhuǎn)變?yōu)橛芍黧w到主體的社會活動。二是體現(xiàn)在人與社會的互構(gòu)關(guān)系上。人是包含了自由意志在內(nèi)的具有主體性而非單向度的實體,人不是一個封閉概念,社會性因素自然而然地融入自我當(dāng)中,網(wǎng)絡(luò)社會中的人始終與社會本身處在一個相互建構(gòu)、相互影響的系統(tǒng)之中,社會始終承載著人類的實踐活動而非僅作為一個場域而外在于個人,人們的意識、行為形塑著網(wǎng)絡(luò)社會的結(jié)構(gòu),反過來又受到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和社會關(guān)系的決定。
(三)重建認同:對人和社會異化的再造
認同意指社會成員確證相互之間具有共同的文化屬性或價值方面的相似性。形式上的認同是個體間基于技術(shù)理性形成的,要改變這種情況,就要以實質(zhì)認同取代形式認同:一是要確立個體的自我認同,以此明確參與主體的主體地位和治理權(quán)力;二是要確立主體間的社會認同,以形成治理共識,獲得實現(xiàn)共治的條件;三是要甄別社會認同的機制差異,以滿足共治的內(nèi)在要求。
首先,自我認同包括對自我屬性的確認以及他人對自我的確認,前者表現(xiàn)為個體基于自我意識而認識“自我”,后者表現(xiàn)為個體通過與自我發(fā)生關(guān)系的其他利益相關(guān)者的社會交往而認識“自我”,這兩個環(huán)節(jié)的認同是相互交織的:個體通過自我認同將自我同一性變成現(xiàn)實化的主體,又在社會場景中,與其他個體出于不同層面的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產(chǎn)生在認知和價值評價上的一致意見[ 李萍:《論道德認同的實質(zhì)及其意義》,《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9年第1期。]。自我通過對自己行為的持續(xù)性反思不斷確立自我的同一性,這也符合吉登斯所認為的自我同一性需要、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個體的獨立,個體的自我認同就可以成為對抗現(xiàn)代性同質(zhì)化、均質(zhì)化的有力武器[ 李萍:《論道德認同的實質(zhì)及其意義》,《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9年第1期。]。
其次,在現(xiàn)實社會中,人們之間的相互認同構(gòu)成了社會認同的一個隱含因素,是穩(wěn)定社會秩序、實現(xiàn)共同目的的內(nèi)在條件之一。社會認同表現(xiàn)為個體與其他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價值和行動取向。美國社會學(xué)家科爾曼曾定義,社會認同是包括了對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認可、對周圍社會的信任和歸屬、對有關(guān)權(quán)威和權(quán)力的遵從等多方面的含義[ 王春光:《新生代農(nóng)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xiāng)融合的關(guān)系》,《社會學(xué)研究》,2001年第3期。]。這表現(xiàn)出歸屬性傾向,表現(xiàn)出個體面向所在群體和公共生活世界,承認了相應(yīng)的社會規(guī)范,接納了相應(yīng)的身份角色,以此確認自身在其中的位置,獲得對群體和社會的歸屬。
最后,社會認同機制主要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網(wǎng)絡(luò)對原有的社會建構(gòu)進行了去中心化的處理,信息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單向傳遞態(tài)勢,個體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進行傳遞主體和形式的轉(zhuǎn)換,這種雙向的互動模式不斷沖擊著中心邊緣式的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網(wǎng)絡(luò)社會的種種多樣性特征打破了現(xiàn)有的社會認同機制,使對價值的認同和對意義的接受替代了對固定群體的認同。“在社會生活網(wǎng)絡(luò)化背景下的認同,已經(jīng)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學(xué)和個體心理學(xué)界定的個人認同或身份認同。個體的身份認同實質(zhì)上是尋求個人怎樣得到社會的認可,這種認同思考的是個體在社會中處于何種層面、地位或角色,希求的是個體得到社會某種層面或某種群體的認可和接受。網(wǎng)絡(luò)社會中的認同發(fā)生了根本變化,甚至是顛覆性的變化,因為網(wǎng)絡(luò)社會中的認同不再是個體被社會認同,而是被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起來的個體怎樣評價、認可和接受社會。”[ 劉少杰:《網(wǎng)絡(luò)化時代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變遷》,《江淮論壇》,2011年第5期。]網(wǎng)絡(luò)主體之間結(jié)成了新的認同模式,借由網(wǎng)絡(luò)平臺,通過對話交往的形式,以自由意見和協(xié)商民主的方式,形成主體間的共識,趨向于形成新的社會認同,這既保障了主體權(quán)力的發(fā)揮,又體現(xiàn)了共治的內(nèi)在要求。
三、主客二分到主體間性:網(wǎng)絡(luò)共治模式的有效實現(xiàn)
網(wǎng)絡(luò)管控依賴于封閉的權(quán)力系統(tǒng),催生了權(quán)力主客體的絕對分化,失衡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失范的權(quán)力運行也在相互掣肘中背離了權(quán)力的社會性和公共性。與此相反,網(wǎng)絡(luò)共治依賴于開放的權(quán)力系統(tǒng),催生了基于主體間性的權(quán)力主體。網(wǎng)絡(luò)共治下的多元參與者使用的權(quán)力是一種不可壟斷的社會權(quán)力,多個權(quán)力主體通過平等參與和對話協(xié)商的交往行為監(jiān)督和制衡主體權(quán)力,達成對網(wǎng)絡(luò)社會價值的認同和對網(wǎng)絡(luò)社會公共事務(wù)的共識并實現(xiàn)合作。
(一)網(wǎng)絡(luò)共治主體間的權(quán)力制約
網(wǎng)絡(luò)事務(wù)和環(huán)境造成的不確定性致使網(wǎng)絡(luò)管控模式以及它所依托的統(tǒng)治階級—被統(tǒng)治階級的主客二分權(quán)力失靈,網(wǎng)絡(luò)管控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越來越受到質(zhì)疑。網(wǎng)絡(luò)屬性為其他主體賦權(quán),形成了制約統(tǒng)治階級權(quán)力的新生力量,對主客體的重置和對社會性的申明又激發(fā)了參與者的主體意識,由此形成主體和主體之間的權(quán)力參與形式。其他主體的加入需要在自我中心主義中尋求平衡。由此,主體間性提供了一種新的網(wǎng)絡(luò)治理思路,基于主體間性實現(xiàn)了對統(tǒng)治階級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主體間性不是對主客體的徹底否定,而是對主客體關(guān)系進行選擇性的繼承,保持對主體權(quán)力所導(dǎo)致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警惕和對過度運用權(quán)力的質(zhì)疑,以確保權(quán)力運行方向和路徑的合理性。
主體間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既是現(xiàn)代行政管理體制發(fā)展的重要產(chǎn)物,也是網(wǎng)絡(luò)共治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對于行政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來自外在于它的社會權(quán)力,通過對行政主體、行政行為、作用對象等方面的監(jiān)督來約束行政權(quán)力自身,這是網(wǎng)絡(luò)治理過程中對統(tǒng)治階層權(quán)力進行限制的合理手段之一。治理權(quán)力在不同主體間的流動可以促成主體間的合理監(jiān)督和有效交流,從而使各項公共事務(wù)在不同權(quán)力的角逐中通過商討得以解決。網(wǎng)絡(luò)社會中主體間的權(quán)力制衡,表現(xiàn)為參與者除了是構(gòu)成治理權(quán)力的主體之外,還是構(gòu)成交往權(quán)力的主體。這表明網(wǎng)絡(luò)參與者既擁有權(quán)力,又處于制約之中。交往權(quán)力來自公眾之間的話語交往,是在進行商議后形成的具有一定共同意志的力量,旨在權(quán)力博弈中謀求最廣泛公眾的公共利益。這暗含了網(wǎng)絡(luò)治理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群體掌握話語權(quán),而是不同主體間通過網(wǎng)絡(luò)這一公共領(lǐng)域進行交往行動,表達各自的權(quán)力訴求,并在產(chǎn)生沖突時進行不同程度的讓步,進而保證網(wǎng)絡(luò)社會秩序趨于合理發(fā)展。由此,主體間的權(quán)力制約是實現(xiàn)網(wǎng)絡(luò)共治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釋放網(wǎng)絡(luò)社會活力、推動網(wǎng)絡(luò)社會發(fā)展的動力來源,最終實現(xiàn)網(wǎng)絡(luò)共治對網(wǎng)絡(luò)管控的超越。
(二)網(wǎng)絡(luò)共治主體間的交往行為
網(wǎng)絡(luò)共治是依靠不同主體通過多種交往行為達成共識,平等和協(xié)商交織于互動交往當(dāng)中,最終形成主體間的認同,構(gòu)織出社會共同體的交往秩序。
平等體現(xiàn)在主體準入身份的話語平等。網(wǎng)絡(luò)空間是一個向公眾開放的公共平臺,參與者在網(wǎng)絡(luò)社會中不受階層和社會身份的限制,而“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的誕生,為相對自發(fā)的、靈活的、自治的公共辯論提供了多樣性的場所。按照哈貝馬斯的解釋,隨著歷史性的公共領(lǐng)域的崩潰,已經(jīng)逐漸退入各自私人領(lǐng)域的公民,又一次以一種公共力量出現(xiàn)了”[ 安德魯·查德威克:《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學(xué):國家、公民與新傳播技術(shù)》,任孟山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第117頁。]。網(wǎng)絡(luò)中交往的個體“既不是作為某種職業(yè)的從業(yè)者也不是作為某種物品的消費者出現(xiàn)的,因而他們往往是具有獨立人格的‘私人,而這些私人一旦就普遍利益問題達成共識,他們的共識就不再是普通心理學(xué)意義上的‘個人意愿,相反,這些共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公意”[ 許英:《論信息時代與公共領(lǐng)域的重構(gòu)》,《南京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2年第3期。]。這表明,任何與公共事務(wù)相關(guān)的利益相關(guān)者都可以加入商討過程中來,理想的公共領(lǐng)域“應(yīng)提供開放的公共論壇,尊重弱勢社群的發(fā)言空間,呈現(xiàn)多元化的報道以彰顯公共領(lǐng)域的精義及多元社會的理念”[ 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173頁。]。網(wǎng)絡(luò)為實現(xiàn)多元主體共治的自由進入、平等交流與協(xié)商對話提供了平臺支持和技術(shù)支撐。
協(xié)商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體間為形成統(tǒng)一意見而開展的自由認同形式。在網(wǎng)絡(luò)社會中,信息愈發(fā)多樣,個體對信息的選擇也呈現(xiàn)隨意性傾向,這很容易出現(xiàn)意見的分歧甚至沖突,但在協(xié)商語境下,意見分歧和沖突都基于平等立場的表達,都以達成共識為目標,分歧和沖突并不具備絕對性意義,通過協(xié)商對話總是能解決沖突、達成共識。協(xié)商過程不同于顯性契約的約定,也不意味著多元價值體系下的虛無主義,而是在一種相對活躍的社會環(huán)境中,擴大和保證社會成員公共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為社會成員提供在價值觀上共商的基礎(chǔ)。
交往行動對交往主體經(jīng)由協(xié)商所確定的語境當(dāng)中的互動行為進行協(xié)調(diào),通過平等溝通和協(xié)商達成共識。將交往行動運用到網(wǎng)絡(luò)治理當(dāng)中,是參與主體通過公開參與,自主發(fā)表意見,在平等公開的語境下,就公共事務(wù)或政治事務(wù)達成共識。隨著網(wǎng)絡(luò)交流平臺的建立,人們“能夠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平等地隨時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個人開始對自己周圍的一切事務(wù)感興趣,尤其是對那些原本認為歸國家和政府管理的事務(wù)投入了極大熱情”[ 陳衛(wèi)星:《網(wǎng)絡(luò)傳播與社會發(fā)展》,北京廣播學(xué)院出版社,2001年,第327頁。]。私人話題借由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傳播和參與主體的交往行為而被打上公共的烙印。可見,交往行動正是由個體走向公共、由個體意見走向共識的必由之路,也是參與主體達成合作、共同參與網(wǎng)絡(luò)治理的必要途徑。
(三)網(wǎng)絡(luò)共治主體間合作的達成
合作是人類存在于社會中的一種基本生活方式,合作與交往也始終相伴相生,因而,合作從本質(zhì)上來看就是一種交往關(guān)系,而交往關(guān)系的斷裂就在于技術(shù)理性及其背后所依據(jù)的主客二分對人造成的異化。要克服技術(shù)理性的統(tǒng)治缺陷,就要重新尋求建立理性的根基和途徑。以主體間性為基點,通過交往和共識建立起交往理性,以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來實現(xiàn)對技術(shù)理性的揚棄構(gòu)成了主體間形成合作的有效途徑,網(wǎng)絡(luò)合作共治由此成為擺脫技術(shù)理性網(wǎng)絡(luò)治理模式的代表。
合作的達成以肯定利益相關(guān)者的個人利益為前提,通過公開的辯論和協(xié)商妥協(xié),在相互理解的基礎(chǔ)上形成關(guān)于共同利益的共識,實現(xiàn)由個體到公共的轉(zhuǎn)向。對共同利益的認同依賴于對交互主體性的尊重,由此形成的共識既代表共同意志,也代表個體意志,是參與主體經(jīng)由協(xié)商自由選擇的結(jié)果,因而也對參與主體具有內(nèi)在的約束力。網(wǎng)絡(luò)作為一種開放的、便捷的非線性傳播方式,每個公眾都可以作為獨立個體參與到網(wǎng)絡(luò)社會中,網(wǎng)絡(luò)的立場代表的就是公眾立場。由此,參與主體通過公開討論的方式闡述相互之間對于公共事務(wù)和個體利益的期望以及相關(guān)的行為標準,并賦予共同利益以普遍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合作共識。
主體間的相互理解是達成合作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理解是對主客體預(yù)設(shè)的拋棄,是對基于他者視角理解主體行為。通過主體間的交往行為,人們產(chǎn)生交往理性,形成對他人的理解。理解的過程就是主體間意見逐漸達成一致的過程,主體間基于共同的信念,合力對一種意見內(nèi)容表示同意。當(dāng)個體以網(wǎng)絡(luò)治理主體的身份而存在時,盡管可能出現(xiàn)不同主體間的利益角逐,但其最終旨趣都趨向于達成公共利益和穩(wěn)定的網(wǎng)絡(luò)社會秩序,這樣的結(jié)果指向必將推動參與主體經(jīng)由理性選擇達成合作。
總之,在網(wǎng)絡(luò)治理過程中,“主體間性”始終貫穿于合作共治過程,個體、技術(shù)與權(quán)力之間不再表現(xiàn)出主客二元對立的立場,而是以相互承認與尊重為前提,以協(xié)商、理解的對等關(guān)系取代一方對另一方的威脅壓迫關(guān)系,參與主體也不再只是技術(shù)理性下被異化的單向度的個體,而是在交往行為中以交往理性為判斷依據(jù)的具有自我意志的主體。由此,主體間達成普遍有效的合作,共同參與到網(wǎng)絡(luò)治理過程當(dāng)中,最終實現(xiàn)以網(wǎng)絡(luò)共治取代網(wǎng)絡(luò)管控的模式變革。
From the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o Intersubjectivity: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Liao Heping,Xing Shuo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develops through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o Internet co-governance, which embodies the logical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o intersubjectiv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l lies in the dual presupposi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he opposition of the two is misplac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 from subject to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logy, power and people and society by resetting subject and object from the bottom logic, reaffirming sociality and rebuilding ident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co-governance model constructed depends on the open power system, which will fundamentally negate and reverse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caused by subject-object differentiation, abandon the ruling defect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give birth to the power co-governance subject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tersubjectivity. Through communication actions,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finally reach a consensus of respect,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realize the sublat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wit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the cooperative co-governance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Key words: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intersubjectivity;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internet co-governance
[責(zé)任編校 陳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