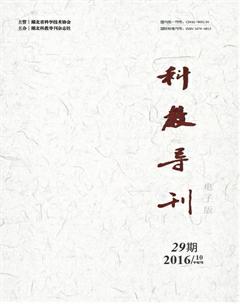淺析課堂話語模式的模糊與缺失
朱淵
摘 要 本文在主體間性視域下檢視英語課堂話語模式,分析了課堂話語模糊與缺失的制度、慣習以及知識三重情結,以期將課堂教學活動從情結操控下的機械化活動中解放出來,建構有意義的社會交往活動。
關鍵詞 主體間性 制度情節 慣習情節 知識情結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情結常用于表示對某種情感或信念的執著和堅守,不易擺脫,并無貶義。如果堅守的是正確的信念,按照正確信念做事,多有好結果。如果堅守的是消極的信念而不自知,按照消極信念做事,往往事與愿違。在長期的高職英語課堂教學與實踐中,課堂話語仍以傳遞“客觀知識”為中心,這直接導致師生對話不對稱,課堂話語呈現封閉、靜止狀態;更不知不覺陷入了總想避免又無力回避的“內容空泛”與“對話主義烏托邦”的情結。筆者依據現行高職英語教學課堂話語模式背后內因機理分析,大致總結為三種情結:制度情結、慣習情結以及知識情結。
1制度情結
從社會權力分配角度看,在學校和教育機構中,教師受到社會的委托對學生施加教育影響,在教師個體與抽象的社會整體之間的中介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體現著社會對教師的要求。教師往往是社會、國家和學校的代言人,承擔著傳承社會文化、轉達國家意志和參與學校管理的任務。教師的話語代表著理性話語(專家學者對文化教育的解釋和說明)和權威話語(社會權力機構對教育的規定和要求)。傳統上,教師和學生在學校結構系統中處于不同的階層。教師被賦予管理、指導、監督學生的權力,而學生則相應地被管理、被指導、被監督,處于層級結構的下層。話語權正是人的社會地位在話語符號系統中的折射和反映。學生的課堂話語權本應是學生作為“人”所固有的權利。可是由于“官本位”的影響,產生了學校服從政府、老師服從學校、學生服從老師的怪圈。學生處于教育鏈中的最末一節,學生的地位也就無從保障,使學生話語權力缺乏生長發育的土壤,學生的話語權也就遭到剝削而缺失。
2慣習情結
“慣習”是布爾迪厄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這種課堂“慣習”的產生從他們接受教育時便開始得到培養。當此種慣習完全融入到傳統課堂中,他們就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即“就像在自己家一樣”。教師幾乎擁有了所有的話語權,至少是話語主動權, 學生話語權缺失現象也就自然產生,師生雙方都習慣于“教師講——學生聽”的課堂慣習。我國竭力倡導“師道尊嚴”,教師是知識、禮儀的化身,占據絕對權威,學生普遍存在敬畏戒備的心理。教師話語霸權現象屢見不鮮,教師課堂上話語量比例過大直接導致學生開口機會不足,學生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觀念逐漸被弱化與忽視。“滿堂灌”的教學模式,師生間“支配—依附”的交往范式, 主體間“慣習”性的不對等使學生的參與成為一種被動的和附屬性的參與,學生在課堂交往中往往處于“失語”的狀態。
3知識情結
現代知識觀是以主客觀相分離為基礎的,它追求的是把那些熱情的、個人的、人性的成分從知識中清除。知識主要是被看作完全的客觀“事實”的領域,它是外在于個體的。這樣一來,知識就完全脫離了對人的內在意義,喪失了與人建立“交互主體性關系”的能力。知識不再被視為一種可探詢的、可切磋的東西,恰恰相反,它變成了一種被管理和被掌握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就從生成自我意義系統的自我形成中被剔出了。仿佛知識就存在于那里,它是客觀而固定、遙遠而冷漠、崇高而威嚴的。學生與知識的關系僅僅是一種簡單的“鏡式反映”關系,學生與知識完全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學生唯一的任務是,用各種方式方法吸納課程中給定的確定的“真理”,拾起一個又一個“知識筐”,學習的全部目的就是掌握這樣的知識。高職學生的英語基礎雖歷經初高中的積累,知識體系往往支離破碎,長期未得英語學習自信心,入學起便對英語學習表現出明顯的焦慮,消極等負面情緒,很難構建知識對于自己的意義關系。
教師要堅定信念,與學生共筑主體間性圖景,將外語教學的工具理性融于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然解放之中,將課堂教學活動從制度、慣習、知識情結操控下的機械化活動中解放出來,使之變成師生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彼此協作,共同探索世界,一起建構有意義的社會交往活動。
參考文獻
[1] 辛斌.語言、權力與意識形態:批評語言學[J].現代外語,1996.
[2] 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70+173.
[3] 鐘啟泉.課程流派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26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