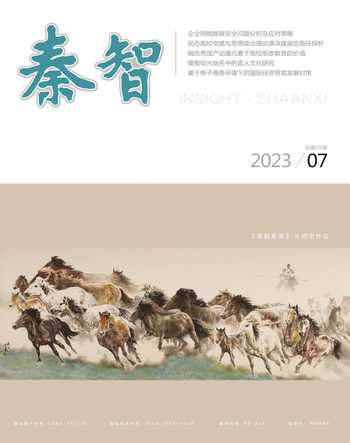動態環境問題下綠色條款司法發展進路探究
[摘要]環境問題的復雜多樣性與現實緊迫性日漸突出,綠色原則應運而生,成為物權排他性所應受的內在約束,成為司法裁判的明確要求和普遍限制。但環境問題具有不特定性與多變性,與綠色條款的靜態設立存在內在沖突,綠色原則司法化給法官的司法能力、司法化提出了較高的挑戰。只有用發展的眼光看動態環境問題,在裁判理念、思維慣常與權益革新等各個層面精準把握綠色原則的發展精髓,才能通過司法裁判真正推動資源節約、科技進步、環境保護,實現綠色條款價值。
[關鍵詞]民法;綠色原則;規范結構;法律適用;司法審判
[中圖分類號]D91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3.07.007
一、綠色原則司法化的理論延伸
《民法典》綠色原則的出現既“體現了民法綠色化的呼喚”[1],又“回應了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現實”[2]。目前學界的論證思路大多從綠色原則的自身價值、入法必要性入手,以緊密結合典型司法個案為方法,深刻解析該原則在司法領域的治理現狀,并剖析困境,最后從條文本身、立法主體、司法主體等視角給出對策建議。通過文獻的檢索發現,目前對綠色原則的研究尚處發展初階段,關于該條文司法適用方面的文獻儲量更是無法與其他傳統原則相提并論,因此學界在理論分析上有借鑒德國法、英美法等國外思維模式的傾向。目前司法審判案例亦不夠充分的現狀,不僅呼吁案件實踐的積累,更亟待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指引。
綠色原則在司法領域的落地,不僅有理論到實踐的鴻溝需要逾越,更有環境問題的動態不特定性與綠色條款自身特性的限制。呂忠梅認為,雖然我國學者較早主張物權法的綠色化,但是現行的《民法典》與全然的生態環境保護關懷依舊存在差距[3]。而綠色原則能否在司法適用中加以應用應被重點關注,因為良好的司法適用會及時補救綠色原則自身的弊端,即綠色原則對法律解釋和漏洞的補充作用需要司法實踐的檢驗和發展[4]。
二、靜態條款與動態環境的治理困境
(一)司法裁判的侵害標準難以統一
審判實踐中,在判斷是否構成相鄰污染侵害時,標準不一致的情況比較突出。以相鄰關系為例,在具體個案中,劉某與某房地產公司相鄰采光、日照糾紛一案,法院以原告建筑采光雖然受被告顯著影響但光照時間仍然達標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卻未顧及其住宅價值因而減損的事實[5]。而《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百九十四條中規定,“建造建筑物,不得違反國家有關工程建設標準”“不動產權利人不得違反國家規定棄置固體廢物”。對此,有觀點認為“超標擔責”“達標免責”;也有觀點認為“公法違法性與相鄰制度毫無關聯,即使行為合法、排放達標,也不意味著就不會侵犯相鄰關系,因此需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正是相鄰制度和環境管制的不同之處,也是相鄰制度區別于環境管制的特點和優點[6]。不同解讀與不一判定極易侵害當事人權益,甚至減損司法權威。
(二)綠色原則與物權限制的關系把握不當
部分法官因缺乏綠色原則適用的傳統和經驗,沒有很好地掌握適用綠色原則的理念和方法,導致誤用和濫用的發生。如在“梁兔兒與石樓縣林業局恢復原狀糾紛”一案中,被告毀掉原告栽種的一百多畝杏樹而栽種刺槐,法官必須避免僅以綠色原則為根據而支持政府在征收和征用過程中的程序違失,以免對物權人的合法權益造成過度限制或侵害[7];而法院判決事實上使得在被告明知未征得小區業主同意的情形下,獲得了擅自改變小區公共綠地景觀的合法性,架空了全體業主的財產權以及對建筑物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權利[8]。再比如在“上訴人溫某、某酒店與上訴人某老干部活動中心租賃合同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導致合同解除的違約承租人無權請求出租人賠償剩余租賃期內裝飾裝修價值損失;但二審法院認為,根據綠色原則的規定,對于殘存之裝飾裝修,一審法院認定拆除后帶走不妥應予以糾正,于是以綠色原則突破了違約承租人裝修殘值補償請求的一般性禁止規定[9]。
這些矛盾的產生與物權限制的初衷亦不相符。綠色原則本是物權合理讓渡于環境保護的前提,卻基于其過于開放的綠色原則內涵與外延,成為公權力不當限制公民財產權益的管道。“我國司法系統需要加強法官的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同時要摒棄形式主義,更加注重實質性的公正判斷。[10]”,若不加以節制,在一些情況下,綠色原則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并被視為限制公民擁有物權的立法產物。綠色原則與物權限制的距離需要充分結合立法初心,但顯然在現實操作上這一價值難以衡平。
(三)新興環境權益是否入法爭論不一
環境問題的多元性與動態性使新興環境權益的設定處于尷尬境地,司法實踐對此類權利是否應予保護各地,裁判尺度亦不一。比如眺望權,即觀景權,是房屋的所有權人和用益物權人從其房屋向外眺望一定景觀,從中獲得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的權利。我們國家的法律雖已設定了相鄰關系中權利類型的列舉,但尚未包括視覺衛生權、眺望遠景權等新型權利。在“丁偉、馮波等排除妨礙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因眺望權并非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保護權利,故對于原告提出被告侵犯其眺望權,法院不予支持[11]。但在“黃星煌等訴無錫市錦江旅游客運有限公司等相鄰關系糾紛”案中,判決認定雖然眺望遠景權、視覺衛生權并未被規定在我國有關相鄰關系法律的權利范圍內,但它們應該被納入相鄰關系的范圍之內。在相鄰關系中,眺望遠景權應當被限定于必要的容忍程度,是否構成妨礙應該以有利生產、方便生活以及公平合理的原則為基礎來確定,不能僅僅以有遮擋就可以強制性保護。
三、綠色條款動態審理司法突圍路徑
(一)裁判思維的動態革新
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在裁判理念和裁判方法上加以更新。首先,在裁判理念上要破除所有權絕對化的理念,認同物權負有社會義務的正當性,“財產權所有者享有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義務,環境義務成為財產權的內在內容而非外部限制,具體就綠色原則在物權限制中的司法適用而言,法官在裁判涉及綠色原則的物權限制糾紛時,應該在理念上認同物權負有社會義務的正當性[12]。”其次,應該恰當遵循比例原則,并確保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需要程度與物權限制的程度相平衡,防止適用綠色原則時對物權人的權益造成過多的負面影響。比如“梁某訴黃某排除妨礙糾紛案”中,被告父母生前在原告所有的宅基地上種植一株蘋婆,該樹樹齡超過30年,法院認為,原告作為土地使用權人,有權要求被告排除妨礙,但案涉樹木已種植多年,如果將其砍伐不利于資源保護及有效利用,將案涉樹木搬離梁某的用地紅線范圍即可。該案即以綠色原則限制了原告要求砍伐該樹木的訴訟請求,很好地貫徹比例原則。
(二)適度容忍的靈活適用
雖然法條中將違反國家規定作為相鄰污染侵害的判斷標準,但司法實踐中,對于未超過國家規定,超出一般人的容忍限度的,還是應該給予司法救濟。當然,這需要結合個案的情況進行利益衡量。至于如何判斷是否超出一般人的容忍限度,具體而言,“要對被侵害利益的種類、利益、性質、被侵害程度、加害行為樣態、受害方具體情況和加害方具體情況,并結合不動產利用的先后關系、污染者所從事行為的社會價值和必要性綜合衡量[13]。”適度容忍的相關理念,是將民法所倡導的友善和諧之底層邏輯加以發揚的具象形態,有賴于民眾對公序良俗的內化與認可,亦有賴于立法者、司法者及時的概念辨析與文書補足。
(三)以發展目光審視新興權益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以權利類型化和法定化為原則,但生態保護與物權限制的關系不是絕對的,要應時變化。比如視野開闊的感覺確實是一種愉悅,但眺望權要求法律提供保護,這顯然超越了正常生活的需要,特別是在高樓林立的大城市中,要求這種權益顯然超出了滿足正常生活需要的限度。從法律性質、產生原因及法定義務的層次來看,眺望權應歸于地役權保護的范疇,地役權是當事人逾越相鄰關系限度而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其范圍可以突破基本的生產、生活需要而擴大到更高層次的精神、物質享受之需,但是看見風景及美好景觀難以成為社會大部分群體所認可的“維護正常生產、生活的最低需要”。因此,現階段將眺望權等同于法定的相鄰權予以強制性的保護是不現實的,但是司法實踐應不排斥當事人通過設立地役合同予以約定。
生態保護與物權限制作為一種動態適應關系,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可能會有不同的側重和要求。如在“劉某訴上海市靜安區某小區業主委員會等業主撤銷權糾紛”一案中,業主大會或業主委員會依據民法典第272條“業主對其建筑物專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業主行使權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作出禁止業主在其私有產權車位上安裝車輛充電樁的決議。法院判決支持原告,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的安裝將會給原告使用清潔能源的車輛提供便利,減少對化石能源的消耗,它在利益衡量過程中受到相對傾斜的優先考量,實現生態環境保護之目的,順應了科技進步、綠色發展的時代潮流。可見,在司法個案中,新興的事物或是權利應與立法本心與環保原則進行價值掛鉤、法益參考,以發展的目光看待靜態的綠色條款。
四、結語
綠色原則的出現被給予實現“物盡其用與綠色使用”價值目標的厚望,有力回應當下環境治理難題。但無論從理論探究還是個案分析來看,綠色原則的司法化之路道阻且長,由于該命題的新穎,學界與實務界關于其材料略顯單薄,從而引申出裁判難統一、限制欠清晰、規則待完善等治理困境。隨著裁判思維的更迭、和諧社會中適度容忍的發揚以及新興權利的逐步充實,在多變的環境問題下,綠色原則司法應用將逐步走出困境,實現動態問題的靈活應對。
參考文獻:
[1]徐國棟.綠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4.
[2]張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制定[J].中國法學,2017(2):5-24.
[3]呂忠梅.關于物權法的“綠色”思考[J].中國法學,2000(5):46.
[4]陳甦.民法總則評注(上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69.
[5]參見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區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3827號民事判決.
[6]呂忠梅課題組.綠色原則在民法典中的貫徹論綱[J].中國法學,2018(1):5-27.
[7]陶凱元.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切實貫徹實施《民法典》綠色條款[J].法律適用,2020(23):3-7.
[8]參見(2019)蘇0582民初2569號民事判決書.
[9]竺效.論綠色原則的規范解釋司法適用[J].中國法學,2021(4):83-102.
[10]林來梵,張卓明.論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從規范性法學方法論角度的一個分析[J].中國法學,2006(2)122-132.
[11]參見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遼01民終5474號民事判決書.
[12]鄭少華,王慧.綠色原則在物權限制中的司法適用[J].清華法學,2020,14(4):159-179.
[13]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472.
作者簡介:王加世(2001.11-),女,漢族,浙江紹興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民商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