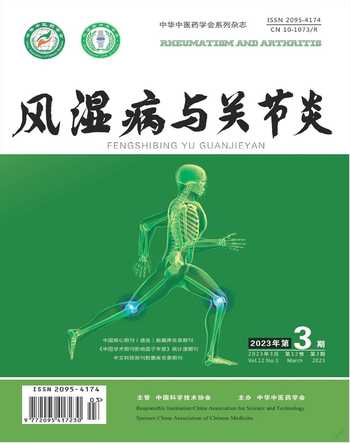基于溫陽法論治強(qiáng)直性脊柱炎探析
王紅森 韋尼
【摘 要】 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屬中醫(yī)學(xué)“大僂”范疇,陽虛是其重要的發(fā)病基礎(chǔ)。首先,強(qiáng)直性脊柱炎患者以陽虛體質(zhì)居多,督脈為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的主要病位,督脈虧虛衛(wèi)外不固,則風(fēng)寒濕邪侵襲肌表,痹阻經(jīng)絡(luò)氣血,日久釀生痰濁、瘀血等病理產(chǎn)物,導(dǎo)致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發(fā)病。其次,葡萄膜炎、肺間質(zhì)纖維化、骨質(zhì)疏松、焦慮抑郁狀態(tài)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并發(fā)癥的出現(xiàn)也多與陽氣不足有關(guān)。因此,溫陽是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的主要治療原則。從溫陽以祛邪、溫陽以通絡(luò)、溫陽以養(yǎng)臟3個(gè)方面入手,達(dá)到陽氣充沛流暢,化痰祛瘀以及通絡(luò)止痛的治療目的。但溫陽是一個(gè)非常廣泛的概念,絕非單純使用溫?zé)崴幯a(bǔ)充陽氣,而是要順應(yīng)陽氣充沛流暢的特點(diǎn),且注意溫補(bǔ)與溫通并重。在具體臨證遣方用藥上應(yīng)該擅用辛味藥,取其“能行、能散、能補(bǔ)”的功效特點(diǎn),同時(shí)還要不忘陰中求陽,靈活配伍甘溫甘寒類養(yǎng)陰藥,以求“陰生陽長”及久郁之燥熱邪熱傷陰。
【關(guān)鍵詞】 強(qiáng)直性脊柱炎;溫陽法;督脈虧虛;辛味藥;陰中求陽
強(qiáng)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一種由遺傳、環(huán)境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導(dǎo)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好發(fā)于青壯年,以骶髂關(guān)節(jié)、脊柱關(guān)節(jié)突及脊柱旁軟組織慢性炎癥為主要臨床表現(xiàn)[1]。AS屬中醫(yī)學(xué)“大僂”范疇,現(xiàn)代中醫(yī)學(xué)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總結(jié)AS是在正氣不足的內(nèi)因作用下,風(fēng)、寒、濕、痰濁、瘀血等病邪相互作用,導(dǎo)致經(jīng)絡(luò)氣血運(yùn)行不暢而發(fā)病[2]。目前,中醫(yī)學(xué)對于AS的辨證分型尚無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各醫(yī)家根據(jù)自身學(xué)術(shù)思想及臨床診療經(jīng)驗(yàn)將AS分為不同證型或不同時(shí)期進(jìn)行論治。筆者認(rèn)為,鑒于AS發(fā)病部位與人體督脈循行路線高度重合,而督脈為人體“陽脈之海”,且《素問·骨空論篇》有“督脈為病,脊強(qiáng)反折”之說,可推知陽虛與AS發(fā)病、進(jìn)展及預(yù)后等密切相關(guān),甚至可以作為AS發(fā)病的始動(dòng)因素。因此,臨證可從溫陽論治AS,但需結(jié)合患者具體病情辨證論治。
1 陽虛與AS發(fā)生、發(fā)展
1.1 陽虛體質(zhì)與AS的發(fā)生 “大僂”一詞首見于《素問·生氣通天論篇》,其云:“陽氣者,精則養(yǎng)神,柔則養(yǎng)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可見陽虛與大僂的發(fā)生密切相關(guān)。現(xiàn)有研究發(fā)現(xiàn),AS發(fā)病與陽虛體質(zhì)密不可分。蔡美美等[3]運(yùn)用中醫(yī)體質(zhì)量表對107例AS患者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結(jié)果發(fā)現(xiàn),AS患者幾乎全是偏頗體質(zhì),其中又以陽虛質(zhì)者占比最高,約32.71%。錢佳麗等[4]進(jìn)一步對AS患者及其家系成員共254人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AS患者病理體質(zhì)中陽虛體質(zhì)占比最高,為11.6%,顯著高于AS患者家系中的健康人群。體質(zhì)是人體在先天稟賦和后天獲得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形態(tài)結(jié)構(gòu)、生理功能和心理狀態(tài)等方面綜合且相對穩(wěn)定的固有特質(zhì),不同體質(zhì)人群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對疾病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的傾向性不同,即《靈樞·五變》曰:“肉不堅(jiān),腠理疏,則善病風(fēng)。”“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粗理而肉不堅(jiān)者,善病痹。”陽虛體質(zhì)人群較健康人群多存在先天陽氣不足,衛(wèi)外功能較薄弱,而風(fēng)寒濕等外邪又易傷陽氣,可輕易突破衛(wèi)表并逐漸深入筋骨,最終發(fā)為大僂。除了陽虛體質(zhì)與AS發(fā)病密切相關(guān)外,還有學(xué)者通過中醫(yī)證候?qū)W研究發(fā)現(xiàn),腎虛督寒證、腎陰虛證、濕熱痹阻證和瘀血痹阻證是AS患者最具代表性的4個(gè)證候群,其中腎虛督寒證占比最高,而腎陰虛證兼見腎陽虛,濕熱痹阻證兼有脾陽虛,提示陽虛也是其他證型演變的基礎(chǔ)[5]。國醫(yī)大師朱良春[6]認(rèn)為,AS病機(jī)以陽氣虛弱為基礎(chǔ),尤以腎督虧虛為根本。
1.2 陽虛邪湊與AS的發(fā)展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指出:“陽者,衛(wèi)外而為固也。”表明陽氣充沛流暢是抵御邪氣侵襲的關(guān)鍵。吳氏扶陽學(xué)派傳人彭江云[7]認(rèn)為,陽虛邪湊是AS病情進(jìn)展的關(guān)鍵,尤其偏重于腎陽與督脈的虧虛。王上增[8]認(rèn)為,AS患者腎氣不足一方面可引起脊柱骨髓不充,陽氣不足難以抗邪;另一方面可導(dǎo)致督脈失養(yǎng),陽氣循行不暢,化生痰濕、瘀血,進(jìn)而加重AS病情。劉健[9]則強(qiáng)調(diào)不可忽視脾陽虛在AS病情進(jìn)展中的重要作用。脾陽虛則陽氣化生不足,腠理失固,外邪易襲;同時(shí),脾陽虛還可造成津液運(yùn)化失常而化生痰濕,痰濕與瘀血互結(jié)亦可加重AS病情。《靈樞·百病始生》云:“風(fēng)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dú)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fēng),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由此可見,在AS發(fā)病中風(fēng)寒濕等病邪是外因,陽氣虧虛是重要內(nèi)因。AS患者多屬陽虛體質(zhì),衛(wèi)陽不足無力抵抗外邪;又因督脈為人體“陽脈之海”,行于人體脊柱正中,所蓄灌之陽氣既溫養(yǎng)自身,又溫養(yǎng)脊柱及周圍關(guān)節(jié)筋肉、皮膚腠理。陽氣不足則督脈、脊柱、周圍關(guān)節(jié)筋肉、皮膚腠理失養(yǎng),無力抗邪,風(fēng)寒濕邪更易侵犯脊柱正中,痹阻經(jīng)絡(luò)氣血,日久勢必耗傷本已不足之陽氣,釀生痰濁、瘀血等有形之病理產(chǎn)物,進(jìn)而促進(jìn)AS發(fā)生、發(fā)展。
1.3 陽虛與AS的脊柱損傷 最大程度保護(hù)脊柱功能,避免及減少脊柱強(qiáng)直畸形是AS的主要治療目標(biāo)。目前,有不少學(xué)者主張臨證論治AS應(yīng)首辨“寒熱”,因“寒”與“熱”性質(zhì)不同直接決定了AS患者的脊柱損傷程度,其中“寒”主要指腎虛督寒,而“熱”主要為濕熱痹阻。陳愛萍等[10]回顧性研究277例AS患者寒熱證候分布特點(diǎn)與脊柱結(jié)構(gòu)損傷的相關(guān)性,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寒證組AS患者脊柱結(jié)構(gòu)損傷程度較熱證組更為嚴(yán)重。孔維萍等[11]也發(fā)現(xiàn)了相似的結(jié)論。韓善夯等[12]進(jìn)一步研究發(fā)現(xiàn),盡管熱證組AS患者C反應(yīng)蛋白、紅細(xì)胞沉降率等炎癥指標(biāo)水平高于寒證組,但骶髂關(guān)節(jié)炎CT分級卻低于寒證組。筆者在臨床工作中也發(fā)現(xiàn),不少辨證屬濕熱痹阻等熱證的AS患者起病急,疼痛晨僵癥狀重,初次就診時(shí)間更早,且擁有更高水平的炎癥指標(biāo),但并未出現(xiàn)嚴(yán)重的骶髂及脊柱關(guān)節(jié)病變;而辨證屬腎虛督寒等寒證AS患者起病較隱匿,疼痛晨僵癥狀輕,往往容易延誤治療時(shí)機(jī),較早就出現(xiàn)骶髂及脊柱關(guān)節(jié)強(qiáng)直畸形。筆者認(rèn)為,熱證AS患者雖未表現(xiàn)出畏寒、肢冷、體倦、納呆、便溏等陽虛表現(xiàn),但此時(shí)體內(nèi)陽氣已虛,只是程度不重而尚未表現(xiàn);但隨著濕熱、痰瘀等病邪進(jìn)一步耗傷陽氣,陽虛證候逐漸顯現(xiàn),進(jìn)而加重AS病情造成脊柱損傷。
1.4 陽虛與AS的并發(fā)癥 葡萄膜炎是AS最常見的并發(fā)癥之一。何路等[13]總結(jié)王為蘭臨證經(jīng)驗(yàn),認(rèn)為腎陽不足是AS伴發(fā)前葡萄膜炎的基礎(chǔ)。腎陽不足則津液、血液運(yùn)行無力,痰濕、瘀血內(nèi)傷,日久可耗傷陰津,從而導(dǎo)致肝陰不足、目失所養(yǎng),使?jié)駸岫拘八僖u于目,變生急性前葡萄膜炎。骨質(zhì)疏松也是AS患者常出現(xiàn)的并發(fā)癥之一。孔維萍等[14]發(fā)現(xiàn),腎虛督寒證AS患者的骨密度顯著低于濕熱痹阻證患者,強(qiáng)調(diào)在治療中要注意扶助陽氣。此外,由AS引發(fā)的肺間質(zhì)纖維化也不容忽視,雖然關(guān)于其中醫(yī)病因病機(jī)研究較少,但由于腎為人體一身陽氣之本,而肺的陽氣亦有賴于腎陽的充養(yǎng),故陽氣不足在AS患者繼發(fā)肺間質(zhì)纖維化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田麗等[15]認(rèn)為,肺間質(zhì)纖維化的病機(jī)根本在于“陽化氣”不足,治療上應(yīng)注重溫陽化氣。王加豪等[16]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肺間質(zhì)纖維化患者多存在肺腎陽氣不足,治療時(shí)不可忽視溫補(bǔ)肺腎之陽。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陽氣不足是AS伴發(fā)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的基礎(chǔ),或因脾腎陽虛,元神失養(yǎng),無力鼓舞精神,或因陽虛濕阻,氣機(jī)運(yùn)行不暢,瘀血痹阻而致。
2 溫陽是AS的主要治療原則
2.1 溫陽以祛邪 鑒于AS發(fā)病關(guān)鍵在于陽虛邪湊,故臨床上治療AS當(dāng)從溫陽祛邪入手,尤以溫壯腎陽為主。陽氣充沛流暢,則外邪可散,內(nèi)邪得化,肢體經(jīng)絡(luò)氣血運(yùn)行無阻,《扁鵲心書》曰:“凡治痹,非溫不可。”范永升[17]認(rèn)為,濕邪是AS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致病因素,強(qiáng)調(diào)在溫陽的基礎(chǔ)上靈活運(yùn)用不同藥物祛除濕邪,如以寒濕為主者,常用附子、制川烏、細(xì)辛等溫化寒濕,并配伍防風(fēng)、羌活、獨(dú)活等風(fēng)藥宣散水濕;以痰濕水飲為主者,常以苓桂術(shù)甘湯為基礎(chǔ)溫陽化氣、利水祛濕。沈家驥[18]則將制附子、制川烏、制草烏三藥合用,認(rèn)為制附子性大熱且走而不守,制川烏“氣鋒銳且急”,制草烏止痛力更甚,三者配伍功專力宏,共奏溫陽散寒祛濕之效。筆者認(rèn)為,AS的發(fā)生、發(fā)展是在陽虛基礎(chǔ)上多種病邪趁虛而入,形成痰濁、瘀血等病理產(chǎn)物相互作用,而上述病理產(chǎn)物又可進(jìn)一步耗傷陽氣,加劇痰濁、瘀血的形成,以此形成惡性循環(huán)。因此,辨治AS一定要敢于打破該惡性循環(huán),臨證時(shí)以溫陽為基礎(chǔ),聯(lián)合散寒、祛濕、化痰、散瘀等藥物,使體內(nèi)陽氣充足,氣血津液循行得以暢通,減少痰濁、瘀血等病理產(chǎn)物的生成。
2.2 溫陽以通絡(luò) 疼痛是AS患者的主要臨床表現(xiàn),筆者認(rèn)為,無論是“不通則痛”,還是“不榮則痛”,都與陽氣不足有關(guān),治療上當(dāng)以溫陽為基礎(chǔ),將“通”與“榮”兩者相互滲透。蔡余力等[19]運(yùn)用曹貽訓(xùn)經(jīng)驗(yàn)方以補(bǔ)腎通陽之法治療AS患者,結(jié)果顯示,可以顯著改善AS患者夜間疼痛、晨僵等癥狀,并有效降低血清腫瘤壞死因子-α、轉(zhuǎn)化生長因子-β1等炎性因子水平。田元生[20]認(rèn)為,AS病機(jī)要點(diǎn)除了腎陽虛外,還存在督脈瘀阻,提出“補(bǔ)腎通督祛瘀”的治療原則,采用任督周天大艾灸療法促進(jìn)陽氣循環(huán)流動(dòng),使任脈通、督脈固,可有效減輕患者疼痛癥狀。閻小萍[21]則強(qiáng)調(diào)治療AS時(shí)應(yīng)注意運(yùn)用華佗夾脊穴溝通督脈,既可溫養(yǎng)溫通陽氣,又能祛除兩經(jīng)邪氣,使經(jīng)絡(luò)通暢,疼痛自減。
2.3 溫陽以養(yǎng)臟 《素問·痹論篇》云:“痹病,五臟虧虛為之大因。”強(qiáng)調(diào)臟腑虧虛在痹病發(fā)病中的重要作用。AS發(fā)病初期病位多在肌表經(jīng)絡(luò),病久正虛邪進(jìn),病位由表入里,深入心、肝、脾、肺、腎五臟,導(dǎo)致病情進(jìn)一步加重,并造成多種并發(fā)癥,影響重要臟器功能。鑒于此,明·李中梓在《醫(yī)宗必讀》中提出治痹“在外者祛之猶易,入臟者攻之實(shí)難;治外者散邪為急,治臟者養(yǎng)正為先”的原則,即注重溫補(bǔ)五臟之陽氣。王鴻旭等[22]采用肉蓯蓉、鎖陽、白術(shù)、黨參、茯苓等溫補(bǔ)脾腎陽氣藥物治療AS,并與西藥甲氨蝶呤對照,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治療組在降低癥狀體征評分及實(shí)驗(yàn)室指標(biāo)方面更為明顯。仇湘中[23]則強(qiáng)調(diào)平補(bǔ)法當(dāng)貫穿AS治療始終,培補(bǔ)后天以養(yǎng)先天,臨證多在補(bǔ)腎強(qiáng)骨湯的基礎(chǔ)上重用黃芪、白術(shù)等健脾益氣之品。劉健[24]更強(qiáng)調(diào)脾陽不足對AS發(fā)生及演變的重要性,臨床上常用藥對薏苡仁、山藥健脾化濕,用桂枝、附子、杜仲等溫腎陽以補(bǔ)脾陽。
3 用藥特點(diǎn)
3.1 溫補(bǔ)與溫通并重 《醫(yī)理真?zhèn)鳌吩唬骸瓣枤饬魍ǎ帤鉄o滯,自然百病不作。陽氣不足,稍有阻滯,百病叢生。”由此可見,陽氣不僅要“足”,更要“通”,否則后果不只是“百病叢生”,還可能會(huì)導(dǎo)致疾病的遷延不愈。隨著病情進(jìn)展,AS患者常常出現(xiàn)臟腑、氣血津液的虛損,以及體內(nèi)痰濕、水飲、瘀血等病理產(chǎn)物并存的情況,這些病理產(chǎn)物阻礙氣血津液的正常循行,同時(shí)消耗人體自身陽氣,所以在治療過程中必須“補(bǔ)”“通”并重,既要顧及臟腑陽氣的虛損,又要兼顧祛除體內(nèi)的病理產(chǎn)物。臨床上,以陽氣不足為主者,可選擇黃芪、白術(shù)、黨參、狗脊、巴戟天、淫羊藿、補(bǔ)骨脂等;以陽氣不通為主者,可選擇附子、桂枝、麻黃、細(xì)辛、威靈仙、羌活、獨(dú)活等。紀(jì)偉[25]治療AS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早中期多溫通,晚期多溫補(bǔ),即治療早中期患者多用獨(dú)活、羌活、防風(fēng)、海風(fēng)藤、威靈仙等,治療晚期患者多用淫羊藿、鹿角片、狗脊、黃芪、黨參、白術(shù)等。但需要注意的是,陽氣不足與陽氣不通可同時(shí)存在,這就要求仔細(xì)辨別兩者主次,在用藥上有所偏重。
3.2 擅用辛味藥 《素問·至真要大論篇》云:“辛甘發(fā)散為陽。”汪昂在《本草從新》中指出:“辛者,能散,能潤,能橫行。”可見辛味藥順應(yīng)人體陽氣升散、流動(dòng)的特點(diǎn),能夠促進(jìn)人體陽氣的循行流動(dòng),從而推動(dòng)機(jī)體內(nèi)氣血津液的循行。在AS的治療中,應(yīng)該擅用辛味藥,如附子、干姜、細(xì)辛、補(bǔ)骨脂、淫羊藿、巴戟天、菟絲子、威靈仙、羌活、白芷、桂枝、蒼術(shù)、半夏、生姜、陳皮等。溫天燕[26]擅用細(xì)辛治療AS,多以全草入藥并先煎30 min,再加入其他藥物相互牽制,用量可達(dá)15~30 g;認(rèn)為細(xì)辛既散表寒又溫里陽,通表達(dá)里,可獲奇效。周彩云[27]則擅用威靈仙治療AS,認(rèn)為威靈仙“走而不守,宣通十二經(jīng)絡(luò)”,入膀胱經(jīng)溫通陽氣且通絡(luò)止痛。辛味藥種類繁多,在治療AS時(shí)應(yīng)根據(jù)藥物的歸經(jīng)及患者具體證型特點(diǎn)進(jìn)行更細(xì)致的選擇。如寒邪明顯者,可選草烏、制川烏、附子等辛熱之品溫陽散寒;陽虛明顯者,則多用淫羊藿、巴戟天、補(bǔ)骨脂等辛溫之品溫壯腎陽;痰濕偏重者,可多用蒼術(shù)、半夏、陳皮、蠶砂、草豆蔻之類。此外,葉天士認(rèn)為“絡(luò)主血”“久病入絡(luò)”“血結(jié)必入于絡(luò)”,強(qiáng)調(diào)“絡(luò)以辛為泄”“絡(luò)以辛為治”,首創(chuàng)“辛味通絡(luò)大法”,主張以辛味藥物宣通行散治療痹滯不通。對于伴有瘀血證候的AS患者,還需聯(lián)合紅花、桃仁、川芎、當(dāng)歸、乳香、沒藥等辛味藥祛瘀通絡(luò);而對于病史長久,或痰瘀互結(jié)明顯且常規(guī)藥物治療效果欠佳者,還可聯(lián)合露蜂房、土鱉蟲、全蝎、地龍、蜈蚣、水蛭、穿山甲等蟲蟻類辛味藥搜剔絡(luò)邪,攻積除堅(jiān)。
3.3 不忘陰中求陽 《醫(yī)貫·陰陽論》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明·張景岳也認(rèn)為“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強(qiáng)調(diào)補(bǔ)陽時(shí)應(yīng)注意“陰中求陽”。采用溫陽法治療AS并不意味著選擇用藥時(shí)一溫到底,尤其是對病程長久者,應(yīng)該根據(jù)患者氣血津液的虧虛狀況適當(dāng)滋陰養(yǎng)血。黃勝光[28]臨證治療AS時(shí)多將附子、桂枝、杜仲等溫陽之品與熟地黃、山茱萸、枸杞子、黃精等養(yǎng)陰之藥配伍,防止溫燥太過而傷陰,并通過養(yǎng)陰生血達(dá)到“陰生陽長”的目的。痰濁、瘀血是AS發(fā)生、發(fā)展中形成的有形之邪,若不能及時(shí)祛除,日久必化生邪熱,即《金匱要略》所云:“痞堅(jiān)之處必有伏陽。”而長期使用溫陽類藥物亦可耗傷陰液加重燥熱,患者可出現(xiàn)心煩、燥熱、口咽干、心悸、舌質(zhì)暗紅、脈數(shù)等表現(xiàn)。因此,除甘溫類養(yǎng)陰藥外,AS治療有時(shí)還需聯(lián)合甘寒類養(yǎng)陰藥,如生地黃、麥冬、天冬、知母、玄參等,取清熱潤燥透熱之意。但需要注意的是,此類甘溫或甘寒類養(yǎng)陰之品劑量不可過大,否則有助濕生痰、滋膩礙胃之弊。
4 小 結(jié)
陽虛是AS重要的發(fā)病基礎(chǔ),一方面AS患者以陽虛體質(zhì)居多,督脈虧虛衛(wèi)外不固,則風(fēng)寒濕邪侵襲肌表,痹阻經(jīng)絡(luò)氣血,日久釀生痰濁、瘀血等病理產(chǎn)物,導(dǎo)致AS發(fā)病。另一方面,葡萄膜炎、肺間質(zhì)纖維化、骨質(zhì)疏松、焦慮抑郁狀態(tài)等AS并發(fā)癥的出現(xiàn)也多與陽虛有關(guān)。因此,溫陽是AS的主要原則之一。從溫陽以祛邪、溫陽以通絡(luò)、溫陽以養(yǎng)臟三個(gè)方面入手,達(dá)到陽氣充沛流暢,化痰祛瘀以及通絡(luò)止痛的目的。但溫陽是一個(gè)非常廣泛的概念,絕非單純使用溫?zé)崴幯a(bǔ)充陽氣,而是要順應(yīng)陽氣充沛流暢的特點(diǎn),注意溫補(bǔ)與溫通并重。在具體臨證遣方用藥上應(yīng)該擅用辛味藥,取其“能行、能散、能補(bǔ)”的功效特點(diǎn),同時(shí)還要不忘陰中求陽,靈活配伍甘溫甘寒類養(yǎng)陰藥,以求“陰生陽長”及久郁之燥熱邪熱傷陰。
參考文獻(xiàn)
[1] 謝雅,楊克虎,呂青,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脊柱關(guān)節(jié)炎患者實(shí)踐指南[J].中華內(nèi)科雜志,2020,59(7):511-518.
[2] 袁都戶,郭會(huì)卿.強(qiáng)直性脊柱炎中醫(yī)證型分析及辨證論治的研究進(jìn)展[J].風(fēng)濕病與關(guān)節(jié)炎,2021,10(7):78-80.
[3] 蔡美美,游玉權(quán),陳長賢,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中醫(yī)體質(zhì)特點(diǎn)研究[J].風(fēng)濕病與關(guān)節(jié)炎,2017,6(7):44-46,57.
[4] 錢佳麗,余毅,毛盈穎,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家系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和中醫(yī)體質(zhì)分析[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17,32(12):5599-5602.
[5] 沈逸,丁泓百,程鵬.278例強(qiáng)直性脊柱炎患者中醫(yī)證候分類研究[J].上海中醫(yī)藥雜志,2020,54(7):34-38.
[6] 周淑蓓,鄭福增,展俊平.國醫(yī)大師朱良春運(yùn)用培補(bǔ)腎陽湯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臨床經(jīng)驗(yàn)[J].時(shí)珍國醫(yī)國藥,2020,31(4):966-967.
[7] 楊顯娜,唐海倩,凌麗.彭江云教授運(yùn)用強(qiáng)脊方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淺談[J].風(fēng)濕病與關(guān)節(jié)炎,2021,10(7):29-31.
[8] 武圣超,沈錦濤,李紅旗,等.王上增教授運(yùn)用溫腎通督法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J].河南醫(yī)學(xué)研究,2018,27(13):2305-2307.
[9] 董文哲,方妍妍,文建庭,等.劉健教授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J].風(fēng)濕病與關(guān)節(jié)炎,2018,7(8):47-49.
[10] 陳愛萍,路素言,邵培培,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入院患者寒熱證候特點(diǎn)及其與脊柱損傷和疾病活動(dòng)度關(guān)系研究[J].北京中醫(yī)藥,2018,37(5):440-442.
[11] 孔維萍,金玥,朱笑夏,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寒熱證候的脊柱結(jié)構(gòu)損傷特點(diǎn)[J].中醫(yī)雜志,2015,56(12):1026-1029.
[12] 韓善夯,孫美秀,甘可,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中醫(yī)證候分型與炎癥相關(guān)性分析[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19,34(12):5957-5959.
[13] 何路,張茂菊,李紅艷,等.王為蘭學(xué)術(shù)思想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伴發(fā)葡萄膜炎的經(jīng)驗(yàn)體會(huì)[J].中國中醫(yī)眼科雜志,2017,27(5):339-340.
[14] 孔維萍,朱笑夏,金玥,等.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寒、熱不同證型的骨密度與疾病活動(dòng)度特點(diǎn)[J].中日友好醫(yī)院學(xué)報(bào),2015,29(3):151-153,157.
[15] 田麗,張偉.基于“陽化氣,陰成形”理論的肺間質(zhì)纖維化發(fā)病機(jī)制及治療探討[J].時(shí)珍國醫(yī)國藥,2019,30(3):647-648.
[16] 王加豪,張偉.淺論陽虛在間質(zhì)性肺疾病中的作用[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21,36(2):1126-1128.
[17] 楊科朋,高祥福,王新昌,等.范永升教授治療脊柱關(guān)節(jié)炎經(jīng)驗(yàn)[J].風(fēng)濕病與關(guān)節(jié)炎,2019,8(7):33-35.
[18] 沈宇明,文繼紅,沈家驥.沈家驥運(yùn)用中醫(yī)藥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J].中醫(yī)藥導(dǎo)報(bào),2021,27(4):187-191.
[19] 蔡余力,張興彩,張厚君,等.補(bǔ)腎通陽法調(diào)節(jié)強(qiáng)直性脊柱炎患者TNF-α和TGF-β1的研究[J].中醫(yī)藥學(xué)報(bào),2017,45(3):70-73.
[20] 張婷婷,張玉飛,楊坤鵬,等.田元生教授補(bǔ)腎祛瘀通督法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J].時(shí)珍國醫(yī)國藥,2020,31(4):971-974.
[21] 楊永生,劉瓊,王紅梅,等.閻小萍教授基于治未病理論從腎督虧虛論治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的經(jīng)驗(yàn)[J].風(fēng)濕病與關(guān)節(jié)炎,2021,10(8):43-46.
[22] 王鴻旭,蒿長玲,李現(xiàn)林,等.舒督通絡(luò)方治療脾腎陽虛型強(qiáng)直性脊柱炎臨床研究[J].中醫(yī)臨床研究,2018,10(30):99-102.
[23] 薛凡,鄧豪,鄧咪朗,等.仇湘中教授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介紹[J].中國醫(yī)藥導(dǎo)報(bào),2019,16(18):133-135,140.
[24] 孫廣瀚,劉健,龍琰,等.劉健教授從脾虛濕盛論治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抉微[J].浙江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44(4):373-376.
[25] 孟闖闖,紀(jì)偉.紀(jì)偉教授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探析[J].浙江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7,41(6):502-505.
[26] 王英杰,丘文靜,溫天燕.溫天燕綜合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J].世界中西醫(yī)結(jié)合雜志,2017,12(8):1069-1071.
[27] 劉珊,武妤霞,李詩雨,等.周彩云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經(jīng)驗(yàn)淺析[J].遼寧中醫(yī)雜志,2018,45(1):36-39.
[28] 楊朔,賀守第,徐劍峰,等.黃勝光教授治療強(qiáng)直性脊柱炎臨床經(jīng)驗(yàn)[J].湖南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38(7):760-764.
收稿日期:2022-10-11;修回日期:2022-11-25
作者單位: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東方醫(yī)院,北京 100078
通信作者:韋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