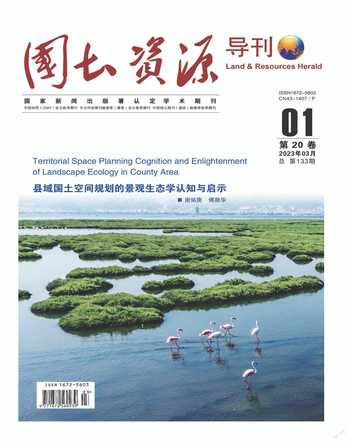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的國家公園邊界劃定研究
曾麗婷 戴冰武 曾毅 呂煥哲 譚暢 王一淳



摘? ? 要:國家公園邊界的劃定是公園設立、規劃設計、實施管理的首要環節,對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護至關重要。現有研究多從定性角度對國家公園邊界劃定的原則、過程、影響因子進行分析。采用定量加定性的方式,基于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的同時考慮管理可行性劃定國家公園邊界的研究較少。本研究以擬建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劃定為例,提出一套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結合管理可行性要素模擬劃定國家公園邊界的方法。研究結果顯示:(1)優化后的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面積約2 833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6.11%;(2)優化后的洞庭湖國家公園范圍以10個自然保護地為主要組成部分,包括了周邊生態功能重要、生態系統脆弱、自然生態保護空缺的區域,各自然保護地之間的聯接度較好;(3)擬建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與現有自然保護地的邊界及生態保護紅線擬合度較高,可有效促進現有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
關鍵詞:生態安全格局;國家公園;邊界;洞庭湖
中圖分類號:TU984.18?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1672-5603(2023)01-06-08
Research on Boundary Delimitation of National Park Based on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Take the Proposed Dongting Lake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
Zeng Liting, Dai Bingwu, Zeng Yi, LvHuanzhe, Tan Chang, Wang Yichun
(1.Hunan Planning institute of Land and Resources, Changsha Hunan 410119;
2.Hunan Key Lab. of Land & Resource Evaluation & Utilization, Changsha Hunan 410119)
Abstract:The delimita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boundary is the primary link of the park establishment, planning,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is crucial to the integrity protection of the ecosystem. The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impact factors of boundary delimitation of national parks from a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delimit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ecosystem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easibility of management by adop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study proposes a set of method to simulate and delimit the boundary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nd the management feasibility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boundary area of the optimized Dongting lake national park is about 2 833 square kilometers, accounting for 6.11%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study area; (2) The scope of the optimized Dongting Lake National Park is mainly composed of 10 natural reserves, including areas with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 fragile ecosystems, and gaps in na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reserves is good; (3) The boundary of the proposed Dongting lake national park and the existing nature reserve an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have a high fitting degree,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xisting nature reserve.
Keywords: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national park; boundary;Dongting lake
0 引言
國家公園是國家生態安全的關鍵區域,是最重要的自然保護地類型[1-2],其邊界的劃定是公園設立、規劃設計、實施管理的首要環節,對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護至關重要。王夢君等[3]提出了將自然地理、生物資源、旗艦動物物種、資源利用、資源管理、基礎設施、社區作為國家公園范圍劃定中的主要因子。閔慶文[4]認為打破條塊分割、破碎化嚴重的現象是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的目的之一,行政邊界應在可行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服從于保護需求,國家公園邊界劃定須優先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劉增力[5]以擬建青海湖國家公園為例,在考慮自然地理、生物資源、重點保護物種等自然資源本底因素基礎上,疊加管理可行性因素,劃定國家公園邊界。孫喬昀等[6]以擬建松嫩平原國家公園為例,選取生態系統完整性、自然本底原真性、管理可行性3個方面的指數,通過歸一化疊加分析,模擬劃定國家公園邊界。目前我國已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5大國家公園,對于國家公園邊界的劃定仍處于探索階段,在劃界過程中并無一套規范的流程和方法。現有研究多從定性角度對國家公園邊界劃定的原則、過程、影響因子進行分析。采用定量加定性的方式,基于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的同時考慮管理可行性劃定國家公園邊界的研究較少。
國家公園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最重要、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自然保護地類型,生態過程也最完整[7],而生態安全格局對維護和控制生態過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8],是判別和建立生態系統完整性空間的重要依據[9],因此,通過生態過程的分析,構建生態安全格局,是判別國家公園生態系統完整性空間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湖南省委、省政府積極推動設立洞庭湖國家公園[10]。研究借鑒已有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劃界方法,結合洞庭湖區實際,通過識別國家公園“傘護種”和“旗艦種”的重要棲息地,選取影響其生態過程的關鍵因子,利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判別生態安全關鍵性區域,并結合現行國土空間規劃三條控制線等管理可行性要素,模擬劃定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探討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的國家公園劃界的合理途徑,對于湖南省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劃定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洞庭湖地處長江中游,湖南省東北部,由東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組成,是我國第二大淡水湖、長江最重要的調蓄湖泊,被譽為“長江之腎”。本次研究范圍包含東、南、西洞庭湖及周邊河湖沖積平原、環湖丘陵崗地、低山區域,行政區劃上包括益陽、常德、岳陽3市及長沙望城區(圖1),共25個縣(市、區),總面積約4.64萬km2。研究區內現有東洞庭湖、西洞庭湖、壺瓶山、湘陰橫嶺湖等11個自然保護區和大通湖、大云山、石牛寨、老祖巖等75個自然公園,有中華鱘、長江江豚、胭脂魚、大天鵝、小天鵝等多種國家一、二級保護物種,且原生性陸生維管植物眾多[11],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
1.2 數據來源
國土變更調查(2020年)、數字高程模型、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等數據來源于湖南省自然資源部門,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自然保護地數據來源于湖南省林業部門。研究統一采用2000國家大地坐標系和1985國家高程基準作為空間定位基礎,采用50 m×50 m柵格。
1.3 研究方法
研究基于“源—匯”理論,識別洞庭湖區重要生態源地,根據已有相關研究及湖區實際選取洞庭湖區生態安全的主要影響因素作為阻力因子,利用層次分析法計算各阻力因子權重,并通過加權疊加形成綜合阻力面,再利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簡稱MCR)模擬洞庭湖區指示物種從重要生態源地擴散的生態過程,判別生態安全關鍵性區域,生成洞庭湖國家公園初始邊界,保障生態系統完整性空間。在此基礎上,結合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及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等管理可行性要素進行優化,形成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具體的技術路線如圖2所示。
(1)識別重要生態源地。“源”在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中一般特指指示物種或珍稀物種棲息地,是生態過程中物種擴散的源點。在國家公園的設立中,為提高生物多樣性而確立的保護對象通常是多個物種,一般以傘護種和旗艦種為指示物種,它們所反映的對自然保護地的生境需求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研究通過分析傘護種和旗艦種棲息地生境特征、文獻綜述研究、咨詢生物學專家,結合洞庭湖區自然保護地現狀確定重要生態源地。
(2)建立阻力面。物種擴散時實現對空間的控制和覆蓋需要克服特定影響因素的阻力,這些影響因素構成了生態過程中物種擴散的阻力因子。科學構建生態安全阻力因子評價體系,對生態過程模擬、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生態系統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研究以現有傘護種和旗艦種對生境的要求,結合既有文獻研究和洞庭湖區實際情況,選擇土地利用類型、降水量、坡度、高程、距城鎮的距離、距道路的距離、距河流的距離等生態安全影響因素作為阻力因子。土地利用類型決定了是否適合物種生存;高程和坡度影響物種的活動范圍;降水量對重要生態源地的生態系統具有顯著影響[12];距城鎮、距道路的距離決定了物種活動受人類活動干擾程度,距河流的距離越近則越有利于生物活動[13-14]。利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阻力因子權重,根據各單因子內部要素對物種的影響,結合已有相關研究[15]確定各阻力因子的相對阻力值,將阻力值賦為5個等級(表1),數值越大表示對物種擴散的阻力越大。物種克服阻力因子形成空間運動趨勢的時空連續體稱為阻力面,相同阻力值的空間組成的等阻力線類似于等高線,阻力面類似于地形表面。通過Arc-GIS10.6提取單因子各要素形成單因子阻力面,根據各阻力因子權重采用柵格計算器綜合疊加7個單因子阻力面,加權求和得到生態安全綜合阻力面。
(3)判別初始邊界。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是衡量物種在從重要生態源地到目的地運動過程中克服阻力所耗費代價的模型,該模型可通過Arc-GIS10.6中的成本距離分析模塊實現。其最小累積阻力值的大小與物種距離重要生態源地的空間距離及其通過阻力面的阻力值大小正向相關,反映了物種擴散的趨勢。最小累積阻力值可作為判斷單元之間連通性與相似性的依據[16]。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MCR表示從重要生態源地j在空間中擴散至某點的最小累積阻力值;f為MCR與變量間乘積(Dij×Ri)的函數;Dij表示重要生態源地j至其他重要生態源地i所經過的空間距離;Ri表示重要生態源地i在空間中某一方向上的擴散阻力系數。
基于最小累積阻力模型,利用成本距離工具,以重要生態源地為基礎,綜合阻力面為擴張耗費距離,形成最小累積阻力面。根據最小累積阻力值的門檻值,可以識別重要生態源地緩沖區及生態源地間的連接通道等空間位置與邊界,判別生態安全關鍵性區域。擬定國家公園邊界需要一個面積規模適宜、生態過程完整的大尺度閉合空間,洞庭湖區內作為重要生態源地的多個自然保護區相互獨立,需考慮各重要生態源地之間的連通性。研究以現有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技術標準為依據,借鑒已有國家公園劃界方法,結合國家公園生態系統完整性、規模適宜性要求,擬提取最小累積阻力值發生急劇變化的門檻值所形成的區域,作為洞庭湖國家公園初始邊界[16]。
(4)結合管理可行性優化邊界。國家公園劃界除考慮國家代表性、生態重要性特征外,基于資源保護及管理的角度,還應將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保護管理基礎、全民共享等管理可行性要素納入統籌考慮。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是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國土安全的剛性管控邊界[17];現有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等自然保護地具備良好的保護管理基礎;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占主體有利于實現統一保護[18],對新設立國家公園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研究將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現有自然保護地范圍、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保護管理基礎作為管理可行性的主要考慮因素(表2),對初始邊界方案進行優化,形成國家公園邊界。
2 結果分析
2.1 重要生態源地的空間分布特征
研究選取白鶴、中華秋沙鴨、大鴇等傘護種和旗艦種的主要棲息地作為重要生態源地,包括東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西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南洞庭湖省級自然保護區、湘陰橫嶺湖省級自然保護區(圖3)。從空間分布上看,重要生態源地以現有洞庭湖湖面及周邊內陸灘涂、森林沼澤為核心,主要位于岳陽縣、湘陰縣、漢壽縣、沅江市境內。東洞庭湖自然保護區位于岳陽縣西北部、緊鄰岳陽縣中心城區,南洞庭湖省級自然保護區南部緊鄰沅江市中心城區,受人類活動影響干擾程度較大。東洞庭湖、南洞庭湖、湘陰橫嶺湖自然保護區規模相對集中,連通性較好。西洞庭湖自然保護區相對獨立,連通性較差,應重點關注與其他重要生態源地及生態脆弱地區的生態聯系[19]。
2.2 綜合阻力面的空間分布特征
綜合阻力面結果(圖4)表明,區域內空間異質性顯著,阻力低值區位于以東、南、西洞庭湖為核心的河湖沖積平原,高值區分布于人類活動密集的中心城區及坡度較大的丘陵崗地。值得注意的是,岳陽市中心城區、沅江市中心城區緊鄰重要生態源地,阻力值較高,因此后續針對洞庭湖區生物多樣性保護應重點關注其對國家公園邊界劃定的影響,考慮城市擴張需要,預留一定的發展空間。
2.3 初始邊界的空間分布特征
分析結果(圖5)顯示,初始邊界包括岳陽市西部、益陽市北部、常德市東部的部分區域,具有較高的完整性及連通性,總面積約3 309 km2,占研究區面積的7.14%。以東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橫嶺湖4個自然保護區為核心的區域間形成了連續的低阻力通道,源間聯接度較好。該區域主要土地利用類型為內陸灘涂、湖泊水面、沼澤草地等,坡度在5°以內,距城鎮、道路較遠,是國家公園中傘護種和旗艦種的重要棲息地。
2.4 初始邊界優化結果分析
東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西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南洞庭湖省級自然保護區、湘陰橫嶺湖省級自然保護區作為傘護種和旗艦種的主要棲息地,具有國家代表性,且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較好,有一定的保護和管理基礎,應優先劃入。初始邊界東部邊緣有岳陽市中心城區、南部邊緣有沅江市中心城區,考慮到城鎮發展的需要,預留一定的空間作為城鎮擴張緩沖區。初始邊界南北部邊緣有大量集中連片的永久基本農田,應予以避讓。考慮到保護的完整性、連續性,將與初始邊界范圍接壤的部分生態保護紅線內用地優先納入國家公園范圍。同時,初始邊界周邊生態環境脆弱、需優先保護的國有土地也作為優先劃入的一部分。
優化后的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面積約2 833 km2(圖6),占研究區總面積的6.11%。優化后的洞庭湖國家公園范圍涉及東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西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南洞庭湖省級自然保護區、湘陰橫嶺湖省級自然保護區、大通湖國家濕地公園、漢壽息風湖國家濕地公園、汨羅江國家濕地公園、南洲國家濕地公園、瓊湖國家濕地公園、龍虎山省級森林公園10個自然保護地,包括了周邊生態功能重要、生態系統脆弱、自然生態保護空缺的區域,各自然保護地間的聯接度較好。擬建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與現有自然保護地的邊界及生態保護紅線擬合度較高,可有效促進現有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
3 討論
研究利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判別初始邊界,結合管理可行性要素進行優化,劃定洞庭湖國家公園邊界。研究選取的阻力因子主要側重生態系統保護完整性方面,還不夠全面、系統,且數據質量和處理方式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分析結果。在結合管理可行性要素進行邊界優化方面,因選取的生態保護紅線、模擬城鎮開發邊界等數據為未批復的階段性成果,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最終邊界的判定。研究主要側重于從區域尺度及宏觀視角進行邊界判別及劃定研究,最終的劃界應結合現場踏勘進行確定。
當前國家公園體制剛剛建立,對于國家公園邊界的劃定仍處于探索階段。國家公園的設立往往以現有一個或多個自然保護地為基礎進行整合優化,而同一個地區內的多種自然保護地類型,通常存在權屬界線交叉重疊,管理問題突出的情況。通過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為首要原則,進行生態過程模擬,建立各自然保護地及生態脆弱地區間的生態聯系,在此基礎上結合管理可行性要素進行優化,從而劃定國家公園邊界的探索,對國土空間規劃背景下需整合優化自然保護地的擬建國家公園劃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R/OL].(2019-06-26)[2022-03-05].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497.htm.
[2] 唐小平,欒曉峰.擬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J].林業資源管理,2017,(06):1-8.
[3] 王夢君,唐芳林,孫鴻雁.國家公園范圍劃定探討[J].林業建設,2016(01):21-25.
[4] 閔慶文. 國家公園劃界須先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N]. 中國自然資源報,2021-11-09(03).DOI:10.28291/n.cnki.ngtzy.2021.003655.
[5] 劉增力,孫喬昀,曹赫,等.基于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的國家公園邊界探討——以擬建青海湖國家公園為例[J].風景園林,2020,27(03):29-34.DOI:10.14085/j.fjyl.2020.03.0029.06.
[6] 孫喬昀,鮑夢涵,黃晗雯,等.擬建松嫩平原國家公園邊界劃定研究[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22,44(01):103-112.
[7]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R/OL].(2019-06-26)[2022-03-05].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497.htm.
[8] 俞孔堅.生物保護的景觀生態安全格局[J].生態學報,1999(01):10-17.
[9] 吳可,李寒冰,韓博.山東省生態安全格局識別及優化策略研究[J].林業資源管理,2020(03):89-94.
[10] 湖南省政府答復建議:國家林草局支持建設洞庭湖、張家界國家公園 [R/OL].(2021-07-14)[2022-03-05].http://lyj.hunan.gov.cn/lyj/xxgk_71167/gzdt/mtkl/2021
07/t20210714_19917490.htm.
[11] 趙祥祥. 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3.
[12] 初小靜,韓廣軒.氣溫和降雨量對中國濕地生態系統CO2交換的影響[J].應用生態學報,2015,26(10):2978-2990.DOI:10.13287/j.1001-9332.20150921.017.
[13] 王雪然,萬榮榮,潘佩佩.太湖流域生態安全格局構建與調控——基于空間形態學-最小累積阻力模型[J].生態學報,2022,42(05):1968-1980.
[14] 安冠霖,郭晉平.文峪河流域景觀安全格局構建與健康度評價[J].林業調查規劃,2021,46(03):114-125.
[15]韓宗偉,焦勝,胡亮,等.廊道與源地協調的國土空間生態安全格局構建[J].自然資源學報,2019,34(10):2244-2256.
[16] 劉希朝,李效順,韓曉彤,等.基于最小阻力模型的資源型城市景觀安全格局診斷研究——以徐州市為例[J].生態經濟,2020,36(06):221-229.
[17]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國土空間規劃中統籌劃定落實三條控制線的指導意見? [R/OL].(2019-11-01)[2022-03-05].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1/content_5447654.htm.
[18] GB/T 39737—2020,國家公園設立規范[S].北京:國家林業和草原局,2020.
[19] 李忠武,王磊,冉鳳維,等.基于APCS-MLR模型的西洞庭湖沉積物重金屬來源解析[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19(02):1-14.
收稿日期:2023-01-10;? ? ? ? ? ? ? ? ?改回日期:2023-02-22。
*基金項目:湖南省重點研發計劃項目 (編號:2019SK2101)。
*第一作者簡介:曾麗婷(1988—),女,碩士,工程師;從事國土空間規劃工作;E-mail: 5248803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