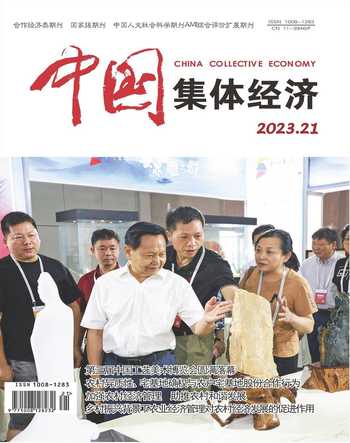收入分配視域下群體性勞資事件研究
孫曉曦
摘要:在群體勞資事件不斷增加的情形下對其進行制度經(jīng)濟分析是必要的。目前,我國群體性勞資沖突主要體現(xiàn)在權(quán)利爭議。其中,因勞動報酬引發(fā)的爭議是誘發(fā)勞資沖突的首要原因。文章基于2000年以來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借助協(xié)整理論并進行廣義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檢驗,得出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數(shù)量與勞動者報酬占比成反比,而與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占比成正比的結(jié)論。根據(jù)產(chǎn)權(quán)理論研究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殘缺、勞動報酬占比收入下降與勞工“體制外抗爭”的內(nèi)生關(guān)系,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勞資三權(quán)”;建立工資增長長效機制,完善再分配調(diào)節(jié)機制的建議。
關(guān)鍵詞:群體性勞資事件;勞資困局;收入分配;報酬占比;實證分析
一、研究背景
作為市場經(jīng)濟中重要的社會關(guān)系,恩格斯認為勞資關(guān)系是“全部現(xiàn)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zhuǎn)的軸心”。目前,我國“國家統(tǒng)合模式”勞動關(guān)系基本完成市場化轉(zhuǎn)型,但勞資困局日益嚴峻。根據(jù)《中國法治藍皮書》,勞資事件占我國群體性事件的36.5%,對我國經(jīng)濟、社會建設(shè)構(gòu)成重大威脅,亟須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二、文獻綜述
群體性勞資事件是群體性事件研究在勞資領(lǐng)域的深化表現(xiàn)。關(guān)于群體事件,國內(nèi)外學者已經(jīng)形成社會沖突論、集群行為論、相對剝奪論、模仿論、感染論、匿名論、轉(zhuǎn)軌論、表達機制缺陷說等理論流派。
(一)國外研究
國外學者對群體性勞資事件的研究主要有兩條主線:其一,研究群體性勞資沖突最激烈的表現(xiàn)形式(罷工);其二,研究群體性勞資沖突解決機制問題(集體談判、三方協(xié)商制度)。前者如Hicks產(chǎn)業(yè)糾紛模型(1963)、A-J模型(Ashford and Johnson,1969)、相互依存選擇行為理論(Thomas Schelling,2005);后者如組織行為學理論(Max Weber,1920)、產(chǎn)業(yè)民主理論(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947)。目前,國外學者引入博弈論和系統(tǒng)論(Hayes,1984;Turk,1984;Tracy,1987),利用實驗經(jīng)濟學、信息經(jīng)濟學(Mauro,1982)和博弈論研究方法,側(cè)重對勞動關(guān)系沖突進行比較研究(Zupnov and Josip,1993)、實證研究(Corn and Dand,2002)和實例研究(Fehr,2012)。
(二)國內(nèi)研究
國內(nèi)學者對群體性勞資事件的研究沿著內(nèi)涵、成因、理論、治理的思路不斷深化。1. 群體性勞資事件的性質(zhì)內(nèi)涵:從強調(diào)事件的對抗性、價值屬性轉(zhuǎn)向可控性、工具屬性,視事件為勞資間利益博弈的正常表現(xiàn),具有“合理不合法”性(吳清軍、許曉軍,2010)。2. 群體性勞資事件的成因:從單純的權(quán)利分析轉(zhuǎn)向制度分析。單光鼐(2010)將其歸納為勞工權(quán)益崛起,以及勞動權(quán)益受損(劉長龍,2012),而吳清軍、許曉軍(2010)認為集群越軌的行為源于制度化利益表達渠道缺陷,以及分配失衡(李曉寧、馬啟,2012)。3. 群體性勞資事件演化過程:從現(xiàn)狀描述轉(zhuǎn)向機理分析。伍美云(2014)拓展希克斯模型,得出基于政府壓力雇主妥協(xié)線和工人抵制線的變化規(guī)律;董延芳、劉傳江等(2017)運用公平理論,提出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人們的集體行動之間憤怒路徑和效能路徑。4. 群體性勞資事件治理:從對策建議轉(zhuǎn)向制度設(shè)計。常凱(2004)認為解決事件的關(guān)鍵應(yīng)以勞權(quán)為本位;崔向陽(2007)提出勞資合作的平等性定理、長期性定理、嵌入性定理;平衡勞資博弈能力的提出(王明亮,2010)以及締結(jié)長期合約(朱福林、何勤,2012)可避免勞資博弈的“囚徒困境”。桂林、尹振東等(2016)認為,補償式維穩(wěn)政策可能使公共治理陷入維穩(wěn)悖論,社會長治久安之本在于增強法治建設(shè),為群眾提供利益表達渠道。5. 研究方法:從文獻研究轉(zhuǎn)向數(shù)理分析。劉德海(2011)利用博弈論分析我國勞資沖突的動態(tài)演化階段過程。李艷(2012)通過構(gòu)建勞資協(xié)議博弈模型,探究事件中勞資博弈的結(jié)果。
政治、經(jīng)濟、社會、技術(shù)和國際五方面的因素,或多或少都影響著群體性勞資事件發(fā)生的宏觀生態(tài)環(huán)境。然而,馬克思也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guān)”。所以,筆者認為收入分配是影響群體性勞資事件的根本原因。近年,我國群體性勞資事件持續(xù)逐年上升。第一,由于人力市場機制的局限性,在已發(fā)生的集體勞動爭議和群體性勞資事件中,勞動報酬、社會保險成為爭論的焦點。勞方的訴求主要表現(xiàn)為提高工資薪酬、追討工資和社會保障。第二,大部分群體性勞資事件發(fā)生在農(nóng)民工聚集企業(yè),即在收入機制相對不穩(wěn)定的群體中,說明勞動收入保障機制存在缺陷。第三,勞動收入與資產(chǎn)收入失衡。勞動收入在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中的占比較低,致使多數(shù)勞動者淪為弱勢群體。在群體性勞資事件中,即使該群體并非直接利害關(guān)系人,但共情心理使他們?nèi)菀酌模蔀槭录膮⑴c者。目前,對勞動者報酬份額下降的解釋主要有要素配置說、技術(shù)進步說、FDI說、制度影響說等。然而,筆者試圖從固本清源的角度對勞動收入減少在群體性勞資事件中所起作用以及如何避免此類事件進行研究。
三、研究設(shè)計
(一)勞動力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
分析勞動力報酬的相對變動趨勢主要通過居民、企業(yè)、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變化得以觀測。我國勞動報酬占比的趨勢變動通常用收入法核算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來計算。按收入法核算,GDP可細分為四種收入要素:營業(yè)盈余、固定資產(chǎn)折舊、勞動者報酬、生產(chǎn)稅凈額。其中,勞動者報酬體現(xiàn)勞動收入變化即勞動者所得,固定資產(chǎn)折舊和營業(yè)盈余體現(xiàn)資本收入變化即企業(yè)所得,生產(chǎn)稅凈額體現(xiàn)政府收入變化即政府所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持續(xù)提高,勞動者報酬也逐年攀升,但占比卻呈現(xiàn)出波動下降趨勢,自1988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從70.2%,降至51.8%。
(二)實證分析
目前,我國群體性勞資沖突主要表現(xiàn)為權(quán)利爭議。根據(jù)2000年以來勞動爭議案件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引發(fā)勞動爭議的原因可歸結(jié)為: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待遇、福利以及勞動合同。其中,因勞動報酬引發(fā)的爭議位于勞資沖突誘因的首位。因此,從收入分配視角探究群體性勞資事件的成因更為有效。
1. 基本假設(shè)
(1)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與勞動者報酬成反比。
(2)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與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成正比。
(3)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對勞動者報酬有擠占效應(yīng)。
2. 數(shù)據(jù)來源
為分析勞動者報酬、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與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關(guān)系,選取勞動者報酬(LDBC)、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ZFSY)作為收入分配的評價指標,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shù)(ZYAJ)作為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評價指標。其中,“GDP總額”“勞動者報酬”“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根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各省市“收入法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求和整理并計算。由于2000年之前“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shù)”以及資方收益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空缺,本文主要分析自2000年“分配結(jié)構(gòu)”與“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shù)”的相關(guān)性。
3. 實證研究
(1)變量的說明及平穩(wěn)性檢驗。為消除價格因素影響,采用以2000年為基期的人均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指數(shù)進行了平減,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并取對數(shù)變換消除異方差影響,記LLDBC、LZFSY、LZYAJ為相應(yīng)變換后的自然對數(shù)序列。
運用協(xié)整理論分析之前,通過ADF檢驗,確定時間序列的平穩(wěn)性,具體分析結(jié)果如表1所示。3個差分后的序列均為一階單整I(1),不存在單位根問題。考察殘差序列的自相關(guān)性,經(jīng)查DW檢驗表,可得du=1.54 (2)協(xié)整分析。如果多個非平穩(wěn)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平穩(wěn),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guān)系,由于LLDBC、LNZFSY、LZYAJ都是I(1)序列,符合變量單整階相同的協(xié)整條件。JJ協(xié)整檢驗如表2、表3所示,結(jié)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3個變量之間存在多于兩個協(xié)整關(guān)系,滿足VEC 模型建立的前提條件。 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shù)的誤差修正模型為: ECMt-1=ZYAJt-1+1.9428LDBCt-1-1.0806ZFSYt-1-19.0021 (4.592)? ? ?(-3.480) Δ(ZYAJt)=0.0411+0.4129Δ(ZYAJt-1)+0.29260.4129Δ(LDBCt-1)-0.82410.4129Δ(ZFSY-1)-0.8774ECMt-1+εt (0.366)? (1.374)? ? (0.237)(-0.897)? ? (-2.528) 上式中,括號內(nèi)的是t統(tǒng)計量。在誤差修正項(ECM)中各變量的t統(tǒng)計量都顯著,并且誤差修正項的t 統(tǒng)計量也顯著,且系數(shù)為-0.877,說明從長期來看,勞動者報酬對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長期彈性為-1.943,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對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長期彈性為1.081。而短期來看,由于短期變動的t統(tǒng)計量不顯著,說明勞動者報酬和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對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短期內(nèi)不存在因果關(guān)系。 (3)脈沖響應(yīng)分析。由于各變量之間是協(xié)整的,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具有均衡關(guān)系,但受到隨機干擾的影響,上述變量可能偏離均衡值。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是檢驗系統(tǒng)內(nèi)各個變量對其他變量的沖擊反應(yīng)。該函數(shù)表現(xiàn)了在初期給某變量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時,系統(tǒng)內(nèi)其他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對這一沖擊的反應(yīng)度。由于該函數(shù)正交化變換的結(jié)果依賴于各變量的順序,因此,本文選用廣義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Koop,1996)來考察變量的沖擊影響以及影響力的持續(xù)時間。依據(jù)Monte Carlo 模擬方法,可得沖擊標準差,并將沖擊響應(yīng)期設(shè)置為15,得到如下脈沖響應(yīng)曲線圖。 從圖1可以看出,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對勞動者報酬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yīng)為負,在第3期迅速降到-2.28,隨后雖有波動,但從第8期開始穩(wěn)定在-1.9左右,說明勞動者報酬的提升會減少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數(shù)量。究其原因在于2010以后,國家提出包容性增長理念,主動調(diào)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效應(yīng)開始顯現(xiàn)。 從圖2可以看出,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對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yīng)為正,在第2期下降至0.135,第5期迅速上升到0.172,隨后雖有波動,但從第8期開始穩(wěn)定在0.16左右,說明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的提升會增加勞資爭議事件的數(shù)量。 從圖3可以看出,勞動者報酬對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yīng)為負,在第1期下降至最低值-0.025,然后在第2至6期呈波動趨勢,并從第6期開始穩(wěn)定在-0.02左右,說明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的提升對勞動者報酬產(chǎn)生了擠占效應(yīng)。原因是:在國家稅收總體穩(wěn)定前提下,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的提升意味著勞動者報酬份額的下降。 (三)基本結(jié)論 綜上,勞動者報酬占比當期下降并不必然引發(fā)群體性勞資事件,但從長期看,勞動者報酬和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對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具有因果關(guān)系。弱勢群體的擴大是一個漸進過程,勞動者對當年初次分配占比變化并不敏感,但勞動報酬占比持續(xù)下降將使勞動者產(chǎn)生弱勢群體心理,固化“被剝奪感”,進而采取集體行動,一個偶發(fā)事件即可能誘致事件發(fā)生。廣義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的結(jié)果也表明: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的數(shù)量與勞動者報酬成反比,而與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成正比,且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對勞動者報酬產(chǎn)生了擠占效應(yīng)。顯然,資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對勞動者報酬的長期擠占,勞動者報酬占比持續(xù)下降成為群體性勞資事件形成的深層次原因。 四、結(jié)果討論 面對勞動報酬占比持續(xù)下降,或偏低現(xiàn)象,國內(nèi)外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闡釋。技術(shù)創(chuàng)新說認為,技術(shù)創(chuàng)新提高了對資本的替代,企業(yè)能夠獲取大部分經(jīng)濟剩余。因此,穩(wěn)定勞動者報酬份額必須更多關(guān)注資本節(jié)約型技術(shù)進步的作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動說認為,勞動者報酬份額下降部分是由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動導致的,特別是二元經(jīng)濟體制下,轉(zhuǎn)型期勞動力收入份額下降是一種規(guī)律性現(xiàn)象。制度影響說認為勞動力市場制度對勞動者報酬份額的影響,因為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嚴重制約著勞方議價能力,從而影響到其收入份額。然而,上述學說均采用特定行業(yè)或某一歷史時期的數(shù)據(jù),盡管具有一定的理性,研究結(jié)論并不全面。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產(chǎn)權(quán)是分析經(jīng)濟社會的邏輯起點,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是勞動者公平交易的前提。因此,本文試圖從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及其延伸的最低工資制度安排解釋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問題。 (一)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殘缺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說明只要法定權(quán)利可以自由交換,且交易成本等于零,那么法定權(quán)利的最初配置狀態(tài)對于資源配置效率而言無關(guān)緊要。根據(jù)產(chǎn)權(quán)理論,降低交易費用,提高市場交易效率的前提在于明晰產(chǎn)權(quán)。因此,勞動者對其勞動力擁有完全產(chǎn)權(quán),是降低勞資交易費用以及勞動者公平交易的前提。勞動力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交易中的產(chǎn)權(quán)權(quán)利包括:勞動者自主決定其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的交易;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交易價格的公平合理;勞動力供給過程中的人身尊重;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受損時的合法保護途徑。 轉(zhuǎn)型期內(nèi),我國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殘缺是導致不公平交易的本源。 1. 勞動力自主交易權(quán)不完整。所謂勞動力的自主交易權(quán)是指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交易完全由勞動者自主決定,根據(jù)其經(jīng)濟狀況、勞動偏好等,勞動者作為“經(jīng)濟人”有權(quán)依據(jù)其所掌握的信息理性決定其是否向資方提供勞動力供給。人格獨立和自愿是自主交易的核心。然而,中國經(jīng)濟改革自上而下推動,相當多的勞動力進入市場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特別是國有企業(yè)改制中,職業(yè)經(jīng)理人的“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被突出,普通職工的“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被弱化(邢成雙,2009),他們喪失國有企業(yè)主人身份,或成為改制后私營企業(yè)、國有控股企業(yè)的工人,被迫受雇于資本;或被迫“下崗”。無論是從客觀事實、還是主觀感受,他們都在演繹著由“剝奪被剝奪者”到“被剝奪者”的轉(zhuǎn)變,其獨立人格受損,被迫進行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交易。 2. 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交易價格不合理。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交易價格主要由勞動力供求決定。為防范資方利用強勢地位對勞方公平交易價格權(quán)利的侵害,國家設(shè)立最低工資制度,鼓勵資方提供的薪酬能滿足勞動者“體面勞動(Decent work)”的要求。然而,轉(zhuǎn)型期內(nèi),由于最低工資制度在設(shè)計上的缺陷,“地板工資制”泛濫,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卻不能得到合理的工資報酬。國內(nèi)私營企業(yè)資方通過違規(guī)加班,延長工時等手段侵占勞動報酬;國有企業(yè)濫用勞務(wù)派遣,通過大量臨時用工等手段“合法”實現(xiàn)同工不同酬;跨國公司則依據(jù)國籍歸屬關(guān)系,采取差異化薪酬政策。其結(jié)果是勞動力交易價格被扭曲。 3. 勞動者的人身權(quán)殘缺。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的特殊性在于其與勞動者人身不可分離。勞動者在勞動過程的人身安全、健康、名譽等應(yīng)得到保護,然而,由于勞動法制未被有效執(zhí)行,企業(yè)出于成本考慮,往往并未為勞動者提供有效的勞動保護和安全保障。實踐中,已經(jīng)發(fā)生的“開胸驗肺”事件加劇了社會對勞動者人身權(quán)、健康權(quán)的擔憂。而在一些奉行強勢管理文化、半軍事化管理的企業(yè),體罰、辱罵管理行為仍較為普遍,這無疑將加重勞動者的屈辱感。 4. 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保護制度殘缺。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受損時,勞動者應(yīng)能通過組建工會、集體協(xié)商、集體行動(罷工)、集體訴訟等手段維護其產(chǎn)權(quán)權(quán)益。我國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保護制度并不完整,具體體現(xiàn)為:勞動者自由結(jié)社權(quán)(組建工會)受到限制,勞動者無法通過集體力量平衡勞資博弈能力;勞動者并不享有集體行動權(quán)(罷工),其體制內(nèi)的“威脅”不可置信;勞動仲裁訴訟程序繁瑣,成本高昂,勞動者無法及時獲得國家公權(quán)救濟。 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殘缺,使轉(zhuǎn)型期的中國勞動者只能在“資本雇傭勞動”中處于弱勢地位。反映在收入分配中,其報酬份額相對比例下降將成為必然。面對資本的天然強勢,以及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保護制度的不周延,進行“合理不合法”的“體制外抗爭”成為勞動者的“理性”抉擇。 (二)“地板工資制”替代最低工資制度 勞動力產(chǎn)權(quán)殘缺直接導致“地板工資”取代“最低工資”,即資方基于產(chǎn)權(quán)強勢,視最低工資為基本工資。但在法理和學理上,基本工資并不等同于最低工資。基本工資作為最穩(wěn)定的工資形式,是指職工在法定工作時間內(nèi)完成工作任務(wù)或勞動定額時企業(yè)必須支付的基本勞動報酬。基本工資應(yīng)當能夠保證職工本人及其平均贍養(yǎng)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依據(jù)是員工所在職位、能力、價值核定;而最低工資具有強制性,是用人單位依法應(yīng)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國家確立最低工資標準的初衷在于保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的合法權(quán)益,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顯然,基本工資水平應(yīng)高于最低工資標準。 轉(zhuǎn)型期內(nèi),國內(nèi)企業(yè)將最低工資曲解為基本工資是資方實現(xiàn)對勞動者報酬侵占的重要手段。我們可以用下式簡單測度資方如何利用最低工資制度擠占勞動者報酬。 y1=wa+wb+wc+wd(1) 這里的y1表示職工收入總額,wa表示基本工資,wb表示加班費,wc表示獎金,wd表示其他收入 y2=wm+wb+wc+wd(2) 這里的y2表示職工收入總額,wm表示最低工資,wb表示加班費,wc表示獎金,wd表示其他收入 由于wm≤wa (3) 因此,y2≤y1(4) 假定:y1-y2=y(tǒng)3 (5) 則Y3就是企業(yè)利用最低工資制度對勞動者報酬的直接擠占。發(fā)達國家,最低工資與國內(nèi)平均工資比率多分布在40%~60%之間;發(fā)展中國家多分布在70%~90%之間。由于國內(nèi)企業(yè)普遍將最低工資視為基本工資,因此,利潤侵占工資在轉(zhuǎn)型期內(nèi)已經(jīng)成為社會常態(tài),并引發(fā)國外勞工組織關(guān)注。 五、結(jié)語 勞動報酬并非群體性勞資事件頻發(fā)的唯一直接誘因,事件的發(fā)生還受社會輿論、法治環(huán)境、國際背景等因素影響綜合作用的必然結(jié)果,但收入分配失衡是問題產(chǎn)生的最終根源。故破解勞資困局,應(yīng)平衡勞資產(chǎn)權(quán),持續(xù)提高勞方產(chǎn)權(quán)收益。 (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勞資三權(quán)”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前提在于平衡勞資產(chǎn)權(quán),而平衡勞資產(chǎn)權(quán)的重中之重在于完善“勞資三權(quán)”,即勞工結(jié)社權(quán)、集體談判權(quán)和集體行動權(quán)。作為勞資契約自治的前提,“勞資三權(quán)”的強化有助于弱者實現(xiàn)博弈平衡。為應(yīng)對勞權(quán)貧困、機制殘缺,國家要強化“勞資三權(quán)”的工具性、救濟性、輔助性,在主體塑造、資格確認、信息披露與保密、定期或常規(guī)談判、程序安排等方面進行審慎制度設(shè)計,矯治勞資失衡。建立勞資對等博弈、合理定價與公平交易的關(guān)系、機制、平臺與格局(陳步雷,2012)。 (二)建立工資增長長效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制度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改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態(tài)勢,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須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改革工資決定機制、工資增長機制,完善工資集體協(xié)商制度、實現(xiàn)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同步。現(xiàn)行最低工資制度覆蓋面窄,最低工資標準過低,存在被資方濫用危險。國家應(yīng)擴大最低工資制度覆蓋面,將臨時用工、短期聘用等納入最低工資制度適用范圍;明確最低工資應(yīng)達到城鎮(zhèn)居民收入水平的60%;引入生活工資制,保障勞動者能“體面勞動”。 (三)確立橄欖型分配格局,完善再分配調(diào)節(jié)機制 “橄欖型”分配格局,即中等收入者占多數(shù)的收入分配結(jié)構(gòu)有助于社會穩(wěn)定。通過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低、擴中、抑高,縮小居民、行業(yè)、城鄉(xiāng)、區(qū)域收入分配差距。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國家應(yīng)完善以個人所得稅、房地產(chǎn)稅、遺產(chǎn)稅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diào)節(jié)機制。在保護合法收入同時,規(guī)范隱性收入,清理不合理收費,取締非法收入,改革因行政壟斷、資源壟斷、牌照壟斷而產(chǎn)生的畸形收入。 參考文獻: [1]何勤.中外群體性勞資沖突研究綜述[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5):60-63. [2]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J].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張曉峒.應(yīng)用數(shù)量經(jīng)濟學[M].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9. [4]朱善利.微觀經(jīng)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三版),2014. [5]邢成雙.國有企業(yè)并購重組中的勞動者權(quán)益保護[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09. [6]趙志泉.薪酬管理[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 [7]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低工資規(guī)定》第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第21號令). [8]吳家?guī)?勞資關(guān)系與產(chǎn)業(yè)發(fā)展[M].華泰書局,199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群體性勞資事件網(wǎng)絡(luò)輿情阻燃機制與治理研究”(課題編號:18BGL23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科技型企業(yè)創(chuàng)業(yè)失敗修復機制與再創(chuàng)業(yè)意向的扶持對策研究”(課題編號:18CGL00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失敗污名如何不污?企業(yè)創(chuàng)業(yè)失敗后的印象管理策略與再創(chuàng)業(yè)行為關(guān)系研究”(課題編號:72002206)。 (作者單位:中共河南省委黨校河南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