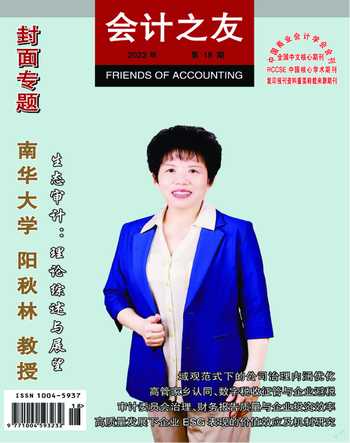域觀范式下的公司治理內涵優化
李曦輝 陳溫都蘇
【摘 要】 公司治理作為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微觀保證。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下的公司治理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關注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下的委托—代理問題,強調從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出發,通過激勵與監督約束委托人行為,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然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始終不能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甚至對一系列的公司丑聞無能為力,時不時把公司治理問題推上風口浪尖。文章對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下公司治理存在的困境進行了理論闡釋,基于經濟學域觀范式,從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三個維度對公司治理內涵提出了優化建議。
【關鍵詞】 公司治理; 西方經濟學; 域觀范式; 現代企業制度
【中圖分類號】 F234.3;C93-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3)18-0122-08
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的公司治理研究,因其在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本市場實踐前沿之間發揮著天然紐帶作用,至今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學術活力。西方主流經濟學用單一的經濟理性維度刻畫現實世界,以“經濟人”假設為邏輯基礎強調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此經濟學范式下的公司治理關注的是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下的委托—代理問題,即通過簽訂契約、激勵與監督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進而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或公司利潤最大化。然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始終不能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甚至對一系列的公司丑聞無能為力,時不時把公司治理問題推上風口浪尖。現有公司治理實證研究多從高度抽象化、模型化的微觀經濟學范式出發,檢驗負債融資[ 1 ]、資本市場開放[ 2 ]等融資因素,機構投資者參與[ 3 ]、投資者保護[ 4 ]、股權結構設計[ 5 ]等股權結構特征,以及數字經濟[ 6 ]、管理層能力、企業價值等因素的邏輯關系。理論研究則聚焦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踐的歷史演化脈絡[ 7-8 ]、國別比較[ 9-10 ]、法律設計[ 11 ]以及數字經濟時代下的體制機制探索[ 12 ]等,也有學者關注政府行為[ 13 ]等制度視角及中國文化[ 14 ]等文化角度。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公司治理理論,為企業界的經營管理活動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實戰建議,但仍然是在微觀經濟學范式下的現實刻畫,利潤最大化目標下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的研究無法還原具有域觀特質的公司治理實踐。本文試圖用域觀經濟學范式,從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三個維度優化公司治理內涵,以期在復雜多樣的經濟形勢和經濟環境下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下公司治理的困境
(一)股票期權從理論到實踐的失靈
股票期權制度的誕生,最初是為了解決高額的所得稅累進稅率侵蝕企業高管薪酬的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曾高達92%的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導致眾多企業高管的薪酬大部分被所得稅扣除。為了避免這種高額的累進所得稅對高級管理人員的不利,菲澤爾(PFIZER)制藥公司決定以股票期權的方式向全體員工支付薪酬,即員工可以通過在未來的任意一個時期行權兌現個人收益,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15 ]。作為一種新型的薪酬分配模式,盡管股票期權制度的初始目的是合理避稅,卻因具有兼顧長期激勵和監督約束功能被眾多公司采納。按照委托—代理理論,公司股東作為委托人,在與作為代理人的經理人簽訂契約之后(即解決了參與約束與逆向選擇問題),為降低代理成本,仍需要利用激勵和監督手段解決經理人員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忽視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問題,也就是進一步解決激勵相容約束與道德風險問題[ 16 ]。股票期權制度恰恰在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建立了資本紐帶,把代理人的個人利益與公司利潤(股東財富)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二者的效用函數具備了目標一致性,無形中發揮了激勵和監督經理人員行為的作用,進而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委托—代理問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經濟學范式和“股東至上主義”的公司治理模式下,股票期權制度迅速被西方眾多公司奉若神明,當作有效解決公司治理矛盾的一劑良藥,得到了美國社會各界的美譽,《商業周刊》評價道:“股票期權制度曾像魔法棒一般地刺激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
然而,被捧上神壇、作為繁榮美國20世紀90年代經濟的“魔法棒”的股票期權制度存在致命的內在缺陷——催生新的道德風險。股票期權將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公司股價緊密相連,即經理人員為了未來行權時能夠取得高額收益,會嚴格約束個人行為,采取良性可持續的經營行為。從理論上講,似乎能使經理人員的個人收益與企業經營業績緊密相連,然而時常事與愿違。一方面,股票期權的價值來自股票市場價格與期權行權價格的差額,即良好的公司股票市場價格使經理人員行權時的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經理人員作為公司的“內部人”掌握著眾多設備、財務、人力等資源,有充分的權力操縱財務數字,利用不正當手段推動股票價格的上漲,人為增加股票期權對他的價值,甚至當股票市場價格有低于行權價格趨向時,可能選擇利用“內部人”的地位修改行權價格或行權期,進而達到避免自己的股票期權收益受損的目的。也就是說,當股票期權制度將管理層利益與股票價格聯系在一起時,利用在公司的地位與權力操控影響股票價格的因素,可能會成為管理人員實現個人收入最大化的最優選擇和隱藏動機。簡言之,本為克服道德風險和短期行為的股票期權可能會因經理人員的地位而誘發新的道德風險,特別是在股價非理性時,新的道德風險會更頻繁[ 17 ]。股票期權制度存在的內在缺陷,使其成為21世紀初安然、世通等眾多公司財務丑聞(見表1)爆發的重要誘因,正如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所言:“一些公司出現巨大的財務‘黑洞,股票期權是漏洞之一。”
(二)代理人侵蝕委托人事件層出不窮
西方經濟學奉行“經濟人”假設,即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主體,然而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現代公司中,委托人與代理人自委托代理關系發生時便存在因目標函數不一致而產生的利益沖突,即委托人的目標是公司經營良好、股價不斷上漲,進而通過公司價值的最大化實現個人財富的積累,而代理人的目標則是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包括財富、社會地位和更多的閑暇,因此委托—代理問題被看作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用“富家管事”的比喻形象地闡釋了股份公司中委托人與代理人的矛盾,他認為在處理公司資金方面,不同于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員為自己打算,股份公司的董事是為他人效力,因而很難讓股份公司的董事像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員那樣用意周到地監督公司財產的用途。正因如此,股份公司在經營業務方面難免存在疏忽和浪費[ 18 ]。也就是說,只有在代理人全心全意為委托人工作與服務時,委托代理關系才能產生經濟效益。但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天然存在的目標函數不一致、經濟責任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和契約不完全等矛盾[ 19 ],注定代理人不可能完全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為準則。正如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 20 ]指出的:“如果委托代理人雙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會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動。”
由此可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代理人侵蝕委托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代理人的收入取決于個人業績水平和公司的股票價格,出于對個人財富的追求和保證經營業績以避免因業績不佳導致的在經理人市場中的聲譽損毀等,代理人往往表現出短視主義傾向,將公司資本投資于短期收益率高、長期收益率可能為負的投資項目,使公司資產流失,造成對委托人利益的損害。第二,在股權高度分散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為代理人控制公司籌資、投資、人事任免等經營活動的管理權力,打造個人商業帝國、實現內部人控制開啟了方便之門,由此造成委托人權力弱化,形成“強管理者,弱所有者”局面。第三,在職消費成為代理人侵蝕委托人利益的另一種重要手段。代理人在職消費天然存在的難以識別“公私”屬性的特點,為代理人無限度滿足私人貪欲、追求至高的財富地位和享受“皇家”待遇蒙上了一層面紗。科泰國際(TYCO)前總裁丹尼斯·考斯洛斯基向公司借貸2.74億美元購買私人房屋、游艇和家具,花費210萬美元為妻子籌辦皇家級生日晚宴[ 21 ],正是代理人利用在職消費中飽私囊的真實寫照,經理人員利用公司內部權力和地位擴大在職消費成為美國20世紀80年代企業經濟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三)出資人與勞動者關系不存在合理性可能
恩格斯認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從微觀層面上看,出資人與勞動者的關系貫穿了企業生產要素經營和分配的各個環節,也是現代企業公司治理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一方面,出資人與勞動者在契約地位上存在不平等。出資人可以利用自己豐富的資源優勢和勞動者經濟緊迫性的劣勢,巧妙制定對自己有利的契約,用盡可能低的工資換取盡可能多的勞動力或勞動時間。馬克斯·韋伯闡明了出資人和勞動者關系形式平等但實質不平等,且“財產分配上的不平等受到法律保障”的悖論。韋伯認為,雖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有權與任何企業者簽訂任何內容的勞動契約,但這種權利對于尋找勞動機會的勞動者在實質上是不平等的,勞動者并不能在決定勞動條件上具有選擇權或發揮影響力,但企業所有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契約自由的結果變成了讓擁有財富的人充分運用市場規則,在無礙于法律的限制下,利用市場資源取得對他人的權勢[ 22 ]。
另一方面,出資人與勞動者在利益分配上存在沖突和對立。亞當·斯密在討論勞動工資時指出,勞動者的普通工資取決于勞動者與雇主簽訂的契約,但二者在利益關系上是不一致的。勞動者需要依靠勞動工資維持生活,因而勞動者總是期望獲得更多的工資,而雇主則是想要用更少的勞動報酬換取勞動者多得多的勞動,時常聯合起來減低勞動者工資。在勞動者與雇主的爭議中,地主、農業家、制造者或商人依靠其積蓄的資本總能維持得很久,而失業的勞動者因為失去了維持生活的收入來源很少能維持一個月,更沒有能夠維持一年的失業勞動者[ 18 ]。亞當·斯密眼中出資人與勞動者之間的“利害關系”恰是反映了出資人財產所有權與勞動者生存權的對立:勞動者的最基本目標是謀求工資福利等維持基本生活的生產資料的最大化,而作為雇主的出資人則是謀求財富(利潤)的最大。馬克思從本質上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出資人與勞動者的關系是不平等和對立的,是出資人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榨。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控制并占有了工人的勞動和產品,生產出來的新產品的價值超出了為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支付的價值,這些新產品又以商品的形式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進入流通領域,而超出的這部分價值作為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簡言之,在西方經濟學范式下,出資人以“資本”為中心,尋求擴大生產并占有企業剩余索取權,忽視了勞動者擁有的具有高度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出資人和勞動者的關系表現為不平等、對立和沖突,缺乏一個合理的脈絡。
二、經濟學域觀范式簡述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起源于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第一次把經濟研究的邏輯起點聚焦于個人,其范式承諾為:假定每個人都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即從每個人的私利出發,社會財富可以實現有效增加并實現最大化。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則把現代經濟學徹底形式化、抽象化、數理化,即用高度抽象的數理模型讓經濟學變得更“精致”“科學”,其范式承諾就是把“經濟理性”以外的全部影響因素作為“干擾因子”排除在經濟學邏輯建構體系之外,抽象出單一的可以用價格數字代表、用數學公式計算推演的“經濟理性”因素,讓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王冠上的明珠”。從橫向角度看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可以發現,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牛頓力學的影響,即把經濟活動想象為牛頓力學中勻質、絕對的物理空間,“粒子”般的經濟活動主體在沒有“摩擦力”和“阻力”的市場空間中自行運轉,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社會財富的增加。然而,這樣“科學”“精致”的經濟學是嚴重脫離現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認為,“在完美的形式邏輯外觀下,經濟學也有其內在的邏輯缺陷,不僅在邏輯推演中過度依賴‘假定條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脫離現實甚至無視真實的,為了貫徹工具理性而往往丟失本真價值理性。也就是說,經濟學作為以演繹邏輯為主線的推理表達體系,實際上是存在‘邏輯斷點的”[ 23 ]。在域觀經濟學的開創性論文中,金碚對經濟學底層邏輯的假定和推論進行了邏輯檢視,認為:第一個假設是“目的”假設,即假設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第二個假設是“自私”假設,假設人的一切行為目的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是自私的;第三個假設是“經濟人”假設,假定人有能力進行理性計算,人人都是精于計算的利己主義者;第四個假設是“利潤最大化”假設,從自然人經濟人假設直接推論出企業法人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第五個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假設在如同“空盒子”般的市場空間中,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看不見的手)可以保證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可以實現市場的“一般均衡”。對于第一個假設,認為暫且承認它的“公理性”,以避免陷入人是否“理性”的爭論。對于第二個假設,認為除了“經濟人”假設以外,還有“資本主義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以及“復雜人”等一系列假設,并非只有“經濟人”一種假設可以自圓其說。對于第三個假設,認為從自私假設推論出“經濟人”假設,只是在人的個人主義自私性中加入了“經濟理性”,“經濟人”假設只是經濟學追求邏輯自洽性的一個權宜之計,或是“次優選擇”,并不是經濟學邏輯的唯一。對于第四個假設,從個人主義“經濟人”假定直接推演出“利潤最大化”目標,更是一種武斷的推論,并不符合經濟現實。企業是法人,本身并不會感覺到利益得失,它們既不會因盈利而快樂,也不會因損失而痛苦,他為什么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呢?對于第五個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已不是假定,它是假想在“空盒子”般的市場空間條件下,由假想的原子般的自利經濟主體進行最優化理性決策而推導出的結果,并非真實的存在。經濟學抽象體系中存在的邏輯斷點導致經濟理性同現實世界間存在明顯的矛盾不合,彌合經濟學抽象邏輯之斷點,“最重要的就是必須依靠各種‘價值文化因素和手段(價值文化可以體現為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顯性或隱性人際交往關系)”[ 23 ]。
金碚[ 23 ]指出:“我們將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及其體現的社會道德)和制度形態的特質,統稱為各不同商域的‘文明型式(對于較小的商域,可以稱為‘文化類型)。這就奠定了商域經濟學的學理基礎和學術邏輯,即經濟理性和一定的價值文化及制度形態互動交融表現為各商域的文明型式。商域經濟學假定商業活動受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三方面因素的決定和影響,經濟理性的邏輯具有內在一致性和抽象性,而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則具有豐富性、復雜性和多元性。”具體而言,域觀經濟學的范式承諾是:經濟社會是以具有不同特質的“商域”構成的,不同商域中的經濟現象、商業活動以及經營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價值文化特質和制度形態特點。即域觀經濟學抽象出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三個商業活動的決定或影響因素,用經濟理性的邏輯一致性與抽象性,以及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的復雜性、豐富性與多元性,構建邏輯嚴謹、內容豐富的經濟學分析體系,彌合經濟學微觀—宏觀范式的邏輯斷點[ 23 ]。金碚等[ 24 ]認為:“現實經濟世界中的行為主體,不是抽象的同質性‘粒子,即行為目標相同的個人和企業,而是具有域觀特質的行為主體,并且,還有各種社會性的行為體——家庭、社會組織、利益集團等。換句話說,經濟社會是以具有不同特質的‘商域所構成的。不同性質經濟主體(行為體)的行為張揚(極端化),可能導致行為體間關系的性質變化。那么,如何刻畫市場經濟中各類行為體的特征,就是經濟學需要著力關注和研究的,而不應僅僅以同質性微觀經濟主體的抽象假設將其忽視。企業并非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微觀‘黑箱,而是存在各種不同域態類型的企業,其中:有自利型企業,也有兼利型企業;有私人所有的企業,也有國家所有的企業,還有社會企業(即以社會利益為目標而以市場經營為手段的企業)。因此,對各類企業不能都僅僅以‘經濟人來理解,以‘假定抹殺其特質,而要進行深入的理論解釋和特征刻畫。”面對具有顯著域觀特征的企業域類群體的公司治理,僅以“經濟理性”來理解,追求同質化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顯然抹殺了其獨特的域觀特質,只有融入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因素,才能對具有域觀特質的公司治理進行深入的理論解釋和特征刻畫。
三、域觀范式下公司治理內涵優化
(一)經濟理性張揚具備明確邊界
西方經濟學奉行自由市場理論,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公司自誕生起便具備了經濟理性的張揚,公司治理表現為“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一致性。張揚經濟理性是市場配置資源的表現,即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通過價格機制的協調,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張揚經濟理性有其天然的優勢:第一,市場分工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分工提升勞動效率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來,分工制帶來了勞動生產力的巨大進步,以及勞動技巧和判斷力的熟練和精進。各行各業中,凡是能夠采用分工制的工作,一旦采用分工制,就能相應地帶來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和生產技術的純熟,甚至政治修明的社會中,最底層人民普遍富裕的情況也是分工制促進產量不斷增大帶來的好處[ 25 ]。這種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便是來自市場分工促進生產技術和分配方式的不斷成熟。第二,市場競爭可以調動經濟主體活力。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不斷調整自己的經濟活動以適應價格變化帶來的市場變動,而邊際收益的遞減讓個別生產者不得不及時改良生產工藝、提高勞動生產率,以重新獲得較高的收益率,取得競爭優勢。換言之,生產者只有不斷創新升級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而所有經濟活動主體的創新便能推動整個行業的轉型升級,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正如哈耶克認為:“正是現代條件下勞動分工的這種復雜性……使競爭成為適當地實現這種調節的唯一方法。”充分競爭下,經濟主體基于價格體系傳遞的市場信號及時調整經濟活動,才能實現經濟活動高度的“多樣性”“復雜性”和“靈活性”[ 26 ]。金碚[ 27 ]認為,發展制造業是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必經之路,市場經濟帶來的充分競爭,會促使制造業創新技術、轉型升級,進而形成先進的制造業體系。第三,市場機制保障公司治理的運作。科斯[ 28 ]在論及市場時提到:對存在于趨近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企業而言,精密的規則和規章體系是正常情況下不可或缺的。在現代經濟中,包括商品交易所和證券交易所在內的新市場對經濟活動(交易活動)的參與者進行規范組織,為其提供規范交易所需要的約束條款和爭端解決機制,對交易活動所需要的時間、種類及雙方責任等個體行為進行詳盡約束,并對違反交易規則的參與者進行相應的制裁。市場載體的成熟和市場規則的明確,為現代公司的運行、交易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環境和規則保障,有效降低了隱性交易成本,保障公司治理的有效運作。
域觀經濟學作為一種范式承諾,并不是對經濟理性的否定或摒棄,而是承認經濟理性的主導作用,就像金碚[ 29 ]所說的:“當年的‘思想解放,本質上就是解除對經濟理性的束縛。思維方式的轉變非常符合中國的務實精神,結果則是讓經濟理性得以張揚,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工業化進入加速推進的進程。”中國改革開放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承認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正是對經濟理性的張揚,也成了改革開放后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
(二)價值文化成為公司治理的影響因子
關于企業的性質,科斯[ 28 ]指出:經濟學家眼中經濟體制作為一個“有機體”由價格機制協調“自行運轉”的描述,在企業中是不存在的,人們沒有辦法在所有的方案之間進行精準的分析、預測和選擇,“企業的本質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這表明,經濟體制的運行不僅受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理性的指導或價格機制的協調,而且要受到其背后隱藏的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的影響。價值文化是根植在人類腦海中的行為準則,不同價值文化背景下的群體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會受到其所處的文化背景的影響,公司治理作為社會經濟關系的微觀表現形式,同樣離不開價值文化的影響。正如金碚[ 30 ]認為:“不同國家的企業管理者對有效企業組織的看法是很不一樣的,這種不同的看法是由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價值體系所決定的,非常根深蒂固。”
經濟活動是在不同的文明背景下誕生的,孕育于中西方不同文明下的公司治理也定然具備各自顯著的域觀特征。哈耶克[ 26 ]認為:現如今被我們熟知的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的個人主義的基本原則上逐漸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這種個人主義的最基本特征充分尊重人的個性,即個人可以在自己的范圍內承認看法和趣味的至高無上,并發展自己的天賦和愛好。金碚[ 30 ]認為:以個人主義為基本特征的英美文化對經濟學有著深刻影響。英美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利益的獨立性,社會福利是個人利益的函數,每一個人都從自身利益出發,表現出“趨利避害”的個人行為。現代經濟學是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這種文明推崇高度的個人自由主義,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像梁漱溟[ 31 ]所言:“西洋近代社會之所以為個人本位者,即因其財產為個人私有。恩如父子而異財;親如夫婦而異財;偶爾通融,仍出以借貸方式。”反映到公司治理上,就表現出以“產權”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模式,尊崇“資本權利至上”,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
中國文明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有著和西方顯著不同的內涵。中國文化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為中心,演化出倫理為本的社會,即人自出生起便建立了與他人的關系,人始終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生活,不能離開社會。人們之間的種種關系構成了倫理。倫,便是“倫偶”,是指人與人之間相處形成的關系;理,是指在關系之上形成的情感與道義。這種倫理關系沒有遠近親疏的邊界,不會形成對抗,而是由近及遠,引遠入近,不分彼此,不計較你我。倫理關系既是彼此間的情誼關系,也是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倫理本位的社會文化反映到經濟生活上,財產的歸屬具有“共產”的特征,這種共產不是以“團體”為單位的集體所有,而是以“倫理關系”為單位共有。這種倫理關系下的財產不是個人私有,也不是社會集團所有,更不是一個家庭所有,而是倫理關系的參與者共有,關系越親厚,越要共有[ 31 ]。可見,中國的經濟活動與西方強調的“私有產權”有著明顯的不同,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發展起來的公司治理也不單是以“股東財富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正如華為以員工持股計劃治理公司,在股權結構上,創始人任正非僅以自然人持有公司1.01%的股份,其余98.99%的股份則由在職員工、退休及業務重組員工持有[ 32 ]。這種公司治理的內涵顯然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下以“產權”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具有顯著的中國情境下的價值文化特征。
(三)制度形態構成公司治理的外在條件
經濟活動離不開經濟活動主體所處的制度環境。戴維斯和諾思把制度環境定義為用以建立生產、交換和分配的一系列基本政治、社會和法律規則的集合。這個集合中包含著對經濟主體選舉、產權和合約權利的行為約束[ 33 ]。巴克豪斯[ 34 ]在分析影響市場經濟運行的因素時指出: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需要比自由貿易、公平交易還要多的更多的東西,它離不開制度結構的設計,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個“制度”不僅僅是經濟活動賴以存在的財產權利歸屬和基礎設施,更要包含與經濟活動相適應的思維習慣。他認為制度形態是保障市場經濟平穩運行的外在條件,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自由主義的指導。經濟現象和商業活動發生在具有不同域觀特征的商域里,人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在不同商域中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特征傳統文化又孕育出具有不同特質的制度形態,決定或影響著人的價值觀念和經濟行為[ 35 ]。
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認為,即使一個國家的新興產業是沒有競爭力的,但對其進行保護或許可以將其扶植起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它就可以自立了。這說明產業的發展需要國家的扶植和保護,企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其治理模式和良性運轉更離不開制度形態的優化。馬克·羅伊[ 36 ]在分析政治環境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時指出,政治制度決定了公司的所有權、發展規模、盈利模式、產品形式,以及公司的籌資活動、投資活動、內部權利分配,甚至影響著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的關系。第一,民營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濟活動的開展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完善不能脫離宏觀的制度環境。針對新冠疫情突發為民營企業發展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迅速部署相關部門,制定出臺一系列紓困幫扶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出臺費用減免和補貼措施,鼓勵減免或延期收取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房租,降低民營企業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另一方面,出臺創新貨幣政策工具,聯合金融機構,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降低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這種在宏觀經濟發展出現危機時國家對企業的紓困幫扶,正是制度形態的彰顯。同樣,在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理論中,市場經濟中的企業細胞也需要政府的保護和調控。第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的重要主體,國有企業的發展和不斷深入改革更是制度形態優勢彰顯的重要體現。國有企業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獨具域觀特征的經濟形態為制度前提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是具有獨自特質的企業群體,在世界企業群類中是一個現實存在著的經濟域類。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系中,國有企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成長壯大,表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態的強大現實生產力[ 37 ]。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不能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要把握發展國有企業的制度邏輯和國有企業自身的社會政策目標,聚焦主責主業,提高自身核心競爭力的同時,肩負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任。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
首先,本文從西方經濟學發展演化脈絡入手,對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下的公司治理困境進行了理論闡釋。第一,股票期權從理論到實踐的失靈。西方經濟學范式下,股票期權制度把經理人員的個人收益與企業經營業績緊密相連,理論上可以起到激勵和監督經理人員經營行為的作用,有效解決委托代理問題,但由于經理人員的內部人優勢,仍會引發新一輪的道德風險行為。第二,代理人侵蝕委托人事件層出不窮。委托—代理問題是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存在天然的目標函數不一致、經濟責任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和契約不完全等矛盾,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治理結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代理人侵蝕委托人利益的問題。第三,出資人與勞動者關系不存在合理性可能。在西方經濟學范式下,出資人以“資本”為中心,尋求擴大生產并占有企業剩余索取權,忽視了勞動者擁有的具有高度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出資人和勞動者的關系表現為不平等、對立和沖突,缺乏一個合理的脈絡。
其次,本文基于經濟學域觀范式,從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三個維度提出了公司治理內涵的優化建議。第一,經濟理性的張揚具備明確邊界。張揚經濟理性就是承認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能夠有效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經濟主體的活力與積極性,進一步而言,市場載體的成熟和市場規則的明確,為現代公司的運行、交易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環境和規則保障,有效降低了隱性交易成本,保障公司治理的有效運作。第二,價值文化成為公司治理的影響因子。文化是根植在人類腦海中的行為準則,公司治理作為社會經濟關系的微觀表現形式,離不開價值文化的影響。孕育于中西方不同文明下的公司治理具有各自顯著的域觀特征。第三,制度形態構成了公司治理的外在條件。經濟活動離不開經濟活動主體所處的制度環境,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濟活動的開展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完善不能脫離宏觀的制度環境,中國共產黨對宏觀經濟的指導以及公司治理的深化改革,便是制度形態優勢的彰顯。
(二)未來展望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 38 ]。公司治理作為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微觀保證。展望未來,域觀范式下的公司治理,需要研究學者在理論層面的不斷深入挖掘以及企業界管理人員在實踐中的應用和探索。
一方面,經濟學域觀范式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誕生的,具有高度的理論意義。用域觀范式優化公司治理內涵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次新的嘗試,然而域觀范式的強大學術活力絕不僅限于公司治理內涵的優化,需要理論建構和實證主義的深化及探索,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公司治理理論,實現公司治理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中國化。另一方面,社會文明的進步離不開科學知識的變革,域觀經濟學作為對經濟學微觀—宏觀范式的中國化、現實化的變革,將帶來中國經濟與管理實踐的進步。中國情境下的公司治理實踐,需要超脫委托—代理理論下的治理機制與治理結構框架,基于不同企業的域觀特質,從經濟理性、價值文化與制度形態三個維度探索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用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管理理論指導企業管理與公司治理實踐的不斷深化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軍嶺,李率鋒,郭宇燕,等.民事訴訟、負債融資與公司治理[J].金融論壇,2022,27(2):41-50.
[2] 馬亞明,馬金婭,胡春陽.資本市場開放可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質量嗎:基于滬港通的漸進雙重差分模型檢驗[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1,36(4):81-95.
[3] 呂昊,賈海東.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行為指引制度研究[J].證券市場導報,2022(1):72-79.
[4] 燕艷.從投資者保護看上市公司治理[J].中國金融,2021(12):60-61.
[5] 馬連福.股權結構設計與公司治理創新研究[J].會計之友,2020(17):2-7.
[6] 祁懷錦,曹修琴,劉艷霞.數字經濟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基于信息不對稱和管理者非理性行為視角[J].改革,2020(4):50-64.
[7] 姚云,于換軍.國外公司治理研究的回顧:國家、市場和公司的視角[J].金融評論,2019,11(3):92-109.
[8] 王欣.公司治理的多元演變與深化路徑:“十三五”回顧與“十四五”展望[J].財貿研究,2021,32(2):102-110.
[9] 劉漢民,韓彬.兩權分離與公司治理的演進:英美經驗與我國實踐[J].商業經濟與管理,2022(4):42-53.
[10] 舒偉,張咪.公司治理:新趨勢與啟示[J].管理現代化,2020,40(2):76-80.
[11] 趙旭東.中國公司治理制度的困境與出路[J].現代法學,2021,43(2):89-105.
[12] 陳德球,胡晴.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創新與實踐前沿[J].管理世界,2022,38(6):213-240.
[13] 陳冬華,徐巍,沈永建.嵌入理論視角下的中國公司治理與政府行為:一個整體框架[J].會計與經濟研究,2021,35(3):35-54.
[14] 田妮,張宗益.中國文化如何影響公司治理:一個述評[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9,35(5):12-20.
[15] 高闖.經理股票期權制度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26.
[16] 謝德仁.經理人激勵與股票期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8.
[17] 張紅鳳,孔憲香.股票期權制度:理論·實踐·反思[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180-181.
[18]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下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17: 180-181.
[19] 張孝梅.委托人與代理人的目標沖突及融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11.
[20] 邁克爾·詹森,威廉·梅克林.企業理論:管理行為、代理成本與所有權結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1] 石建勛.美國怎么了:美國公司丑聞的全景透視[M].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2003:303-304.
[22] 馬克斯·韋伯.非正當性的支配[M].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40-141.
[23] 金碚.關于開拓商域經濟學新學科研究的思考[J]. 區域經濟評論,2018(5):1-13.
[24] 金碚,等.域觀經濟學研究[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21.
[25]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上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17.
[26]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義,馮興元,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7] 金碚.新時代充分競爭型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取向[J].經濟縱橫,2020(10):66-73.
[28] 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M].盛洪,陳郁,譯.上海:格致·三聯·人民出版社,2014.
[29] 金碚.中國經濟發展中理性觀念演變歷程[J].江蘇社會科學,2019(1):1-8.
[30] 金碚.何去何從: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
[31]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32] 馬艷,徐文斌,馮璐.華為員工持股對企業經濟關系的影響與特色[J].教學與研究,2020(8):42-53.
[33] 陳昕.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88.
[34] 巴克豪斯.經濟學是科學嗎:現代經濟學的成效、歷史與方法[M].蘇麗文,譯.上海:格物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5] 金碚.試論經濟學的域觀范式:兼議經濟學中國學派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2):7-23.
[36] 馬克·羅伊.公司治理的政治維度:政治環境與公司影響[M].陳宇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37] 金碚.中國國有企業再探究:域觀取向的現實觀察[J]. 社會科學文摘,2022(6):78-80.
[38] 中國政府網.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
content_5721685.htm,2022-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