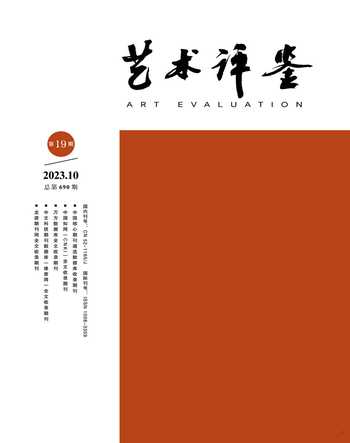表演者視角下南豐儺舞的傳承與發展
任鑫
【摘 ? 要】儺,起源于上古時期人們的祭祀活動,最早用于宮廷除病消災。千百年來,儺文化不斷傳承發展,形成了今日中國南方各地區豐富多彩的儺文化。南豐儺舞是第一批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的儺舞品類,在申遺成功后被各類專家學者所重視,對其進行不同層面的深入研究。近年來對南豐儺舞的研究多圍繞“非遺保護”“文化內涵探究”等理論層面,而南豐儺舞舞臺化創作和表演相關的文章卻“寥若晨星”,因此筆者從表演者視角出發,探尋南豐儺舞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南豐儺舞 ?儺舞表演 ?“非遺”傳承 ?職業舞者
中圖分類號:J7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3)19-0080-06
儺,是上古時期人們以除病消災、祈求風調雨順為目的儀式,因在儀式過程中舞蹈屬性明顯,所以又被稱為“跳儺”,其中舞蹈的部分被后人稱為“儺舞”。儺的歷史悠久,在《禮記·月令》中載:“季春之月,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可見在周代,官方就十分重視儺祭,分別在三月、八月、十二月舉行國儺、天子儺、大儺三種不同規格的儺祭。通過周代官方對儺的重視程度可以推斷出,儺的起源要早于周代,很可能與儀式文化相關,并且儺祭作為上古時期的重要儀式,在上古時期和之后的封建時代受到官方和民間的共同重視。
一、緣起——南豐儺舞與儺舞表演者
(一)儺與南豐儺舞的起源與發展
南豐儺起源于漢代,南豐紫霄鎮黃砂村民國年間的《金砂余氏重修族譜》重刊傅太輝的《金砂余氏儺神辨記》中有這樣的記載:“輝嘗考宋時邑志舊本載,漢代吳芮將軍封軍山王者,昔常從陳平討賊,駐扎軍山,對豐人語曰:此地不數十年必有刀兵,蓋由軍峰聳峙,煞氣所鐘,凡爾鄉民一帶介在山輒,須祖周公之制,傳儺以靖妖氛。”這段文字是對江西地區跳儺的最早文字記載,證明了越人將軍吳芮于漢初傳儺于南豐地區,在儺儀傳入之后,受到了南豐地區人民的推崇與重視。
時間推移到唐代,儺儀在宮廷與民間的發展均十分繁榮,《新唐書·禮樂志》詳細記載了大唐宮廷儺儀的盛況;唐玄宗時代官修的《大唐開元禮》中也對各州縣等行政單位儺儀的規模與形制進行了規定。唐代官儺盛行,鄉儺也同樣繁榮。據傳,南豐縣白舍鎮甘坊村于唐代就已經建立儺廟,當地儺班部分節目的動作形制自唐代就開始傳承。
脫唐入宋,宋代對儺儀的管理更加寬松,《夢粱錄》中載,宋代的儺儀由皇家娛樂機構負責,負責部門的改變體現了官方對儺儀更加開放的態度。與此同時,南豐儺舞在兩宋時期也加入了先人或民間傳說中除傳統儺儀以外的對象,如宋代兩帝都詔封過的軍山神吳芮,他在漢初將儺傳入南豐地區,受到南豐人民的愛戴,在儺祭時與其他儺神同享香火與祭拜。
元代時期由于當政者的民族與文化不同,無論是官儺還是鄉儺都幾乎停滯。但至明初,南豐跳儺的傳統逐漸恢復,石郵村儺神廟中碑文《石郵鄉儺記》由明初吳姓家族貢生吳其馨所著,其中載:“石郵之儺,自明宣德支祖潮宗太尹公出宰潮州海陽縣令,政績有聲,百姓歌功頌德……按《晉語》所謂‘衣偏裻之衣,必盡敵而返者,即以除厲疫而大驅之也。所歷之城鄉時疫立止,即立廟于治署,朔望朝服祀之。”①可見石郵村儺為族儺,由吳氏家族從潮州帶來。但有些學者對此起源持懷疑態度。《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江西卷上》中載,1983年采風小組遠赴廣東潮州追溯石郵村儺舞起源,并未找到當地儺舞相關的歷史記載或民族風俗。明清時期,南豐儺舞十分繁榮,跳儺也成了當地民眾習俗性的民間活動,民眾普遍將儺祭作為特定節日的必要活動,相信儺儀可以為其消災解禍。
縱觀儺的歷史流變,其符合舞蹈藝術發展由“儀式”到“表演”,由“功利”到“娛樂”,由“官方”到“民間”,由“儀”到“舞”的普遍規律。儺從嚴肅的儀式到娛人形式的表演,其功能在不斷改變。儺的表演者也從周代的天子攜群臣,到唐代的宮廷專職儀式表演人員,再到兩宋的宮廷娛樂表演人員,最后到明清時期的民間儺班。從表演者的視角分析,儺舞的表演從最開始的功能性的祭祀,逐漸向娛人與娛神共存的表演性質轉變。表演者的身份不斷平民化,表演內容不斷娛樂化,表演形式不斷地域化,這三點是儺舞作為起源于遠古的儀式舞蹈,其文化與表演形式時至今日仍能傳承的重要原因。
(二)儺舞的表演者與儺的關系
舞蹈,作為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最大特點在于其所運用的藝術材料就是人的身體,任何人都擁有表演舞蹈的材料,因此任何人都能接受和欣賞舞蹈。有部分學者認為,在上古時期“舞”與“巫”同源。儺是印證此學說的一個范例。儺源自上古時期的除疫儀式,表演者有“巫師”“祭祀”等身份的存在。在之后的朝代中,儺舞中的舞蹈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立且非功能性的藝術形式。儺舞表演者與儺的關系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不盡相同。根據儺的歷史與當代儺舞的發展現狀,筆者總結出儺舞表演者與儺的三重關系。
其一,儺舞表演者是儺儀的承載者,從上古時期到如今,儺舞表演一直是儺儀的一部分,沒有儺舞表演,儺儀作為除疫儀式的主要內容就無法完成;沒有儺儀,儺舞本身就失去了其部分意義。其二,儺舞表演者是儺舞的主體,任何舞蹈產生的基礎都是舞者的身體,儺舞也不例外,無論是功能性儺儀還是表演性的儺舞,表演者本身永遠是舞蹈的主體。其三,儺舞表演者是儺文化傳承的載體,儺文化是上古時期流傳至今的優秀傳統文化,儺文化的主旨、表現形式與傳承內容,無不在儺舞表演者的每一次表演中呈現。
誠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儺舞表演者的身份及其與儺的關系都有所不同,筆者下面從儺舞表演者的角度出發,從歷史中探尋他們身份的變化。
二、流轉——儺舞表演者身份的轉換
從儺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儺舞的表演者,其身份分別在周代、唐宋、明清、民國時期、改革開放后五個時期有所轉變。
(一)周代至唐宋——宮廷儀式專人
首先是周代時期,儺第一次被官方指定為國家層面的除疫儀式,其規格之高,是前代所未有的。儺受到上古時期儀式文化的影響,在周代之前與其他宮廷或民間儀式一樣,由主持儀式的專職人員完成。在周代,《禮記·月令》中明確記錄了“仲秋之月(八月),天子乃儺”,證明當時周天子每年至少參與一次儺儀,并要與專職人員一起進行儀式流程。一年中的其他儺儀(國儺、大儺)并未明確記載有天子參與,但就文獻對儺儀規格的描述,在西周時期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時代舉行如此大規模的儺儀,必定是由天子授意、由官方舉辦。因此,周代的儺舞表演者的身份地位是儺舞歷史中最高的,上至國家權力地位最高的周天子,下至文武百官、專職人員以及平民百姓,每當儺儀舉行,他們既是儀式的參與者,也是儺舞的表演者。誠然,儺儀在周代官方的興盛得益于周代完備的禮樂制度,但不可否認的是,周代儺舞的規格和參與人員的地位處于整個儺舞發展歷史中的頂峰。
時至唐宋,官方儺舞經過長期發展,儀式本意猶存,但其規格與形式較周代有較大調整。《新唐書·禮樂志》載:“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為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為瘞埳,各于皇城中門外之右。”②可見唐代儺儀依然聲勢浩大,但表演者從皇帝群臣變為了貴族黃門子弟以及專業的樂舞儀式人員,也對儺舞的服裝、流程等進行了詳細的規范。《新唐書》對唐代宮廷儺舞的記錄印證了唐代宮廷樂舞與儀式樂舞的空前繁榮,也印證了儺舞這類儀式類舞人在唐代已經開始了專門化與職業化。在唐代,儀式類樂舞與表演類樂舞的建制規模與表演形式有明顯的區別,如儺這種儀式類樂舞只能在特定的時間由特定的人表演,但到了宋代,宮廷負責機構的變化使得儺舞更具表演性與娛人性。據宋《夢粱錄》載:“禁中除夜呈大驅儺儀,并系皇城司諸班直,戴面具,著繡畫雜色衣裝,手執金槍、銀戟、畫木刀劍、五色龍鳳、五色旗幟……謂之‘埋祟而散。”③由此可知宋代負責儺舞表演的不再是宮廷負責儀式的機構,而是轉為皇室娛樂機構負責,并且不再由專職儀式人員主持,儺舞除疫儀式的功能性在宋代再一次被弱化,表演者也從貴族黃門子弟與專門人員變成了宮廷職業樂舞人員,其身份地位更加世俗化。
除了宮廷官方組織的官儺外,唐宋時期由民間組織的鄉儺也十分盛行,以南豐為例,雖然儺儀建制規模無法與官儺相比,但儺舞在村鎮各地流傳的世俗化與地域化從客觀上推動了儺舞的傳承與發展。在鄉儺傳承的過程中,儺舞表演者的身份又一次出現了轉變。唐宋時期,宮廷儺舞表演者大多是職業舞人,其作為皇室“資產”,為皇室及百官服務,他們以舞蹈為職業,并以此為生。鄉儺的表演者則不然,大部分的鄉儺儺班都由當地民眾組成,在舉行儺儀時,他們是專職的跳儺與儀式人員,在其他時間,他們仍是民眾身份,參與生產活動。從當代“非遺”傳承的視角分析,現代大部分儺班表演者的身份多與古代鄉儺類似,也正是從唐宋時期起,儺的傳承與發展從宮廷緩慢下沉至民間。
(二)明清至當代——民間文化傳承人
明清時期,儺傳播與表演的重心從宮廷轉為民間,以南豐為代表的各類儺舞在中國南方地區廣為流傳。在明代之前,關于儺舞的記載多出自官方史書,到了明清時期,各地方志、家族志、地方傳記等民間文字資料均開始記載有關當地儺舞、儺儀、儺戲等有關活動,明清時期的儺儀形式與儺舞內容,已經與如今各地的儺舞有了很大聯系,如南豐縣石郵村儺舞就是此時由吳姓家族表演傳承,并一路發展至今。正如劉健教授所說,民間舞是一種生長狀態如草根一樣的“活化石”,偶爾在正史中被不經意地記錄,主要是自我長成和發展。但重要的是,它們不是外在于民間的附屬物,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因此任何人的“改教”都意味著改變以往的和當下的生活方式,這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十分漫長的甚至幾乎不可能完成的過程。從歷史脈絡上看,儺傳承的時間與地域跨度之廣,足以證明其是中國民間舞的典范之一。
民國時期,隨著我國各地鄉村“戲班子”的活躍,“跳儺”也隨著地方戲劇的發展而發展,變得更加世俗化,一些儺班將地方戲曲、武術、雜技等融入儺舞之中,創作出了許多儺舞節目,這些節目淡化了儺作為除疫儀式的內容,降低了儺舞的功能性,更加突出了儺的表演性質。民國末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儺舞一直作為南方各地民眾傳統的儀式表演;20世紀60—70年代,以南豐為代表的各地儺儀及儺舞表演全部被迫停止;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南豐儺舞重新煥發生機:1996年11月,文化部命名南豐縣為“中國民間藝術(儺舞藝術)之鄉”;2006年,南豐儺舞成功入選我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至今日,依托國家政策的支持,越來越多的學者及舞者開始研究、學習南豐儺舞,并將其不斷發揚光大。
從周代的祭祀儀式到如今的南豐縣“非遺”,儺文化一直古樸且神秘地傳承著,承載儺文化終端的,正是那一代代儺祭中舞動的身體。從周代的天子群臣,身體力行;到唐代的儀式大典,專人起舞;到宋代的宮廷舞人,娛人為先;再到明清、民國的廣為流傳,民眾先行,儺舞表演者的身份在不斷平民化的同時也在不斷“非職業化”。事實證明,這種去職業化的民間傳承方式能夠讓古代樂舞傳播得更廣泛。隨著國家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南豐儺舞的傳承環境受到不利影響,當代縣城、鄉村里的年輕人大多不愿接受老一輩的傳承。因此,南豐儺舞如少數其他傳統民間樂舞那樣出現了“斷代危機”。自發性的繼承方式在當下確實無法承載大多數傳統民間樂舞的傳承。隨著“非遺”政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職業舞者以“表演者”的身份開始在不同場域表演南豐儺舞,他們深入鄉村采風,學習南豐儺舞,并以南豐儺舞為基礎,創作新的民間舞作品,成為南豐儺舞傳承與發展的新力量。
三、延展——當代表演者視角下的南豐儺舞表演
儺舞自有記載以來,表演者的身份就在不斷變化,官儺表演者自唐代開始直至明清,都由宮廷職業樂舞人擔任;明末清初時,官儺與其他大多數傳統宮廷樂舞一起,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儺舞的流傳從宮廷轉為民間的過程,也是儺舞表演者身份轉變的過程,這種身份轉變的優勢在于能夠讓儺文化與本地文化相結合,并最大程度上保證儺舞在民間的傳承,簡而言之,明清之后各地民間儺舞的傳承方式保證了儺舞傳承的可持續性和各地儺舞的獨特性,豐富了當下儺舞的表現形式。南豐儺舞被納入“非遺”名錄后,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在國家“非遺”政策支持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許多舞蹈學、民族學、社會學等相關專家學者對南豐儺舞進行了保護性與溯源性研究。與此同時,許多民間職業舞者開始了對南豐儺舞的采風學習,進行南豐儺舞的傳承與發揚。
(一)身體力行——當代職業表演者實踐經驗總結
筆者作為職業民間舞者,有幸于2020年9月赴南豐縣石郵村,同石郵儺班“八伯”饒金泉學習儺舞中的“開山”“紙錢”“雷公”“關公”四個節目。在學習的同時,筆者對南豐儺舞的歷史、表演形式、表演者現狀進行了探尋與了解。石郵村儺舞的傳承方式為古樸的“頭人制”,即石郵村儺班傳承人固定為八位,按照入班次序定為“大伯”至“八伯”,每一位“伯”在石郵儺舞的表演中都有著明確的分工。自吳氏祖先傳儺至此,“頭人制”的傳承方式一直未曾改變,這種傳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石郵儺舞傳承的規范性與穩定性。
通過采風與學習,筆者加深了對南豐儺舞文化的了解。通過學習得來的儺舞素材和編導的二次創作,舞臺形式的南豐儺舞作品《開山》誕生了。這部作品的動作素材均取材于南豐儺舞中的節目“開山”。作品在保留了南豐儺舞自身風格的同時,增加了中國民族民間舞、現代舞等動作元素,結合創作音樂、舞臺燈光服裝道具等舞臺表演元素,將石郵儺舞舞臺化,旨在通過新的創作方式更好地發展南豐儺舞。作為當代職業表演者,通過總結表演過程中的心得體會,想從當代職業舞者的視角提幾點對南豐儺舞的看法。
不同于其他民族舞或民間舞,南豐儺舞沒有一套完整的“學院派”專業院校教學體系,因此儺舞的表演對從舞蹈院校畢業的職業表演者來說是陌生的。其一,在職業表演者的學習與表演經歷中并沒有與之相關的表演經驗;其二,由于南豐儺舞獨特的動作元素和表演方式,職業表演者作為舞蹈演員的“通識”表演經驗無法有效地應用于本作品的表演之中。正是因為需要解決上述問題,職業表演者需要在本作品排演前先行前往南豐儺舞的發生地——石郵村進行南豐儺舞的田野調查與節目學習。進行田野調查,了解石郵村儺舞的歷史脈絡與精神文化,是為了從思想上了解南豐儺舞,從而幫助當代職業表演者找到正確的表演狀態,準確地調動表演情緒。
在動作上,南豐儺舞與其他民間舞有很大差別,因此跳南豐儺舞對職業舞者“已經接受專業化規訓”的身體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筆者作為專業院校畢業的職業舞者,在石郵村學習南豐儺舞之時感受到了其與傳統舞臺表演不同的發力方式與動作編排方式,例如短暫且急速地收縮、上身晃動結合腳下的快速跳躍等,在一些節目中還會出現長時間重復的單一動作。筆者在學習這些動作時,詢問傳承人動作的具體規格和做法,傳承人表示他們也無法準確地描述出這些動作的具體規格。在南豐縣的每一個村、每一個傳承人,甚至跳每一場儺時,少部分動作都有可能會因為環境、人員,甚至跳儺者的狀態不同而有所變化,究其原因,是民間南豐儺舞“言傳身教”的師徒制傳承模式,此類模式也是中國大部分民間舞蹈的傳承方式。由石郵村儺舞不尋常的發力方式與不清晰的動作規格認識到,一方面此類舞蹈動作的學習不符合職業舞者平日里排演舞蹈作品的狀態,可能拖慢舞者學習的進度,并干擾舞者對動作本身的認識,此為職業舞者學習此類民間舞蹈的不利條件;另一方面對動作規格要求的減少和發力方式的不同,也會讓舞者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讓舞者結合自身的動作經驗進行傳統舞蹈的舞臺化創作。
不同于其他舞臺表演作品以“動作”為先,在《開山》這部作品中,由儺舞文化內涵所提供的“內驅力”是本部作品所要呈現的更為重要的內容,其在舞臺上的直接表達就是舞者的表演狀態。由于儺舞除疫祈福的特殊功能,起舞之人本身就是“儀式”的角色,在舞臺之上,表演者也需要抓住儺舞的本質,進入到一種虔誠、投入的表演狀態。
(二)多元發展——職業舞者與傳承人的不同職責
筆者作為“外鄉人”,來到石郵村學藝,結合學習儺舞的過程、與傳承人的交流、進行儺舞的二度創作與表演的感受,總結出了職業舞者與傳承人在南豐儺舞表演上的不同之處。
對于南豐儺舞,職業舞者與傳承人的表演場域不同。石郵村儺班的表演場域有村中儺神廟,村內東、西位祠堂,太尹公家內,村中各戶與周圍各村。作為儀式舞蹈,表演場域是南豐儺舞乃至整個儺儀得以成立的根本,石郵儺班在石郵村及周邊村落跳儺,其處在石郵儺舞的本源場域,只有在這個場域,石郵儺舞才得以完整呈現。而職業舞者的表演場域主要集中在舞臺空間,場域的改變讓舞者在表演時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即使可以做到動作完全相同,職業舞者也難以還原出南豐儺舞的完整本源形態。
表演場域既是某個場地的物理概念,也是對于當地文化認同的心理概念,由此可以發現職業舞者與儺舞傳承人的第二個不同之處——身份認同的不同。儺舞的傳承人是儺文化的傳承者,也是儺儀的籌劃者、儺舞的表演者。在石郵村,跳儺儀式從農歷大年三十開始,到正月十六結束,儀式要經過起儺、演儺、搜儺、圓儺四個步驟,儺舞的八個節目存在于“演儺”之中,對于儺班傳承人,整個跳儺儀式都是十分重要且嚴謹的,這種對于傳統堅守的信念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他們對自己儺班“傳承人”身份的認同,這種身份認同源自儺文化本身與當地的地域文化。而對于職業舞者而言,其在跳儺舞時更多體現的是對職業表演者身份的認同,所以其在起舞時會更多關注舞蹈動作本身,而且由于沒有傳承者身份的阻礙,其和職業舞蹈創作者更容易對傳統的儺舞動作元素進行提取和改編,進行舞臺化的二度創作。
四、結語
對于南豐儺舞傳承與發展而言,傳承人與職業舞者分別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無論是“非遺”制度還是民間自發,一個民間舞蹈的傳承離不開其傳承人,傳承人承載的是技藝的相關文化、技術、表現形式,他們是傳統技藝的載體。職業舞者經過多年專業的舞蹈訓練,并從事舞蹈表演相關工作,需要在不同舞種、不同作品中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他們是舞蹈的載體。當代南豐儺舞的傳承與發展,傳承人更多地起到了“守”的作用,在堅守傳統儺舞文化與技藝的基礎上進行發展,而職業舞者更多地起到了“發揚”的作用,通過自身的表演及創新,讓南豐儺舞在專業舞臺這個普及化的專業場域中“發揚光大”,讓更多的人看見并了解南豐儺舞。
參考文獻:
[1]陳戍國點校.周禮·儀禮·禮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9.
[2]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編輯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江西卷上[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3]曲六乙,錢茀.中國儺文化通論[M].臺灣學生書局,2003.
[4]曾志鞏.江西南豐儺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5]余大喜.中國儺神簡論[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1999(03):46-53.
[6]劉建.民間舞蹈“活化石”解[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5(04):45-47.
[7]劉永紅.論江西儺舞進入高校舞蹈教學的必要性[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8(02):107-112.
[8]羅斌.假面陰陽——安徽貴池儺舞的田野考察與研究[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7年.
[9]張嫣然.石郵村“跳儺”的表演特征[D].北京:北京舞蹈學院,2014年.
[10]舒斯強.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南豐儺舞的傳承與保護研究[D].蘭州:西北民族大學,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