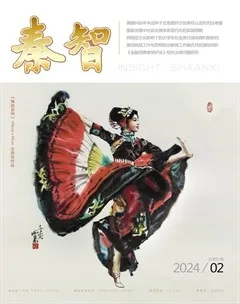初構(gòu)、瓦解與重塑:彝區(qū)漢人文化身份認(rèn)同問題的敘事研究
[摘要]民族間的遷徙互動(dòng)、文化融合以及文化身份的認(rèn)同等一直以來(lái)都是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重要議題。本文采取敘事研究的方式,以一個(gè)從小生活在彝區(qū)的漢族人為研究對(duì)象,再現(xiàn)其成長(zhǎng)經(jīng)歷,以求分析她的文化身份塑造過(guò)程。通過(guò)調(diào)查、訪談發(fā)現(xiàn):研究對(duì)象在經(jīng)歷了初步塑造文化身份階段、因制度與固有漢族人身份而自我懷疑階段、走出彝區(qū)后的文化身份重塑階段三個(gè)階段后,形成了獨(dú)特的文化身份。希望本文可以為有關(guān)民族文化影響和身份認(rèn)同研究提供參考,并為民族融合與團(tuán)結(jié)提供新的思路。
[關(guān)鍵詞]身份認(rèn)同;彝區(qū)漢族;敘事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G0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2.027
一、研究背景
云南省是我國(guó)民族種類最豐富的省份,除漢族以外,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少數(shù)民族有彝族、白族、傣族、苗族、傈僳族等25個(gè),其人口數(shù)達(dá)1621.26萬(wàn)人,占全省人口總數(shù)的33.6%。此地少數(shù)民族文化蓬勃發(fā)展,民族文字眾多,民族信仰復(fù)雜。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的歷史發(fā)展,云南各民族同源異流、異源合流又源流交錯(cuò),不斷分化融合,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交融地區(qū)。正是由于這樣的交匯融合及交錯(cuò)居住和土地互嵌,各族民眾之間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廣泛的文化互動(dòng)與社會(huì)交往。因此,關(guān)于云南省乃至整個(gè)西南地區(qū)的民族間遷徙互動(dòng)、文化影響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認(rèn)同等問題成為不少學(xué)者關(guān)注的議題。
本文的研究者將采用敘事研究的方式,從文化交融互動(dòng)的角度,探索一個(gè)彝區(qū)漢人的文化身份認(rèn)同問題,分析她的自我身份建構(gòu)以及彝族文化對(duì)她成長(zhǎng)之路的影響。研究者認(rèn)為,運(yùn)用敘事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更好地呈現(xiàn)彝區(qū)文化對(duì)研究對(duì)象心理與行為的影響過(guò)程,凸顯其在構(gòu)建文化身份時(shí)心理活動(dòng)的豐富性和情境性。
二、研究設(shè)計(jì)
(一)研究對(duì)象的選取
本文選取的研究地點(diǎn)為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縣大可鄉(xiāng)大可村,石林縣有漢、彝、白、傣、苗等26個(gè)民族,少數(shù)民族人口89422人,占總?cè)丝诘?5.8%,是名副其實(shí)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其中,大可鄉(xiāng)地處石林彝族自治縣西南部,作為鄉(xiāng)政府的所在地,大可村中的居民多為漢族,而毗鄰此地的就是一個(gè)名叫“者衣”的彝族村落。者衣村往東為玉屏山,往西是老鴉坡,村落座于兩山之間,有向外的通路。本文的研究對(duì)象小趙就來(lái)自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縣大可鄉(xiāng)大可村,她作為一個(gè)漢族人,在大可村與者衣村的文化交融、經(jīng)濟(jì)往來(lái)、人情互動(dòng)中成長(zhǎng),深受彝族文化的熏陶,而這一漫長(zhǎng)的耳濡目染過(guò)程也深刻地塑造了她獨(dú)特的文化身份。
(二)研究過(guò)程的實(shí)施
本文的研究者在搜集相關(guān)資料后,初步了解了小趙的生活環(huán)境,并制定出訪談大綱,與小趙開展了三次訪談。訪談的方式為半結(jié)構(gòu)訪談,其主要內(nèi)容包括個(gè)人成長(zhǎng)經(jīng)歷、對(duì)彝區(qū)文化的看法、與彝人互動(dòng)方式的改變以及自我文化身份塑造的過(guò)程幾個(gè)方面。
(三)對(duì)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通過(guò)訪談,研究者將小趙的生活經(jīng)歷與身份認(rèn)同分為三個(gè)階段:彝族文化影響下的初步塑造文化身份階段、因制度與固有漢族人身份而自我懷疑階段、走出彝區(qū)后的文化身份重塑階段。由此,研究者歸納并復(fù)原出小趙的成長(zhǎng)之路。研究者通過(guò)整體——內(nèi)容以及整體——形式的分析方法對(duì)資料進(jìn)行分析,闡述小趙構(gòu)建文化身份的過(guò)程。其中,整體——內(nèi)容的分析方法是利用個(gè)體完整的生活故事,聚焦于所描述的內(nèi)容,而整體——形式則是著眼于生活故事的劇情發(fā)展和完整結(jié)構(gòu)。
三、研究分析
(一)認(rèn)同感形成——文化身份的初構(gòu)
小趙的祖輩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可村,她本人也無(wú)從追溯祖先何時(shí)遷入此地。小趙的父母是家中第一代走出大山的人。但小趙說(shuō),他們走出了大山,可又似乎沒有離開大山,他們是漢人,卻又像無(wú)數(shù)彝人一樣,扎根于崇山峻嶺之中,因?yàn)樗麄兩诖耍查L(zhǎng)于此。
“我對(duì)于彝族人的印象最早來(lái)源于一次上山采摘,那時(shí)我很小,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清到底是幾歲了。家里的長(zhǎng)輩帶著我,背著筐子,沿著老鴉坡一路往上,后來(lái)就聽到了歌聲,家里的老人說(shuō),是隔壁村的女人也上山了。我聽不懂她們?cè)诔裁矗杪暫芨甙海覇栁业睦贤馄牛f(shuō),那是彝語(yǔ)歌。”
“等我再長(zhǎng)大一些,能記起的事就多了。比如火把節(jié),再比如隔壁村哪個(gè)女人結(jié)婚了,我們就會(huì)跑到那邊去看他們殺豬,有些慈祥和藹的老婆婆會(huì)給我們吃的,當(dāng)時(shí)覺得那邊的新娘子長(zhǎng)得漂亮,穿得也漂亮,脖子上戴著銀首飾,亮閃閃的。我們幾個(gè)小女孩子湊到一起說(shuō),將來(lái)也要穿著那樣的衣服嫁人。”
不難看出,小趙對(duì)于彝族的印象初構(gòu)是美好的,這種美好與初次面對(duì)彝人時(shí)情境的描繪、彝人展現(xiàn)出的親善以及彝族文化的外在表現(xiàn):服飾,這樣的文化符號(hào)相連接,而小趙對(duì)彝族文化的初步認(rèn)同就是源自這種美好。初印象的美好消解了不同文化交融時(shí)可能帶來(lái)的文化震撼,使小趙更容易接受彝族文化,她生活在彝族文化的浸染下,并于潛移默化中,無(wú)意識(shí)地成為了其中一員。“穿著那樣的衣服嫁人”就可以看作是小趙塑造自己不同于其他漢人文化身份的第一步。
(二)認(rèn)同感的強(qiáng)化與動(dòng)搖——文化身份在制度背景下的瓦解
1.文化學(xué)習(xí)帶來(lái)的認(rèn)同感強(qiáng)化
“我們這里的小學(xué)、初中還有高中,里面有大量的彝族學(xué)生,就連有些老師都是彝族人。上小學(xué)的時(shí)候,他們有時(shí)會(huì)帶領(lǐng)我們學(xué)習(xí)彝族歌曲,說(shuō)一些彝語(yǔ),有的我能聽懂,有的聽不懂。后來(lái)上了初中,課間操要學(xué)彝族舞,那會(huì)才不分你是彝族還是漢族,大家一起跳,穿一樣的彝族衣服。我們同學(xué)也不會(huì)說(shuō)你是漢族人,你不能穿我們的衣服。在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都是一樣的。”
相較于無(wú)意識(shí)的、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這種構(gòu)建于學(xué)校制度體系下的學(xué)習(xí)無(wú)疑強(qiáng)化了小趙對(duì)于彝族文化的認(rèn)同感。小趙作為一個(gè)學(xué)生,在沒有偏差地接受學(xué)校傳輸?shù)闹R(shí)后,真正走進(jìn)了彝族文化之中。一起跳彝族舞、穿彝族服飾是小趙從接受文化身份走向認(rèn)同文化身份的重要轉(zhuǎn)折,當(dāng)所代表彝人的文化符號(hào)出現(xiàn)在一個(gè)漢族人的身上時(shí),外界很難再去用生理因素確定其真實(shí)身份,而小趙對(duì)彝族文化的認(rèn)同感也通過(guò)外在環(huán)境的反應(yīng),得到深刻強(qiáng)化。
2.被標(biāo)簽化和污名化帶來(lái)的認(rèn)同感動(dòng)搖
“那時(shí)我交了幾個(gè)彝族好友,他們當(dāng)中有些人就來(lái)自者衣,或者石林的其他地方,我們以前就見過(guò)。還有些是從很遠(yuǎn)的地方來(lái)的,比如紅河、楚雄什么的,上高中之后也見過(guò)一個(gè)涼山那邊的姑娘,他們的經(jīng)歷與我們截然不同。家里有些大人們說(shuō),那些從紅河來(lái)的彝族小孩,父母都吸毒,可實(shí)際上并不是那樣,但我也會(huì)害怕,會(huì)覺得他們說(shuō)的都是真的,因?yàn)楫?dāng)時(shí)剛出來(lái)那個(gè)什么湄公河大案。久而久之,我好像也沒什么彝族朋友了。”
從身邊簇?fù)碇姸嘁妥迮笥眩經(jīng)]什么彝族朋友,其中經(jīng)歷了彝族人被標(biāo)簽化與被污名化的過(guò)程。廣泛傳播的流言、貼在彝族人身上的標(biāo)簽以及子虛烏有的污名,使小趙開始對(duì)彝族身份的認(rèn)同產(chǎn)生動(dòng)搖。盡管小趙身處彝區(qū),漢族文化在此地并不算一種強(qiáng)勢(shì)文化,但這種不平等的標(biāo)簽化行為仍然體現(xiàn)了自上而下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小趙最初對(duì)于彝人以及彝族文化的美好印象,同時(shí)將原本已認(rèn)同的文化身份與現(xiàn)有的污名割裂開,使小趙的認(rèn)同感出現(xiàn)了動(dòng)搖。
(三)認(rèn)同感的再現(xiàn)——文化身份的重塑
1.離開家鄉(xiāng)后的自我審視
研究者第一次見到小趙時(shí),她正坐在寢室的桌邊,手上戴著一個(gè)明晃晃的銀鐲子,在聽到室友夸贊鐲子好看后,她說(shuō),這是彝族人的銀器首飾。隨后,小趙從箱子里翻出了一條鑲嵌著刺繡花邊的裙子,展示給大家看,她說(shuō),這是彝族人的傳統(tǒng)服飾。當(dāng)室友問起彝族人的舞蹈時(shí),小趙大方地跳了起來(lái)。
趙:“當(dāng)時(shí)她們問我,你是彝族人嗎?我說(shuō)不是,她們又問,既然不是為什么你會(huì)帶著這么多彝族人的東西?我突然答不上來(lái)。”
研究者:“那你覺得自己現(xiàn)在能答上來(lái)嗎?”
趙(笑):“現(xiàn)在?現(xiàn)在我可能會(huì)說(shuō),我是一個(gè)精神彝族人。”
趙:“她們后來(lái)會(huì)問我很多關(guān)于彝族的事情,會(huì)對(duì)我很好奇。在問我一些問題的時(shí)候,她們也不會(huì)說(shuō)他們彝族人怎么樣,而是會(huì)問你們?cè)趺礃樱谶@個(gè)時(shí)候,我好像又成了當(dāng)初在操場(chǎng)上穿著彝族裙子跳舞的小孩兒,在離家?guī)浊Ч锿獾牡胤剑矣肿兂闪艘妥迦恕N沂矣延X得我對(duì)彝族文化了如指掌,她們會(huì)要我拍一些那里的照片,會(huì)覺得我?guī)サ囊妥逡路芎每矗任以倩氐侥沁叄ヅe著手機(jī)通過(guò)視頻給她們介紹的時(shí)候,我覺得我就是這里的人,這變不了的。”
小趙對(duì)于文化身份的初步重構(gòu)來(lái)源于一些對(duì)彝區(qū)毫不了解的陌生人,她們幫助小趙重新識(shí)別了早已根深蒂固于她思維中的文化符號(hào)。在身份認(rèn)同理論中,“身份識(shí)別”強(qiáng)調(diào)本質(zhì)“再現(xiàn)”,即能夠辨別自身社會(huì)關(guān)系與文化結(jié)構(gòu)。小趙在陌生環(huán)境下,身處于一種由他人建構(gòu)起來(lái)的語(yǔ)境中,在這樣的語(yǔ)境里,她通過(guò)識(shí)別與再現(xiàn),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已經(jīng)認(rèn)同的文化身份。
2.回到家鄉(xiāng)后的身份重塑
2021年6月,小趙大學(xué)畢業(yè),來(lái)到曲靖市工作,那里距她家鄉(xiāng)的縣城有差不多兩三個(gè)小時(shí)的車程。在這里,小趙的生活逐步歸于平靜,她的文化身份也基本定型了。
“我就是一個(gè)生長(zhǎng)在彝區(qū)的漢族人,我身上沒有流彝族人的血,但是我卻被彝族人的文化熏陶至今。現(xiàn)在回家之后,我還是會(huì)去隔壁村子里逛逛。今年夏天,我和爸媽回去參加了火把節(jié),就和小時(shí)候一樣,沒什么改變。者衣的彝族人會(huì)來(lái)我們村里擺地?cái)偅u了錢再?gòu)奈覀冞@里買些東西回去。我也了解了更多有關(guān)彝族人的故事,去年五月份我去石屏看了花腰彝,他們和我們這里的彝族還是不太一樣的,但都很美好。”
訪談的最后,小趙再次提到了“美好”,在這樣接納、強(qiáng)化、動(dòng)搖再到重塑的過(guò)程里,小趙作為一個(gè)漢族人,卻認(rèn)同起了彝族的文化身份,或許正如她所說(shuō),她是一個(gè)“精神上的彝人”。
四、結(jié)語(yǔ)
研究者認(rèn)為,研究對(duì)象之所以會(huì)形塑出這樣的文化身份,主要因?yàn)橐妥逦幕膹?qiáng)大影響力、生活環(huán)境的固有條件以及制度規(guī)則,其中,民族地區(qū)的文化教育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作為一個(gè)漢族人,小趙自小接受的教育都與少數(shù)民族息息相關(guān),彝族文化符號(hào)在教育之中逐漸深刻在了小趙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dòng)中。正是因?yàn)槊褡宓貐^(qū)的無(wú)差別民族文化教育,浸染了小趙的思想,促使其塑造出了不同于其他漢人的文化身份。除此之外,在她的生命歷程里,每一個(gè)階段遇到的不同類型的人和這些人與她形成的人際關(guān)系也是關(guān)鍵因素。
回顧整體研究,本文在研究方法與分析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者與研究對(duì)象相識(shí)多年,在研究的過(guò)程中存在經(jīng)驗(yàn)引導(dǎo)和先入為主,不利于研究的客觀性。同時(shí),研究對(duì)象在敘述過(guò)往經(jīng)歷時(shí),也可能存在自我加工或記憶模糊等情況,因此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次研究中,研究者所選取的研究對(duì)象或許只是彝區(qū)漢人中的個(gè)例,她的生活經(jīng)歷具有一定的獨(dú)特性,但這樣的研究仍然可以為有關(guān)民族文化影響和身份認(rèn)同研究提供參考,并幫助人們思考彝族地區(qū)的文化教育對(duì)文化傳播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同時(shí)為尋找推動(dòng)民族融合與民族團(tuán)結(jié)的方式提供新思路。
參考文獻(xiàn):
[1]云南統(tǒng)計(jì)年鑒[EB/OL].http://www.yn.gov.cn/.
[2]郭家驥.云南民族關(guān)系調(diào)查研究[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0.
[3]袁東升.從相交到相融:一個(gè)多民族交錯(cuò)聚居村寨族際互動(dòng)與混融的民族學(xué)探討[J].廣西民族研究,2019(3):50-58.
[4]田友誼,張迪.民族地區(qū)農(nóng)村特崗教師離職問題的敘事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1):76-82.
[5]區(qū)劃人口[EB/OL].石林彝族自治縣人民政府,2023-4-17.http://www.kmsl.gov.cn/c/2023-04-17/6624104.shtml.
朱涵婧(1999.10-),女,漢族,河南鄭州人,碩士,研究方向:家庭社會(huì)學(xué)、民族社會(huì)工作。
- 秦智的其它文章
- 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下虛擬教研室建設(shè)價(jià)值與民辦院校實(shí)踐
- “雙一流”背景下中醫(yī)藥院校管理類專業(yè)學(xué)科建設(shè)路徑探索
- 建筑院校環(huán)境設(shè)計(jì)專業(yè)形態(tài)構(gòu)成課程思政內(nèi)容創(chuàng)新研究與實(shí)踐
- 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下的高校思政教育創(chuàng)新研究
- 教育實(shí)習(xí)對(duì)小學(xué)教育專業(yè)師范生職業(yè)認(rèn)同的影響研究
- 思政理念下“水污染控制原理和工藝”課程教學(xué)改革與實(shí)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