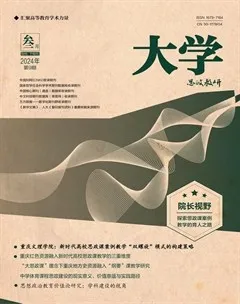學科互涉視角下高校課程思政實現的問題與對策
摘" 要:學科互涉是知識生產的重要機制,本質是知識的多元整合。以學科互涉為新視角,從課程思政的概念性學科互涉、工具性學科互涉和批判性學科互涉三個層面分析高校課程思政的內在機理。重新審視高校課程思政的實現會發現概念性學科互涉的廣度不夠,會導致專業課與思政課協同育人的效果不佳;工具性學科互涉無法深入,會導致思政元素挖掘得不深不實;學科互涉缺乏有效整合,會導致思政元素挖掘的匱乏。學科互涉視角下高校課程思政實現的對策應考慮,勾勒貿易區,以構建課程思政實現的有效場域;搭建學科互涉的連接橋梁,暢通互動和溝通;重構學科邊界,實現課程思政的育人價值。
關鍵詞:課程思政;學科邊界;學科互涉;思政元素
中圖分類號:G640"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4)09-0067-05
《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指出:“所有課程都承擔好育人責任,守好一段渠、種好責任田,使各類課程與思政課程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1]目前全國高校都非常重視課程思政建設,并不斷修正完善課程思政教學的考核體系。課程思政的實質是思政教育與專業課程教育的有機融合,更是一種知識傳授和價值培養相統一、知識育人和立德樹人相統一的整體性課程觀念。學科互涉理論發展至今已相對成熟,以學科互涉視角重新審視高校課程思政的實現過程,可以更加清晰地發現課程思政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并提供新思路,探討新對策。
一、學科互涉與高校課程思政的邏輯關系
(一)學科互涉的理解
學科的概念由來已久,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其設立的初衷是為了提高科學研究效率。學科領域是知識創新的主戰場,知識創新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基礎與先導。近年來隨著社會不斷進步以及科技的迅猛發展,學科之間也在不斷分化,邊界不斷分明,高等教育對學科的劃分更加明確,高校對不同學科類別的管理與扶持也更加細化和具體。伯頓·克拉克認為,學科急劇發展是由知識的快速增長和聚集引發的,學科不斷發展為學科分支,這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非常顯著。
學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是在20世紀初,由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在描述“跨越委員會的學科分類的研究現象”時首次使用的。在學科互涉發展的歷史上,公認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以知識的專業化和現代學科出現為標志的萌芽階段;以通識教育和學科互涉研究為標志的發展階段;作為一門學術研究領域發展的興盛階段。[2]對于學科互涉的理解,內維爾等認為是整合不同學科之間的理論與方法、資料與數據的過程,形成對復雜問題的綜合性理解。雷普克則認為學科互涉需要在學科深度、學科廣度和學科互涉整合之間取得平衡。[3]克萊恩認為劃分學科互涉不同層次的標準是學科互動的“力度和親密度”。國內學者歐陽忠明認為,學科互涉的整合是對于現有理念和知識進行批判性評價和創造性的聯合,從而形成一個新的整體或實現認知的發展。[4]也有國內學者將學科互涉分為交流型、方法型、項目型、平臺型四種模式。基于以上理解,學科互涉是指不同學科之間,為了解決同一問題,通過理論、方法和技術等的溝通和互動,實現知識多元整合的過程,并最終突破壁壘,實現問題的解決。
(二)學科互涉與課程思政
當前,我國高校課程思政實現的重點多是基于某一學科內部的科學實踐、問題分析、建設路徑等,由此衍生立足學科專業優勢對課程教學中所蘊含的思政元素進行有效、精準、全面挖掘的進一步思考,同時要與課程教學有機融合。[5]課程思政的實現需要深刻認識課程思政的內涵,尋找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探尋知識育人的融合點,從而打破學科邊界,突破傳統思維的束縛,實現知識的深度關聯與融通,探尋融合學科知識以達到育人的目的,而學科互涉強調學科之間知識的多元整合,有助于采用新的思路審視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學科知識界限及界限之間的融合與超越情況。
首先,學科互涉理論與課程思政是整體論上的統一。經過深入與持續的研究,課程思政理念已經被公認為整體課程觀視角,逐步被廣大師生和管理者所接受,這有助于破解以往思政教育過分依賴思想政治理論課,緩解“孤島化”的現實困境。[6]思政教育可與其他課程整體化、思政教育的概念外延化、思政教育突破傳統單向灌輸方式,實現現代化。[7]
學科互涉理論注重的是學科的整合,在課程思政的實現中,以整合為手段,以達成跨越學科邊界的整體目標,課程思政可以借助學科互涉理論實現高校所有學科專業的整體性聯系與融通,從而實現思政育人。學科互涉理論可以通過課程思政的實現,加快理論中國化的進程,不斷完善理論的運用和實踐,豐富理論體系,夯實理論基礎,拓展理論影響,強化理論深度,從而印證理論的時代意義,二者在整體論上是統一的。有國內學者認為,當前高校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思政元素往往會主體分化,高校應善用整體性系統思維有機整合、聚焦提煉、靈活運用課程思政元素。[8]
其次,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堅持問題導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指出,堅持問題導向是新時代高校思政工作的重點。[9]課程思政建設在當下更應該堅持問題導向,重點破解課程思政所面臨的各類困境。有國內學者認為在高校的課程思政教學中同樣需要以目標問題為導向,將其作為課程思政教學改革的重要途徑,著力推進當前高校課程思政教學改革。[10]高校課程思政的實現,應通過學科互涉的思維和方法,對知識進行整合,達成知識探究和價值育人的目標,防止出現“兩張皮”,進而解決實際問題。與此同時,學科互涉理論的研究與應用,也是以問題導向為前提的,是以不同學科之間存在的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從學科融合的視角看待實際問題,以具體概念等為基礎,探尋其中的關聯性,通過方法和理念的轉變、借用,實踐性的審思突破界限的可能,批判性考量技術和方法,從而跨越學科邊界,獲得新的解決問題的途徑,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在堅持問題導向上一致。
二、學科互涉視角下課程思政的內在機理
克萊恩認為,學科互涉的研究包含三個層次:一是概念性學科互涉,強調從多學科融合的視角探討問題的解決方式,從而實現知識整合;二是工具性學科互涉,主要通過相關概念、理念、方法和技術的簡單借用或移植,從而解決社會實際問題;三是批判性學科互涉,主要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強調跨越不同學科、項目之間的邊界,從而獲得對現實世界的整體認知。[11]本研究將聚焦以上三個層次探究學科互涉視角下課程思政實現的內在機理。
(一)課程思政的概念性學科互涉
課程思政的概念性學科互涉,即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運用多學科融合的視角分析問題,從而使各門課程與思政課協同并進、同頻共振,實現全過程、全方位育人。課程思政要求思政教育對所有課程的全覆蓋,實現與所有專業課程的相互滲透、融合,推動形成所有課程合力育人的目標,這種融合更多體現在學科廣度的拓展。課程思政的概念性學科互涉強調每個學科對現實問題提供基于自身學科特性的解讀與回應,滲透并不頻繁,極少涉及學科之間的深度交叉與有機融合,更多的是從學科自身出發,將學科自身的特點、特質、關聯點等明確出來,對跨越學科邊界的可能進行探討、研究和分析,往往是某一概念或論述的合作或交流,或是項目驅動下的簡單交叉。
(二)課程思政的工具性學科互涉
課程思政的工具性學科互涉,即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從自身學科基礎出發,借助聯系緊密的兩門或以上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基于對自身學科深度的拓展,攝取一切有利于自身發展的資源,目的是深入挖掘自身所蘊含的思政元素。課程思政的工具性學科互涉,更加強調知識的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學科發展建設進程,回答課程思政面臨的現實問題上具有解釋力和應對能力。課程思政的工具性學科互涉突出挖掘挖思政元素,推動學科間的緊密聯系和共生發展,激發內驅力,從而促進學科的積極發展。
(三)課程思政的批判性學科互涉
課程思政的批判性學科互涉,即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要跨越或重構學科邊界,以整體性認知的角度重新審視實際問題,掃清障礙,從而使思政教育有機融入課程教學全過程,實現專業知識與思政教育元素的有機關聯,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學科互涉具有批評功能,既具有創造物質價值的工具屬性,更是認識論的重構。現如今的課程思政育人模式,是育人理念的不斷創新和精進實踐,體現了高校內涵式發展的目標定位。課程思政的批判性學科互涉更加突出整合性的共建和反戰,真正實現知識的跨學科屬性,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最終形成“大思政”格局。
三、學科互涉視角下高校課程思政實現的現實困境
(一)概念性學科互涉廣度不夠:專業課程與思政課協同育人效果不佳
近年來,各高校在課程思政的建設中,基于學科戰略嘗試構建分課、分科、分層的課程思政體系。[12]但從整體效果看,由于學科之間存在壁壘,未能實現多學科的融合,尤其是在跨度較大的學科間,知識的整合存在問題,致使思政元素碎片化,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首先,學科的廣度不是要縮小學科認識論的視野,由于學科邊界的存在,單一學科知識以孤立形式存在,但在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往往要面對真實情境以及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學科的產生是源于知識分類的需要,知識是在學科之間被分離和肢解的,而現實問題也逐漸演變為多學科的、橫向延伸的、多維度的、跨國界的以及全球化的。[13]現階段,課程思政要求所有課程與思政課同向同行,但由于概念性學科互涉的廣度不夠,單一學科的視角和知識構成無法真正探尋到問題的本質和核心,對思政元素廣泛挖掘難以發揮應有的助推和指導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知識與專業課程知識,如果元素挖掘不充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知識體系容易滑入專業課知識中,這是對課程思政啟發式教學的極大干擾,容易造成由啟發式教學到灌輸式教學的境地。
其次,由于學科制度的劃分越來越具體,逐漸形成學術部落和領地,學科間的交流、溝通不暢通,缺乏完善、系統的體系構建,思政元素的挖掘無疑會在學科內部存在高度同質化的現象,最終只會形成“孤島”困境。另外在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也存在思政元素的使用過于隨意,植入課程教學生搬硬套,弱化了課程思政的學理內涵,無法產生價值引領的積極反饋。[14]這會導致很多知識孤立存在,難以建構系統的學科知識體系,學科理論自覺需要實現自身理論體系的完善,提升理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也有國外學者認為強分類學科的整合需要學者之間更緊密的互動和協作,并且整合的程度在不同類型的跨學科課程中會有不同的表現[15]。國內對于跨學科、多學科、超學科以及學科交叉等問題的研究,經歷時間短,概念性學科互涉的結果多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現,造成不同學科知識之間的流通互鑒更多呈現為機械疊加而不是有機融合,學科知識之間無法有效聯結,最終變成思政元素的粗放堆積和生搬硬套,難以真正融入學科教學體系之中。
(二)工具性學科互涉無法深入:思政元素挖掘不深不實
首先,學科深度主要是辨別問題與資源分配之間的沖突。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觀念理念的貫徹和執行往往不夠深入。課程思政的實現往往需要借助整體性的理論視角進行深入分析,如果不能明確學科定位,無法從學科深度推動工具性學科互涉的有效實施,思政元素的挖掘必然會出現不深不實的問題。
其次,工具性學科互涉無法深入實施,課程思政的實現中,隱性思政元素往往無法深入挖掘。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就學生獨立的知識庫而言,包含個體知識和公共知識兩部分,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與之相對應的是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聯系和轉化,[16]這期間往往會出現個體知識過度社會化問題,即隱性知識過度顯性化。隱性知識對學生個人的能力培養和技能訓練有著深遠的影響,進一步反映出教師的教學行為和學生的學習行為之間的聯系,從而影響教學效果。[17]石中英教授認為,個體知識公共化是一種自我反思的過程,是促使知識達成共享,以獲得價值和知識創新的過程,有利于知識的傳授。[18]當個體知識在一定的境遇下過度公共化,即隱性知識過度顯性化時,表現為可教與不可教的知識都顯性化,忽視了學生個體的個性化發展,使得課程思政對學生價值觀的培養千篇一律,造成思政育人效果的弱化。
與此同時,公共知識的被動個體化正在逐步影響教師課程思政能力,任課教師往往僅有一門學科的專業背景,對挖掘思政元素的能力不足,或是僅從自身專業背景挖掘思政元素,對專業知識的深層次的育人元素領悟不足,教師的育人方式方法單一,學生只能被動接受,無法主動探尋,更無法身臨其境與感同身受,公共知識內化為個體知識的過程往往被動地由教師的外化所代替,無法主動在實踐中學習和獲取新的隱性知識。
(三)學科互涉缺乏有效整合:思政元素的匱乏
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思政元素匱乏的問題,根本原因是知識的生產在學科互涉缺乏整合的前提下受到阻礙。吉本斯把傳統學科認知語境下的知識生產模式概括為“知識生產模式1”,把更廣闊的、跨學科的社會和經濟情境生產模式命名為“知識生產模式2”,傳統模式1生產的知識不但晦澀難懂,且更多是為了學科內部高深知識的研究而衍生和發展的,無法充分體現育人功能和育人價值。[19]新知識的生產需要一個開放的環境與適合的場域。過分強調學科邊界,阻礙不同學科知識間的流動、融通,會阻礙新知識的生產。[20]克萊恩也認為,學科化的研究無法適應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不能勝任知識生產和創新的使命。實際上,在如今高度全球化、共享化、智能化的新時代,學科體系所要提供的知識絕不再是被壟斷、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和掌握的高深知識,而是對大眾而言培養和養成自我修養的知識。
四、學科互涉視角下高校課程思政的實現路徑
(一)勾勒貿易區,構建課程思政實現的有效場域
克萊恩認為學科互涉中的貿易區,是不同學科文化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一個集合體。學科互涉在廣度上的內生需求,產生了共同的貿易區,其是兩個以上不同學科在互涉過程中形成的混合場域。學科互涉所形成的貿易機制對所屬成員自身研究范式、方法以及學術規則的生成和互動提供便利,成為有效銜接不同學科知識體系進行互涉活動的橋梁。課程思政的實現,應該充分勾勒貿易區,借助貿易機制,通過多種不同解讀問題的方式闡述同一問題,以知識多元整合替代以往的單一傳輸,從而實現價值傳遞功能。各高校應該基于不同學科專業的特色和優勢,研究制訂個性化育人目標,充分借助貿易區的場域,挖掘知識體系中蘊含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內涵,予以提煉、歸納并有機融入課程教學中。不同課程也可以通過貿易共同體的方式,探尋思政課與專業課在基本理論知識的契合點,實現思政元素的有效挖掘,推動形成“大思政”格局。
(二)搭建學科互涉的連接橋梁,暢通課程思政實現的互動和溝通
各高校在課程思政實現過程中基于自身科學視界的基礎上,加大力度在學科互涉的深度上下功夫,搭建學科互涉的橋梁,實現互動和溝通的暢通,從而加快課程思政實現的進程。首先,學科互涉的研究需要搭建學科之間深度互動和溝通的橋梁。托尼·比徹認為,基于純軟、硬科學,應用軟、硬科學的劃分,學科范圍間的界限很清晰、合理,[21]要加強課程思政實現的思想認識,增強課程思政實現的整體意識,形成知識整合的整體性認知,融入賦予學生“價值生命”的思政元素,組織和構建借助不同學科知識體系和課程思政元素的有效銜接,逐步推進到深入學科核心與本質的思想教學,實現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提升。[22]其次,由于各學科與思想政治理論學科存在學科邊界,要避免課程思政建設中,思政的學科知識體系對本學科知識體系的硬融入,造成學科知識傳授課時、學時、任務等的弱化甚至是知識替代現象的出現,搭建各學科專業與思政課同向同行、協同育人的有效橋梁。
(三)重構學科邊界,實現課程思政的育人價值
課程思政要充分實現其育人價值,必須跨越和重構學科邊界,最終有機融入課程教學之中。學科邊界存在著自身的滲透性,學科之間的劃分并不是絕對對立的關系。這種邊界滲透性只有強弱之分,并不存在純粹無滲透的學科邊界。[11]近年來跨學科研究、交叉學科研究等呼聲越來越高,意味著知識生產需要進行更為豐富和復雜的邊界活動,不但可以突破傳統領域界限和學術規訓,同時也釋放了探索新知的能量。課程思政的實現,要求基于學科邊界的客觀存在,深刻認識到學科知識之間并非絕對的非此即彼,而是基于二者差異性的基礎,使二者更好地進行有機融合。學科互涉下的重構,凸顯了當前知識邊界跨越的程度,更加要求拓展學科知識的邊界。完成學科邊界的跨越學科互涉的程度越高,能夠產生新的知識就越多、越有價值,課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才能更加深入,不同學科知識的思政元素才能匯聚,真正引領學生的價值觀養成。
參考文獻:
[1] 教育部. 關于印發《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的通知[EB/OL]. (2020-05-28)[2021-06-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 歐陽忠明. 跨溪建屋:學科互涉視閾下人力資源開發學科構建研究[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1.
[3] Repko.A.F.Interdisciplinarity research:Process and theory[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Inc,116-125.
[4] 歐陽忠明. 邊界的跨越和知識的整合[J]. 河南社會科學,2010(05):126-129.
[5] 石艷麗. 關于構建高校課程思政協同育人機制的思考[J]. 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8(10):41-43.
[6] 陳華棟. 課程思政:從理念到實踐[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17-25.
[7] 閔輝. 課程思政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育人功能[J]. 中國高等教育,2017(03):21-24.
[8] 黃寧花. 系統思維視域下高校課程思政建設的價值意蘊實、踐反思與優化路徑[J]. 高校教育管理,2022,16(05):106-115.
[9]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負責人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答記者問[EB/OL]. (2017-12-06)[2021-06-2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712/t20171206_320712.html.
[10] 趙志鳳. 基于目標問題導向的課程思政教學改革研究[J]. 黑龍江科學,2022,13(09):158-161.
[11] 克萊恩. 跨越邊界[M]. 姜智芹,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9-10.
[12] 蒲清平. 高校課程思政改革的趨勢、堵點、痛點、難點與應對策略[J]. 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21(09):105-114.
[13] 莫蘭. 復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M]. 陳一壯,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4.
[14] 張弛. 課程思政升級與深化的三維向度[J]. 思想教育研究,2020(02):93-98.
[15] 文雯. 知識視角下大學跨學科課程演進及其特點[J]. 中國大學教學,2022(04):75-82.
[16] 余文森. 個體知識與公共知識[M].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0:55.
[17] 程龍. 隱性知識過度顯性化及其救贖[J]. 全球教育展望,2015(07):31-39.
[18] 石中應. 緘默知識與教學改革[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01(03):101-108.
[19] 邁克爾·吉本斯. 知識生產的新模式[M]. 陳洪捷,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5-30.
[20] 解瑞紅. 矛盾與反常:大學學科固化的危機[J]. 江蘇高教,2014(06):80-83.
[21] 托尼·比徹. 學術部落及其領地[M]. 唐躍勤,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10.
[22] 張明進. 課程思政元素的有效挖掘與融入策略[J]. 河池學院學報,2021(04):106-110.
(責任編輯:胡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