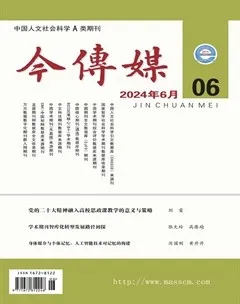田園治愈劇的審美意識探析
任春陽
摘 要: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講述了一群失意的人在云南相遇與互愈的故事。不同于青春偶像劇、古偶劇、歷史劇以及獻禮劇,該劇不再拘泥于固化的審美模式、單一愛情敘事的審美意向、傳統價值導向的審美意識,而是通過對敘事內容的創新、敘事風格與節奏的有序雜糅,以及對受眾審美心態轉變的總體預測與主流價值觀的精準融合,呈現出了一種新的田園治愈電視劇風格。本文對該劇的審美意識進行了簡要分析,探討它在敘事層面的審美意識表現,旨在為田園治愈劇的敘事與審美提供一種新的創作思路。
關鍵詞:《去有風的地方》;敘事;審美意識;主流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6-0086-04
一、引 言
隨著社會節奏的加快,觀看影視作品逐漸成為大眾放松精神娛樂的一種途徑,為人們提供了更好的精神慰藉,《去有風的地方》正是在此社會環境下應運而生。《去有風的地方》并不是首部田園治愈劇,在此之前,《萬物生靈》《山茶花開時》《森林民宿》以及《兩個人的小森林》都具有一定的田園治愈劇特點,只是這些作品并未引起受眾過多的關注,這與其敘事內容、敘事風格、審美意識傳播上的創新與融合不足,以及創作者與受眾的審美意識未產生強烈共鳴和情感互動具有一定的關系。《去有風的地方》秉承平淡真實的生活敘事理念,雜糅了田園治愈劇的敘事特點,用生活本真的力量帶給受眾不一樣的心靈治愈體驗,在眾多具有強烈審美戲劇沖突性的影視劇中脫穎而出,引發了受眾的審美共鳴。
二、敘事內容的多元化:審美模式的更新
仲呈祥先生曾指出:“比較其他文學藝術形式更多地受制于舞臺、局限于動作或囿于語言等因素,電視劇是一種講故事、講‘好故事、‘講好故事的藝術。”[1]以往對于優秀電視劇文本的評判標準為文本戲劇沖突性是否強烈,能否通過這種強烈的戲劇沖突性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從而獲得高收視率回報。隨著社會的發展,受眾對電視藝術的審美意識逐步提高,并對相對傳統的敘事手法與審美模式產生了反思,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領了電視劇文本創作中的多元化發展與審美意識創新。作為敘事節奏舒緩的田園治愈類現實題材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之所以能在眾多具有戲劇沖突性的電視劇中脫穎而出,不僅與所處的時代環境相關,還與敘事內容的多元化、突破審美模式的審美意識相關,田園式的敘事框架、群像式的主題呈現、多樣式的人物塑造,既是創作者審美意識更新下敘事內容的創新,又是受眾審美意識的轉變與提高。該劇評分能夠低開高走,也是創作者與受眾之間審美意識實現雙向互動的結果。
(一)田園式的敘事架構
敘事架構分為多種類型,多以強烈有序的矛盾沖突為主。而田園式敘事的電視劇或電影帶給受眾更多的是一種溫暖的敘事感受,主人公常常在遭遇困難或磨難時,將萬事拋諸田園之中,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找到一處美好的治愈空間。《去有風的地方》整部劇都在悲痛中得到治愈并尋找到了在生活中重新出發的力量,該劇一開始,許紅豆在失去摯友陳南星后仍堅持在酒店上班,大病一場后辭職來到云南,在記錄生活的同時一遍又一遍地懷念與摯友的曾經,最后,在一次又一次生活與時間的治愈中再次提起摯友時,變得不再那么悲傷,而是帶著祝愿更好地去生活。同樣,劇中對陳南星父母悲傷的敘事呈現也不再像以往電視劇中對失孤家庭祥林嫂般的形象刻畫,更多是一種綿長又被生活和時間治愈的敘事呈現。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這種敘事架構不僅能直擊受眾心靈,也使受眾的審美意識潛移默化地發生了改變。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不僅為受眾提供了尋找美好生活的范本,讓受眾從中汲取力量,也讓創作者與受眾之間達成了審美意識的共通。
(二)群像式的主題呈現
群像戲很早便出現在影視作品中,相對成功的作品頗多。近年來,群像戲敘事類電視劇頻頻出圈,既有《甄傳》《瑯琊榜》《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等群像敘事古裝劇,又有《覺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間》等群像敘事時代劇,還有《歡樂頌》《我在他鄉挺好的》《三十而已》《二十不惑》《閃耀的她》等都市女性群像劇等,這些不同體裁類型的群像敘事電視劇各具特色,深受受眾喜愛。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在敘事主題上并沒有延續純愛情敘事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強的審美創造性,并且敘事場景、實景更加多元化,不同人物故事的背后有著不同的敘事主題。比如,許紅豆失去摯友陳南星后來到云南,開始了自我人生意義的思考和心靈的療愈;胡有魚因不滿父親規劃自己的人生,堅守音樂夢想來到云南小鎮的酒吧中駐唱寫歌;娜娜作為網紅歌手遭到網暴后,偶然來到云南小鎮,躲避現實的喧囂;馬爺創業失敗后,為了壓制自己的創業欲望而來到云南小鎮;夏夏在浮躁的心境中找到了安定方法;謝之遙因童年經歷而選擇從大城市回鄉創業;大學生村書記小黃,一家三口分散各地助力鄉村發展;云南小鎮上的阿嬸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有著不同的思想主題,如關于思考、夢想、堅持、和解、鄉村振興等,這些不同的主題最后形成了受眾所期盼的敘事氛圍與結局。這種群像式敘事主題的呈現讓受眾感受到了更多的生活和人性的真實,也是當代社會環境下主要的審美意識中契合受眾審美期待的敘事主題之一。
(三)多樣化的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是敘事藝術的核心問題,既是一部作品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又是衡量一部作品甚至一種敘事門類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的重要標志[2]。人物塑造本身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在不同的電視劇作品中,創作者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中對于人物的塑造通常追求極致,將人性中美好或者丑惡的一面呈現到最大化,從而形成強烈的戲劇沖擊力。同時,對于現實人物的塑造,既有偏于理性的刻畫,也有偏于感性的美好呈現,而《去有風的地方》進行了人物形象感性與理性的雙重塑造,讓受眾開始從劇中人物身上尋求審美共鳴,從而實現感性與理性的動態平衡,這既符合中國影視作品中對于人物塑造的審美共識,又將當下受眾的審美需求融入其中。該劇中的每個人物都有感性的一面,但生活同樣也是現實的,感性的失去、理性的前進正是映射了當下社會環境中人們的真實生活狀態,體現出真實社會現象與思想的碰撞,從而讓電視劇人物更符合受眾的審美需求。
三、敘事風格的雜糅:審美意向的追求
如今,我國電視劇已形成了諸多不同的敘事風格,這些敘事風格是在電視劇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成熟起來的,是電視劇創作者進行風格化探索的結果。從整體來看,我國電視劇敘事風格表現出多樣化與多元化、世俗化與通俗化、雜糅性與融合性等主要特征[3]。近年來,各種類型題材的電視劇皆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突破,敘事風格越來越多樣化,創作者與受眾對于審美意識的追求呈現出雜糅局面,古裝劇從宮斗、宅斗到大女主再到群像戲,都市劇從愛情到職場再到現實的揭示;青春偶像劇從純愛風到傷痛文學,再到與懸疑、喜劇的雜糅;歷史劇從歷史名人到百姓,更有各種敘事風格元素的融合,雜糅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劇種類型,比如,2022年開年爆火的無限流穿越懸疑劇《開端》。至此,越來越多的電視劇敘事風格被呈現在熒幕上,開始走進受眾的視野中。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作為2023年的開年新劇,其治愈、偶像、地域、情感等元素平衡雜糅的敘事風格,就像一股別樣的清風吹進了受眾渴望療愈的心中,獲得了廣泛好評。
(一)治愈系的審美感受
現實題材作品的生命力不僅僅是對現實社會的客觀記錄和對個人情感的主觀抒發,更是如何正確引導和弘揚道德觀、是非觀、價值觀,如何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抒發人民美好愿望、向觀眾傳遞向善向美的正能量的一種方式[4]。以往我國具有治愈色彩的現實題材作品并不多,而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則是一部少有的治愈系現實題材作品,該劇整體敘事風格較為舒緩,沒有強烈的矛盾沖突。劇中許紅豆在經歷摯友離開后,心理遭受了很大的沖擊,于是,她選擇辭職去云南實現自己與摯友之間的旅行約定,并在“有風小院”結識了一群各有憂愁的伙伴。該劇用臺詞“風的形成與流動”比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身處相同情境的人更容易惺惺相惜,正如“有風小院”中這群“同病相憐”的平凡人的相互治愈,給予了受眾一股別樣的情感共通力;同時,這種治愈系的創作風格通過調動受眾的審美感官體驗,實現了高度互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藝術作品本身的收益與帶動現實中審美經濟的雙贏。比如,劇中所展現的云南美景,使其既獲得了較高收視率,同時也推動了云南旅游經濟的發展。
(二)地域系的民族風格
近年來,現實題材作品已成為整個電視劇市場的一股重要力量,更多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映射和再現。自2020年以來,現實題材作品層出不窮,出現了不少有關鄉村振興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更多是呈現鄉村如何振興的實際過程,較少展示現實地域的風景和生活狀態,而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是在云南小鎮進行實景拍攝,劇中的民宿也真實存在,并恰到好處地展現了云南小鎮的地域風格。近年來,回歸自然成為大眾的審美向往,但這種向往在快節奏的社會環境中難以實現。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通過鏡頭,讓受眾跟隨劇中的人物一起觀賞云南特色的地域美景、感受輕松愉悅的生活氛圍,扎染、木雕、馬場、果園、油菜花田以及當地女性的民族服飾,不僅展現了云南的地域特色,也讓受眾與劇中的阿奶、阿嬸隔空相識,詮釋了一種新的審美感受。除此之外,具有云南特色、俏皮婉轉的民謠也凸顯了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令受眾審美意識與民族意識得到了共通,地域敘事與情感共鳴完美融合。比如,該劇在拍攝宣傳片時,為了更好地展現宣傳片中的鏡頭而配以相應的音樂,音樂起,畫面出,受眾仿佛身臨其境,從而使整部劇對這種自然地域景色的記錄滿足了當代受眾的審美需求。
四、敘事發展的時代性:審美意識的轉變
格伯納等學者提出的涵化理論對“主流化”和“共鳴”進行了闡釋,揭示了大眾媒介將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加工成可以普遍共享的“符號(Symbol)”,讓大多數人對此產生強烈“共鳴”而成為“主流”[5]。正如主旋律電影的出現一樣,受眾價值觀與生活態度的轉變,催生了諸多鄉村電視劇,盡管這類電視劇展示了鄉村生活的真實面貌,但是缺少對現實生活溫情治愈一面的刻畫。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將現實生活與主流價值引導進行了較好地融合,在大眾審美觀念轉變與主流價值導向之間實現了動態平衡,獲得了受眾的青睞與好評。
(一)大眾審美觀念的滿足
誠如彭文祥教授所言,在傳統的影視藝術生產中,創作者只能憑借主觀經驗去判斷影像文本,進而將作品投入到觀看市場去接受受眾的檢驗,而在互聯網環境下,諸多大數據可以使影視藝術創作者了解用戶(粉絲)的觀看習慣和互動行為,進而更好地掌握他們的觀看需求[6]。近年來,網絡IP改編的作品,逐漸占據了影視劇的半壁江山。自2011年開始,電視劇作品從網絡文學改編而來的數量逐年遞增,網友及粉絲成為電視劇創作方向的主要影響因素,受眾愛看什么,創作者便向著哪個方向創作,比如,《甄傳》《瑯琊榜》等高口碑電視劇。而《去有風的地方》是原創劇本,既做到了對傳統文本創作的創新,又做到了對當下受眾審美的精準把握。編劇水阡墨與王雄成擅長溫情治愈的現實題材作品的創作,其中《以家人之名》這部作品的氛圍便與《去有風的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家人之名》以親情治愈敘事為主,以愛情友情為輔;《去有風的地方》則是以風景治愈、心靈敘事為主,其中穿插著友情、愛情、親情以及家國情懷,塑造出了一個個平凡鮮活的人物,這種審美敘事滿足了大眾對自然的向往、對劇中人物的情感共鳴、對生活態度的改變以及對人生理想的思考轉變,形成了滿足當下大眾審美觀念的電視劇作品。
(二)主流價值導向的融合
現實題材作品在創作時較多地融入了主流價值導向,其創作依托于現實,借助“鮮明的‘話題意識直擊大眾的敏感神經,以此保持現實題材創作的新鮮感與敏銳度”[7]。近年來,有關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話題頗受關注,相關的電視劇作品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熒幕中,比如,口碑收視雙豐收的《山海情》、真實事件改編的《大山的女兒》、農村女性拼搏創業的《幸福到萬家》以及其他有關鄉村振興的電視劇《花開山下》《山河錦繡》等,這些電視劇將國家對鄉村振興的高度重視內化為一種審美意識融入作品中,是主流價值引導與審美意識精準融合的體現。但是,審美不僅存在審美愉悅的主觀能動,還存在審美疲勞的客觀事實,同話題電視劇的頻繁創作難以持續吸引受眾注意力,容易導致同質化創作趨勢。雖然創作者在《去有風的地方》中也提及了鄉村振興的話題,未刻意將主流價值引導以一種矛盾沖突的敘事展現出來,而是通過一種幽默化的方式進行了創作。比如,在修建書屋做特色旅游的計劃實施中,村民對房屋的租金價格咬口不放、高材生謝之遙回村創業遭到父親的阻撓,該劇并未過多地刻畫這些矛盾情節,更多是以風趣幽默的片段敘事簡述矛盾過程,核心展示了矛盾解決后詼諧中透露出的溫情,同時,家國情懷的展現也以人物塑造為切入點進行敘事,這種反套路敘事既給受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給受眾帶來了審美愉悅與思想陶冶。
五、結 語
綜上所述,隨著大眾審美觀念和生活態度的轉變,人們開始愛上了慢下來的生活,促使了一些田園治愈劇的出現,但是,其數量相對較少,甚至在電影中也不常見。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向受眾展示了一種別樣的電視劇類型,也因創作的審美意識與受眾的審美意識達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獲得了受眾較高的評價。《去有風的地方》是田園治愈劇的開始,而不是巔峰,希望后期田園治愈劇的創作能加入更多元素,挖掘出更多的創作可能。
參考文獻:
[1] 何世劍,劉罛.試論中國歷史題材電視劇的“當代性”[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科學版),2016,47(4):98-102.
[2] 張蕾.略論電視劇中的人物塑造[J].當代電影,2009(9):102-104.
[3] 秦俊香.中國電視劇敘事風格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6):88-90.
[4] 劉穎.現實題材電視劇敘事新面貌[J].當代電視,2020(10):49-52.
[5] 張?.社會化媒體對家庭倫理劇的撕裂與彌合:以電視劇《都挺好》為例[J].藝海,2020(8):96-97.
[6] 彭文祥.當前網絡影視的新實踐與新美學[J].藝術百家,2018,34(1):203-208.
[7] 戴清.近年來現實題材電視劇的創作癥結[J].東岳論叢,2017,38(3):169-175.
[責任編輯: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