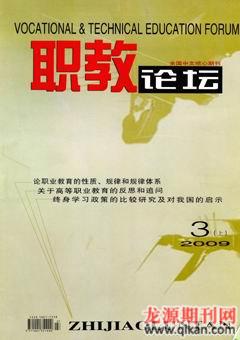論高職教育的四個準備不足
摘要:快速發展與變革中的高職教育在實踐中表現出四個準備不足:一是物質準備不足,辦學條件、建設速度遠遠滯后于規模擴張速度,難以滿足高技能人才培養需要;二是思想準備不足,不論是社會還是高職院校自身對于大眾化背景下的高職教育思想認識不充分,未能樹立大眾化的高等教育人才觀、質量觀;三是理論準備不足,對高職教育的基本理論問題缺乏研究,特別是對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問題“什么是高職教育”缺乏理論詮釋,高職教育的改革與實踐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四是政策準備不足,現有的法規政策多為宏觀指導性的,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已有的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法規政策對高職教育的特殊性缺乏考慮。
關鍵詞:高職教育;準備不足;物質準備;思想準備;理論準備;政策準備
基金項目:廣州市教育科學“十一五”重大課題“廣州市高職院校內涵發展研究”(編號:06A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查吉德(1975—),男,江西德興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高職所副研究員,副所長,主要從事高職教育研究。
中圖分類號:G71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7518-(2009)07-0021-03
1999年國家實施高校擴招政策后,我國高等教育迅速進入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特別是高職教育出現了超常規發展態勢。正如謝維和教授所言,這種態勢十分令人鼓舞,因為這為大量的適齡青年開辟了就學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同時也不免引起人們擔心,畢竟我們對進行規模這樣大的擴招在物質上和思想上的準備都還不充分。[1]作為中國高等教育擴招主力軍的高職教育,這兩方面準備不足的問題尤其突出。另外,由于高職教育在我國還屬于新生事物,只有20幾年的發展歷史,相應的理論與政策也準備不充分。
一、物質準備不足
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38所辦學條件“黃牌”院校,其中有34所是高職院校,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高職院校整體辦學條件狀況令人擔憂。這幾年高職院校規模擴張速度非常迅速,招生數由1998年的430492人增至2006年的2929676人,增長了580.54%;在校生數由1998年的1174117萬人增至2006年7905046萬人,增長了573.28%,[2]但相應的辦學經費卻并沒有同步增長。正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張堯學司長所言,投入額度與發展速度反差大,增加投入遠遠跟不上發展的實際需要,辦學條件建設遠遠落后于擴招速度,難以滿足擴招對教育資源的需求。[3]換句話說,高職教育整體上對于大規模擴招在物質上并沒有作好充分準備,尤其是辦學經費投入嚴重不足,為了獲得辦學經費,學校又不得不擴大招生規模以獲得更多的學費收入。以國家第一批、第二批示范性建設院校為例,作為中國最好的70所高職院校,三年平均政府撥款占總收入的46.21%,學費占42.15%。如果除去1所民辦學校,69所公辦院校三年平均政府撥款占總收入的比例為46.86%,學費占41.66%。[4]可見,即使是公辦高職院校仍有相當一部分辦學經費來自學生的學費。雖然這一平均數表明政府投入依然是占大部分,但平均數掩蓋了學校間的差異,事實上有相當一部分高職院校的大部分辦學經費來自學費收入。據對69所公辦示范性建設院校的統計,有3所示范性建設學校學費收入占到經費總收入的70-80%,有6所學校學費收入占60-70%,有10所學校學費收入占50-60%。
累計有19所示范性建設院校其學費收入占到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見表1) 公辦示范性建設院校政府投入尚且如此,那些非示范性建設院校、民辦高職院校的經費投入更是不容樂觀。可以想象,一所公辦學校要靠學費維持辦學,它將很少有經費投入到辦學條件建設當中去,包括校內實訓室建設、師資隊伍建設、圖書資料建設,等等。
另外,高職院校自身發展基礎與人才培養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辦學條件的不足。一是高職院校由于辦學歷史相對較短,辦學條件的積累不足;二是高職院校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其專業多數是面向市場的新興專業,引進教師有一定難度,特別是“雙師型”教師,加上專業變化周期較短,教師隊伍建設難度較大;三是作為以高技能人才培養為目標的高職院校,其對辦學條件的要求較高,特別是設備淘汰更新周期較短,從而增加了辦學成本。
二、思想準備不足
高等教育大眾化不僅是一個數量指標,它更多的是一種高等教育思想觀念的變化,要求突破精英階段的高等教育思維模式,樹立大眾化的高等教育人才觀、學生觀、質量觀、發展觀,等等。然而,面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
挑戰,不論是社會還是高職院校自身在思想觀念上都顯得準備不足。

首先,社會對高職教育的思想認識準備不足。當前國家賦予高職教育前所未有的戰略地位,并委以前所未有的社會使命,要求高職教育“為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服務”、“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為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職業能力服務”,為“把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提升我國綜合國力、構建和諧社會”服務。然而,社會各界對國家給予高職教育如此高的戰略地位,委以如此重大的社會責任認識不足。正如我國高等教育專家潘懋元先生所言,高職教育的戰略目標與戰術措施矛盾,政策措施不配套,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低投入,高收費;二是招生錄取,先本后專;三是錄用人才,學歷劃線;四是院校地位,本正專副。[5]第一、二、四點體現了政府對高職教育思想認識不足,第三點體現了社會用人單位對高職教育認識不足,這種認識正是精英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表現,延用精英高等教育質量標準來評價高職教育,視高職教育為“三流”的高等教育,并在政策上、在資金投入上、在人才選拔上自然向本科院校傾斜。因此,當前不論是政府決策部門還是用人單位依然沒有樹立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和人才觀,對于新生事物——高職教育在思想認識上缺乏準備。這種認識給高職教育的發展帶來不良影響,使其陷入“政府投入不足—辦學條件差——人才培養質量差——生源質量差——人才培養質量差—畢業生就業率或就業質量低——政府不愿投入……”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的發展困境之中。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導致辦學條件差,從而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由于人才培養質量差,進而影響了考生的選擇,導致生源質量差,生源質量差反過來又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人才培養質量差又影響了社會用人單位的選擇,造成畢業生就業率低,就業質量差,由此進一步影響政府投資的積極性。(見圖1)

其次,高職院校自身的思想認識準備不足。這種認識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高職院校缺乏正確的辦學定位。受傳統精英教育和學科教育的影響,一些高職院校熱衷于升本科,熱衷于學科教育,而對于高職的類型地位缺乏充分的認識,沒有認識到作為一種新的高等教育類型,高職院校應有不同的發展軌跡,沒有認識到高職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和地位,沒有認識到任何一種教育都能辦出一流水平,都能贏得社會的理解和尊重。二是沒有樹立正確的人才觀。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生源的素質發生了很大變化,絕大多數高職生的文化基礎非常差,但教師往往以傳統“大學生”的要求嚴格要求學生,但現實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往往會采取“放棄”的態度,即感覺高職學生是“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很少有教師反省,不是學生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人才觀出了問題,以及按這種人才觀開展的教學實踐出了問題。三是教師對自身的角色缺乏認同感。由于當下高職院校的社會地位普遍較低,還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理解和尊重,從而造成高職院校教師對自身的角色地位普遍缺乏認同感,甚至有種自卑感。沒有認同感,教師也就不可能熱愛這份職業,充其量將之視為謀生的手段。不熱愛這份職業自然對工作也就缺乏熱情,不會將之視為自己的人生事業而不懈追求并力求做到最好。[6]
三、理論準備不足
中國高職教育的發展歷史只有20幾年,快速發展的歷史更是非常短暫,相比基礎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職教育研究不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水平都非常薄弱。特別是當前高職教育正處于一個大發展、大變革時期,迫切需要高職教育理論的指導,然而事實上這方面的理論非常匱乏,尤其是高職教育的基本理論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甚至是整個職業教育的基本理論也沒有得到有效詮釋。徐國慶博士將這種狀況視為職業教育理論貧困。[7]原國家委職業技術教育司司長孟廣平認為,職業技術教育的根本理論問題很需要研究,職業技術教育搞了這么多年,但在理論上太弱,沒有理論支持。[8]原國家教委副主任王明達也認為,由于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比較晚,理論研究薄弱,對一些基本問題展開研究討論很有必要。[9]由于缺乏基本理論的指導,高職教育的改革與實踐只能不斷摸索、不斷“試誤”,這種摸索和“試誤”必然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使高職教育的發展充滿了變數和不確定性。這種變數和不確定性有時會付出慘痛的代價(這方面我國已有過不少教訓),因為教育是面對人的一種實踐活動,她容不得我們“反復”,她不是生產“產品”,失敗了還可以回流再修正或者按次品處理;她也不是物理實驗,失敗了再來。因此,任何一項教育改革都應該是非常慎重的。
當前影響高職教育改革與實踐比較突出的基本理論問題就是什么是高職教育?這個問題是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問題。雖然當前理論界或者政府有關文件基本認為高職教育是一種高等教育類型。既然是一種新的類型,那它就必須有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當下關于高職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問題并不明晰。有學者認為高職姓“職”、名“高”,或有學者認為高職姓“高”、名“職”,但不論是姓什么,還是沒有解決其基本內涵與外延的問題。到底“高”是其內涵,還是“職”是其“內涵”?如果“高”是其內涵,那又“高”到什么程度?那“職”又是什么?是外延,如果是外延,那又延到什么范圍?如果“職”是內涵,那它又“職”到什么程度?“高”又是什么?是外延,那又延到什么范圍?因此,即便有些學者認為找到了什么是高職教育,但筆者認為已有觀點對什么是高職的解釋是經不起追問的。而這個問題作為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問題,對高職教育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充分解決,那我們的高職教育改革與實踐就不可能清楚為什么出發?到哪里去?
四、政策準備不足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為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強了對職業教育立法及政策制定工作,但宏觀層面的原則性政策、法規多,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不足,如經費投入、校企合作、先培訓后就業、職業資格證書等方面的政策依然不完善。如1996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對職業教育體系、實施和保障條件作了規定,明確了高等職業教育的法律地位,但該法是精英教育階段的產物,對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和新問題缺乏預見性,而且該法總體上偏重于中等職業教育,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特殊性缺乏考慮。另外,對于企業和政府在發展職業教育中的責任雖有所規定,但不夠具體,缺乏實施細則,對于不遵守有關條款的情況,缺乏補救措施。如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企業、事業組織應當接納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學生和教師實習;對上崗實習的,應當給予適當的勞動報酬。然而,對于如果不接納學生實習的企業或事業組織該如何處理則沒有相應的規定。正因為如此,該法自實施以來,沒有發生一起個人或企事業單位因沒有遵守《職業教育法》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倒不是企業做得有多好,而是缺乏法律措施監督企業承擔應有的職業教育責任和義務。又如《職業教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本地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本部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職業學校舉辦者應當按照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足額撥付職業教育經費。各級人民政府、國務院有關部門用于舉辦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財政性經費應當逐步增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挪用、克扣職業教育的經費。然而,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不履行經費義務則沒有相應的處罰措施,由此,導致職業院校經費普遍得不到保障,多數地方政府或行業部門未能按生均進行撥款,有些學校不得不通過擴大招生,增加學費收入來獲取辦學經費。另外,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律政策對高職教育也有匡范作用,但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更多地指向普通高等教育,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特殊性也缺乏考慮。如1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對高等教育基本制度、高等學校的設立、高等學校的組織和活動、高等學校教師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高等學校的學生、高等教育投入和條件保障等作了法律規定,但對高職教育的校企合作、職業資格證書等等內容都缺乏考慮。
可見,針對職業教育的法律政策和針對高等教育的法律政策對于高職教育的特殊性均缺乏考慮,而且這些政策更多的是宏觀指導性的、原則性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特別是對于地方政府、企業的責任缺乏法律政策的監督,使一些法律政策難以落實。因此,要促進高職教育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相應的法規、政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轉引自:王洪才.大眾化高等教育論——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文化——個性向度研究[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42-44.
[2]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3]轉引自:王洪才.大眾化高等教育論——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文化——個性向度研究[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序1-2.
[4]查吉德.國家示范性建設高等職業院校辦學狀態統計分析[J].職教論壇,2007,(11)上.
[5]潘懋元.弘揚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探索高職發展中的若干問題,轉引自: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研究中心.溯源與創新——弘揚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推進新時期高職特色發展[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查吉德.高等職業教育三論[J].廣東師范學院學報,2008,(9).
[7]徐國慶.職業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
[8]歐陽河等.職業教育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211.
[9]歐陽河等.職業教育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210.
責任編輯:肖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