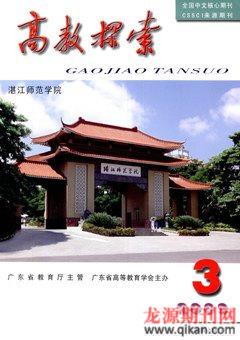“我-你”世界:“主體間性”視域下的大學師生溝通取向
龔怡祖 朱園園
摘 要:主體性和主體間性都是有關主體屬性的哲學認識,由主體性向主體間性轉變體現了教育主體觀的深刻嬗變,推動著師生關系由對象化領域向交往領域挺進。其中,“類主體”思想奠定了新型教育主體觀,“主體間交往”提供了師生溝通的實踐機制,“我-你”世界勾勒出師生溝通的現代取向。為了突破對象化語境,邁入“我-你”世界的殿堂,教育主體需要彰顯溝通德性、調整溝通姿態、拓展溝通疆域:共樹“師道”和“學道”兩種尊嚴,將工具溝通姿態升華為心靈溝通姿態,由片面的知識傳授擴展為完整的“生活世界”。
關鍵詞:大學師生溝通;類主體關系;主體間性;交往機制;“我-你”世界
師生關系是教育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關系,一切教育行為及結果最終要在師生關系中實現并獲得。然而,人們卻觀察到當下大學教育的一個普遍現象:“教師與學生的接觸日益減少,師生關系日益疏離”[1]。顧明遠教授指出:“優良的師生關系是一種巨大的教育力量,也是一種珍貴的教育資源。”[2]金生鈜也認為,“師生關系是教育活動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就是教育本身表現的方式”[3]。而在優良師生關系的滋育中,如何進行溝通是一個重要的命題。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學師生溝通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方式也發生著深刻的變革。
一、教育主體觀的深刻嬗變:由主體性向主體間性飛越
研究師生關系,離不開教育主體觀的問題。主體性和主體間性都是有關主體屬性的哲學認識,它們分屬不同時代、不同哲學思想指導下的主體認識范疇。由“主體性”的主體屬性認識發展到“主體間性”的主體屬性認識,意味著人類社會的主體觀實現了重大飛越。
1. 個人主體性之“黃昏臨近”
馬克思曾提出,人的“主體性”發展要經歷三個歷史階段,即人的依賴關系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及其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基礎之上的自由個性階段。[4]這說明,馬克思相信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狀況是制約人的主體性發展的現實因素。人類社會早期,生產力不發達,人作為“主體”并沒有太多的自由,基本上處于對自然和對群體的依賴關系階段;進入工業社會以后,生產力明顯提高,科學技術的力量開始無往而不勝,人憑借物質力量享有了越來越多的支配自然的自由和獨立于群體的個性,實現了渴望已久的“主體性”。然而,在工業文明“物化本性”的驅使下,自然和世界日益被視作科學技術改造的對象和實現人類目的的工具,“主體性”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占有性人格,占有式個人主義日漸膨脹:人越來越陷入了唯我論,人與自然、他人的關系也因此出現了危機。人與自然的關系失衡,使人自身的自然生存環境受到破壞,其生存基礎已不再牢固如往昔;人與他人的關系失衡,使人們陷入了過度的緊張、競爭和對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際交往準則像毒液一樣在社會機體里蔓延。隨著個人自我中心傾向愈演愈烈,“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日漸擴大,個體越來越走向‘封閉的自我”[5]。恰如美國哲學家弗萊德·R·多爾邁(Fred R.Dallmary)所說,“主體性的觀念正在喪失它的力量……主體性正在衰落”[6]。
曾幾何時,人類依靠自己的努力,使人的“主體性”登上了馬克思所預言的第二個階段,只是還沒有來得及自我陶醉,這種“主體性”就已經接近極限了。
2.“主體間性”思想之“朝陽浮現”
在“主體性”走向衰落和人類交往出現危機的同時,一些杰出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開始思考人類認識主體問題的新路徑,由此催生了從占有式個人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從單子式個人主體到類主體的重大觀念革命。這一觀念的變革,宛如一輪旭日噴薄而出,適應了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當代西方哲學家中,最早提出應該從“主體性哲學”走向“主體間性哲學”的人,是現象學的創立者、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Edmund Husserl)。
現象學研究人的意識是怎樣認識客觀存在的。胡塞爾晚年針對人們對現象學的批評,同時也為了消解“人的主體性悖論”、擺脫主體論中的唯我論傾向,提出了“主體間性”理論,探討唯我主體向交互主體過渡的問題,即一個主體怎樣與另一個完整的主體相互作用、共同運作。他認為,意識經驗的內容既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而是與二者相關的意向性結構。“他人”的存在通過移情和共現的方法,可以被先驗地構造出來;如果將“自我”與“他我”的主觀性都置于“主觀間共同性”之中去對待,就可以將每一個“自我”所感知的世界作為“大家的世界”來構造。[7]如此一來,“我”在特殊視界內所知覺的對象也就成為其他人同樣可以知覺的對象;對于“我”來說是存在著的客觀性,也就成為對于其他人來說同樣也是存在著的客觀性。胡塞爾就這樣消解了“唯我主體”的獨斷境地,把“主體性”改造為“主體間性”,使他的現象學理論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
跳出純思辨的哲學解釋學視野,將“主體間性”與現實世界的內在發展力量聯系起來思考,“主體間性”毫無疑問是一種當代觀念,它并不是某種先在的意識或“關系質”一直在等待著人類去發現它,而不過是人類對自然、他人、自我及其相互關系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或不得不發生變化所致。影響這種看法發生變化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與信息社會所創造出來的“社會共同生產能力”有關,在某種程度上與當代人對于“全面發展”要求的迫切程度在提高也有關。
“主體間性”思想的出現,使馬克思所預言的第三個“主體性”階段初露端倪。
3. “主體間性”思想的教育價值
在大多數認同“主體間性”思想的教育學家眼里,“主體間性”是一種有別于“主體性”的、新的主體屬性認識,它其實就是一種具有“交互”功能的主體性,或者說是主體間的交互關系規范。過去,在“主體性”概念的規引下,教育主體屬性是指個人作為主體并且在他的對象化活動方式中與其他人或物所形成的、以自身占據雙方關系中的中心或主導地位的“我-它”型關聯性意識。現在,由“主體間性”所表征的教育主體屬性,是指個人之間以主體與主體的對等身份發生關系,并且在其交往活動方式中,以雙方共同占據中心或主導地位為基礎的“我-你”型關聯性意識。這種有關教育主體屬性的認識,強調交往關系中的雙方均具有主體性,注重平等的互動與互補,主張以理解為目的。
“主體間性”概念的建立,極大地否定了建立在對象化活動基礎上的自我主體性,不僅確證了教育主體之間應當是一種平等的交往關系,而且極大地擴大了不同的教育主體實踐活動的范圍。教育主體(教師)與教育主體(學生)之間通過相互尊重的思想交流與交鋒,共同分享彼此的觀點與經驗,不但可以在各個學科和專業領域實現相互間的無礙交流,完成視域的融合與提升,達到和諧的人際關系境界,而且每一個受教育的個體在與教師的平等交往中,可以更準確、更清晰、更立體地形成相對于他人的那一個“自我”。
對于教育理論來說,如果將“主體間性”看作一種先在的獨立關系,那它就是玄虛的,教育主體就會被它所眩暈;但是如果將它看作是由于人深化了對自我以及對周圍世界的認識而得到的一種理論概括,那它就是有用的,就可以為教育者所利用。對于教育理論的發展來說,“主體間性”思想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它為教育主體理論提供了新的哲學范式和方法論原則。
二、主體間交往:現代師生溝通的實踐取向
哲學關注的往往是永恒的世界和生活的基礎問題,但并不是生活本身。哲學只有誠心誠意地回歸生活,才能夠生根、開花、結果。教育領域是“主體間性”思想走出哲學領域、向生活世界進軍的一個重要實際應用領域,它也因此而脫下了形而上的純思辨外衣,得到了哲學領域所不能提供的社會實踐土壤,“使先驗意識回到生活世界的實踐中并呈現出來”[8],并且對當代師生關系的變革產生了一定影響。
1.“類主體”關系勾勒出新型教育主體觀
以往的各種主體性教育教學理論,在解釋教育活動中的師生關系時都沒有能夠超出“主客關系”的框架。無論是“教師中心論”還是“學生中心論”,也無論是單主體論還是雙主體論,它們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將教育主體看作單子式的主體。單子式主體的最大特點,在于它是一種相對于客體而存在的主體,它不能夠離開客體而獨自存在。也就是說,在單子主體的另一面只能看到客體,不可能看到其他的單子主體。因此,單子式主體之間不存在“我-你”性質的交往邏輯基礎,無論它們如何努力,最終還是要回到“我-它”性質的對象化關系中去,注定走不出這一惡性循環的困境。
在揚棄傳統的單子式主體理論的基礎上,有些教育研究者提出了“類主體”概念。[9]“類主體”概念舍棄了傳統教學過程中的主客關系框架,以一種對教育主體的全新理解,顛覆了以往的教育主體觀。它在解釋教育活動中的師生關系時,不再簡單地把雙方看作傳統的單子式主體,而是視為一種“類主體”。類主體雖然也是個人主體,但是這種個體“具有類本質”[10],而類本質恰恰是“主體間性”的基本特征。由于類本質或主體間性是單子式主體所不具有的,這就構成了師生之間各將對方視為“同類”的交往邏輯機制,同時從理論上抽掉了“對象化行為”在師生關系中的合法性基礎。在“類主體”的行為世界里,教育教學活動是在“我-你”主體不可或缺、不能分離、相互吸引、相互完善的關系中進行的,“每一方只有在它與另一方的聯系中才能獲得它自己的規定性,此一方只有反映了彼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11]。只要有一方主體破壞了“主體間性”這種交往邏輯,另一方主體就有淪于被客體化、被對象化境地的危險,教育教學活動就會發生扭曲,教育的本真意義就會喪失。
2.“主體間交往”提供了師生溝通的實踐機制
教育教學活動是一種以“促進”學生的身心發展為目的的社會實踐活動,可是,誰來促進?怎么促進?只要師生進入了教育教學活動,他們就會本然地成為“類主體”,就能本能地產生“主體間性”嗎?這就進一步涉及了新的教育主體觀還必須解決實踐機制的問題,即主體理論如何向溝通實踐轉化并推進。
不能否認師生關系是一對矛盾,“主體間性”只是師生之間的一種潛在的主體屬性,正常情況下它只是處于一種“被激發態”,能否被激發,則取決于教育實踐機制①。同樣一群師生,采取不同的教育實踐方式去激發其“主體間性”,其結果可能呈“陽性”,也可能呈“陰性”。注重“交往”功能的教育實踐觀認為,只有當師生都把教育教學視為雙方互為主體的一種交往活動的時候,他們之間才能夠結成“類主體”關系,而體現類本質的“主體間性”才會現身。所以,在教育教學活動中,教育主體是否具有平等交往意識,是刺激主體間性“分泌”的重要“激素”; 教育主體是否建立了平等交往實踐方式,是師生能否生成“類主體關系”的關鍵機制。教育是一種源于精神內部的活動,只有當具有交往特質的溝通行為在師生之間真正發生時,教育教學活動的雙方才得以共同進入一種屬于人的存在形態,為他們從主體性姿態跨越到“主體間性”姿態搭建起橋梁。
“主體間交往”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教育溝通實踐機制,它賦予并規定了師生溝通的新內涵、新特質、新形式、新方向,只承認在具有交往特質的溝通行為中,師生才有可能締造思維活躍、心理相容、相互接納的氛圍,產生精神相遇的感覺,既真誠地把對方當作知己從而充分地去理解對方,又敢于與對方展開坦率的思想交鋒與學術交鋒,在交鋒的過程中加深對知識和問題的理解,共同達致對客觀世界之規律與主觀世界之意義的本真領悟。
三、突破對象化語境:構建師生溝通的“我-你”世界
“溝通”與“交往”在英、德等語言里幾乎沒有區別,它們在本文中也只具有修辭意義上的差別。在傳統的師生交往關系中,中國人雖然也提倡尊師愛生,但教師常常不經意地進入居高臨下的位置,所謂耳提面命也;學生也常常不由自主地進入亦步亦趨的狀態,所謂“上所施,下所效”也。雙方身不由己地墜入“主-客”關系怪圈和對象化活動的語境之中。師生關系要想打破這種宿命的結局,教師必須首先放下身段,以融入情感的交往姿態去與學生溝通;學生也必須挺直腰板,以謙恭但不膽怯的交往姿態去與教師溝通。如此,雙方才有可能邁進“我-你”世界的殿堂。
1. 彰顯溝通德性:共樹“師道”和“學道”兩種尊嚴
在大學師生關系中,需要倡導兩種溝通德性——“師道尊嚴”和“學道尊嚴”。教育固然需要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但也不能缺少“師道”與“學道”的尊嚴。《尚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12]可見,師道尊嚴古已有之,但觀其內涵,與今人之理解懸殊已甚遠。不過,所幸歷史上還有韓愈。韓愈作為教育思想家,有兩篇流傳千古的教育論文。一篇《師說》,顯然是講師道尊嚴的;一篇《進學解》,其實就是講學道尊嚴的。這兩篇文章對中國教育思想的發展影響頗深:“師道尊嚴”彰顯著教師的職業責任感與道德自律水平,為師不正、治學不嚴,教師何以傳道、授業、解惑、垂范?學生又怎能服膺教師?“學道尊嚴”弘揚的是學生的學業責任感與道德自律水平,求知不誠,為學不實,學生何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教師又怎能順利地與這樣的學生溝通?兩種尊嚴代表了不同主體在教育教學活動中的自覺與良知,是雙方希望和要求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建立共居主體地位這樣一種平等交往關系的“心靈契約”和“法意表示”,是“我-你”理解世界的形成前提。兩種尊嚴都是師生交往關系中不可缺少的,只強調其中的一種是片面的。教師教得再明白,學生就是不明白,教學還是沒有成功。在師生之間,如果有了“師道尊嚴”,又有了“學道尊嚴”,就能夠形成教育主體之間既有自尊的張力、又有他尊的引力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教育教學局面,使“主體間性”得到淋漓盡致的揮灑。
2. 調整溝通姿態:由晦澀的工具溝通邁向明亮的心靈溝通
師生在教育教學活動中不僅應該有尊嚴地進行交往,還應該做到用真話而不是假話來進行溝通,用體會他人而不是分析他人的方法來理解對方。溝通行為的首要特質是真誠性,溝通中不應該有特權的地盤——即不應當允許只對單方面具有約束力的交往規范存在。建立在功利動機基礎上的溝通態度在教育里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有價值的教育交往。真誠性是人的一種珍貴情感,薩特將這種情感意識看作是“理解世界的某種方式”,基爾凱郭爾甚至把“融合于生活的情感體驗”看作是“正確理解對象和自我的惟一途徑”。哈貝馬斯則認為,在溝通活動中,交往者一般需要預設三種有效性條件,即真理性、真誠性及正當性[13],顯然他也是非常強調真誠的重要性。的確,一旦功利心被帶入教育交往過程,溝通就被異化了,溝通的真誠性和效果也就隨之大打折扣,交往雙方無形中會受到某種心理暗示,感受到某種不公平或強制性的心理壓力,甚至感受到被人“算計”了。這就是為什么生活中城府太深的人,別人會害怕甚至拒絕與其溝通。現實中,具有不良溝通意識或習慣的教育者,只有堅決調整溝通姿態,重建真誠性,由偏狹晦澀的工具溝通世界向寬敞明亮的心靈溝通世界邁進,才有可能被學生重新接受,進而登堂入室觸摸到他們的心靈,實現其對學生的精神熏陶和人格感染作用。
3. 拓展溝通疆域:由片面的知識傳授擴展到完整的“生活世界”
知識與生活相比,生活是第一性的。首先,生活規定著人對知識的態度和追求;之后,知識又對人的生活態度和追求產生反作用。人的成長,歸根到底是在其生活世界中實現的。所以許多教育家才堅持認為,教育的任務在于它“是直面人的生命、提高人的生命、為了人的生命質量而進行的社會活動,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中最體現生命關懷的一種事業”[14]。如此看來,教學過程就不僅僅是一個掌握知識、發展智慧的認知過程,而且必須是一個“完整的人”的生成過程,是教學主體雙方從思想、價值、人格、個性等諸多方面運用和發揮自我,進行“創造性的教”與“創造性的學”的特殊交往過程——“雙方各自的訴求與實踐構成了教學活動的現實內容,建構著充滿教育性、探索性和創造性的教學場景,不斷地改變著教學的進程、方式和結果,為大學創造著知識深化與教學深化的機遇,指引著大學教學活動的未來發展方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