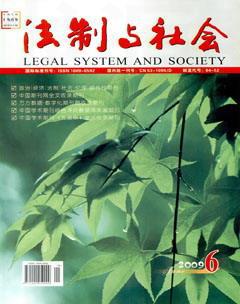關于人身保險利益原則適用方式的探討
徐 彬 盧 偉
摘要人身保險利益是為實現預防賭博和道德風險而設立的制度,其在保險業健康有序的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在適用中,無論是英美法系采用的利益主義原則,還是大陸法系的同意主義原則總顯得捉襟見肘,無法應付日益復雜多變的社會和人身保險業發展需要。本文擬從分析利益主義,同意主義和我國割裂的折中主義入手,提出統一的折中主義適用方式。
關鍵詞利益主義同意主義割裂折中主義統一折中主義人身保險利益
中圖分類號:D922.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6-096-02
人身保險利益自產生那一天起就擔負著確保保險制度健康發展,遏止不良因素發生,保護被保險人的生命健康的功能。人身保險利益的種類表現為兩種:利益(人身上之經濟利益、法定關系)和被保險人同意。根據采用對利益種類選擇的不同產生了兩種適用原則:人身保險利益原則和同意主義原則。
一、域外現有保險立法關于人身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
(一)利益主義
英國《人身保險法》規定:任何人或團體不得以無任何利益關系的他人之生命或其他危險投保,也不得以賭博為目的加入保險,否則,違反本法規定而訂立的保險合同一律無效。為確保這一制度得以順利實施,英國對人身保險利益適用采用了嚴格的金錢利益原則,即其不能僅是精神利益或者期待利益。在英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主要表現為:法律規定的人身保險利益和約定的適法的人身保險利益。
法定的人身保險利益在英國有兩種:第一,以自己的生命和身體為保險標的。第二,配偶。約定的人身保險利益主要體現為:第一,雇主與雇員;第二,共同債務人;第三,合伙人;第四,具有金錢利益關系的父母與子女之間。
英國對人身保險利益的適用采取了直接的利益主義原則,且以嚴格金錢主義加以限制,為防控道德風險的發生,可謂用心良苦,但英國保險法的規定卻無法回避一廂情愿之嫌,拿自己生命做賭注的客觀存在,離婚的時有發生,對親情的經濟化衡量都使得保險業的發展處處掣肘,即沒有實現真正意義的防控道德風險的功能,而同時又阻礙了保險業的發展。
美國雖和英國同屬于一個法系,但美國并沒有繼承英國保險法傳統,美國許多州放棄了英國嚴格金錢主義原則,在對人身保險利益的范圍認定上更人性化、合理化。美國對于人身保險利益的規定不僅包含了以嚴格的金錢利益為基礎的保險利益,而且還包括能為一般人能夠認可的合理期待,甚而至于感情關系。《加利福尼亞保險法》、《紐約保險法》及美國1943年《保險法》都對此做了相關規定。
(二)同意主義
同意主義適用原則是大陸法系國家普遍采用的原則。即判斷是否具有保險利益的標準是看是否取得了被保險人的同意。這一原則看似不負責任,其實,同意權并非憑空產生的,同意權仍然是基于保險利益而產生的權利,而這正是基于:“任何人對于自己的生命或身體具有無限的保險利益”的法律確認。
現行法國保險法對就他人生命訂立的生命保險合同規定如下:由第三人訂立之以被保險人的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保險合同,未經被保險人以載有一次性給付保險金額之書面表示同意,否則無效。德國最初《保險法》和現行的《德國保險合同法》159條第2款對此也做了相關規定,可見德國曾是兼用了人身保險利益和同意主義兩種原則。
現行日本《商法》第647條規定:“規定以第三人的死亡支付一定金額的保險契約必須經該第三人同意。”明確了生命保險合同應以是否經過被保險人同意作為合同是否有效的評判標準。但被保險人為保險金額的受領人時,不在此限。”韓國《商法》第731條也有類似規定,可見,被保險人的同意在日韓也是保險利益產生的唯一依據。
二、我國《保險法》對于人身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割裂的折中主義
2003年實行的我國《保險法》第12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第56條第1款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條件的合同,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金額的,合同無效。”第53條規定具有保險利益的主體有:第一,本人;第二,配偶、子女、父母;第三,與投保人有撫養、贍養或撫養關系的家庭其他成員、近親屬;第四,經過被保險人同意而為其訂立保險合同的,視為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同時我國《保險法》第61條規定:“人身保險的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被保險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由其監護人指定受益人。”該法第63條規定:“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可以變更受益人并書面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收到變更受益人的書面通知后,應當在保險單上批注。投報人變更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由此可見我國在人身保險利益的適用上是兩種方式并存的,其采用的是割裂的折中主義原則,而對于投保人的這種區分規定是不合理的,本法53條前三款的規定僅需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即可,沒有體現對被保險人自己對自己生命健康權處分的尊重,因為任何人只對自己具有無限的權利,即便直系血親亦無權處分另外一個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因此作為投保人都應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而本法53條最后1款,第61條、62條的規定又過于寬泛,這樣投保人、受益人完全可以通過強迫,賄買等方式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這種規定同樣無法阻止道德風險的發生。
三、關于人身保險利益原則適用方法的評析
(一)對利益主義的評析
利益原則中,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存在的特定利益關系是投保人取得以被保險人的生命和身體作為保險標的進行投保的必備的法定要件;而且不論何種人身保險合同(意外傷害保險合同,健康保險合同和人壽保險合同等)皆以“利益主義原則”作為保險利益產生的判斷依據。這種單一的“利益主義原則”雖然較好地體現出了“保險的宗旨在填補損失,”但無論是英國的嚴格金錢主義原則還是美國關于人身保險利益較為寬泛的規定,都是對親情血緣關系百分百良性發展的肯定,都是一廂情愿的通過現狀對未來血緣親情關系穩定持續的推定,而事實上夫妻離婚,父子離心,親朋反目者比比皆是,且其忽略了被保險人自身的存在。忽視了被保險人對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所享有的排他的人身權利,因此,單純的采用人身保險利益原則顯然剝奪了這種應該專屬于被保險人的人格身份權的處分權利,這不僅在保險立法上形成一個漏洞,也造成保險實踐中被保險人對自己的生命不能主動加以保護的不良后果,因為僅以某種特定關系的存在就確認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人身保險利益,不會發生道德風險,顯然是完全客觀判斷的結果,而這顯然不能用來判斷以自然感情的為基礎的姻親關系。如配偶一方以他方為被保險人投保后,殺害他方的案件時有發生。
(二)對同意主義的評析
大陸法系國家所采取的“同意主義原則”與英美法系國家的“利益主義原則”相對。英美法系國家旨在通過法律對利益關系的確定使保險利益能充分體現出保險的補償與保障功能,而大陸法系國家則基于如下原因不采用人身保險利益原則:第一,保險利益為特定人對保險標的關系,且保險實踐中多以此作為確定保險金額的尺度,但基于生命無價,此原則無法適用。第二,適用保險利益原則使被保險人的生命和身體安全掌控于他人之手,顯然是對天賦人權的諷刺。第三,同意主義原則本身即是基于保險利益而產生,其在否定人身保險利益適用制度的同時,并未否認人身保險利益的存在,而更是對人身保險利益的一種尊重。同意主義原則認為:被保險人的同意是對其人格身份權利經由客觀分析,主觀判斷后的自行處分,完全可以作為人身保險利益原則適用的替代,發揮其預防道德風險的功能。但如果說人身保險利益原則失之于客觀的話,那么同意主義原則則失之于主觀,畢竟一個人從世界上的現存可以感知的事物所得到的主觀感覺印象不僅依賴于事物本身,而且同樣依賴于事物與感知事物、人的關系(比如距離),智商和經驗(有無民事行為能力和歷事的經驗)以及感知人的表達自由度(積極主動還是被迫脅從)等。我們必須了解在各種情緒狀況,各種視角和距離,各種形式的介質條件下,可能出現感知結果的迥異,這就造成我們無法確認自己的感覺印象忠實的反映了現實,也就是說即使被保險人自己的感知亦不是阻止道德風險的可行之法。且法律把防止因人身保險而產生的謀財害命等道德危險的可能性完全交由被保險人自己把握,卻沒有嚴格的限制制度。“若以第三人之死亡為保險而不可問保險利益之有無者,則可能有不肖之徒以重價收買此種同意書(無異于收買生命)而為保險,如是則危害生命之事必層出不窮;即使要保人實無危害被保險人之意圖,然以他人之生命為賭博,亦屬有背于善良風俗,公共秩序,法律不能予以容忍。”綜上“同意主義原則”的弊端表現在:其并不能有效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杜絕以他人之生命身體做標的來進行賭博。
(三)利益主義和同意主義統一的可能性
通過上文介紹和分析可見,在人身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方式上有人身保險利益主義和同意主義和兼用主義三種情況。通過對各國人身保險利益原則適用的具體方式,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人身保險利益主義還是同意主義都是明示或默示的承認某種特情關系的存在,并最終把其作為保險合同成立的要件的。當然兩者亦存在著不同,主要在于人身保險利益主義更強調人身保險利益的形式性。并把這種利益局限于有限的關系范圍之內。從而使的人身保險利益在保險法律適用和保險業的實踐操作中易于操作,達到防范道德風險發生的目的。而同意主義更強調一種人身保險利益的內容,但這種內容要借助于被保險人自己對道德風險的評估來對是否存在人身保險利益進行確認,此規定即體現了對被保險人的尊重和人文關懷,又能突出被保險人的主觀能動性,把復雜無法量化的人情關系化作簡單易行的當事人同意,使得保險程序成本降低,保險范圍擴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保險業的發展,但兩者在各具優勢的同時,均無法單獨完成防控道德風險的重任。
人身保險利益原則和同意主義原則在適用上各有各的優勢,我們沒必要擇其一,而放棄其他。法律的正義在于追求正義的最大化,在我們無法用其中任何一種方法克服來自于人身保險利益原則和同意主義原則的缺陷之前,我們應該采取一種穩妥的適用方式最大化的加以避免,以實現保險制度設立目的作為立法規定的出發點。
人身保險利益原則和同意主義原則分別以客觀標準性和主觀能動性作為其存在的理由,而主觀和客觀從來就不是對立的。主客觀相結合更能使尊重事實標準和發揮主觀能動達到完美的統一,但結合方式上是值得考究的,是割裂的折中主義并用還是采用統一折中主義值得研究。
四、人身保險利益原則適用方法的重構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人身保險利益原則和同意主義原則應是對兩個不同人身保險利益主體投保人和受益人統一采用的。
其一,投保人在訂立人身保險合同時應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取得同意既視為其對被保險人具有人身保險利益。這樣對于保險業本身來說,首先能夠確保交易的順利進行,滿足投保人為被保險人投保的欲望,擴大保險范圍;其次通過被保險人自己的判斷和分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預防來自于投保人的道德風險,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其二,受益人則必須對被保險人具有具體的人身保險利益,對受益人作為人身保險利益主體的限定可以限定保險的范圍,防止賭博,同時由于受益人是與被保險人具有特情關系的人,所以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保險道德危險發生的機率,達到保護被保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目的,發揮保險的最大功能。
但受益人對被保險人所享有的利益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應受民法關于主體民事能力,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等相關規定的限制。
筆者通過對現有人身保險利益的適用方式(利益主義原則和同意主義原則)進行比較分析,認為兩種適用方式各有優缺點,他們無法單獨完成預防賭博和防范道德風險的重任,也有礙于保險業的發展。基于此,筆者建議修改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采用投保人取得同意即視為具有人身保險利益,而受益人必須具有具體保險利益的統一的折中主義原則。
——與林剛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