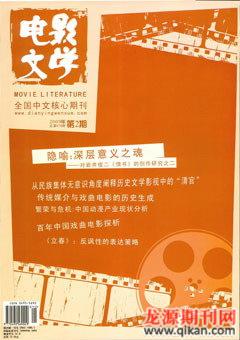淺談女性主義視角下張愛玲與王安憶的文學比較
白寶善
[摘要]張愛玲和王安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兩個奇異的亮點。在張愛玲與王安憶上海傳奇的書寫與建構中,女性主義是她們筆下最能體現女性社會與市民意識的載體。張愛玲與王安憶的作品將女性作為立文的視角,時刻關注著女性的命運,從生存狀態、情感層面等對女性加以觀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顯出鮮明的女性主體意識。
[關鍵詞]女性主義;張愛玲;王安憶;人文關懷
一、引言
在張愛玲與王安憶的女性主義小說中,情感與婚姻是其貼近小說主題、描寫女性生存狀態的切入點,寫得最多,頗為得心應手。不同的是,在關照女性的生存境遇時,張愛玲始終用冷靜的目光自發審視女性的寄生心理和奴性病疾,王安憶則采用熱切的眼光自覺地關注著女性的獨立、堅韌與成熟,張愛玲的作品重在揭示,王安憶的作品則更多地呈現出一種贊賞的態度。
二、奴仆到女人的回歸
1,依附寄生的女性
張愛玲集中揭示了男權話語社會里女性精神奴役的創傷及其對男性的依賴。在漫長的封建男權社會話語中,“天道陽尊陰卑,人事男尊女卑”,女性作為被放逐于男性權力文化之邊緣人與失語者。“五四”以后成長起來的女作家們,都先后對男性的中心話語表達了強烈的反抗。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傷痕累累的心靈及其對平等、自由、獨立精神的渴求,在冰心、丁玲、蕭紅等的作品中被屢屢展示。然而,這些作品中少有對女性自身在漫長的男權社會中逐漸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進行審視,而把女性的深重災難完全歸之于男權中心社會。“張愛玲對女性群體的心理病疾有更為清醒的認識,在她的筆下出現了女性的自我觀照、自我審判、自我解構的新氣象,并且她把筆力集中在揭示女性的負面”。愛玲的小說世界里的女性都是自覺自愿地居于男性的腳下,心履斑斑,掙扎在百孔千瘡的感情世界里。身為女性,張愛玲冷眼靜觀,她對女性群體的不幸遭遇和心理瘤疾有著清醒的認識。她認為,造成女性卑下地位和不幸命運的原因,固然是由于男權話語社會及其意識形態,但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和馴順奴性,則是其解放自身的重要障礙。
2,堅韌成熟的心靈
在王安憶所處的年代,時代的發展與經濟上的相對獨立使女性逐步擺脫了服從男性統治的地位,大都在社會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王安憶筆下,女人的情感婚姻大都可列為“謀生”之外的“謀愛”。這些女人執著地追求著愛情,在感情的漩渦中苦苦掙扎,甚至在愛情的尋找中迷失了自我。《逐鹿中街》中的女教師陳傳青,因擔心丈夫古子銘有外遇而不辭勞苦,日日跟蹤著丈夫,與古子銘作著心智的較量。《米尼》中的米尼,偶然與阿康相識相愛,阿康因偷竊被捕后,米尼竟也靠偷竊養活自己與阿康的孩子,后來又在阿康的誘引下墮落成了妓女并參與了賣淫組織,墜入一個骯臟、丑陋的罪惡世界。米尼的自甘墮落是為了“情”,最終迷失于情網而為男人所出賣。如果說張愛玲的女性意識一定程度上尚處于自發狀態,王安憶則是以自覺的姿態來正視女性的。當女性擺脫了男權意識的控制,她們逐漸變得獨立、成熟而堅強,在女性意識的覺醒中相繼投入到社會生活中,飾演自己的角色,展現自己的風采。王安憶的作品更多地關注女性的成長,表現出對女性命運的人文關懷。
三、對女性主義文學的承傳與拓新
張愛玲可以說是現代女性主義小說的第一人。張愛玲將自己對人生的觀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傳奇》的扉頁上所寫:“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里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
王安憶作為受張愛玲影響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對海派精髓領會最深的一位,在小說創作中繼續拓展著自張愛玲以來建構的女性主義文學的新天地,并對“張派”一脈作最富有創造力的延伸。對上海這個多面體,王安憶有著理性的認識,在她的上海書寫中,沒有對時尚的炫耀與展覽,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她緊緊依偎著多姿多彩、新鮮潤澤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風花雪月的故事演繹中,滲透著包括價值取向、審美風格、文化意蘊、市民情趣在內的民間寫作立場。“上海這城市在有一點上和小說特別投緣,那就是世俗性。上海與詩、詞、曲、賦,都無關的,相關的就是小說。”
我們在王安憶的女性主義小說中實實在在地讀出了歷史的滄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惡,可以說,王安憶是在一步步地向堅韌的人生態度靠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小說創作是承接了張愛玲透視世俗人生的衣缽,但她對女性主義人生的體會更帶有主動性和自主性。在關注重大社會問題上,王安憶也表現了她獨特的人生態度和鮮明的個人立場。作品在展現女性主義生活世俗的同時,也在向我們展現人性,不是知識分子的某一群體而是大眾的人性。如果說張愛玲留給人們更多的是關于蒼涼和凄美的追憶,王安憶更多的帶給人們的是關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種臨危不亂、處事不驚的人生哲學宣言。
四、女性主義視角下張愛玲與王安憶的文學價值
張愛玲與王安憶分別以其女性意識和人文關懷,從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人手,就生存狀態、情感層面等描寫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為代表的市民精神狀況。張愛玲的作品從歷史場景中的女性人手,側重表現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束縛,與女性意識覺醒的艱難歷程,自發地審視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劇的深層內因,對女性的“原罪意識”進行展露和鞭撻,目光犀利,悲天憫人。作為新時期的女性作家,王安憶以平實的格調,注重描寫女性主義生活場景中女性外在生存價值與內心體驗,自覺致力于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權力的爭取,表達女性生存的韌性,贊賞其蓬勃的生命力,以熱切親近的目光傾心關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在社會變革中尋找女性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具有更深厚的社會內涵。她們的作品對于豐富小說與女性寫作,具有積極的意義。張愛玲與王安憶對女性主義生存狀態的刻畫展示著女性生活的精髓,“這種對以女性為代表的市民精神的描繪滲透了作家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觀照,也使得上海這個都市更富有迷人的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