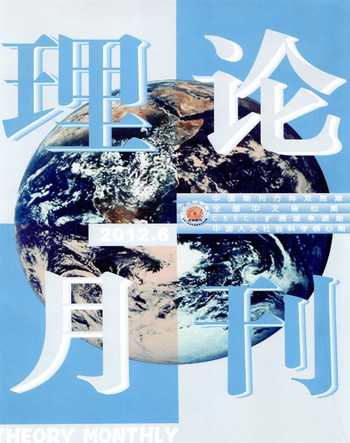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矛盾的一種補償形式
摘要:意識形態必有其生發的深層社會根源,這一根源就是社會矛盾。社會矛盾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自身的矛盾。針對社會矛盾這一結構性創傷,人類需要尋找彌補創傷的觀念形式,此即意識形態。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對意識形態起著促生作用。意識形態是社會矛盾的一種補償形式,這從神話、宗教和現代意識形態中可以清楚地領略到。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常從事實解釋、價值目標、實現策略等方面,展現著應對社會矛盾的方略,這更體現了意識形態如何作為社會矛盾的補償形式。由此,意識形態的起源、本質和作用得以考察。
關鍵詞:意識形態;社會矛盾;補償形式
中圖分類號:B016.9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6-0044-04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08CZX006)。
作者簡介:盧永欣(1978-),男,河南沈丘人,哲學博士,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講師、碩士生導師。
對人們來說,有一個很讓人困惑的問題:為什么需要意識形態?可能有人認為,意識形態本來就是人類的宿命,正如阿爾都塞所說:“人是意識形態的動物”。因此它并不因人的好惡而存亡。如果這樣。那么人類就應該被動地等待這一宿命的處置,而無力窺探其運作的玄機并對其施以有效的影響嗎?又有人可能認為,意識形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有利于社會統治或社會整合。但這種說法并不能從根源上解釋清楚為什么意識形態會存在,或者借用法國思想家涂爾干的觀點,這種說法誤把“功能解釋”當作“因果解釋”,即把意識形態所起的功能(社會統治或社會整合)看作其產生的原因。
那么,從深層的社會根源看,是什么促生了意識形態呢?筆者認為,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夠如影隨形地伴隨人類社會,必有其生發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社會矛盾。以下,本文將簡要闡釋社會矛盾,然后結合對人的想象能力和超越訴求的分析。并通過神話、宗教、現代意識形態等實例,最終明確“意識形態是社會矛盾的補償形式”這一基本命題,由此深化對意識形態的起源、本質和作用的認識。
一、社會矛盾及其特點
本文所說的社會矛盾,主要指人與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及人的內在世界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存在者,人不僅要從自然界中攫取財物,也要與他人以及整個社會打交道,而且人還要面臨個人內部問題的困擾,這些構成了現實的社會矛盾。因此社會矛盾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與自然的矛盾。這里把人與自然的矛盾歸于社會矛盾。是因為人與自然的矛盾具有社會性。馬克思說:“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人的存在是有生命的存在,人的首要的歷史活動是依據自然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并在這一歷史前提下生產其它的東西。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過程。人依靠大自然生產物質產品,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人類社會。在這一過程中人也擴展著自然的范圍,并不得不與“更大的自然”打交道。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人從自然中獲得生存資料,但又遭受著自然的限制,感受著自然的威力。人與自然的這種矛盾正是社會矛盾的一個方面。
第二。人類社會自身的矛盾。人類活動最重要的結果是生產出了真正的屬人的世界,即社會。人類社會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創造物。人類活動一方面創造了供人們生活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另一方面,這些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又獲得了獨立性,并形成了一種客觀的力量。也就是說,這個創造物反過來成了異于人的東西,成了壓制人的東西。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對人的異化,在具體的社會歷史中就表現為各種社會矛盾。國家矛盾、種族沖突、制度不公、階級差別、財富差距、強權壓制等等,都是社會矛盾的具體體現。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生產方式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階級矛盾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矛盾。不過,也有理論家力圖對馬克思的矛盾觀進行補充和修正。例如湯普森就說:“馬克思認為,階級的統治和附庸關系一般構成了人類社會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平等和剝削的主要軸心。……雖然馬克思強調作為不平等和剝削基礎的階級關系的重要性是對的,但他卻傾向于否定或壓低兩性之間、民族集團之間、個人和國家之間、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集團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他傾向于認為階級關系構成了現代社會的結構核心,認為它們的轉變是未來擺脫統治的關鍵。這些強調和設想今天不能認為是自明的。我們今天生活在階級統治和被統治仍舊起重要作用的世界里,但其中還有許多其他形式的沖突,而且在某些背景下它們有著同樣甚至更重要的意義。”英國學者拉倫在《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中也認為馬克思過于著重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實際上,種族壓迫、性別壓迫、殖民壓迫等形式的社會矛盾仍需引起人們的重視,這些“對女性、少數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具有影響的性別統治、種族統治和殖民統治”的社會矛盾在現代社會中同樣顯眼。
第三,人自身的矛盾。作為社會組成因子的個人,也充斥著矛盾。個人所包含的矛盾,是人與自然的矛盾以及人類社會自身的矛盾在人的內在世界的反映。這種矛盾雖然沒有前兩種社會矛盾那么具體和宏觀,但依然客觀存在。作為個體的人,我們時時感受到這種矛盾的存在。關于個體內部所包含的社會矛盾,一些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已經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例如弗洛伊德把人格構成分為本我、自我、超我,認為人本身處于這三層人格結構的矛盾之中。另一位精神分析學家拉康也把人分為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實界三種人格結構,并揭示了在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實界中人的矛盾狀態。在具體生存中,人焦灼地感受著內在矛盾的存在,并在不斷的超越和就范、選擇和堅持中對這些矛盾進行應答。
社會矛盾是社會的結構核心,是社會諸要素內部和要素之間的關系狀態。這種關系狀態,我們一般稱為對立統一。這不僅表現為矛盾要素內部和要素之間的對立、差異、分裂和不一致,也表現為這些對立、差異、分裂和不一致的最終解決。但是一般說來,社會矛盾的對立、差異、分裂和不一致的狀態是社會矛盾的凸顯狀態,人們對社會矛盾的體悟和感受也主要是針對這種狀態。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對立狀態視為矛盾的主要特點。這正如列寧所說:“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拉倫甚至認為,對抗才是矛盾的真正本質。他說:“在我看來,討論非對抗性的矛盾是沒有意義的,這并不只是因為馬克思并沒有區分對抗和矛盾,還主要是因為矛盾是由對抗來界定的。……換句話說。所謂的非對抗性的矛盾壓根就不是矛盾。”社會矛盾呈現的分裂的、對抗的、不一致的狀態是社會矛盾的凸顯狀態。
社會矛盾猶如殘缺的社會創傷,它是人必須要遭遇的社會事實,它構成了人的真實的生存境遇。因此,對于社會矛盾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創傷,人們必須要尋找到填補創傷、解決矛盾的方式。意識形態就是這樣一種應對社會矛盾的具體方式。社會矛盾是意識形態的緣起地,正是在社會矛盾這一創傷性的社會裂口上,滋生了意識形態。
二、超越、想象與意識形態的產生
社會矛盾造就了人的生存之困,人在矛盾中經歷和感悟著自己的生存。人生活在矛盾的近旁,焦灼地感受著矛盾給自己帶來的困窘。但是,正如自然界中哪怕是一頭牲畜都不會甘心于籬笆的限制一樣,人也不會甘心于社會矛盾對自己的困擾,他要超越社會矛盾的囹圄。人是社會矛盾的承載者,他必須要對自己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做出應答。“應答”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要有所“應”。就是人們必須要直面自己不得不面臨的社會矛盾;二是要有所“答”。就是人們必須對社會矛盾給出解答和處理方式。意識形態就是人對社會矛盾做出的應答方式。或者說是人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隨附現象——在以實踐的形式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總是如影隨形地伴隨其中。意識形態產生于人的具體的生存境遇,而人的具體的生存境遇,就是矛盾著的社會現實。在意識形態的產生上,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人是超越性動物,人不會甘心囿于慘淡的社會矛盾,終日受其困擾。超越是人的本性,人是社會矛盾的承載者,也是它的超越者。人的超越本性與人的想象能力有關。想象是人的一項基本生存能力,這種能力使得人類能夠不斷地構造世界的意義,拓展世界的范圍,從而演繹人之為人的真諦。在自然進化中,人類似其他動物的一些適應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單薄,但是人卻發展出了其他生物所沒有的能力,比如想象力。人的超越本性和人的想象能力是并行的。人類的這些稟賦給了人應對社會矛盾的潛能。超越是對社會矛盾的超越,想象是在社會矛盾基礎上的想象。想象源于現實的社會生活,源于真實的社會矛盾。人生活在矛盾著的社會現實中,但人具有想象的能力,這種能力給予人繼續生存的勇氣。想象提供了一個可能的世界,一個希望的空間。這種可能的、希望中的世界源于矛盾著的現實,是想象成就了這種世界。
一些哲學家,如康德、胡塞爾等,對想象問題都進行過探討。但他們的討論主要限于意識的內在性構造和知識的可能性問題,并沒有走出傳統的意識哲學的藩籬。也就是說,他們沒有從現實的物質生活,從人的具體生存和社會實踐的角度思考想象問題。馬克思說:“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意識的問題只有從現實世界和具體的生活實踐才能得到最終解答,這對想象也如此。為什么要想象?想象的根源何在?這些問題只有從人的生存狀態,從矛盾著的社會現實出發才能被徹底理解。這就要求對想象問題的思考必須走出純粹的認識論模式,從而把這一問題安置于更寬厚的社會一歷史域中,即從現實的實踐活動去理解它。這是一種思維范式的變化,馬克思開始實現這種變化。馬克思在想象問題上的貢獻,是把想象與現實的物質生活實踐結合了起來。他認為,物質活動方式的受限性以及其他的社會矛盾,使得人們會以某種想象的方式——如宗教——去補償這一種矛盾。例如他在批判施蒂納的觀點時說:“它把宗教的人假設為全部歷史起點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產代替生活資料和生活本身的現實生產。”
想象具有非凡的創造性和建構力,它甚至能建構某種“真實的”東西。在想象的研究上,法國左翼思想家C.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做出了較多思考。卡斯托里亞迪斯對想象問題的貢獻,主要體現他對想象的創造性的強調,以及對想象的社會一歷史因素的考察。英國學者湯普森在介紹卡斯托里亞迪斯的思想時說:“社會一歷史世界的想象要素,正如社會一歷史世界本身一樣,一直被傳統思想所誤解。這種傳統思想一直把想象視為是某種在場的東西的反映或特殊的映像。卡斯托里亞迪斯拒絕了這種設定以及這種設定所依據的經典本體論,他認為,想象就是產生任何可能的對象和意象關系的東西:它是形象和形式從無到有的創造活動,沒有這種創造,就不可能有對事物的反映。從社會一歷史層面出發,想象解釋了社會制度的緣起、動機和需要的構成,以及象征主義、傳統和神話的存在。”卡斯托里亞迪斯繼承了康德的積極性想象力的思想,他把想象稱為“創造性核心”。他認為,社會制度是通過想象而建構起來的,想象是社會建制的基礎,社會中的其它因素,如情感、需要等,也都可以在想象中尋找解釋。想象凝聚著社會,并構造了社會中那些被認為是真實的東西。
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使得其要以某種方式去解決社會矛盾。人們解決社會矛盾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思想中的解決,就是在思想中給出應對和消除矛盾的方式;另一種是現實的解決,就是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去解決社會矛盾。不過,即使是實踐的解決方式,也往往要和思想中的解決方式相伴,這是因為并不存在沒有人的意識參與的實踐活動。這兩種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都與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有關,它們代表著人在不滿足當下的矛盾境況時的生存訴求。這種生存訴求的意向空間是由想象建構而成的。想象源于人的生存之困,人們必須要以某種方式去補償社會矛盾對自己的困擾,想象提供了這種補償。想象的創造性使它能創設出“替代”當下的生存困境的別樣世界,并引招人們去追求——這正是被稱為意識形態的東西。人的超越性和想象力,給予了其生存于社會矛盾之上的能力。在對社會矛盾的超越中,在對未來世界的想象建構中,萌生了意識形態。
三、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矛盾的補償形式
以上,本文初步闡釋社會矛盾對于意識形態的緣起作用,并指明了人的超越性和想象能力對于意識形態的構造作用。接下來,本文將結合實例,最終明確意識形態如何作為社會矛盾的補償形式。
社會矛盾是人類社會必然的構成部分。西方學者齊澤克認為:“社會是由永遠阻止它達到和諧、透明、理性的整體性的對立、斷裂一由破壞每一個理性的總體化的阻礙——‘結合在一起的。”社會領域正是圍繞著基本的分裂和對抗構建起來的。“社會總是一個不一致的領域,這一領域圍繞著某種構成性的不可能性構建而成,它被某種核心‘對抗所穿越。”社會矛盾呈現出分裂的、對抗的、不一致的狀態,這是社會矛盾的主要特點。社會矛盾猶如殘缺的社會創傷,它是人必須要遭遇的社會事實,它構成了人的真實的生存境遇。因此,人們必須要尋找到填補創傷、解決矛盾的方式。意識形態就是這樣一種應對社會矛盾的方式。下面,筆者將從神話、宗教及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人手,探討意識形態的這一功能。
神話源于人們生存方式的受限性以及其它的社會矛盾。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除了自然力之外,社會力量也對神話起著促生作用。社會力量對人來說也是異己的,并以類似自然力一樣的必然性支配著人。因此,馬克思認為神話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中國的盤古開天、夸父追日、西方的普羅米修斯盜火等神話故事,都是人們以想象的形式去應對矛盾的具體方式。
神話要通過敘事來表現,拉倫在《意識形態的概念》中評述格雷馬斯等人的理論時說,一般而言,神話常采用以下敘事模式:
巫師——英雄——惡人
國王——公主——英雄
在該模式中,各個行動位(Actants,“行動位”在此指巫師、英雄、惡人、英雄等)之間的關系代表著社會矛盾沖突以及矛盾的最終消除。即:“在神話故事中有著敘事要去解決的根本的沖突或矛盾。或許英雄和惡人的沖突被構造出以表現階級間的社會矛盾,而惡人的挫敗則象征著在實踐中不能解決的矛盾在思想中得以解決。”神話代表著人的超越訴求,它是人們通過想象建構出的思想體系。通過該體系,那些現實中不能解決的矛盾最終被故事中的英雄完結。這樣,人們以思想的方式“解決”了社會矛盾。
和神話具有類似特征的是宗教。宗教能夠給人們提供精神慰藉,以使人們逃避社會矛盾的困擾。馬克思說:“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一種顛倒了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在此,“顛倒的世界”是指充斥著矛盾的社會現實,而“顛倒了的世界意識”就是指在這種社會現實基礎上產生的虛幻意識——宗教。宗教給那些苦難中的或對現實一籌莫展的人們提供了精神慰藉,或說提供了避難所。馬克思說:“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宗教是被壓迫生靈創造出的供自己倘佯、呼吸的最后一塊領地。馬克思說宗教是人的鴉片,這一隱喻主要并不是用鴉片的毒性去比喻宗教。從物性上講,鴉片還是緩解疼痛的藥劑。宗教也是如此,宗教可以使人不再去直面慘淡的社會事實。在現實中遭受困窘的人們,往往會到宗教中尋找歸隱之路。宗教制造了供人們信仰、追求的另一個世界,這個異在世界是現實世界的產兒,因此,宗教可視作現實世界的補償形式。如神話一樣,宗教也由人們的想象能力構造而成,它生長于社會矛盾之上,并為人們規避社會矛盾提供了幻象空間。
廣義而言,神話和宗教都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但是從限定意義上來說。原初的神話、宗教和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有些不同。這主要因為,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是人類世界觀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結果。在人類早期,世界觀主要體現為神話和宗教。但這種情形逐漸隨著世界觀的理性化而改變。現今的意識形態。就是以這種理性化的世界觀為標榜的。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制度合法化的論證方式,其理論的根基逐漸從對人類異己力量的尋求,轉為在人類自身理性中尋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明了人類社會的這一變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
意識形態理性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意識形態世俗化的過程。這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理論架構的基礎從天國降到了人世,而且還因為和意識形態密切關聯的權力,也不斷地世俗化。宗教權力轉向世俗權力,權力的論證資源也從神話、宗教轉向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這也正如伊格爾頓所說:“意識形態屬于現代——屬于這個世俗的、科學的、理性的、偉大的新時代,它的目標是將人們從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來,從關于上帝、貴族和專制君主的虛假顛倒中解放出來,并恢復他們作為充分理性的、自我決定的存在者的尊嚴。它是在心靈自我層面上的資產階級革命;它立志根植于大地來重構心靈,剖析我們接受和組合感覺材料的方式。以使我們介入這一重建過程并使它朝我們所希望的政治目標前進。”
這種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代表了誕生于啟蒙時期的“意識形態”概念的主要特點。在以理性為標榜的現代社會,意識形態融合了人的超越訴求,它會把人的超越訴求訴諸一種美好的圖景,并認為其是可以實現的——現在的矛盾可以解決,將來的美景也會實現,一切都會好起來。因此,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就是要把握它所根植的基礎(社會矛盾)及其所蘊含的超越訴求。由此才能夠理解為什么意識形態和權力如此密不可分。意識形態成功的奧妙就在于能夠把人的超越訴求和權力結合起來。它會告訴人們:“我所倡導的,就是你們所追求的;你們所追求的。就是我所倡導的。”由此,人的超越訴求被挾持。當然,如果二者的結合不理想的話,意識形態也會面臨危機。
以上,筆者從神話、宗教和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三個方面,闡明了意識形態如何作為社會矛盾的補償形式。意識形態對社會矛盾的補償,有兩種主要樣態:消極補償和積極補償。消極補償,就是要回避和掩蓋社會矛盾;積極補償,就是要揭示和解決社會矛盾。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意識形態就是回避和掩蓋社會矛盾。但這種觀點并不能涵蓋意識形態與社會矛盾之間的全部關系。這是因為,每種意識形態總要盡力代表更多人的超越訴求,使得人們有追求、有盼頭,由此才能維持人心。如果一種意識形態要維持自身生計,并為一定群體的利益或權力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論證的話,它就不能無視社會矛盾的存在,而是要對這些社會矛盾做出自己的指認、解釋和說明,并依據一定的價值目標,提出解決矛盾的方針策略。只有如此,意識形態才能夠更好地維持人心,整合社會群體,調動社會行為。
一般來說,意識形態包括事實認知、價值目標和實現策略三個結構層面,比如對“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來說,其事實認知層面是要描述社會現狀、指出社會中的“不自由”現象;其價值目標層面是要倡導“自由”價值理念并號召人們去追求;其實現策略層面是要提出實現自由的具體方案,如憲政、選舉,等等。從中看出,意識形態作為一整套思想體系,其各個構成層面都要對社會矛盾給予應答。再如,辛亥革命前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列強入侵、政體僵化、民生凋敝等。當時的各種意識形態,無論是保守的、改革的或改良的,都必須對這些社會矛盾給出解釋說明,并提出各自的價值目標和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案。譬如,保守派從中國長期的君主統治的歷史文化事實出發,強調維持王權的重要性。改良派則著眼于綜合各種社會事實,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世界局勢、社會穩定等方面來思考問題。而改革派強調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長期的封建帝制,認為針對中國積疴難返的社會現實,必須采取重病下猛藥的方式解決問題。這些實例都說明了意識形態和社會矛盾的內在關系,并進一步詮釋了“意識形態是社會矛盾的補償形式”這一命題。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John B.Thompson: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3][英]喬治·拉倫,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場[M],戴從容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俄)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Jorge Larrain Marxism and ideology,London;Basingstoke:Macmillan,1983.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John B.Thompson: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
[8][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等,圖繪意識形態[M],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9]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lc Verso,1989.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Jorge Larrain:The Concept of ideology,London:Hutchinson,1979.
[12]Terry Eagleton: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4.
責任編輯:文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