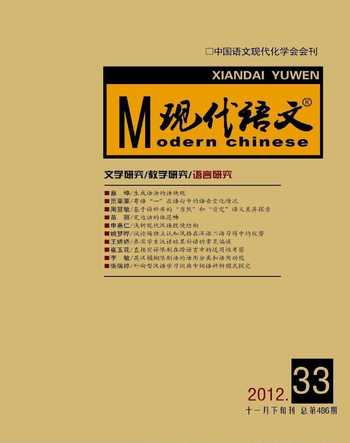《詩經》與《左傳》雙音詞比較研究
摘 要:先秦已出現雙音詞,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詩經》與《左傳》中便存在著大量的雙音詞。《詩經》和《左傳》雖然處于同一時期,但在許多方面仍存在著差異。本文通過比較二者的異同,證實了漢語詞匯在這一時期開始了明顯的雙音化傾向。
關鍵詞:《詩經》《左傳》雙音詞 單音詞 比較 雙音化
漢語詞匯從以單音詞為主,發展到以雙音詞為主,是漢語發展史上的一大變化,這個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事實表明,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兩周時期,這一變化就已經開始了。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伴隨著這些變化,漢語也在不斷發展,表現在詞匯上,出現了相當數量的雙音詞。漢語詞語雙音化的原因是交際的需要。從客觀方面看,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情況下,人們的生活領域和認識領域還比較狹窄,靠單音詞基本能夠滿足交際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詞匯需求增加,同音詞大量出現,容易混淆,為了區分這些同音詞,雙音詞便應運而生。雙音詞避免了音系復雜化、同音詞過多等弊病,增強了漢語的交際功能;從主觀方面看,雙音詞的出現是為了更形象、生動地反映客觀,進行交際。雙音詞說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看起來整齊,增強了語言的表達力。
《詩經》與《左傳》同為兩周時期的作品,但它們的風格不同,《詩經》口語風格較強,而《左傳》書面語風格更強,因此二者的雙音詞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對這一時期漢語詞匯的雙音化傾向有初步了解。
一、《詩經》《左傳》雙音詞研究概述
前人對《詩經》與《左傳》的雙音詞已經做過研究,程湘清先生在《漢語史專書復音詞研究》中對《詩經》的雙音詞做了詳細的研究,而陳克炯先生在《左傳復音詞初探》一文中對《左傳》的雙音詞做了詳細的研究。本文將在前人的基礎上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
關于雙音詞的判定標準,程湘清先生在《漢語史專書復音詞研究》(2008:39)一書中從漢語特點出發,提出了從語法結構、詞匯意義、修辭特點和出現頻率等方面來判定雙音詞的標準。他認為,在語法結構上,兩個音節結合緊密,不能拆開或隨意擴展的是詞;結構上結合緊密、意義上共同代表一個概念的是詞;處于相同句式的相同位置上雙音組合,其中一個已確認是詞,則其他的雙音組合也考慮是詞;一些見次率很高的雙音組合大致可確立為雙音詞。這些標準詳細完備,因此我們用以判定雙音詞,并從二者雙音詞的數量、詞性、構詞方式以及雙音詞的運用等四方面來進行比較研究。
二、《詩經》《左傳》雙音詞在數量上的差異
據程湘清先生統計,《詩經》中的雙音詞有726個,陳克炯先生統計《左傳》有雙音詞284個(不計姓氏、地名等)。處于同一時期的兩部作品中雙音詞的數量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異,是因為二者的文體風格不同。《詩經》是用西周口語寫成的,在日常的口語交際中,為了更形象生動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人們往往采用雙音詞或者更加復雜的復音詞。《詩經》是一部詩歌作品,它可以配樂歌唱,單音詞顯然不能滿足韻律的需要,于是便采用了更加悅耳整齊的雙音詞形式。而《左傳》是一部歷史散文集,它需要真實地記錄歷史,并且只為社會高層所閱讀,一般的平民百姓很少接觸,因此,它繼續采用流傳已久的雅言作為書寫材料,而雅言中單音詞占絕大多數,只有為數不多的雙音詞。由二者的雙音詞在數量上的差異可以看出,雙音詞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出現并大量運用,而散文中還比較少,漢語出現了言文脫節的現象,但是漢語詞匯雙音化的趨向不可阻擋。
三、《詩經》《左傳》雙音詞在結構上的異同
關于構詞方式的劃分,我們采用黃伯榮、廖序東先生劃分漢語詞匯的標準,將《詩經》與《左傳》中的雙音詞從構詞方式上分為單純詞和合成詞。單純詞又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疊音詞,一是連綿詞;合成詞又分為復合式、重疊式、附加式。其中,復合式又細分為聯合式、偏正式、支配式、陳述式、補充式。
(一)單純詞
1.疊音詞
《詩經》中的這類詞最為常見,據程湘清先生統計,《詩經》中疊音詞有360個,使用了689多次,這正是《詩經》雙音詞的一大特色。在《詩經》的360個重疊組合中,除“滔滔”“高高”“明明”等一小部分是單音詞的重疊而構成的重疊式合成詞外,大部分是單純重疊詞。其中又大都屬于狀態形容詞。例如:
(1)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周南·桃夭》)
(2)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小雅·菁菁者莪》)
《左傳》的疊音詞不多,只有13個。這13個疊音詞是“恤恤”“皇皇”“振振”“閔閔”“熙熙”“煢煢”“遙遙”“穆穆”“蕩蕩”“賁賁”“融融”“鏘鏘”“焯焯”。這些疊音詞與《詩經》中的疊音詞一樣,也大都是來摹景狀物的。例如:
(3)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僖公五年》)
(4)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隱公元年》)
可見,二者疊音詞在數量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原因是疊音詞的出現和發展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疊音詞更能體現詩歌的流動性和韻律性,并且疊音詞在摹景狀物方面比單音詞有更大的優勢,于是《詩經》更多地采用了疊音形容詞,《左傳》較少采用疊音形容詞。
2.連綿詞
《詩經》中的雙音詞除了大量的重疊詞以外,還存在大量的連綿詞。這些連綿詞有雙聲的,有疊韻的,有雙聲兼疊韻的。例如:
(5)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邶風·靜女》)
(6)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秦風·蒹葭》)
(7)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周南·卷耳》)
《左傳》中的雙音詞也存在著連綿詞,這些連綿詞同樣也有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的。例如:
(8)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襄公二十二年》)
(9)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四年》)
(二)合成詞
1.復合式
1)聯合式
《詩經》中的合成詞有雙聲、疊韻以及雙聲兼疊韻的,但由于疊音詞和連綿詞較多,所以合成詞的數量相對較少。例如:
(10)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大雅·棫樸》)
(11)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小雅·小明》)
《左傳》中聯合式雙音詞共96個,占雙音詞總數的33.7%。例如:
(12)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襄公九年)
(13)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昭公七年)
(14)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襄公十四年)
2)偏正式
先秦偏正式雙音詞主要由“名詞和名詞”“形容詞和名詞”“數詞和名詞”三種結構方式構成的名詞,其他方式構成的詞則居少數。《詩經》中偏正式雙音詞同合成詞一樣,相對大量疊音詞和連綿詞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
(15)大夫跋涉,我心則憂(《鄘風·載馳》)
(16)幫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頌·玄鳥》)
《左傳》中偏正式雙音詞共109個,占復音詞總數的38.3%。可見比重也很大。例如:
(17)先王何常之有, 唯余心所命。(《昭公二十六年》)
(18)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昭公二十六年》)
在偏正式雙音詞中,有一種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有一些代表最常用的概念的單音詞(均屬于基本詞匯),往往成為構詞能力很強的詞根。例如:
人:價人(《大雅·板》);私人(《大雅·崧高》)
夫:仆夫(《小雅·出車》);大夫(《魯頌·閟宮》)
民:庶民(《大雅·靈臺》);先民(《大雅·板》)
子:男子(《小雅·斯干》);君子(《大雅·卷阿》)
這些詞根具有很強的構詞能力,每個詞根都可以和大量的單音語素組合成合成詞。廣泛利用詞根復合法構成新詞正是漢語在詞匯方面的特點之一,這一特點不斷發展完善,延續至今天仍然是現代漢語的一大特點。可以說,這些詞根的出現大大加強了漢語詞匯的雙音化趨勢。
3)支配式
《詩經》與《左傳》中的支配式合成詞比較少見,只有寥寥幾個。例如:
(19)睕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小雅·大東》)
(20)雖遇執事,其弗敢違。(《成公三年》)
另外的兩種形式——補充式和陳述式,幾乎沒有。
2.重疊式
《詩經》的疊音組合中大部分屬于單純疊音詞,重疊式合成詞只有少數。例如:
(21)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周頌·敬之》)
(22)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大雅·抑》)
《左傳》中的疊音組合都屬于單純疊音詞,重疊式合成詞沒有。
3.附加式
1)前附
(23)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小雅·巷伯》)
(24)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大雅·板》)
2)后附
(25)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皇矣》)
(26)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小雅·伐木》)
上述結構一般叫作襯字雙音結構,這種結構幾乎是《詩經》中特有的語言現象,在《左傳》等先秦散文中不常見,除了“有”字組成的雙音結構偶爾出現外,其他類型都是十分罕見的。在詞性方面,單音詞與這些襯字結合以后,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在詞義方面,襯字也沒有改變單音詞的意義,也不增添附加的意義和情彩。唯一的不同是形成了輕重相間的雙音節,對詩歌的節奏有著比較重要的影響。《詩經》語言的韻律和節奏,對詞匯的音節有著特殊的要求,當時雖然已經出現了雙音詞,但還不能滿足《詩經》追求韻律的需求,《詩經》中大量襯字的運用只是為了補足四字格式,在韻律上達到和諧。客觀上這一結構促進了漢語詞匯雙音化。可見,《詩經》這種這種韻文文學形式對漢語雙音化有著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比較看以看出,《詩經》雙音詞最大的特點是存在大量的疊音詞、連綿詞、襯字雙音結構以及語用上的析言合用現象。而《左傳》的雙音詞也有自己的特點:
第一,單純詞的數量不多,不像《詩經》大量運用連綿詞和疊音詞來摹聲狀物,寫景抒情。
第二,句法構詞能力大大增強,其中基本成分加附加成分這種構詞方式不占重要地位,但聯合式、偏正式構造的雙音詞數量很多。
第三,基本詞匯中某些表示最常見的事物、反映最常用的概念的根詞,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構詞能力。例如“人”構成的詞有“小人、大人、圣人、庶人、野人”等;以“大”構成的有“大夫、大隧、大路、大命”等。
形成《詩經》雙音詞特點的原因是:《詩經》具有口語風格,講究句式整齊,韻律和諧,它可以配樂歌唱。由于修辭形式、文學表現手法以及聲律節奏的需要,《詩經》中的語言和一般的散文典籍不完全一致,這就必然會在詞匯運用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而形成《左傳》雙音詞特點的原因是它的散文性特點。《左傳》采用流傳已久的雅言,既短小精悍,又準確規范。《詩經》和《左傳》雖處于同一時期,但語言風格的不同造就了二者的差異,二者的差異體現了先秦時期漢語詞匯的雙音化傾向,演變到現代漢語中,雙音詞已經成為漢語詞匯的主流。
參考文獻:
[1]程湘清.漢語史專書復音詞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2]王力.古代漢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3.
[3]朱廣祁.詩經—雙音詞論稿[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4]陳戍國.春秋左傳校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6.
[5]孔丘編訂.詩經[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6]陳克炯.左傳復音詞初探[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1978,(4).
[7]石云孫.詩經雙音詞語分言、合用例釋[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
報,1990,(1).
(李國山東青島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