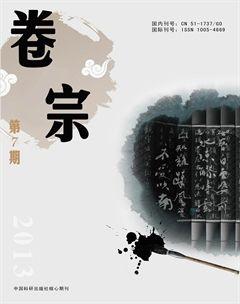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
劉艷
摘 要: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積極參與社會(huì)精神生活的型塑,因而選擇合理的理論工具對(duì)其展開研究就具有了積極的社會(huì)意義。本文對(duì)法蘭克福學(xué)派傳統(tǒng)和伯明翰學(xué)派傳統(tǒng)的大眾文化研究理論進(jìn)行分析,認(rèn)為中國(guó)當(dāng)下的大眾文化研究,可借鑒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理論、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以及費(fèi)斯克的“兩種經(jīng)濟(jì)”理論,將三者進(jìn)行有機(jī)的結(jié)合,同時(shí)也要注意避開理論本身的局限性。
關(guān)鍵詞:大眾文化;研究方法;法蘭克福學(xué)派;伯明翰學(xué)派
中國(guó)的大眾文化崛起于20世紀(jì)后半葉,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大眾文化事業(yè)獲得了蓬勃的發(fā)展,成為與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學(xué)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與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參與了社會(huì)精神生活的型塑。大眾文化的崛起和發(fā)展對(duì)國(guó)民生活方式、國(guó)民性格塑造以及社會(huì)發(fā)展變化帶來了新鮮的元素,使其呈現(xiàn)出了新的面貌。這些改變令人驚喜,但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關(guān)注和焦慮,如對(duì)當(dāng)下大眾審美取向的非議以及網(wǎng)絡(luò)文化對(duì)青年群體心智發(fā)展影響的焦慮。在此情況下,選擇正確的研究方法對(duì)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的發(fā)展現(xiàn)狀,了解其價(jià)值效應(yīng)并指導(dǎo)其健康發(fā)展便具有了積極的意義。本文擬從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的特點(diǎn)、法蘭克福學(xué)派傳統(tǒng)的批判以及英國(guó)伯明翰傳統(tǒng)的批判三方面來進(jìn)行探討。
1 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的特點(diǎn)
要探討研究方法,必須首先明確界定研究對(duì)象。大眾文化這一概念對(duì)于中國(guó)語(yǔ)境,嚴(yán)格來講是個(gè)泊來品,在英語(yǔ)中它對(duì)應(yīng)了兩種表達(dá),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眾文化批判指向的對(duì)象為mass culture, 這一概念被賦予了明顯的貶義色彩,主要指商業(yè)利益驅(qū)動(dòng)的文化產(chǎn)品,如電影、廣告等傳播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品。當(dāng)下語(yǔ)境我們所使用的大眾文化這一概念則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導(dǎo)的popular culture,作為英國(guó)伯明翰傳統(tǒng)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對(duì)“文化”這一概念做了歷史的回溯,認(rèn)為文化應(yīng)是一個(gè)整體全部的生活方式,從而賦予了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關(guān)鍵詞—文化與社會(huì)的詞匯》中稱“大眾文化是民有、民享、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 。從此,大眾文化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而開始成為影響人們生活以及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種現(xiàn)代意識(shí)。隨著對(duì)大眾文化研究的深入,學(xué)者們對(duì)其進(jìn)行了更嚴(yán)密準(zhǔn)確的界定。國(guó)內(nèi)學(xué)者王一川對(duì)大眾文化做出了這樣的定義,它“以大眾媒介為手段、按商品規(guī)律運(yùn)作、旨在使普通市民獲得日常感性愉悅的體驗(yàn)過程,包括通俗詩(shī)、通俗報(bào)刊、暢銷書、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和廣告等形態(tài)” 。
從大眾文化的如上定義,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它的一般特性:大眾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娛樂性、日常性、類型性等。中國(guó)語(yǔ)境下的大眾文化也同樣具備這些特點(diǎn),其中,商品性這一特點(diǎn)尤為吸引人們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開放之前,中國(guó)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物資不豐沛,物資的消費(fèi)形式多為統(tǒng)一分配和按計(jì)劃配額消費(fèi),人們的商品意識(shí)淡漠,物質(zhì)層面如此,在解決人們生存高級(jí)需求的精神文化層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學(xué)界精英文化的牽制,更多的是被動(dòng)接受,而不是對(duì)文化商品的主動(dòng)消費(fèi)。所以,中國(guó)的大眾文化雖然從產(chǎn)生之初就帶有了商業(yè)文化的特質(zhì),追求商業(yè)利益,以?shī)蕵废矠橹饕δ埽捎谄涠探陌l(fā)展史,并未像一些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guó)家形成了完備龐大的文化工業(yè)體系,同時(shí),主流媒體的官方化以及國(guó)家相關(guān)文化政策的指導(dǎo)也使得大眾文化還未徹底淪為謀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國(guó)內(nèi)的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文藝性,商品屬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蘭克福學(xué)派傳統(tǒng)的批判
大眾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蘭克福學(xué)派社會(huì)批判理論的核心。經(jīng)過幾代人的努力,法蘭克福學(xué)派對(duì)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yè)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為后來學(xué)者的大眾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同時(shí)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了批判的標(biāo)靶。霍克·海默,作為該學(xué)派的第一代領(lǐng)軍人物,在研究中將大眾文化概念與文化工業(yè)概念直接等同起來,奠定了大眾文化批判的悲觀主義立場(chǎng)。在法蘭克福學(xué)派看來,大眾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藝術(shù)產(chǎn)品商品化。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體制的運(yùn)作下,大眾文化成為了統(tǒng)治階級(jí)和資本合謀的工具,文化工業(yè)首先通過標(biāo)準(zhǔn)化批量生產(chǎn)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著統(tǒng)治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大眾文化產(chǎn)品,繼而借助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機(jī)制將模式化的文化產(chǎn)品輸送給大眾消費(fèi),從而實(shí)現(xiàn)意識(shí)形態(tài)的灌輸和強(qiáng)化。因而,在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視野中,大眾文化帶有明顯的欺騙性,帶給大眾暫時(shí)的滿足繼而安于虛假的現(xiàn)狀,實(shí)現(xiàn)對(duì)民眾的控制;大眾文化同時(shí)也淪為了統(tǒng)治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工具,通過決定娛樂商品的生產(chǎn),控制規(guī)范著文化消費(fèi)者的需要并進(jìn)而對(duì)其心理意識(shí)進(jìn)行操控;大眾文化的標(biāo)準(zhǔn)化和模式化生產(chǎn)形式扼殺了文化的藝術(shù)性,也抹殺了文化產(chǎn)品的個(gè)性和創(chuàng)造性,消費(fèi)此類文化產(chǎn)品的大眾順而也被同一化。
法蘭克福學(xué)派對(duì)大眾文化進(jìn)行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沿襲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文化霸權(quán)理論”的傳統(tǒng),將文化視為與資本主義進(jìn)行抗?fàn)幍囊粋€(gè)斗爭(zhēng)領(lǐng)域,揭露資本主義文化工業(yè)大生產(chǎn)對(duì)藝術(shù)以及大眾個(gè)性的抹殺,這一理論基調(diào)使其成為了大眾文化批判研究的標(biāo)桿,也成為后繼大眾文化研究學(xué)者不可繞開的理論基石。對(duì)于中國(guó)當(dāng)代的大眾文化研究,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文化工業(yè)理論仍具有良好的指導(dǎo)意義。隨著文化事業(yè)的推進(jìn),文化產(chǎn)業(yè)商業(yè)化,藝術(shù)、文化產(chǎn)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趨勢(shì)。大眾文化的消極效應(yīng)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業(yè)利益和娛樂功能的低俗文化產(chǎn)品的出現(xiàn),對(duì)青年人心智的影響以及消費(fèi)西方批量生產(chǎn)的文化產(chǎn)品對(duì)傳統(tǒng)價(jià)值觀念的質(zhì)疑等,對(duì)這些大眾文化特質(zhì)的批判,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理論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時(shí),由于發(fā)展的局限性,我國(guó)尚未形成完備的文化工業(yè)體系,大眾文化事業(yè)還遠(yuǎn)未徹底的商業(yè)化,淪為商品經(jīng)濟(jì)的附庸,并在社會(huì)主義主流文化的指導(dǎo)和影響下文化產(chǎn)品還具有一定的文藝性,并在某種意義上仍是反映大眾的聲音。鑒于此,在使用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理論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的商品性展開批評(píng)研究時(shí),還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應(yīng)以消除負(fù)面效應(yīng),發(fā)揮正面效應(yīng)為宗旨。
因循葛蘭西的“霸權(quán)理論”,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學(xué)者們看到了統(tǒng)治階級(jí)借助文化產(chǎn)品向大眾受體灌輸意識(shí)形態(tài),以期實(shí)現(xiàn)對(duì)大眾心理意識(shí)的控制,然而,對(duì)大眾文化產(chǎn)品的消費(fèi)行為并未到此終結(jié),作為具有主觀意識(shí)和能動(dòng)性的大眾個(gè)體,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審美傾向和審美領(lǐng)悟,必然會(huì)對(duì)同一化的文化產(chǎn)品做出不同的反應(yīng)和選擇。此時(shí)的大眾文化產(chǎn)品,作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場(chǎng)規(guī)律。大眾文化產(chǎn)業(yè)為了迎合市場(chǎng),就必須揣摩迎合大眾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務(wù)于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志,換句話說,大眾的消費(fèi)意愿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反過來又對(duì)大眾文化工業(yè)形成了挑戰(zhàn),產(chǎn)業(yè)和受眾之間存在著雙向的交流,在這個(gè)意義上,文化就成為了一個(gè)哈貝馬斯口中的“公共領(lǐng)域”,既不屬于市場(chǎng),也不屬于國(guó)家。對(duì)于法蘭克福學(xué)派文化工業(yè)理論的這一局限,哈貝馬斯也曾在自己書中坦承:“大眾文化顯然絕不僅僅是背景,也就是說,絕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極框架,而是定期出現(xiàn)、反抗等級(jí)世界的顛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慶典和日常規(guī)范” 。 對(duì)大眾接受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忽視是法蘭克福學(xué)派文化工業(yè)理論的硬傷。反觀中國(guó)當(dāng)代的大眾文化,無論是在生產(chǎn)還是消費(fèi)環(huán)節(jié)大眾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duì)大眾能動(dòng)性的研究應(yīng)該成為研究的重點(diǎn)。
法蘭克福學(xué)派對(duì)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yè)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悲觀的情緒,這與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以及學(xué)派早期成員的生活經(jīng)歷是有極大關(guān)系的。由于二戰(zhàn)德國(guó)納粹對(duì)猶太人的迫害,學(xué)派有猶太血統(tǒng)的成員如霍克·海默、馬爾庫(kù)塞和阿多諾都曾親身經(jīng)歷納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選擇逃亡到美國(guó)只為尋求人身安全。德國(guó)納粹借助強(qiáng)大的宣傳機(jī)器進(jìn)行反猶太宣傳,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廣大民眾意識(shí)形態(tài)的控制和最終的暴政。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學(xué)者對(duì)此深惡痛絕,繼而站到了助其實(shí)現(xiàn)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業(yè)的對(duì)立面,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研究的展開不具備如此嚴(yán)苛的時(shí)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備特定嚴(yán)苛的生活經(jīng)歷,因而在展開研究時(shí)一種中立的研究態(tài)度就是我們應(yīng)該珍視的,對(duì)大眾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評(píng)價(jià)。
3 英國(guó)伯明翰傳統(tǒng)的批判
與法蘭克福學(xué)派不同,英國(guó)伯明翰學(xué)派從其成立之初就反對(duì)以精英主義立場(chǎng)來研究文化,他們努力擴(kuò)大了文化的內(nèi)涵,反對(duì)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劃分,對(duì)底層的工人階級(jí)的文化,即他們認(rèn)為的本真的大眾文化,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注,并努力發(fā)掘其積極意義。伯明翰學(xué)派的研究?jī)?nèi)容主要涉及大眾文化以及與大眾文化密切相關(guān)的大眾日常生活。其中,大眾媒介始終是該學(xué)派研究的焦點(diǎn),特別是電視的意識(shí)形態(tài)功能。學(xué)派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針對(duì)電視話語(yǔ)發(fā)展出了編碼/解碼理論。就編碼層面而言,霍爾沿襲了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核心理論觀點(diǎn),但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了觀眾的參與,觀眾的欣賞即是對(duì)電視節(jié)目的解碼。霍爾指出,受眾對(duì)媒介文化產(chǎn)品的解讀是與他們?cè)谏鐣?huì)結(jié)構(gòu)中的地位和立場(chǎng)相對(duì)應(yīng)的,他認(rèn)為電視節(jié)目的觀眾可能會(huì)存在三種解碼立場(chǎng):一是主導(dǎo)性—霸權(quán)性立場(chǎng),即觀眾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圖;二是協(xié)商性符碼或立場(chǎng),指觀眾大體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圖,但卻從自身立場(chǎng)和利益出發(fā)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對(duì)抗性符碼,即觀眾完全站到制作的對(duì)立面試圖瓦解節(jié)目中傳達(dá)的意圖。這三種立場(chǎng)很好地分析了觀眾在消費(fèi)電視節(jié)目過程中的主觀能動(dòng)性,也說明觀眾完全可以在積極有效的觀賞中抵制或消解節(jié)目可能傳達(dá)的消極意義,從而彰顯出媒介文化積極的社會(huì)效應(yīng)。
霍爾雖然是針對(duì)電視話語(yǔ)提出的編碼與解碼理論,但不難發(fā)現(xiàn),對(duì)于任何話語(yǔ)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分析,這一模式都具有適用性,這也是霍爾理論備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將視野回溯到中國(guó)當(dāng)下的大眾文化語(yǔ)境,媒體文化正處于蓬勃發(fā)展的欣欣向榮期,人民大眾的參與意識(shí)也空前高漲,無論是長(zhǎng)盛不衰的選秀造星節(jié)目,如湖南衛(wèi)視的“超級(jí)女聲”以及中央電視臺(tái)的“我要上春晚”,還是如今爆紅的電視相親類節(jié)目,如江蘇衛(wèi)視的“非誠(chéng)勿擾”。在這些節(jié)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眾,欣賞消費(fèi)的也是大眾,電視臺(tái)只是提供了一個(gè)平臺(tái)并給與相應(yīng)的引導(dǎo),對(duì)大眾個(gè)體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顯的個(gè)性無從干預(yù)太多,如像從“非誠(chéng)勿擾”舞臺(tái)上走出的“寶馬女”馬諾,她在舞臺(tái)上的極端拜金言論可能也是節(jié)目的導(dǎo)演和編導(dǎo)始料未及的。從傳統(tǒng)意義上講,她的言論完全背離了主流價(jià)值觀念,但節(jié)目之后她迅速躥紅,并獲得了數(shù)量不少的擁躉,這一事件充分說明了大眾自主選擇的可能性和實(shí)在性。如何對(duì)此文化現(xiàn)象做出合理的解釋,霍爾的解碼理論絕對(duì)是理論選擇的不二工具。
承襲伯明翰傳統(tǒng)對(duì)大眾文化以及大眾主觀能動(dòng)性的關(guān)注,約翰·費(fèi)斯克對(duì)大眾文化進(jìn)行了系統(tǒng)完備的理論和個(gè)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眾文化》也被視作關(guān)于大眾文化和后現(xiàn)代文化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費(fèi)斯克的研究主要圍繞大眾能動(dòng)性抵制權(quán)利控制和文化集權(quán)展開,對(duì)大眾文化報(bào)以樂觀主義的態(tài)度,形成了與法蘭克福學(xué)派截然不同的理論觀點(diǎn)。“兩種經(jīng)濟(jì)”理論是費(fèi)斯克一個(gè)重要的理論貢獻(xiàn)。“兩種經(jīng)濟(jì)”即“金融經(jīng)濟(jì)”和“文化經(jīng)濟(jì)”。大眾文化的商品是同時(shí)在這兩種經(jīng)濟(jì)中流通的。“金融經(jīng)濟(jì)”指涉的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商品生產(chǎn)和消費(fèi)過程,注重的是交換價(jià)值,流通的是金錢。費(fèi)斯克之前的大眾文化研究,無論是法蘭克福學(xué)派還是伯明翰學(xué)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圍繞這一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展開研究。但費(fèi)斯克認(rèn)為僅用金融詞匯是不足以對(duì)文化商品進(jìn)行描繪的,因?yàn)橄M(fèi)社會(huì)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實(shí)用價(jià)值,又有文化價(jià)值的,文化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就體現(xiàn)在“文化經(jīng)濟(jì)”中。所謂文化經(jīng)濟(jì)是指,大眾產(chǎn)業(yè)鏈中的觀眾從原來的商品(觀眾通過消費(fèi)文化產(chǎn)品而成為金融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賣給廣告商等)變成生產(chǎn)者,生產(chǎn)出的是“意義”和“快感”。而“原來的商品變成了一個(gè)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yǔ)結(jié)構(gòu),這一話語(yǔ)結(jié)構(gòu)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 。費(fèi)斯克“文化經(jīng)濟(jì)”的提出為大眾的創(chuàng)造力提供了空間,此時(shí)的大眾不再只是消費(fèi)者和商品,其生產(chǎn)者身份使得他們即使仍被支配于體制之中,仍卻能在體制的空隙中努力規(guī)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規(guī)訓(xùn),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質(zhì)性和一致性。因而,大眾文化不是文化工業(yè)生產(chǎn)出的,而是人民創(chuàng)造出的,是進(jìn)步的力量,也是與資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展開對(duì)抗的重要斗爭(zhēng)場(chǎng)域。
費(fèi)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樂觀主義立場(chǎng)對(duì)于推動(dòng)當(dāng)前國(guó)內(nèi)的大眾文化發(fā)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在使用其理論展開研究時(shí)也應(yīng)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經(jīng)濟(jì)”作為理論基石就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業(yè)強(qiáng)制滲透統(tǒng)治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功能,這也奠定了費(fèi)斯克對(duì)大眾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獎(jiǎng)的立場(chǎng),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眾文化的商品屬性所可能帶來的負(fù)面效應(yīng)。同時(shí),在物質(zhì)起主導(dǎo)作用的經(jīng)濟(jì)體制下,資本的力量仍是無比強(qiáng)大的,大眾發(fā)揮能動(dòng)性可以選擇拒絕、抵抗,但要徹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對(duì)權(quán)力集團(tuán)的實(shí)質(zhì)打擊。
中國(guó)當(dāng)代大眾文化正處于蓬勃發(fā)展期,對(duì)民眾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學(xué)界的關(guān)注。中國(guó)當(dāng)代語(yǔ)境下的大眾文化由于自身的發(fā)展特點(diǎn),決定了對(duì)其展開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學(xué)界的相關(guān)理論研究成果,又需要考慮文化現(xiàn)象的本土特點(diǎn),引入相關(guān)的思考。總的來說,西方理論界的法蘭克福學(xué)派傳統(tǒng)對(duì)大眾文化進(jìn)行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以及伯明翰學(xué)派傳統(tǒng)代表人物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以及費(fèi)斯克的“兩種經(jīng)濟(jì)”理論都是研究當(dāng)代中國(guó)大眾文化極好的理論工具。但由于這些理論本身也存在著不足和局限性,可考慮將這些理論的優(yōu)勢(shì)觀點(diǎn)進(jìn)行整合,而盡量規(guī)避相關(guān)理論漏洞,結(jié)合具體的文化現(xiàn)象來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的大眾文化展開研究。
參考文獻(xiàn)
[1] 雷蒙德·威廉斯. 關(guān)鍵詞—文化與社會(huì)的詞匯[M]. 北京:三聯(lián)書店, 2004: 48.
[2] 王一川主編. 大眾文化導(dǎo)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
[3]〔德〕尤爾根·哈貝馬斯. 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M]. 曹衛(wèi)東等, 譯. 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99:7.
[4] 約翰·費(fèi)斯克. 理解大眾文化. 王曉玨、宋偉杰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33.
[5] 羅小青. 當(dāng)代中國(guó)場(chǎng)域中的大眾文化批判—評(píng)法蘭克福學(xué)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J]. 湖北社會(huì)科學(xué),2006年(11):112-115.
[6] 馬馳. 伯明翰與法蘭克福:兩種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徑[J]. 西北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年(3):1-6.
[7] 姜華. 對(duì)費(fèi)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解讀與質(zhì)疑 [J]. 學(xué)術(shù)交流, 2005年(11):119-123.
[8] 喬瑞金,薛稷.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觀念思想探析 [J]. 晉陽(yáng)學(xué)刊,2007年(5):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