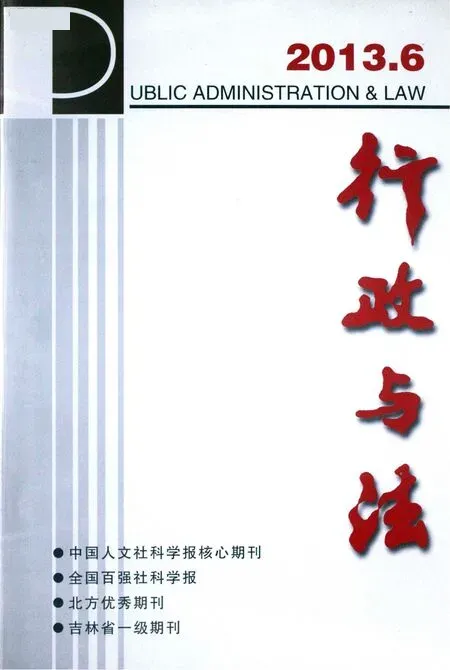保險詐騙罪若干疑難問題探究
□ 古加錦
(武漢大學, 湖北 武漢 430000)
近年來,隨著保險業的擴展,保險詐騙犯罪呈高發態勢。作為現實常發的金融詐騙罪之一的保險詐騙罪,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均存不少爭議及疑難問題, 筆者在此選擇其中三個司法實務中經常碰到但還沒有形成統一認識的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教于學界和同仁。
一、保險詐騙罪的主體爭議
根據《刑法》第198條的規定,保險詐騙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只能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以下簡稱投保人等),包括自然人和單位。有關保險詐騙罪的主體爭議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⒈冒名騙賠。所謂冒名騙賠,是指行為人冒充投保人等采取刑法規定的保險詐騙方式騙取保險金。 如實踐中常常出現的汽修廠經營者及其員工冒充所維修車輛客戶, 采取制造交通事故或者虛構交通事故等方式騙取車輛保險金的。 如果投保人等知道行為人冒充其騙取保險金的,投保人等與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行為人的冒名騙賠行為無疑應定性為保險詐騙罪。 如果投保人等不知道行為人冒充其騙取保險金的, 行為人的冒名騙賠行為是否應定性為保險詐騙罪?有觀點認為,對于冒名騙賠行為,因行為人不是投保人等,故不能以保險詐騙罪處理,只能以詐騙罪或者其他罪名處理。[1]司法實務中對于冒名騙賠行為的處理并不統一, 有的定性為保險詐騙罪,有的則定性為詐騙罪。筆者認為,冒名騙賠的行為應定性為保險詐騙罪。理由是:行為人雖然不是投保人等,但其以投保人等的名義,利用投保人等的保險合同欺騙保險人并騙取保險金, 這與投保人等自己利用其保險合同欺騙保險人并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本質完全一樣, 均不僅侵犯了保險人的財產所有權, 而且侵犯了保險人以保險合同為基礎而建立的保險經營秩序。也就是說,冒名騙賠的行為與被冒名人自己騙賠的行為無論是行為的名義人還是行為侵犯的犯罪客體均是相同的, 從法律評價的角度對兩者的定性應是一致的,均應定性為保險詐騙罪。至于冒名騙賠的行為名義人與行為人實際上不是同一人不影響其事實上是利用保險合同騙取保險金,因此,符合保險詐騙行為的本質。 如果將冒名騙賠行為定性為詐騙罪則忽略了該行為還侵犯了保險經營秩序的一面, 也沒有做到全面評價該行為的性質。
⒉隱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詐騙保險金。隱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是與掛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相對而言的。所謂隱名的投保人,是指按照保險合同實際繳納保險費的人。所謂隱名的被保險人,是指受保險合同保障的財產的實際所有權人。如掛靠經營的機動車輛,其所有權名義上的擁有者與實際上的擁有者不盡一致,以該機動車輛為保險標的時,就會出現名義上的投保人、被保險人與實際上的投保人、被保險人并不相同,后者就是隱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而前者只是掛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當隱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采取刑法規定的保險詐騙方式騙取保險金時,應該如何定罪?有觀點認為,不能成立保險詐騙罪,因為隱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不是保險合同上的投保人、被保險人,不符合保險詐騙罪的主體資格要求, 對其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應定性為詐騙罪或者其他罪名。筆者認為,刑法應堅持實質解釋的立場,而不應拘泥于形式的解釋,以使刑法的適用符合社會現實的發展要求。 而從刑法的實質解釋立場分析,隱名的投保人、被保險人雖然不是形式意義上的投保人、被保險人,但卻是實際上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是真正意義上的投保人、被保險人,完全可以成為保險詐騙罪的主體, 其采取刑法規定的保險詐騙方式騙取保險金的,理應以保險詐騙罪論處。而且,隱名的投保人、 被保險人也是利用保險合同欺騙保險人并騙取保險金的, 同時也侵犯了保險人的財產所有權和保險人以保險合同為基礎而建立的保險經營秩序,符合保險詐騙行為的本質,故應定性為保險詐騙罪。
⒊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詐騙投保人等的保險費。 保險人是指與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并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責任的保險公司。 保險經紀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 為投保人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提供中介服務并依法收取傭金的單位。 保險代理人是根據保險人的委托,向保險人收取代理手續費,并在保險人授權的范圍內代為辦理保險業務的單位或者個人。有人認為,未將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納入保險詐騙罪的調控范圍,造成了法律保護的不平衡,因此建議將保險詐騙罪的主體規定為一般主體。[2]也有觀點認為,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詐騙投保人等的保險費的,也應構成保險詐騙罪。[3]但筆者認為,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詐騙投保人等的,其侵犯的犯罪客體只是投保人等的財產所有權, 而沒有侵犯保險人的保險經營秩序, 本質上屬于普通詐騙行為,應定性為詐騙罪。保險人的保險經營秩序是建立在所有投保人所繳納的保險費的基礎之上的, 保險制度的本質就是借大眾的錢來幫助遭受意外災禍的個別人。投保人等騙取保險人的保險金的,會影響到保險人對于其他投保人等的賠付能力, 危及其他投保人等的利益, 從而危及保險人的保險經營秩序或者說保險制度的運行。而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詐騙投保人等的行為雖然也是發生在保險業務活動中, 違反了保險業務中的誠信原則,因此會影響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的信譽,會影響其未來的保險業務的開展, 但因其詐騙行為所針對的對象不是保險人的保險金,故不會危及其他投保人等的利益,不會危及保險人的保險經營秩序或者說保險制度的運行, 不宜認定為保險詐騙罪, 對其侵犯投保人等的財產所有權的行為定性為詐騙罪可以恰當地評價其行為本質。所以,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沒有將保險詐騙罪的主體擴大至保險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是否有必要將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詐騙投保人等的保險費的行為在立法上規定為其他單獨的罪名則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二、虛構保險標的的表現
保險標的是指作為保險對象的財產及其有關利益或者人的壽命和身體。 虛構保險標的的典型情形是虛構根本不存在的保險標的,即無中生有。如自己沒有汽車謊稱有汽車而予以投保。除此之外,虛構保險標的還存在以下幾種情形:
⒈惡意超額保險。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保險價值,超過保險價值的,超過的部分無效。所謂惡意超額保險,是指故意超過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予以投保, 使保險金額大于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 從而在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時能獲得超過其實際損失價值的保險金。但在計算保險詐騙犯罪數額時, 應減去保險標的的實際損失價值。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超額保險是由于投保人的善意所致,則不屬于保險詐騙。如由于投保人不了解市場行情,過高地估計了財產的價值,即因投保人的善意所致。
⒉惡意重復保險。 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 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 重復保險的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價值的, 各保險人的賠償金額的總和不得超過保險價值。除合同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只有按照其保險金額與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承擔賠償責任。在具體操作中,應是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時從各保險人處獲得超過保險價值的賠償總額。 但在計算保險詐騙犯罪數額時, 應減去保險標的的實際損失價值。
⒊虛構保險利益。 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 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所謂虛構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將無權投保的保險標的予以投保。 如將他人的財物虛構為自己的財物予以投保, 或將與自己并無親屬關系的他人虛構為自己的親人并作為被保險人予以投保。
⒋將不合格的標的虛構為合格的保險標的。 即將不符合投保要求的標的予以投保。 此種情形的保險標的確實存在,只是不符合相應險種的投保要求,屬于以次充好。 如投保人隱瞞被保險人身患絕癥的情況投保人身保險。值得探討的是虛構年齡的情形。被保險人的年齡是決定保險費率的重要依據, 也是在承保時測量危險程度,決定可否承保的依據。一般來說,年齡越大,危險也越大。但在訂立人身保險合同時,要逐個驗明被保險人的實際年齡是有困難的,因此,往往是在發生保險事故或者在年金保險開始要發放時才核實年齡。我國《保險法》第54條規定,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 并且其真實年齡不符合合同約定的年齡限制的,保險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續費后,向投保人退還保險費, 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的除外。據此,“年齡不實”屬于不可抗辯條款。在人身保險合同中,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是否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異議是受到時間限制的。 因為人身保險合同大都是長期性合同,時間愈久,愈不易查清當時的告知是否屬實,而且被保險人死后, 受益人亦不一定能夠了解當初投保時的告知情況。因此,為了保護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保險人一般只能在1-2年內可以投保人告知不實為理由解除保險合同,這個期間就稱為可抗辯期間。超過這個期間即進入不可抗辯期間, 保險人就不得再提出異議,即使投保人確有告知不實的情形,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后仍負給付責任。所以,如果虛構年齡的事實是在人身保險合同成立2年之后才被保險人發現的,不構成保險詐騙罪, 因為符合民事法律的合法行為不能同時又是犯罪行為, 或者說實體法意義上的民刑沖突時應優先適用民法。
⒌事后保險。事后保險是指發生保險事故后才投保或者續保。即為了騙取保險金,行為人將投保前發生的保險事故偽報成投保后或者續保后發生的保險事故。對于實踐中常出現的這類先出險后投保的詐騙行為,有人將其視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的行為;[4](p239)而有人則認為該情形應屬于“虛構保險標的”的行為。[5](p184-186)筆者認為,事后保險應當歸屬于“虛構保險標的”情形。因為發生事故后,標的滅失或者受損,均不符合投保的要求,投保人隱瞞標的已發生事故的真相,欺騙保險人與之簽訂保險合同, 實際上就是將不符合投保要求的保險標的虛構為符合投保要求的保險標的,屬于“虛構保險標的”的行為。簽訂保險合同后,為了騙取保險金,投保人等將保險期前發生的保險事故虛構為保險期內發生的保險事故,是“虛構保險標的”之后騙取保險金的相應具體表現。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騙取保險金,投保人等將保險期滿之后發生的保險事故虛構為保險期內發生的保險事故的, 因為投保時不存在虛構保險標的的情況,故此情形不屬于“虛構保險標的”,但投保人等實際上將保險期內沒有發生保險事故虛構為發生保險事故,可以認定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
三、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定性
依照我國《刑法》第183條的規定,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進行虛假理賠,騙取保險金歸自己所有的,根據其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而分別構成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 有觀點認為, 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只有采取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這種方法進行虛假理賠的,才應以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論處;如果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采取的是其他法定保險詐騙方法進行虛假理賠的, 則應構成保險詐騙罪。所以,投保人等和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共同騙取保險金的, 只有其手段行為是利用了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才可能構成共同犯《刑法》第183條之罪(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 投保人等和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共同騙取保險金,而采取的手段行為是其他法定保險詐騙方法的, 只可能構成《刑法》第198條的保險詐騙罪。[6]筆者認為,上述觀點是對《刑法》第183條規定的誤解。《刑法》第183條的規定屬于注意規定, 用于提醒司法人員對于這種情形的行為應以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論處而不應認定為保險詐騙罪。其實,即使沒有該規定,這種情形的行為也應以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論處。而且,除此之外,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其他法定保險詐騙方法進行虛假理賠, 騙取保險金歸己所有的,也應以職務侵占罪或貪污罪論處。問題在于,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伙同投保人等采取法定保險詐騙方法進行虛假理賠, 共同騙取保險金的應如何定罪?或者說,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應如何定性?
第一種觀點是保險詐騙罪說。有觀點認為,有些不法的投保人等為了順利地騙取保險金,在實施保險詐騙之前或者進行詐騙的過程中,就與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互相勾結,使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審查和確定理賠責任的過程中,明知被保險人所提供的與索賠有關的證明和材料不齊全或不真實,反而予以確認。由于有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充當詐騙分子的內應,往往使得保險詐騙犯罪輕而易舉地實現。對于這種情況,也應當以保險詐騙的共犯論處。[7](p471)該觀點具體分析了投保人等與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互相勾結共同犯罪的作案特點, 但對此得出應以保險詐騙的共犯論處的結論卻忽視了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在整個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因而不能正確反映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共同犯罪性質。
第二種觀點是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說。 有觀點認為,在投保人等向保險公司索賠之后,保險公司工作人員明知投保人等有欺詐行為反而與之勾結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虛假理賠的案件中, 投保人等的詐騙行為由于被保險公司識穿(因為該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代表保險公司) 而不可能因該詐騙行為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產,因而并不成立保險詐騙罪,之后則因共同利用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騙取保險公司數額較大的財產而符合貪污罪或職務侵占罪的共犯的特征, 其索賠之前實施的保險詐騙行為已完全被其后實施的貪污或職務侵占行為所吸收。因而,對內外勾結騙取保險金的各行為人的行為, 應一律以貪污罪或者職務侵占罪論處。[8]該觀點的結論是正確的,即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應一律以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論處, 但其論證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不成立保險詐騙罪的理由值得商榷。 該觀點既然認為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已經代表保險公司識穿了投保人等的詐騙行為,保險公司不存在被詐騙的問題,從而不可能成立保險詐騙罪,那么,又何以認為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與投保人等在其后共同實施的是“騙取”保險公司的保險金行為,從而構成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此時代表保險公司被詐騙的又是誰呢?可見,該觀點的論證是前后矛盾的。其實,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只是在其職務行為的范圍內才代表保險公司, 而其參與投保人等的詐騙行為根本不是在代表保險公司履行職務行為, 當然就不存在其代表保險公司已經識穿投保人等的詐騙行為。事實上,正是因為保險公司沒有識穿投保人等的詐騙行為, 才使得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與投保人等相互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成為事實。
第三種觀點是主犯決定說。 這是源于司法解釋的觀點,如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均采用該觀點。按照這一觀點,投保人等與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內外勾結騙取保險金的, 應依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如果主犯是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則將共同犯罪認定為職務侵占罪或貪污罪;如果主犯是投保人等,則將共同犯罪認定為保險詐騙罪。 該觀點注意到了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與作用對于共同犯罪性質的影響,但主犯是量刑情節,是解決定罪問題之后需要考慮的,根據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是“先量刑后定罪”的思維方式,不符合刑法理論“先定罪后量刑”的要求;一個共同犯罪案件中,往往存在兩個以上的主犯,此時根據哪個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便成為爭論的焦點; 主犯是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來認定的, 而認定各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 不同的法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故根據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會存在一定的主觀隨意性。
第四種觀點是核心角色說加分別定罪說。 該說認為,如果投保人等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則可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為保險詐騙罪; 如果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為核心角色, 則可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為職務侵占罪或貪污罪。但是,在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是保險詐騙罪或者職務侵占罪、貪污罪之后,對不同的共犯人仍然存在分別定罪的可能性。至于最終認定何罪,則要比較各罪的法定刑輕重,以其中的重罪名論處。[9]該觀點中的核心角色說借鑒了德國刑法理論關于正犯與共犯的區別所提倡的犯罪事實支配理論,有其可取之處,但司法實踐中往往存在難以確定核心角色的情形, 此時適用該說便存在疑問; 且確定核心角色的主要依據仍然是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與作用, 實際上與主犯決定說沒有多大區別, 同樣具有上述主犯決定說的不足之處。 該觀點中的分別定罪說借鑒了外國刑法理論關于共同犯罪本質所提出的部分犯罪共同說, 但筆者認為其中存在一些認識誤區。 部分犯罪共同說解決的是雖然各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客觀行為不同,但具有重合性質, 在重合的限度內可以看作各行為人具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 從而在重合的限度內認定各行為人成立共同犯罪,又由于畢竟有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客觀行為超出了重合的限度, 故對各行為人在認定共同犯罪的同時最終又以不同的罪名定罪。例如,張三以搶劫的故意入室搶劫、李四以盜竊的故意在外邊望風,張三、李四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 但由于張三具有搶劫的故意和行為,對張三應定搶劫罪,而李四只有盜竊的故意和幫助行為,對李四應定盜竊罪。可是,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與投保人等相互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雖然各行為人的具體故意內容有所不同,但各行為人通過意思溝通最終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共同故意;雖然各行為人的具體行為表現有所不同, 但各行為人的各自行為之間具有相互補充、相互加功的關系,從而合力為一個整體的共同行為。也就是說,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 各行為人既有共同的故意也有共同的行為, 并不符合部分犯罪共同說所要解決的是各行為人的故意和行為均不相同(但具有重合性質)的情形,故不能以部分犯罪共同說作為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時分別定罪的理論依據。 雖然外國刑法理論關于共同犯罪本質所提出的犯罪共同說存在不同的具體主張,但都強調共同犯罪不僅是各行為人的行為共同而且要求各行為人的故意共同,是共同故意實施犯罪,對于共同故意范圍內所共同實施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并應當統一定罪。因此,根據犯罪共同說對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進行統一定罪才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質特征。
第五種觀點是想象競合犯說。該觀點認為,投保人等與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相勾結騙取保險金, 不論雙方分工如何, 事實上都只有一個完整的詐騙保險金的行為, 這一行為在法律上同時觸犯了保險詐騙罪和貪污罪或職務侵占罪兩個罪名,屬于“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從而構成想象競合犯,可以按照“從一重處斷”的原則處理。[10]該觀點認識到了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既可能構成保險詐騙罪, 也可能構成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似乎構成想象競合犯,但筆者認為,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實際上并不符合想象競合犯的特征。理由是:想象競合犯的“一行為”之所以會觸犯數罪名,是基于該“一行為”造成了多個危害結果(如甲開一槍同時殺死A、重傷B、毀壞貴重財物),從而對該“一行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評價,所以其所觸犯的任何一個罪名都無法全面評價該“一行為”,這也是之所以有人主張對想象競合犯進行數罪并罰的原因,至于理論上與實踐中一般對想象競合犯最終“從一重處” 而不數罪并罰是基于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而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只造成了一個危害結果——騙取保險金, 只不過有的人強調其詐騙的一面而認為其行為性質是保險詐騙, 有的人則強調其利用職務便利的一面而認為其行為性質是職務侵占或者貪污, 但無論是認定為保險詐騙罪還是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均足以評價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性質, 只不過是認定為哪個罪名評價該行為的性質更為準確而已, 其中的保險詐騙罪與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處于非此即彼的關系而不能兩立, 這與想象競合犯中只有同時用數罪名才能恰當評價其 “一行為”的性質是不同的。
筆者認為, 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應一律認定為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 這一行為符合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性質。行為性質是由其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決定的,而其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對行為結果的產生或者說對行為目的的實現起最為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既有保險詐騙的一面(虛構保險標的、編造虛假的保險事故原因、夸大損失程度、 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險事故),又有職務侵占或者貪污的一面(利用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受理、 審查理賠等職務上的便利條件)。那么, 決定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性質的是哪方面的因素呢? 這就要分析對于最終騙取保險金起最為決定性作用的是什么。 如果沒有虛構保險標的等保險詐騙行為,當然就不存在騙取保險金的問題,所以,上述保險詐騙行為是騙取保險金的先決條件。 但上述保險詐騙行為能否最終得逞取決于保險公司工作人員是否識破其詐騙行為,所以,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履行職務行為的情況是上述保險詐騙行為能否最終騙取保險金的決定因素。 如果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識破了上述保險詐騙行為,從而拒絕理賠,上述保險詐騙行為就不可能騙取保險金。 但如果保險公司工作人員明知存在上述保險詐騙行為而仍然參與其中,進而予以理賠,騙取保險金便成為雙方互相勾結行為的確定結果。可見,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之所以能夠得逞, 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在其中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 這也可以從哲學中的內因和外因的辯證關系中得到一些啟發。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內因才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案件中,保險公司的保險金之所以被詐騙, 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是“內因”,投保人等(包括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保險詐騙行為是“外因”,投保人等的保險詐騙行為這一“外因”必須通過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當然,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對此既可能存在故意,也可能是過失甚至無過失) 才能最終實現騙取保險金的目的。可見,利用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對于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目的的實現起著最關鍵的決定作用。因此,將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一律認定為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是符合其行為性質的。
其次,這一行為符合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和司法解釋的精神。《刑法》第382條第3款規定,勾結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 伙同貪污的, 以共犯論處。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 第1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 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第2條規定,行為人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勾結,利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的職務便利, 共同將該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職務侵占罪共犯論處。所以,在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案件中,投保人等勾結保險公司工作人員, 利用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職務上的便利,共同騙取保險公司保險金的,如果該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即國有保險公司工作人員或者國有保險公司委派到非國有保險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全案應定性為貪污罪,否則,全案應定性為職務侵占罪。
另外,需要明確的是,以職務侵占罪對內外勾結共同騙取保險金的行為進行量刑可能會比以保險詐騙罪對其進行量刑更輕,但那是立法的價值取向問題。司法實踐中, 不能為了達到重判被告人的目的而把本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的行為作為保險詐騙罪處理。
[1]肖晚祥.保險詐騙罪的若干問題研究[J].政治與法律,2010,(01):30.
[2]張利兆.關于保險詐騙罪一般主體立法模式的思考[J].人民檢察,2007,(08):60-62.
[3] 侯艷芳. 保險詐騙罪疑難問題探析 [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8,(01):117-120.
[4]劉憲權.金融風險防范與犯罪懲治[M].立信會計出版社,1998.
[5]魏智彬.證券及相關犯罪認定處理[M].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
[6]林蔭茂.保險詐騙犯罪定性問題研究[J].政治與法律,2002,(02):65-66、59.
[7]鮮鐵可.金融犯罪的定罪與量刑[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8] 徐立. 內外勾結騙取保險金行為的定性分析 [J]. 河北法學,2004,(12):113-115.
[9]張明楷.保險詐騙罪的基本問題探究[J].法學,2001,(01):36-40.
[10]劉士心.保險詐騙罪新探[J].當代法學,2002,(03):84.
——與林剛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