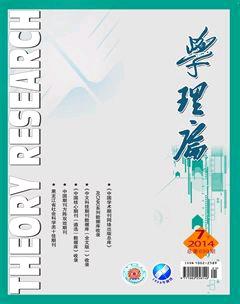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花艷紅
摘 要:《公文寫作與處理》是一門著重培養受體寫作技巧和能力的大學實踐應用類課程。當下的課程建設多以工具理性作為行為指向,無論是教學目的的預設、教材的編寫、課程的設計還是最后教學評價,無法滿足大學人才培養的需求。只有在價值理性統攝下,在教學過程中,真正做到教學目的、教學內容及評價體系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才能使該課程教育走出變相應試教育的思維模式,真正達到大學教育育人與成才的培養目標。
關鍵詞: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公文寫作與處理;現代性;課程改革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1-0215-02
《公文寫作與處理》是大學課程中實踐應用類課程。課程教學的重點通常要求學生通過課程學會撰寫和處理公文。特殊的目的指向使得教學往往會著重于各文種“技法”講授和訓練。但大學教育不在于培養寫作熟練工。教育不僅要求學生掌握課程所涉核心概念、技巧,也在于對學生人格、價值觀的培養,對人作為人的能力和素養的全面提升。對公文寫作與處理課程來說,技法的熟練只是教學內容的一個方面。真正達到讓學生掌握各文中寫作要求、寫出好的公文、合理處理公文,面對社會需要能主動變化,同時在教育過程中也能完成人格塑造和個性培養,伴隨的是學生對公務文書這一客體的深刻認識和理解。因此,在“技”之外,深入理解公務文書價值和意義,能面對不同的實際需要主動變化,在技巧的平臺上,把握“道”,就要做到課程教學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這也成為《公文寫作與處理》課程改革的一個突破口。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馬克思·韋伯在研究現代社會時將人的社會行為作了深入分析,其中區別了兩種不同目的指向的行為類型,包括目的合乎理性的行為(工具理性)和價值合乎理性的行為(價值理性)。所謂工具理性是指“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1]56韋伯認為,人的社會行為中有些行為是針對“目的”,也就是“物”而實施的,是“物化”的行為表現。有些行為則指向“人”:“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56。這是價值理性指引下所產生的社會行為。在價值理性的指引下,人的行為指向的是對“人”存在方式的理解與認識。兩種社會行為的區別在于在采取行為的過程中,施動者對行為預設的結果的選擇和理解。
《公文寫作與處理》作為一門著重培養受體寫作技巧和能力的實踐類課程,當下的課程建設多以工具理性作為行為指向。無論是教學目的的制定、教材編寫、課程設計還是最后教學評價,都著力于對學生“技”把握能力的考查。與此相悖的是,如果課程真正要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避免訓練出“匠人”,就不僅要在課程的整體建設中強調對“技”的訓練,更要明確“技”的意義在哪里——亦即對公文寫作背后的價值理性的深入解析,在課程建設中做到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或者說,工具理性要涵蓋于價值理性之內。
正是在這樣整體理念的轉變中,大學的公文寫作與處理的課程改革才能找到突破點。將原來著重于訓練學生技能的應用實踐類課程,從學生被動接受條條框框的規定與約束,變成主動理解這些規定與約束背后的理念。使學生成為公文寫作與處理中真正的施動者,而不是受制于這些約束的模仿者。能在小小的寫作背后,真正體現出大學教育所帶來的創新與個性培養。完成課程從應“技”教育到人才培養的轉變。
二、理念與教學目的的轉變:從“文”到“人”的理解
課程所教授的所有內容都指向客體:黨政機關行政公文。按照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公文的解釋,這是“黨政機關公文是黨政機關實施領導、履行職能、處理公務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規范體式的文書”。公務文書不是一般性的應用性文書,它的時空場域被限定在黨政機關行使職能的邊界以內。也就是說,“文”的目的指向涉及國計民生的公共與行政事務,“文”的最終受力者是關涉到這些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的社會普通民眾。因此,理解“文”就得理解黨政機關的管理和行政執法的理念,理解“文”就得首先對“人”有深刻的認識。
具體而言,在把握公文之前,需要對現代社會中公共事務及行政管理有一定的理解和認識,包括對其機構、組織運作方式、運作理念的充分理解和熟悉。只有在把握這些“實”的機構運行機制背后“虛”的理念指引,才可能真正理解用以承擔機構運作紐帶的公文的意義和實際效用。這個“虛”的理念都是建立在現代官僚體制中對“人”的理解。自黑格爾、馬克思、韋伯以來許多社會學家、哲學家對現代社會及現代官僚體制所做的一系列深入思考及剖析,都是對不同于傳統社會生活方式的現代人所做的深刻反省和深入剖析。現代官僚體制正是建立在對“人”的理解大轉變的基礎之上。因此,對“人”的理解在公文寫作與處理的教學過程中是根基性的,它左右公共事務運作、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向,也決定了小至一篇通知、函會以怎樣的一種敘述方式出現在整個運作體系中。因此,學“文”不能僅只涉文,對“文”的理解應建立在對“人”理解的之上。
在這一點上,課程其實也完成了對學生人格培養的目的。大學課程不是簡單的技能培訓。既要成“才”也要能成“材”,在大學教育中真正完成從應試到素質教育的轉變,“道”的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智力的培養是大學教育中的一個方面,在這里,理論興趣和實際功用相一致。不管你向學生灌輸的是什么細節,他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這種細節的機會是很小的;如果他確實遇到這種細節,那時他也許已忘記了你曾教他的有關此事的情況。真正有價值的教育是使學生透徹理解一些普遍的原理,這些原理適用于各種不同的具體事例。在隨后的實踐中,這些成人將會忘記你教他們的那些特殊的細節;但他們潛意識中的判斷力會是他們想起如何將這些原理應用于當時具體的情況。直到你擺脫了教科書,燒掉了你的聽課筆記,忘記了你為考試而背熟的細節,這時,你學到的知識才有價值。”[2]48
三、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的轉變:從“然”到“所以然”
“公文寫作與處理”課程所涉及的內容都關涉國家關于《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中關于行政公文的定義與解釋。因此,課程內容有被動性與滯后性的特點。課程中關于知識點的解析主要借助已有現實對這些文種的運用與解釋,以及官方對文種的定義與解釋。在這一點上,課程本身的闡釋與發揮的主動性是受限的。因此,課程講授和教材書寫都容易成為對已有文件的再解釋的過程。教學目的簡化為掌握文種寫作與處理知識。
課程如果只是拘泥于被動知識的傳授,學生所學內容永遠滯后于客體本身的發展和變化。一旦在具體情境中發生變化或者需要靈活運用,個體所能做的只能以滯后的信息來應對多變的環境。這也是許多大學應用類課程看似非常實用,面對實際問題,卻難以適應現實需要,學生本身的應變能力也沒有在其中得到培養與訓練。
要從根源上解決這一問題,就是擺脫簡單工具理性的思維模式,將“知其然”的教學內容轉變為知其“所以然”。從原來識記條例規定轉變為理解知識。從被動接受約束規定轉變為明白針對這些公文的約束與規定的由來,從而完成主體的身份轉換。原來主體是被動接受具有滯后性的課堂教學內容,現在則能在理解因由的基礎上,隨著情境的轉變,主動選擇轉變。在這一層面上,學生從受教育的客體轉變為能夠主動運用知識的主體,主動性在其中得到充分培養與發揮。
四、教學評價的轉變:從“量化”到“合理”的教學評價轉變
教學效果的好壞,總有一個評價的問題。在針對課堂教學效果的評價中,往往更注重教學手段對教學效果實現的效率高低,更注重“量”的考核標準,更注重教學對外在于教學的諸多因素的作用力,譬如像公文寫作與處理這樣的應用類課程如何為外在于教育的社會、經濟等現實大環境做貢獻。
以計量的方式來衡量教育和人的發展,是20世紀以來社會最大的判斷標準的轉變,這也是“現代”中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的轉變之一。這樣一種異化了的衡量標準與生活方式,使得原本是目的的人,變成了手段。盡管古典哲學在現代中國看似已經成為一種古板、迂腐的思維方式,但這種思維方式背后對人本身的思索在當下不斷激化的社會與人的發展沖突中,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在這樣工具理性視域下的教學評價體系的發展,直接導致教學在總體目標與效果上追求短期效應而忽略了人在受教育過程中自身的發展與成長。同時,對課程教學本身而言,也只能片面地通過僵硬的數據來衡量表面上的知識把握的度,對學生作為受教育主體在這個過程中的主動性、個性的種種發展,都無法通過純粹量化的方式來加以權衡。同時,過分依賴外在于教育的諸多因素左右教育效果的評價,會直接導致變相的應試教育。將大學教育轉變為簡單的技能培訓。這樣的熟練工在知識結構、技能發展上總是面對滯后于社會變化的困境。
因此,強調“量化”、“效率”的教學評價模式在價值理性的指引下,可以慢慢形成強調因材施教式的“合理”的教學評價模式。
以“合理”、“效率”、“數量”為關鍵詞的工具理性是現代社會評價所有社會行為的黃金尺度。似乎沒有了數據,我們所得出的所有結論都無法站得住腳。這樣一種知性的思維模式下的生活方式遮蔽了人作為主體在社會活動中最初指向的目的。尤其是大學教育這樣以完善人本身為終極目的的活動,無論是其合理性的論證還是對其最終的考核、評價體系的建立,都全然被工具理性所左右。公文寫作與處理作為一門應用類課程,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的被變相地走入另一種“應試”圈套。看似與社會發展亦步亦趨,實際上無論是從受教育者還是課程本身而言,都故步自封,抹殺的是人的活力與發展潛能。因此,價值理性對工具理性的統攝作為課程改革的突破口,是對當下急功近利的大學教育思維理路的一種轉向性努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懷特海.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卷[C]//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