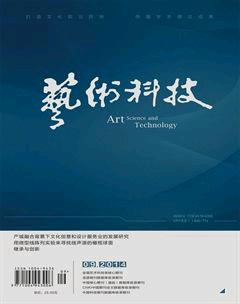實踐中的真知
吳珺
摘 要:田野工作是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基礎,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那我們究竟該如何正確地進行田野工作呢?著名音樂美學評論家蕭梅老師在她的著述《田野的回聲》中給了我們最為全面的回答。
關鍵詞:田野工作;情感交流;實踐;人文關懷
蕭梅老師的著述《田野的回聲》并不是民族音樂學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沒有在方法論層面做出過多闡釋,此書如同它的名字一樣樸實自然,是作者多年田野經驗的一些體驗和感受。我之所以沒有強調本書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因為其研究成果不深入,而是本書帶給我最大的收獲是作者在田野工作中的方式和態度。筆者的田野工作尚淺,在閱讀此書之后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和田野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1 在田野中敏銳的嗅覺
田野工作是民族音樂學學者的研究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成果的優劣往往取決于田野工作的深入程度。誠然,田野工作越久,其研究成果通常也就越深入,但是,如果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田野工作,如何有效地利用寶貴的田野時間呢?所以,田野工作是一件對時間和精力都有著一定要求的工作。
《田野的回聲》一書中,作者的幾次田野工作時間都不是特別長,但卻總能抓住特有的細節進行推敲,得到讓人驚喜的成果。例如,在“森林的啟示”一章中,作者無意間的問話卻發現了鄂倫春、鄂溫克人生存環境被硬性改造帶來的不良后果,從而引發出作者對不同民族原生環境重要性的思考。羅丹說過“生活中從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在田野中同樣如此,本身存在很多美的事物需要我們去探究,但我們往往缺少的是善于發現問題的敏感。蕭梅老師在此書中充分地展示了作為一名學者的學術敏感。在“音響的記憶”一章中,作者在采錄音響資料的時候并非單純的采集音響,而是將工作開始后的所有內容都采錄下來,包括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對話,研究對象之間的交流以及現場的情況等等,這些細節看似沒有價值,實際上卻非常重要。筆者認為,這正是對調查對象全面深刻調查的組成部分,在田野中,研究者的聚焦點往往會集中在音樂事項本身,從而忽略許多細節,結束田野工作之后,憑借記憶彌補田野中的空白并不可取。首先是記憶的準確性值得懷疑。其次,田野中某些瞬間的體會而引發的問題也不能靠后續記憶彌補。真實的記錄田野中的每個瞬間會使研究工作更加真實并有可能會獲得意外的收獲。
對于剛剛進入研究領域的人而言,最困難的恐怕是挖掘研究對象中需要闡釋或者解決的問題。問題意識成了一道瓶頸,抓住問題便如同得到線索,自然可以深入,反之則難以得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田野工作的細致程度或許是尋找問題的關鍵,尤其對“菜鳥”而言,學術敏感度相對較低,更應該忠實的記錄田野中的每個細節,并反復查看獲得的資料,發現可延伸的學術點。筆者認為,《田野的回聲》一書在寫作方面非常重視細節,這也是此書的一大特色,許多有價值的問題都是通過細節展現的。用以小見大的方式,把復雜的問題具體化、細節化,使理論知識變得具體而生動。例如,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對音樂的不同概念;研究對象生存環境對音樂風格的影響;局內、局外人的目的等等,都通過作者在田野中的見聞得到合理的解答。
2 實踐中的理論應用
民族音樂學方法論傳入中國已經許多年,其精神要義是我們學習的重點,但是對剛剛開始進行研究工作的人而言,方法論知識如何在實踐中應用依然是主要問題之一。誠然,親自到田野中必然會獲得更加直觀的體驗和理解,《田野的回聲》卻讓我們提前感受到了田野的氣息,明確了田野工作的目的。
本書雖未提及方法論知識,但無時無刻不體現著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的運用。作者的調查始終建立在對當地民族和民俗的認識基礎之上。例如,在采集苗族飛歌時,作者首先注意到的是“飛歌”名稱與當地自然環境的關系,歌若能“飛”與當地山巒疊嶂的自然風貌有關,山與山之間的交流建立在嘹亮的呼喊之上,原始的呼喊聲在長期傳播過程中漸變為“飛歌”,這或許是對“飛歌”起源最真實的解讀。把音樂事項放置在當地原生的文化環境中不正是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的重要觀點嗎?
筆者認為,理論指導實踐需要研究者對理論知識有足夠的認識,即研究者需要構建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并能在田野工作中靈活運用。缺少理論基礎的田野工作往往效率不高,因為研究者在進入田野后通常是盲目的,不易抓住關注點。面對紛繁多變的田野情況,如果研究者本身具有扎實的理論框架作為指導,那么在實際進行田野工作時便能從容不迫,游刃有余了。
個人理論框架絕不是簡單的理論知識的堆積,而是結合個人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獨立的認識,并且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不斷整理和調整的。個人理論框架的重要性在于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視角都將在此基礎之形成,并直接影響所取得的成果。建構個人理論框架,一方面需要充足的基礎理論知識;另一方面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磨練、修改理論問題,如同“打鐵磨刀”,二者缺一不可。
3 言語中的人文關懷
作者在此書中自始至終以關懷的姿態進行田野工作,體現了一種特有的細膩。作者非常注重與調查對象進行感情交流,這也是田野工作的基礎,是十分重要的。筆者認為,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人文類學科,研究的問題重點是各民族的文化及音樂,這方面內容在很大程度上難以用語言描述清楚,尤其對于知識背景與研究者不同的當代音樂持有人,在交流方面本身就存在障礙。因此,情感上的聯系也就成為一條紐帶,不僅便于交流,更重要的是,民族音樂學方法論中“局內人”、“局外人”的研究視角也暗含著某些情感交流的需要。
“局內人”視角要求研究深入到田野之中,此“深入”不僅是身體力行,而且是身心投入,否則有些文化內涵則難以理解或理解出現偏頗,這必然會影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認識的準確性。筆者認為,“局內人”視角在技術層面不是不能完成,但其內涵是無限延伸的,深入的程度與情感交流存在直接聯系。有些學者妄圖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采風獲得某地區長期流傳的文化內涵且沒有任何情感的交流,那么這個目的就很難完成,即使完成了也是流于表面,無法深入。情感交流即可看作人文關懷,即尊重研究對象。絕大多數研究者在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等方面都優于研究對象,這種身份的差別很容易使研究者以高姿態審視研究對象,如果抱有這種不虛心不謙卑的態度去進行田野工作,會使研究無法取得最大的收獲。在《田野的回聲》中,作者首先就把自己放在了很低的位置上,謙虛的向研究對象求教,展現了自己對研究對象的絕對尊重,這種方式不僅是情感交流的手段,也是研究者自身“體驗”田野的重要部分,許多文化行為必須親自參與才會獲得極為深刻的觀點。
目前,民族音樂學方法論中有的學者推崇闡釋人類學方法,既然需要闡釋,則不可回避個人對研究對象的理解,這種獨特的理解如何獲得?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體驗”。正如筆者上述觀點,人文關懷看似單純,卻蘊含著極為重要的民族音樂學方法和觀點。
4 結語
通過閱讀《田野的回聲》,筆者發現,田野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細致的觀察,理論方法在田野中的運用如同“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研究者,在不斷的實踐和理論學習中,民族音樂學才能真正發展起來,對研究者而言,《田野的回聲》給了我們很多實際的經驗和理論方法運用方面的成果,值得每一位初入此行業的學習者閱讀。
參考文獻:
[1] 蕭梅.田野的回聲——音樂人類學筆記[M].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2] 楊民康.民族音樂學與文化人類學:以中國傳統音樂為例[M].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
[3] 蕭梅.面對文字的歷史:儀式之“樂”與身體記憶[J].音樂藝術,2006(1).
[4] 蕭梅.誰的聲音——以田野工作的視角[J].音樂藝術,2009(1).
[5] 布魯諾·內特爾.音樂教育與人類音樂學:(通常的)和諧關系[J].中國音樂教育,2010(10):9-12.
[6] 布魯諾·內特爾.音樂教育與人類音樂學:(通常的)和諧關系[J].中國音樂教育,2010(11):4-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