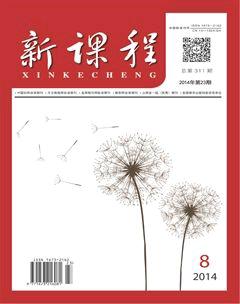古代閱讀教材對當今語文教材編寫理念的啟示
摘 要: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十分重視閱讀教材的編選,反思古代閱讀教材編選的一些觀點和做法,對今天語文教材的編寫有著深刻的啟示。
關鍵詞:語文教材;閱讀教材;教材編寫;編寫理念;啟示
閱讀教學歷來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閱讀教材的編寫
也歷來受到學界關注。我國古代語文教育也十分重視閱讀教材的編選,反思古代的閱讀教材,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寶貴
經驗。
一、強調整本書的閱讀
古代語文教育中,學生進行閱讀訓練所用到的材料主要是四書、五經、一些蒙學讀物以及一些文選類的讀本。閱讀材料“選本”和“整本”的經、史、子、集是并列的,閱讀整本書與讀文選是交替進行的。張志公先生對古代語文教育的教材做過這樣的總結:“縱觀中國古代教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教材的主線,主要的教材是‘四書五經,自漢代以來,直至‘五四前期,‘四書五經是傳統語文教育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利器。文選類教材,是為了便捷學生獲取功名的一條路徑。當然也有極少數選本是為了學生自學編著的。‘四書五經作為主要的經典教材,作為古文教育期進行書面語言讀寫訓練的主要教本,其影響時間之長,發揮作用之大,在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從古代語文教育的發展來看,“閱讀整本的書”和古代語文教育是一脈相承的。
古代閱讀教材的兩條線,以“四書”“五經”為主的“整本書”和以《昭明文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為主的“選本”始終是并行的。但是,自20世紀中期至今,教材卻越來越單一,成了“文選型”教材一統天下的局面,整本書的閱讀被忽略。閱讀教學也隨之轉向注重篇章教學。
關于整本書的閱讀,20世紀40年代初期,葉圣陶先生就在《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一文中指出:“現在的國文教材似乎該用整本的書,而不該用單篇短章……退一步說,也該把整本的書作主體,把單篇短章作輔佐。”其后的許多語文教育家顧黃初先生、董菊初先生、夏丏尊先生等都強調閱讀整本書的意義。閱讀整本書可以讓學生進行各種文體知識的研討以及文體閱讀的訓練,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一部《紅樓夢》,詩詞歌賦曲,奏議函銘誄,凡屬應有,幾乎盡有”;閱讀整本書有利于培養學生良好的讀書習慣,有利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有利于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而“僅單篇短章的教材不僅學生的閱讀量上不去,而且容易使學生眼花繚亂,心志不專,仿佛跑進熱鬧的都市,看見許多東西,可是一樣也沒有看清楚。并且,讀慣了單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范圍之內,魄力就不大,遇到大篇,將會望而卻步。”所以單篇的選文教學,對某一文體的討究不夠徹底,不利于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而且不利于學生養成專心讀書的閱讀習慣。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在“教學建議”部分提到:“培養學生廣泛的閱讀興趣,擴大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讀整本書的思想被重視起來。因此,語文教材的編寫要滲透閱讀整本書的理念,在實際的閱讀教學中,教師也要積極鼓勵并有效指導學生進行整本書的
閱讀。
二、強調閱讀材料的經典性
古代閱讀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學習文獻的思想內容,對文中所傳達的“道”進行闡發。所以閱讀材料的選擇以正統思想為主要標準,閱讀范圍偏重以“四書”“五經”為主的儒家經典。除了儒家經典外,還有一些文選讀本作為閱讀材料,大多為古文選注評點的本子,例如,比較有名的《昭明文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這些選本材料雖然存在編排方式的差異,“選文的標準和范圍也有各自的尺度,有的并且有某些偏見,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重視選用歷來有定評的、膾炙人口的名文”,選本所選的都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名篇佳作,而同代人的作品由于沒有經過一定的歷史沉淀、歷史檢驗,一般不做選擇。由此可見,古代語文教育進行閱讀訓練非常強調閱讀材料的經典性。
學生閱讀優秀的經典著作,會比閱讀一般作品得到更多更好的影響和教育。經典之作不論是其思想內容還是語言表達都堪稱典范,“文質兼美”。經典選文所蘊含的思想精神對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的形成影響深遠。經典選文的語言文字、篇章結構等表現形式合乎語言規范,為學生提供了學習語言文字的樣板,對于提高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語文教材的閱讀選文必須是經過歷史沉淀眾所公認的名篇,讓學生能夠系統學習本民族的優秀文學作品。正如童慶炳教授所說:“必須保證我們有限的教材能給予學生最經典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東西……使我們的后一代真正具備起碼的語文素養。”
三、強調文本細讀,理解作品原意
古人強調閱讀文獻,重要的是理解原意。宋代朱熹極力主張讀書要虛心涵泳,體味作者思想,而不要先入為主。《朱子讀書法》說:“學者讀書,須是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并批評“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后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要真正理解文獻原意,就不能先有任何成見,“讀書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讀書遇難處”,更要“篤志虛心,反復詳玩。”花一番力氣,才可能“理會道理”。這就如同“吃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吃了;須是細嚼慢咽,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個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為知味”。可見讀書必須用心體味,反復揣摩,才能夠真正理解書中的深意。
解讀文本是閱讀教學的關鍵和根本。中學語文閱讀教學低效,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進,原因主要就在于文本分析的不到位、不深入。而教材作為文本的載體,其在編寫時要注意無論是課文導語的設計,還是練習的設計都要引導學生對文本原意進行理解、分析,引導學生直面文本,從文本中獲取信息,提出問題,并聯系上下文,解決問題,在文章里把課文讀懂,做到“以文解文”,沒有必要做過多的注解分析和引證發揮。
參考文獻:
[1]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2).
[2]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74-85.
[3]顧黃初.語文教育論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09.
作者簡介:康建琴,女,1988年11月出生,學歷:碩士在讀,就讀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研究方向:語文教育。